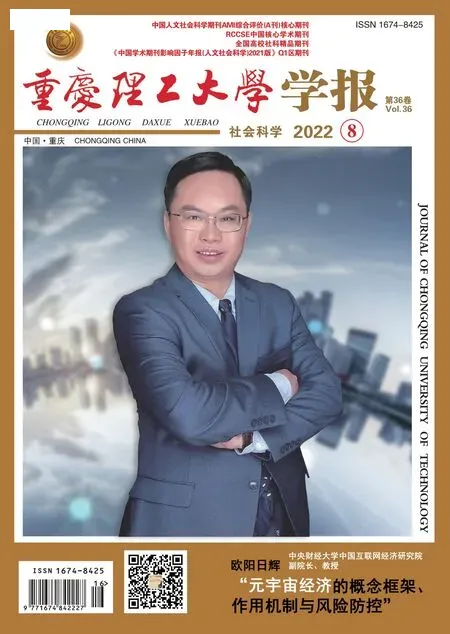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的形成與超越
高斯揚,林曉艷
(1.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 馬克思主義學院, 廣東 深圳 518055;2.濟寧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曲阜 273100)
道德是當代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研究的一個核心話題,主導著當今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本方向。受此影響,國內外學界在關注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時也會把研究目光投向道德領域,試圖從元倫理學的人性、自由等領域,或從規范性倫理學的平等、正義等方面,來論證共產主義思想的合理性。這就形成了學界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但這種研究遮蔽了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本真面貌。恢復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本義,明確道德觀念及其范疇在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中的限度,是當下學界無法回避的一項任務。這項任務不僅要求我們深入考察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的起因和過程,而且要求我們明確道德與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關系。唯此,我們才能超越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
一、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的形成
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是指從道德觀念及其相關范疇出發,闡釋和研究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學術行為。這種行為源自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中的道德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卡爾·海因岑就提出,道德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核心動力。對此,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者根本不進行任何道德說教……不向人們提出道德要求。”[1]275共產主義思想不能建立在資本主義道德觀念上,而應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然而,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相繼離世,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如布洛赫、薩特等人再度從元哲學角度,運用道德觀念,探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他們認為,元哲學領域的道德觀念,如人的自我決定(自由)、自由、發展等是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支撐,也是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在動力。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應建立在一種現實個人及其所在的社會應當確立并遵循的道德原則基礎上。這種觀點引發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界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的關注。
20世紀70年代,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齊雅德·胡薩米站在道德社會學角度,探討了道德在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德可欲性是推動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實踐的重要力量,“在無產階級的意識轉變中,這些觀念發揮了批判性作用”[2]53。此后,道德成為了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進路。以威廉·肖、R.G.佩弗、凱·尼爾森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都參與其中。這些學者或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文本癥候學,或站在新的研究角度,如方法論個人主義,探究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他們認為,道德是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運用道德理論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同時運用了道德范疇來辯護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不能缺少道德范疇的支撐。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進行道德化研究,是理解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關鍵要素。這些學者的關注和探討,使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成為了一種國外學界的研究風尚。
與國外學者相比,中國學者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的關注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改革開放全面展開,人的現代化、自由、全面發展成為了學界探討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爭論焦點。2001年,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3]14作為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人的自由、發展,社會的平等、正義等道德范疇成為了學界探討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進路。從總體上看,國內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與道德的關系、評述當代英美學界在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問題上的特定觀點、介紹當代英美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思想等方面。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學者之所以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如此關注,并不是一時興起或是迎合潮流,而是基于理論和現實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理論方面來看,以道德為切入點展開的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研究符合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趨勢。正義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熱點,當學者們關注正義時必然會涉及正義的內在規范性維度,即道德。但由于馬克思本人對于道德的模糊論述以及道德對建立和穩定現代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許多學者都把這一論題當作一項亟待解決的任務。他們通過積極地分析、探討來呈現和發展這一理論,如上文所述的胡薩米、佩弗和尼爾森等人。他們都是根據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語境中的道德觀念,來重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這種重構引發了廣泛的輻射效應,成為“當代關涉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重大問題”[4]。同樣,在以往唯物史觀的解釋模式中,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中的道德問題并沒有被充分關注,甚至可以說在國外學者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被引入以前,國內馬克思主義者鮮有針對這一問題的直接論述。在這個意義上,道德可被看作是我國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面對這一領域中的新挑戰,吸收、借鑒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界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內容也就成為了國內學界所采取的首要步驟。
其次,從現實方面來看,道德作為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研究的主要內容,絕不僅僅是國內學界對西方理論界的亦步亦趨或盲目跟從,它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現實的積極探索和回應。改革開放的40余年來,我國整體的經濟實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提升和改善,但涉及道德領域,學者卻常用“‘道德失范’、‘道德淪喪’、‘道德危機’之類的字眼形容問題的嚴重性”[5]。道德作為一定文化和歷史傳統中支配人們品格和行為的社會規則,對個人應當怎樣生活、怎樣行動,對一定的社會形態在秩序安排中如何進行策略選擇具有重要的內在指導和約束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夯實國內文化建設根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6]160,“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堅持社會主義道德觀”[6]160,應以道德來引領當代人的社會生活。可以說,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成為國內學界研究熱點,既是理論工作者回應社會發展問題的不斷努力,也是他們對我國社會主義現實的深刻關切。
總體來看,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真實地切中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道德化研究之所以成為理解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進路,有來自理論和現實的雙重需要。在這種需要的驅動下,國內外學界沿著這一進路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不僅推動了當代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與時代問題之間的呼應與互動,而且推高了學界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解讀的熱情,使研究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成為了一種不可回避的學術現象。
二、道德與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之間的關系
雖然學界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已經成為一種不可回避的學術現象,但理論工作者們不能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就接受并使用這一研究路徑,必須對這一研究的前提展開追問。這種追問建立在道德與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之間關系的基礎之上。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馬克思本人如何看待道德問題,他的觀點和態度是什么;第二,馬克思探討共產主義的最終旨趣是什么,道德能否確切地表達這個終極旨趣。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我們才能基本上揭示出道德與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之間的契合程度,并由此來判定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是否能夠作為一條合格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路徑。
首先,就馬克思本人的態度而言,在目前的文本中,馬克思對道德問題進行的具體論述少之又少。在涉及道德觀念及其范疇時,馬克思往往把道德與宗教、法律等并列在一起,從社會階級屬性角度來說明道德。道德的階級屬性是指,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來源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資本主義道德建立在這種物質基礎之上,是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資本主義道德被資產階級定義、闡釋和支配。馬克思將其表達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7]550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道德的內在矛盾性: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倡導的現代西方道德觀念,如平等、自由等,帶給了人們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和行動的熱情;但另一方面,這些道德觀念就其本質屬性而言,來源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領域和交換領域,它們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服務,即馬克思指出的“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范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8]47,對資本主義社會“成員來說真正有價值的唯一活動就是掙錢、積累資本和剩余價值”[9]120。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道德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這種意識形態必會走向毀滅。毀滅它們的,不是哲學的語詞批判,而是與物質生產相聯系的社會運動,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進行的社會革命。
道德的階級屬性決定了其在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馬克思在論述共產主義思想時是一個非道德論者。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發展的全新形態,無論在經濟基礎方面,還是在上層建筑方面,必定會超越以往一切社會形態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馬克思必定會展望,未來的社會不會再有任何意識形態,它會清除一切道德,而非在道德上推陳出新”[10]158。即便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論述共產主義思想時使用了某些道德語言,表露出了一定的道德態度,但這并不是說馬克思會對共產主義思想進行道德化研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將資本主義的道德表述為對勞動個體獨立性和個性的剝奪(1)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參見參考文獻[11]74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制度斥責為對勞動者的壓迫和貶低(2)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參見參考文獻[11]743。。道德不是共產主義社會或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核心范疇。馬克思是要從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出發,建構新的人類社會形態,從而科學地表達人類社會發展的辯證運動。
其次,就馬克思探討共產主義思想的最終旨趣而言,盡管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都表達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義憤,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論述卻并沒有被這種情感主宰,而是將道德與唯物史觀的科學研究相聯系。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現實決定了道德觀念的不同。道德之所以被學者關注,是因為它在理論層面再現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運動,表現了不可逆轉的人類社會形態的辯證發展。道德以“見微知著”的方式,表現了一定社會歷史階段中占社會主體的物質生產關系和生活關系。馬克思曾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來說明道德觀念的不同。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作為共產主義道德原則主要表現為廢除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個人對自身勞動產品的擁有和支配,即個人的勞動“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11]20,因為這一時期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尚不充分,“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12]18。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13]164,那時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開始被打破,舊社會的痕跡煙消云散,道德開始體現為個人的全面發展及社會對個人需要的滿足與秩序的安排,即各盡所能和按需分配。
共產主義的道德不是某種抽象的觀念,也不是某種空洞的口號,而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以及由這種生產方式所確定的社會關系。共產主義的道德應來自人類社會的科學發展規律。這種規律,不僅包含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及社會領域(包含道德)的剖析和批判,而且包含著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揭示。事實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道德思想正是通過科學分析得出的。馬克思從不主張對道德進行先驗的邏輯分析和概念推演,而是主張從人們現實生活的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歷史發展等方面去發掘道德與其他社會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即便有學者指出,“關于社會歷史的事實判斷不同程度地以預設某種價值知識為前提”[14]182。但在一個人的思想中存在道德前提并不能等于其全部思想都以道德化的方式進行。在《道德化的批評與批評化的道德》中,馬克思斥責海因岑對共產主義道德化的理解是一種“傾瀉自己的道德憤怒”[12]333的行為。離開社會發展階段,空泛地談論道德或把道德當作一種普遍原則隨意使用的話,恰恰是一種被馬克思斥責為“犯罪”(3)馬克思指出:“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于我們黨,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關于權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參見參考文獻[12]23。活動的重復。
事實上,馬克思沒有提出一個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的絕對道德命令,沒有將人的自主和自由發展歸因于道德。馬克思拒絕將共產主義思想發展為一種純粹的道德理論,道德化研究不是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旨趣。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主要目標在于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現實的解放,這與西方學界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化研究倡導的內在超越、愛與救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不是一種對于最高善的籌劃和分析,而是一種現實的社會運動。這種運動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物質極大豐富和變革社會關系的總體性革命基礎上。無論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強調的要發展一種通往最高善的合理道路,還是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倡導的那種基于自由、權利、責任和義務的道德理論,都不能承擔起這一任務。實質上,學界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是一條走偏了的道路。
三、超越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
當區分出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與道德的關系,我們就能意識到,共產主義思想作為一種對未來社會形態的闡釋,其中的道德問題必然是與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現狀相結合的,是涵蓋經濟、政治和歷史等方面的復合問題。相應地,超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的思想整體,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與時俱進地把握當下的社會現實。
首先,雖然道德關涉個體層面的自由、自主,社會層面的公平、正義,但道德并不是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研究的全部對象,共產主義思想也不是脫離馬克思思想整體的獨立部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脫離唯物史觀這一思想整體來研究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國內外學者將道德作為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因為他們忽略了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沒有抓住道德與共產主義思想之間的實質性關聯,沒有抓住共產主義思想與馬克思思想各個部分內容之間的有機聯系,沒能把現實的道德觀念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相互融合。因此,他們只能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進行碎片化和割裂式解讀。而超越這種解讀,唯有把握道德在一定社會形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構成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并加以整合,才能恢復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整體性把握。
其次,應堅持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推動事物發展的核心動力。馬克思對于共產主義思想的論述建立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之上。唯物辯證法闡明了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生產實踐基礎,揭示了一定社會形態下道德觀念的具體性,即某種道德觀念總是和人的物質生產實踐相關,是對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社會要素及其關系的反映。這就意味著,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研究始終要堅持實踐立場,致力于解釋共產主義道德觀念所包含的豐富社會物質生產內容。唯有從共產主義社會的道德起源、社會結構及其相關實踐入手,才能掌握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形態的基本要求。以往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的偏頗之處就在于遺忘了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如英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強行將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豐富現實旨向歸結為道德規范,這“實際上是一種后期的經驗實證主義傳統”[15]94。馬克思曾指出,去掉現實世界的矛盾運動,去掉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至多還剩下最純粹的道德”[7]606。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不是孤立的‘人之為精神’的‘心理’和‘人之為群體’的‘倫理’,而是‘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16]。只有堅持唯物辯證法,將人的現實發展作為研究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方法論核心,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所強調的,道德觀念背后的作為總體性力量而起支配性作用的物質生產的邏輯,才會關注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這才是恢復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研究的根本性基礎。
最后,應從社會現實出發。道德作為人類社會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道德的實踐性在于其具有指認現實、超越現實的否定性力量。對共產主義道德研究的關鍵在于如何將這種力量激發出來。盡管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道德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人們對于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關注,促進了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認知,但這種“坐而論道”式的研究并不符合馬克思的要求。反而,它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即便到了21世紀,我們仍需高度重視馬克思對于社會現實的關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中不僅包含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對共產主義的建構,而且包含了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行動和人類解放的堅持。這意味著,我們研究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不應與當下的社會現實相分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遵循新的社會發展規律,把握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共產主義社會生成的條件,明確道德是“確證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科學性、實踐必然性的關鍵因素”[17],唯此才能實現對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