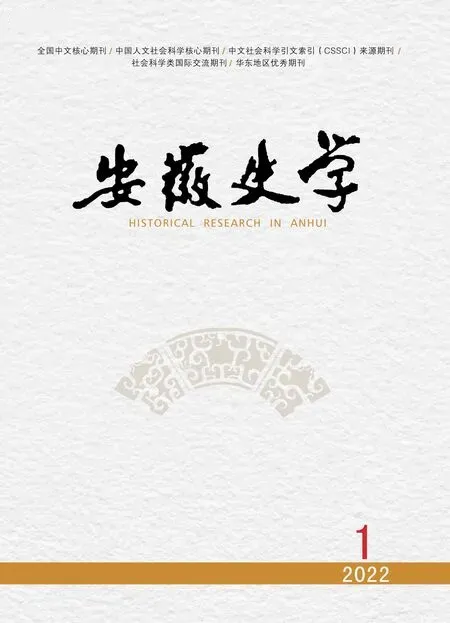小黃冊所見明初浙東地區民田考略
耿洪利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關于明代土地的類別和占有形式,史載:“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后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勛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余為民田。”(1)《明史》卷77《食貨志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81頁。明確指出,明代田土主要有官田和民田兩大類,依據土地所有權,官田即為朝廷或官府所屬,民田則為民間私有。需要注意的是,該則史料是對有明一代土地情況的總體概述,而“厥后”一詞反映出明代官田的種類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就稱謂而言,官田、沒官田和斷入官田均屬官田無疑,余下則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同時,該則史料記載了明代官田多達15種,而民田的類別則較為模糊,或是民田種類較少的反映。學術界一般認為,明代民田的種類主要有新開田、沙塞田、閑田和僧道常住田4種。(2)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中古時代·明時期》(修訂本)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頁。所謂僧道常住田乃寺院的經濟支柱,屬固定資產,不許買賣,洪武十五年詔:“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許買。僧窮、寺窮,常住田土,法不許賣。如有似此之人,籍沒家產”(3)葛寅亮著、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頁。,與“寺觀賜乞莊田”有明顯區別,故屬民田。
有關明代田土及科則問題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明會典》和地方志等資料,在地域上集中于江南等重賦地區,重點探討明代官田的來源、種類和科則(4)可參見周良霄:《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歷史研究》1957年第10期;張忠民:《明代大名府官民田土考》,《河北學刊》1985年第4期;王春瑜、林金樹、李濟賢:《論明代江南官田的性質及私有化》,《晉陽學刊》1985年第5期;林金樹:《關于明代江南官田的幾個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蔣兆成:《論明代杭嘉湖的官田》,《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林楓:《明代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官田重賦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2期;[日]森正夫著,伍躍、張學鋒譯:《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而對民田的研究較少,僅見林金樹(5)林金樹:《明代江南民田的數量和科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曹務坤(6)曹務坤:《明清時期貴州民田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學者的少量成果。因此,學術界對明初官田、民田的具體形態缺乏足夠的認識,對民田在明代土地類型中的占比、歷史演變及其科則問題未能形成系統的研究和認知。
上海圖書館藏《后漢書》《魏書》紙背明洪武三年(1370)處州府小黃冊的發現,不僅為我們再現了明代攢造黃冊之始的面貌,更為研究明初人口、土地和賦役征調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7)關于這批小黃冊的具體情況,可參見宋坤:《北方黃冊填補空白》,《光明日報》2017年8月21日;宋坤、張恒:《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的發現及意義》,《歷史研究》2020年第3期。本文擬對處州府小黃冊所載民田數量、種類和科則等問題進行分析,以期推動明代民田相關問題的研究。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小黃冊所載處州府民田數量和種類
上海圖書館藏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存之于古籍紙背中,原本完整的冊籍被裁切、錯簡,導致這批小黃冊葉碼錯簡不一,內容殘缺不全。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迻錄復原后的完整文書,僅就各葉紙背所載田土之數進行計量學統計,以反映明初處州府民田在各類土地類型中的占比。
(一)《后漢書》紙背所載明初處州府民田之數
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印本《后漢書》共九十卷,其中三十七卷紙背帶有文字,計365葉。初步考證,這些遺存的紙背文書至少涵蓋了遂昌、青田二縣,涉及10個都24個里(8)小黃冊每百戶進行編排與賦役黃冊每110戶為1里在基層組織概念上一致,但小黃冊中未見有“第幾里”的記載,均在“里長甲首輪流圖”右側名以“第幾甲”,這里的“甲”即相當于賦役黃冊中的“里”。500余戶的人口、賦役情況。還有部分完整保留了某一都或一里的人口、田土數據,如卷二第8葉背載遂昌縣建德鄉十五都某里官民田土總計“田一十一頃三十六畝三分五毫五絲二忽、地二畝五分六厘二毫五絲”,第9葉背載同一里“民田一十一頃二十一畝二分六厘五絲二忽……民地二畝五分六厘二毫五絲”。即各類田土總計1136.30552畝,其中民地2.5625畝、民田1121.26052畝,由此推測該里官田之數最多15.045畝,僅占1.321%。同時,小黃冊田土除按土地所有權分官、民二類外,又據不同的土地類別分為田、地二種,民地在土地所有權上應為私有,當屬民田之類。據整理后錄文分析和文書復原,該里小黃冊現存于卷二第6—30葉、卷三第1—29葉、卷四第1—12葉紙背中。
同書卷四第15葉背載青田縣四都“官民田土一百二十四頃一十七畝四分六厘七毫六絲六忽”,第16葉背載“學田六十七畝一分”,第17葉背載“民田一百二十二頃七十二畝九分七厘二毫四絲二忽”。可知青田縣四都各類田土總計12417.46766畝,其中學田67.1畝、民田12272.97242畝,另有官田、民地等共144.49524畝。民地之數由于文書殘缺無法得知完整數據,僅有卷四第28葉背、卷九第13葉背、卷十下第12葉背所載,共計殘存民地2.44626畝。由此推算,青田縣四都民田至少12275.41868畝,約占該都全部田土的98.856%。
余下紙背殘存小黃冊中,均詳載具體人戶信息,戶下田產多為民田。如卷二第1—5葉背載遂昌縣建德鄉十五都某里7個編排不盡人戶和1個外縣寄莊戶信息,其中第1葉背載“民田三分三厘三毫三絲三忽……一戶朱四男,系麗水縣民戶……民田二分七厘五毫”共2戶田產信息,第2葉背載“一戶陳保二”,“民田五厘八毫三絲三忽”,第3葉背載“葉聦俊”戶“民田五分二厘五毫”,第4葉背載“葉保弟”戶“民田二分九厘五毫八絲三忽”,第5葉背載“程福三”戶“民田二分五厘七毫一絲七忽”,以上總計民田1.74466畝。同樣的記錄還見之于卷六十二第2葉背,處州府某縣某都田土總數“官田一十一畝五毫”“沒官田一頃四十五畝六分三厘九毫”“民田三十九頃四畝六厘七毫”,可知該都民田3904.067畝。其余各卷紙背所載均為具體人戶信息:卷二十五載1戶民田1.56畝,卷二十九載4戶民田12.08042畝,卷三十上、下共載41戶民田233.83495畝,卷三十一載27戶民田51.24785畝,卷三十二載17戶民田42.34552畝,卷四十載3戶民田32.38542畝,卷四十一載1戶民田0.14508畝,卷四十二載1戶民田10.39167畝,卷四十八載6戶民田19.0875畝,卷四十九載5戶民田25.57106畝,卷五十一載2戶民田23.04708畝,卷五十二載9戶民田21.02501畝,卷五十三載4戶民田21.07501畝,卷五十五載3戶民田25.04167畝,卷五十七載4戶民田5.875畝,卷五十八載6戶民田65.40701畝,卷六十一載1戶民田0.08333畝,卷六十二載8戶民田15.5417畝,卷六十三載20戶民田1416.22582畝,卷六十四載27戶民田161.24067畝,卷七十載1戶民田6.359畝,卷七十三載8戶民田和民地共119.28247畝(9)該卷6葉紙背中,有4葉載人戶田產涉及民地,另有“西溪義塾”戶,田產明確登載為民田,詳見下文分析。,卷七十四上、下共載9戶民田53.4畝(10)該卷第2葉紙背所載人戶田產為民地。,卷七十五載3戶民田13.122畝,卷七十八載5戶民田46.433畝,以上共計民田2421.79951畝。綜上,《后漢書》紙背現存小黃冊共載處州府民田15822.78587畝。
同時,文書內容也間接反映了明初處州府地區的民田種類,就所有權而言有民田、民地兩種,就田土的具體歸屬而言,還出現寺觀之田和義塾之田。如卷四第3葉背載:“一戶延福觀,系本都道觀,充當本縣弓兵。……民田三十五畝四分八毫三絲三忽。”卷七十三第16葉背載:“一戶西溪義塾,系本都四保,充渡子。……民田九十九畝六分二厘五毫。”2葉所載一者為“延福觀”,屬僧道之列,一者為“義塾”,屬學校之列,但二者之下的田土卻均為民田,與《明史》所載田土種類存在很大出入。結合學術界對明代民田種類的認識可知,此處“延福觀”下的田土應是作為其經濟支柱的常住田,故性質為民田,需繳納稅糧。洪武二十七年詔:“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充當差役。”(11)葛寅亮著、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第67頁。但這里的“延福觀”不僅繳納稅糧,還被編排擔任當地弓兵這一民壯雜役,且卷七十五第13葉紙背殘存的“里長甲首輪流圖”中載有“普化寺”編當洪武四年里長。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規定:“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12)《明史》卷77《食貨志一》,第1878頁。可見,明代僧道與普通民戶一樣被納入冊籍排定里甲應役。明初小黃冊是賦役黃冊推行之前在特定地區試行的一種賦役制度,從具體登載格式上看,在人戶的編排上重田產而非人丁,形成了“以田糧立戶”的基本編戶原則。“延福觀”擁有田產,在向朝廷繳納賦稅的同時,承擔部分差役也就理所當然,也符合朱元璋“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歷代相承,皆循其舊”的治民理念。(13)《明太祖實錄》卷165,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2545頁。
(二)《魏書》紙背所載民田之數
上海圖書館藏《魏書》現存兩個殘本,均為明公文紙印本,且紙背內容均為明洪武三年小黃冊。因此,二者應為同一版本。現存共十三卷248葉,其中243葉紙背帶有文字。據考證,該紙背文書內容主要為龍泉縣小黃冊,另有部分內容疑似為縉云縣所屬,共計涵蓋5個都8個里370余戶的人口、賦役情況。其中,卷四十五第21葉背載龍泉縣二都“官民僧寺等田總計田二十頃一十畝五分七厘八毫三絲五忽”“民田一十九頃九十一畝三分一厘一毫六絲七忽”,即各類田土總計2010.57835畝,其中民田1991.31167畝,占比達到了99.04%。整理錄文可知,該都現殘存一個里的小黃冊信息,主要在卷四十五第1—10、12、16、21、23—30葉和卷四十六第1—7葉紙背中。卷六十四第5葉背載龍泉縣某都某里民田總數619.63395畝。其余各卷紙背還殘存了部分具體人戶的民田信息,其中卷四十五載4戶民田62.025畝,卷六十一載25戶民田534.34191畝,卷六十二載1戶民田0.73333畝,卷六十三載1戶民田1.7(14)該葉背載人戶民田信息有殘,僅能釋讀1.7畝,暫按此數統計。畝,卷六十四載12戶民田220.69685畝,卷六十五載3戶民田70.59856畝,卷八十二載16戶民田127.41248畝,卷八十三上、下載27戶民田109.93982畝,卷八十六載7戶民田15.06367畝,卷八十七載7戶民田8.36666畝,卷八十八載20戶民田24.60976畝,共計民田1175.48534畝。綜上,整個《魏書》紙背共載民田3786.43096畝。
另,《魏書》紙背內容也反映了一些民田的種類,也有與“延福觀”性質相同的寺院田土,如卷六十一第3葉背載:“一戶興善寺昂本軒,本都民戶,系洪武八年里長。……田四十二畝五分八厘三毫三絲三忽。”卷七十三第16葉背載:“一戶常樂寺僧,照鑒堂,本管住,洪武四年里長。……舊有田一頃一十八畝七厘一毫九絲九忽。”兩者均屬僧道之列,“興善寺昂本軒”又明確為“本都民戶”,戶下田產必然為民田無疑,“常樂寺僧”的田產登載格式與“興善寺昂本軒”相同,當同為民田。
(三)小黃冊所載處州府民田種類和田土占比
經上述統計,小黃冊所載處州府民田19609.18349畝。同時,民田的種類有“民田”“民地”“寺觀田”和“義塾田”4種。“寺觀田”為僧道常住田。“義塾田”與小黃冊中的“府學田”和“縣學田”相區別,前者為私人所辦,后者為官府所辦,故而在田土性質上有著本質區別。
此外,《后漢書》卷三十下第24葉背載處州府某都某里“田四頃六十四畝七分三厘一毫一絲一忽”,卷六十三第8葉背載處州府某都“田二十四頃九十八畝一毫三絲二忽”;《魏書》卷八十三上第3葉背載龍泉縣某都某里“田產八頃一十畝二分二厘八絲三忽”,合計3772.95326畝,雖未見田土的類型,卻為統計整個小黃冊所載處州府田土總數提供了依據。
綜合上述研究可知,上海圖書館藏《后漢書》《魏書》兩種古籍紙背所存小黃冊共載明初處州府各類田土23535.23399畝,民田總計19543.83073畝,約占83%,其他類型田土約占17%。需要注意的是,此數僅是基于殘缺文書的統計,完整冊籍中登載的民田占比應還要高一些。由此可見,明初處州府民田之數應遠多于官田等其他類型田土。
林金樹的研究認為,朱元璋平定江南廣大地區之后,籍沒“偽吳助戚之田”和“諸豪強之田”,官田數額因之激增,因此,江南民田數量較少。(15)林金樹:《明代江南民田的數量和科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這種情況在明初確有推行,即朱元璋建國前后的“抄沒官田”,在現存小黃冊中亦有所體現,如《后漢書》卷七十八第2葉背載某戶“沒官田一畝二分一厘”。但是林金樹的研究僅止步于文字敘述,其所得結論尚待商榷。處州府在地理位置上屬江南浙東一帶,小黃冊可見明初民田之數遠多于官田之數。那么,整個浙江乃至整個江南地區,真的是民田數量較少嗎?高壽仙的研究顯示,弘治十五年,江南十二府州中徽州、江西、浙江、常州、寧國、池州、太平、應天、鎮江等府州民田之數高于官田,蘇州府、松江府、和州等府州官田多于民田,但官田、民田之數相差不多,官田僅比民田多1.72%。(16)參見高壽仙:《明代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105—106頁。當然,該研究的對象為納稅地畝,并不包括軍屯田地、牧馬草場、王府莊田等,且距明初130余年,必定有所偏差。上海圖書館藏《后漢書》《魏書》紙背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的發現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短板。明初處州府遂昌、青田、龍泉三縣的民田之數遠多于官田,結合弘治十五年浙江地區民田遠多于官田,則可基本確定明初浙東地區處州府的民田之數應多于官田。同時,縱觀整個明王朝,民田也應整體多于官田,江南地區大抵也是如此。
二、小黃冊所見處州府民田科則分析
明代民田與官田除所有權不同之外,還有一重要區別,即科則不同。所謂科則,意指政府按田地的類別、等級而定的田賦標準。史載:“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17)④⑥《明史》卷78《食貨志二》,第1897、1896、1896頁。因此,科則也可稱之為各類田土向國家繳納的畝稅額度。明代官田科則一直重于民田,《明史·食貨志》載:“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18)④⑥《明史》卷78《食貨志二》,第1897、1896、1896頁。《明會典》記載更詳細:“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場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斗二升。”(19)萬歷《明會典》卷17《戶部四·田土》,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12頁。與《明史》記載相比,增加了蘆地、草場地二則。以上雖記載的是全國范圍的一個均值,但也明確反映出明代官田稅賦重于民田的事實。明代田土稅糧負擔以江南地區為最重,且官田科則遠重于民田,其中緣由《明史》有載:“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以蘇為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20)④⑥《明史》卷78《食貨志二》,第1897、1896、1896頁。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的發現,則為研究明代江南地區的民田科則提供了新的線索。
處州府民田科則究竟如何,現存最早明成化本《處州府志》未見記載。而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中,對各類田土的科則有著明確的記載,如《后漢書》卷四第13葉背載處州府青田縣四都起科則例:“沒官田每畝照依民田則例,起科夏稅正麥六勺,秋糧正米照依舊額起科不等。”可見,該都沒官田與民田的起科相同,均為夏稅正麥六勺,秋糧正米依舊額起科。類似的記載還見之于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公文紙印本《漢書》紙背文獻中,該書傳六九上第41葉紙背載青田縣坊郭里起科則例:“官田每畝照依民田則例,起科夏稅正六勺,秋糧照依原額起科不等。職田每畝照依民田則例,起科夏稅正麥六勺,秋糧照依原額起科不等。學院田每畝照依民田則例,起科夏稅正麥三勺,秋糧照依原額起科不等。”(21)②轉引自[日]竺沙雅章:《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14冊,1973年,第44、41頁。明確登載了官田、職田、學院田3種不同的起科則例:夏稅麥起科相同,均以民田為基準,在具體起科稅率上,官田和職田的起科均為每畝夏稅正麥六勺,而學院田起科為夏稅正麥三勺,僅為官田、職田的二分之一。由此推斷,除學院田外,明初處州府的官田、沒官田、民田、職田的夏稅麥起科率相同,而秋糧則各自依照原額起科不等,民田之賦也低于史籍所載的“每畝三升三合五勺”。此處所載僅為起科則例,即最低納稅額度,在實際的稅糧征收中是否如此?通過對小黃冊中每戶民田畝數和所納稅糧的數據分析,可以回答這一問題。
從小黃冊所載的人戶信息中可以證實,明初處州府民田起科稅率應為每畝夏稅正麥六勺,是民田計畝納稅的最低額度。如,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漢書》傳六四下第34葉紙背載青田縣一戶民田5.767畝,需要納夏稅“正麥三合四勺六抄二圭”,秋糧“正米二升八合八勺三抄五撮”(22)②轉引自[日]竺沙雅章:《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14冊,1973年,第44、41頁。,納夏稅正麥0.34602升(23)鑒于小黃冊所載民田起科稅率額度為夏稅正麥六勺,為便于計算民田數額與夏稅正麥、秋糧正米之間比值,以獲得相應的民田科則,故在計算時將所納稅糧之數全部以“升”作為最基本的換算單位,下同。、秋糧正米2.8835升。每畝納稅分別為0.06升和0.5升,即稅率為夏稅正麥六勺、秋糧正米五合。又,上海圖書館藏《后漢書》卷四第17葉背載:處州府青田縣四都田土總計民田12272.97242畝,共納夏稅“正麥七石三斗六升三合七勺八抄三捽四圭五粟二粒”、秋糧“正米六十一石三斗六升四合八勺六抄二捽一圭”,每畝納夏稅正麥0.06升和秋糧正米0.5升。再如,《后漢書》卷六第15葉背載:“林敬六”戶民田1.706畝,納夏稅正麥0.10236升,秋糧正米0.853升,每畝納夏稅正麥0.06升、秋糧正米0.5升。對比分析,同樣的民田稅率主要分布于《后漢書》卷四、卷六、卷七、卷九、卷十上和十下、卷四十九第33葉、卷五十八第7葉和第8葉、卷六十二第2—13葉和第17葉、卷七十、卷七十三、卷七十四上和七十四下、卷七十五、卷七十八各葉紙背中。由此可知,明初處州府民田起科稅率為每畝夏稅正麥六勺、秋糧正米五合。
那么是否存在較高的科則?《后漢書》卷二第9葉背載:遂昌縣建德鄉十五都某里民田1121.26052畝,需納夏稅“正麥二碩六斗九升一合二抄五捽二圭四粟八粒”,秋糧“正米二十二碩四斗二升六合二勺一抄四圭”,每畝分別納稅為0.24升和2升,即稅率夏稅正麥二合四勺、秋糧正米二升。《魏書》卷四十五第15葉背載:“梅清”戶下民田51.4375畝,納夏稅“正麥一斗二升三合四勺五抄”,秋糧“正米一碩二升八合七勺五抄”,每畝納稅分別為0.24升和2升。這些民田科則無論是夏稅正麥還是秋糧正米,均為起科稅率的4倍。小黃冊中,科則為每畝納夏稅正麥二合四勺、秋糧正米二升者主要分布于《后漢書》卷二至卷三全部,卷四第1—12葉,卷四十至卷四十一全部,卷四十八至卷四十九(第6葉除外),卷六十三第8—26葉和卷六十四全部紙背;《魏書》卷四十五第11、13—15、18葉,卷八十二全部和卷八十三上、下兩卷,卷八十六至八十七紙背。
實際上,明初處州府小黃冊中的民田科則還有第三種情形,即每畝夏稅正麥三合六勺、秋糧正米三升。如《后漢書》卷二十九第14葉背載:某戶下田產2.8畝,需納夏稅“正麥一升八抄”,秋糧“正米八升四合”,稅率為夏稅正麥0.36升、秋糧正米3升。《魏書》卷四十五第3葉背載:“葉壽卿”戶下田1畝,納夏稅“正麥三合六勺”、秋糧“正米三升”,稅糧額度為民田最低起科的6倍。小黃冊中,科則為每畝納夏稅正麥三合六勺、秋糧正米三升者主要分布于《后漢書》卷二十九全部,卷三十上、下兩卷,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全部,卷四十二第23葉,卷五十一第11—12葉,卷五十二第1—2、4—7、13—14、26、28葉,卷五十三都2、6、9、11葉,卷五十五第13、16葉,卷五十七第1—3、17、21葉,卷五十八第2、5、11、25葉,卷六十二第14—16葉和第18—23葉,卷六十三1—7葉紙背;《魏書》卷四十五第1—10、12、16—17、19—30葉,卷六十一全部和卷六十二全部(第13葉除外),卷六十三至六十四,卷六十五全部(第9—10葉除外)紙背。
通過以上分析,共得明初處州府民田3種科則,分別是:夏稅正麥六勺、秋糧正米五合,夏稅正麥二合四勺、秋糧正米二升,夏稅正麥三合六勺、秋糧正米三升,遠遠低于史籍所載明代民田的平均科則“每畝三升三合五勺”,也遠低于林金樹所研究的洪武時期蘇州府民田畝稅科則。(24)林金樹利用洪武《蘇州府志》記載,羅列出民田畝稅五十三升、四十三升、三十三升、二十六升、二十三升、十六升、十三升、五升、三升、一升等十種科則,《明代江南民田的數量和科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處州府位于浙東地區,小黃冊由于殘缺性,僅存3縣的部分內容,但不可否認其在明代民田科則問題上具備了傳統史籍所不具備的獨特價值。同時,該小黃冊也反映出明初處州府民田科則的一些特點,如科則較少,起科率較低,且不同地區存在一定差距。
余 論
民田是明代重要的土地類別和占有形式之一,在各類田土總額中占有絕對的優勢,是征收賦稅的重要來源。通過對明初處州府小黃冊所載內容的統計分析,明確了遂昌、青田、龍泉等縣民田大致有“民田”“民地”、僧道常住田和非官方性質的“義塾田”4種,且民田在各類田土類型中占有絕對的優勢,遠多于官田。
同時,綜合分析小黃冊所載民田之下所納夏稅、秋糧數額,共得明初處州府三種民田科則,其中,夏稅正麥六勺、秋糧正米五合應為最低起科。整體而言,明初處州府民田科則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起科率較低,夏稅、秋糧二者合計不過五合六勺,不足一升,遠低于傳統史籍所載明代全國均值散升三合五勺。二是科則較少且相互之間雖有差距但并不懸殊,三種科則中最高科則是最低的6倍,中間值為最低科則的4倍,且呈現出倍數于最低科則增長的趨勢。雖然由于文書的殘缺性,無法涵蓋整個處州府地區,但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明初浙東地區民田科則的地域性特征。另,明初處州府民田呈現出三種科則的背后,或與明代田土分上、中、下三等有關,而小黃冊所反映的明初家庭經濟的規模、人均土地占有情況和貧富差距等問題,筆者將有另文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