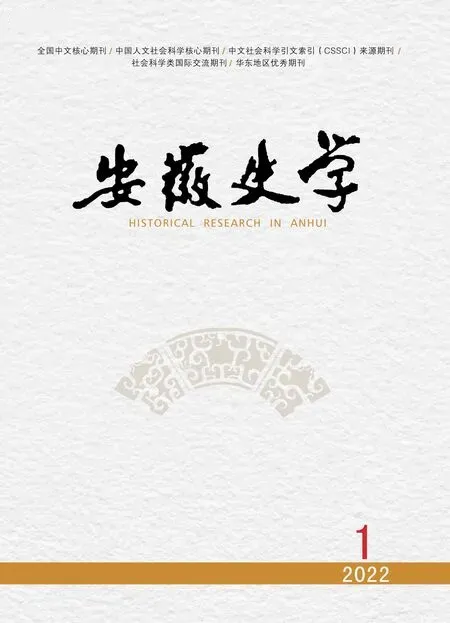試論安福國會對巴黎和會的反應與應對
嚴 泉
(上海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444)
長期以來,人們多是習慣從派系政治角度評價安福國會與民初政治,對其作為立法機關的自身權力運作過程關注不多,其中就包括巴黎和會時期安福國會的研究。(1)顧敦鍒《中國議會史》(蘇州木瀆心正堂1931年版)、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等民國時期議會史研究著作,均沒有關于議會與外交問題的專門論述。近年來的中國大陸地區研究著作,如薛恒《民國議會制度研究(1911—192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中關于議會權力運作的分析,也未包括外交權的行使。而賈德威的《安福國會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雖然涉及安福國會的外交權運行,但在研究巴黎和會時期中國外交時,重點在評析國會的作用與影響,對議會外交過程僅略有提及。臺灣地區學者張玉法《民國初年的國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李守孔《民初之國會》(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4年版)等代表性論著缺乏相關外交問題研究。此外,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J Nathan)Peking Politics,Factionalism and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是從派系政治的角度來解釋民初立憲政治的失敗,并未展開對安福國會的專門研究。民國時期專門論述安福國會的著作《安福禍國記》,對于安福國會與山東問題,主要是收錄駐外公使的來電,評論要點是巴黎和會召開之前的參戰追認與山東路約。(2)南海胤子:《安福禍國記》,《近代稗海》第4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400頁。在鄧野先生關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治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其中涉及到安福國會政治角色的論述,仍然是沿用派系政治的分析框架,較少從國會制度本身運作分析入手。即便如此,鄧著也認為在此期間,安福國會是重要的政治力量,與弱勢的北京政府相比較,是一個強勢國會。(3)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頁。
筆者以為,僅僅從派系斗爭角度解讀是不夠的,安福國會對于巴黎和會時期中國外交問題,除了由于外界輿論壓力而被迫回應外,從立法運作過程來看,很多時候也體現出主動性的特點。本文嘗試從立法實踐的新視角研究安福國會的權力運作,深入探討其實際成效與特色。
一、安福國會對巴黎和會的反應
安福國會成立后不久,1918年11月15日,眾議院在審議“請以中華民國國會名義致電法國國會及英美各國國會祝賀歐戰勝利案”時,議員王文璞就已經開始關注戰后歐洲和平會議。王文璞在發言中指出:“現在國際間之外交,最重國民外交。兩院為代表民意機關,對于政府關于歐洲議和應如何援助,當有相當辦法。本院同人須詳細研究之……歐洲議和,中國派遣代表,在中國系屬創舉,兩院為代表民意機關,對于前往歐洲議和之代表,應如何隆重待遇之,亦須詳為討論。”(4)③《速記錄》,《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66、67頁。
對于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國會最為重要的反應當屬提出外交議案,內容涵蓋和會籌備與中國外交目標,后者又包括收回山東利權、修訂《辛丑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恢復關稅主權等具體訴求。
和會籌備雖然是政府主導,但是仍有議員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參議員韋榮熙提出議案,要求北京政府迅速派員赴歐準備參與和議,并且強調此次和會對改善戰后中國國際地位意義重大,“和議開時非惟議決歐洲種種國際問題,而東亞種種問題亦必取決于此。是此次和議實為吾國生死存亡關頭,萬難緩視者也。”(5)《議員韋榮熙提出請咨政府歐戰終局迅速派員赴歐準備參預和議以救危局案》,《參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3冊,第79頁。和談代表人選是政府籌備工作的重要環節。當時有報紙聲稱當局將派外交總長陸征祥為議和代表。因事先未與國會溝通,有議員對此表示不滿。如安福系要人克希克圖指出:“現在歐戰已經終了,中國本在參戰之列。凡有戰后各種會議,即當然參與。究竟政府對于此事有無準備,抑如何進行?吾輩不得而知。”要求國務總理與外交總長出席國會備詢,介紹包括和談代表等事務籌備工作。同為安福系的光云錦也聲稱:“國會為國民代表,對于參與歐戰和平會議之事,當然與政府共同商酌進行辦法。”(6)③《速記錄》,《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66、67頁。議員陳嘉言等還質問政府對議和應如何預先準備,不致落在人后。(7)《議員陳嘉言等對于政府報告對德奧宣戰經過情形不無疑問及關于和議列席如何準備書》,《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154頁。12月1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在回復陳嘉言等人質問書中稱:“對于議和之事,早經延能熟諳外交人員在部共同討論以為準備。事關外交秘密,未便遽行宣布。”(8)《國務院咨復本院議員陳嘉言等質問政府報告對德奧宣戰疑問及和議列席如何準備文》,《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 5冊,第192頁。
收回山東利權是當時中國外交訴求的重心。參議員何淼森、尹宏慶在院會上提出相關議案,要求北京政府在參加巴黎和會時,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山東主權。何淼森在議案說明中特別引用1915年日本對德國的最后通牒,“第二款云‘為德政府將膠州灣租界全部以還付支那國家之目的。’又云‘如德不允,即須開戰,此為永保亞東平和起見,并無占領土地野心。’”當時日本政府聲明攻占膠州灣德國租借地,是以歸還中國政府為目的。根據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和平宣言,“吾人應定立和約,使各國可得其應有之地方,且可使人民無所畏懼其鄰邦。又言以后各國政府不得私立盟約……德國昔日所租借之膠州灣及其所攫得之種種利益,當然可以提出和平會議,要求收回。”(9)《速記錄》,《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4冊,第98—99頁。尹宏慶認為:“德人強租膠澳,攘我路礦,久為國人所飲恨,而魯省人民尤視為切膚之痛。”目前正值德國戰敗之際,政府應派代表在和平會議上提出收回膠州灣。而膠州灣在戰時復為日本所占,“究其性質是為代表協約各國暫行管理,其應讓歸我國,尤屬公義昭然。”對于膠濟鐵路中日合辦,青島開放為萬國商埠等主張,尹表示堅決反對,認為這是與美國總統和平宣言相違背的。此外,尹宏慶提案還認為應該一起收回英國租借的威海衛軍港。因為英國當時是為了抵制德國在山東擴張而租借的,現在德國已經戰敗,英國似無租借的必要,更何況租期已過并未續約,威海衛問題應該在和平會議上一起提出。(10)《議員尹宏慶對于山東膠州灣膠濟路威海衛請咨政府于歐戰和平會議列席提議收回以重國土而維主權案》,《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4冊,第112—113頁。院會同意將何淼森、尹宏慶等人的有關提案交付外交股委員會審查。
參議院外交股委員會在隨后的審查報告中,對于收回德國租借地的主張表示完全支持,認為這是戰勝國收回敵國從前所占國土問題,條件理由均極為充分,完全可以在和會上提出。但是在收回英國威海衛租借地問題上卻持謹慎態度,認為英國租借的威海衛,是協約國方面的問題,“當茲各國倡言公道,此種問題未始不可提議。”不過畢竟這與處分敵國的條件大有區別,“且此類租借地非止一處,所關亦非止一國,斷無單提威海衛之理。”最后委員會建議關于收回協約國在華租借地,“另為一案,期于勿傷協約之感情,于事方無窒礙,萬不宜于提議收回敵人所占領土案內牽連而及之也。”(11)《審查請咨政府對于歐戰和議列席時提出收回德國租借之膠州灣全部國土案報告》,《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4冊,第102—103頁。審查報告在提交院會審議后,多數表決通過立即咨達政府。
在眾議院方面,杜棣華、李學蓮、饒漢秘、王訥、金紹城等人相繼領銜提出撤廢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租借條約、力爭青島領土、設法收回青島、青島及附帶之鐵路交還我國、索還青島及各租借地案等。(12)參見《議員杜棣華等請政府派員列席歐戰平和會議時提出撤廢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租借條約并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間所訂各條約案》,《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116頁;《議員李學蓮等請政府力爭青島領土與領事裁判權案》《議員饒漢秘等請政府設法收回青島案》《議員王訥等請咨政府派員列席歐洲和議時提出青島及附帶之鐵路交還我國案》,《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138、140、149頁;《議員金紹城等請政府索還青島及各租借地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 5冊,第121頁。因內容與參議院相關提案類似,此處不再贅述。
修訂《辛丑條約》也是一些國會議員期待此次和會解決的外交問題。職業外交官出身的黃錫銓聲稱《辛丑和約》的巨額賠款,與德皇威廉二世當時的主張有關,“德帝詔之曰,此行當用無上武力以制服半教化之國民,使他日毋敢再抗。及至媾和,即實行經濟滅國之毒計,強索四百五十兆兩。”為此他提出四點建議,“一、德奧兩國既屈服于協約國,中國居協約之一,所欠該兩國賠款,當然與其他在中國境內之財產,一律為無條件之沒收,不再交付。二、美國應收之賠款,既經退還為中國辦學經費,以后照舊辦理,毋庸請其減免。三、日本應收之賠款,既有退辦教育之議,尚未實行,在我提議之先,應由我大使探詢日本大使意見,能否定議實行,如能實行,不必提議減免。不能實行,則一律提議。如此交涉,則較為圓融。四、英法俄比意西葡荷瑞九國,及歸英國代理各國應收之賠款,一律提議請求本利全部概行減免。”(13)《議員黃錫銓請咨政府參預議席請將辛丑和約未經交付之賠款全部取銷免予交付建議案》,《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4冊,第116頁。
對于長期存在的領事裁判權的不平等規定,眾議員洪玉麟稱,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人民應歸居在國管轄。“而各國對于我國反有所謂領事裁判權者,本員以為是項機關侵我主權實甚。查英美新約,有收回治外法權一款。”中國作為協約國成員享有平等地位,況且民國建立以來法律體系已經改良,此時應該取消領事裁判權。(14)《議員洪玉麟等請取消領事裁判權案》,《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134頁。杜棣華還特別強調日本、土耳其等國已經撤消別國在其國土之領事裁判權,“此種不公道自由之領事裁判權,在我國刷新政治以來,不復有存留之余地。”(15)《議員杜棣華等請政府派員列席歐洲和議時應提出撤回領事裁判權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 5冊,第112頁。
在參議院院會發言時,黃錫銓著重指出,協定關稅的不平等條約規定,不僅影響海關稅收,“其最重要者厥惟通商,吾國自與各國締結此等條約,商務上實受莫大之影響,且與農業工業亦大有妨礙……中國稅權既完全不能自主,不獨對于財政全失活動之能力。而對于商務,舉凡自由貿易,或保護貿易,或獎勵輸出,或制限輸出,皆不能自伸國權。而對于農工礦業,靡不遏蹴生機,妨害進步。”以棉紡業為例,“如外洋舶來之棉紗棉花等,因進口納完稅之減少,而成本較輕。成本既輕,則賣價亦賤。此在一般人視之豈不謂為好現象,殊不知外洋之棉紗棉花因銷路發達,進口之數日多一日,而本國之棉紗棉花遂瞠乎其后矣。”(16)《速記錄》,《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4冊,第96頁。在其關于恢復關稅主權建議案中,黃呼吁:“今幸協約各國大戰四年,以公理勝強權,以平等處與國。我國獲廁和平議席,亟應根據公理要求平等,于和議席上提出議案,請求修改中國與各國通商新舊約合同章程例案,所有關于協定稅率之條文,概行刪除廢棄,恢復我國自由制定稅率之主權。”(17)《議員黃錫銓請咨政府籌備參與和議請改商約刪除關稅協商恢復關稅主權提出建議案》,《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4冊,第140頁。因建議案不需要經過三讀會程序,經多數表決通過后即日咨達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巴黎和會召開日期的臨近,至1918年12月,國會的關注達到頂峰。在1918年12月7日眾議院第17次會議上,全部14項議程中有關和會外交問題共計10項,數量相當多,具體包括:“組織外交調查會案(議員饒孟任等提出)”“請組織特別外交委員會案(議員王雙歧等提出)”“請政府慎選外交和平會議使節以重外交建議案(議員金明川等提出)”“請政府于派員列席歐洲平和會議時提出請撤廢德國在山東省之膠州灣租界條約并前清光緒二十四年各條約案(議員杜棣華等提出)”“請咨政府力爭青島領土與領事裁判權等問題建議案(議員李學蓮等提出)”“請咨政府設法收回青島案(議員饒漢秘等提出)”“請政府將青島交涉提交和平會議主張交還我國建議案(議員王訥等提出)”“請政府索還青島及各租借地建議案(議員金紹城等提出)”“請取消領事裁判權建議案(議員洪玉麟等提出)”“請政府派員列席歐洲平和會議時提出撤回領事裁判權案(議員杜棣華等提出)”。(18)《速記錄》,《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 5冊,第1—2頁。12月27日,這些議案均通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審查。另據統計,在和會正式召開之前,參議院議員提出主張收回和恢復中國權益的議案就達 6 項,眾議院議員提出此類議案有 11 項之多,其中對于民眾一致認可應該堅持的立場,如收回青島、膠州灣租借地、取消領事裁判權及協定關稅等問題,在兩院得到了多數議員的認同。(19)賈德威:《安福國會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23頁。
安福國會對巴黎和會的積極反應,對北京政府和會外交決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有研究表明,北京政府在參加和會前,確定了3項外交目標:1.領土完整,外國租借地歸還中國。2.恢復國家主權,廢除《辛丑條約》強加給中國的各種限制,特別是外國軍隊撤離中國。3.經濟自由,實現關稅完全自主。(20)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65頁。國會對于和會的外交訴求與北京政府的和會外交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國會權力運作與和會外交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至6月28日閉會,這一時期主要是安福國會第二期常會開會時間。對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關注,成為本會期國會權力運作的中心內容之一,主要包括巴黎和會的應對策略、對日外交與山東問題等。從方式來看,大致分為立法與行政監督兩種。前者主要是指國會議員提出與和會外交有關的提議案、建議案,提交委員會與院會議決后咨送政府。后者則是通過質問權、彈劾權與查辦權的行使,表達國會的質疑與不滿,監督政府的外交活動。
雖然時人對巴黎和會充滿期待,但是外交談判畢竟是非常現實的,充滿了挑戰性,中國在和會上的外交目標如何實現,當然需要應對策略。不僅北京政府和會專使為此殫精竭慮,國會方面也在積極謀劃。在眾議院方面,代表性的議案是議員王葆鋆提出的“對于歐洲和議應恢復及應要求之權利與應提倡之事件及應取之外交政策建議案”,該案在1919年3月22日院會上提出,主張在和會上,將中國外交目標分為現實與理想兩類,現實類包括應該恢復與要求的中國權利,理想類是指應該提倡的外交理念。政治上應恢復的權利:恢復統治蒙藏完整主權、廢止勢力范圍及領土不割讓條約、收回割讓地與租借地;政治上應要求的權利:裁判自主權、華工待遇與移民待遇的改善、不平等條約的改定權;經濟上應恢復的權利:關稅自主與互惠權、路礦自主權;經濟上應要求的權利:各國未付賠償金的免除。應提倡之事件:戰后國際救恤事業、人種差別主義的廢止、平等主義國聯聯盟的建立。在外交策略應對方面,“不可不聯美以為親日之保障,更不可不以平和的外交政策、經濟的外交政策,以與日美英法等國相周旋。我國前此之外交固可以此次之平和會議為解決之機會。而后此之外交更可依此次之國際聯盟為解決之機會。”關于國際聯盟,“除有必要之外,萬不可犧牲主權,以聽鄰之所為。”(21)《議員王葆鋆提出建議政府對于歐洲和議應恢復及應要求之權利與應提倡之事件及應取之外交政策建議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1冊,第115—131頁。4月3日,全院委員會審議王葆鋆建議案,除條件及文字略有修正外,對于原案全體贊成。(22)《全院委員會審查王議員葆鋆建議政府對于歐洲和議應恢復及應要求之權利與應提倡之事件及應取之外交政策一案全體贊成交付公決書》,《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2冊,第62頁。5月2日,院會通過建議案審查報告,決定立即咨送政府。
同樣地,參議院方面也有議員認為對于巴黎和會的立場,首先應贊成國際聯盟,換取協約國好感,然后再要求列強尊重中國國際平等發言權。魏斯炅強調:“我國若不先機自動首先加入聯盟,不獨酷好和平親愛友邦之真誠莫由表示,徘徊中路必受他動之提攜,則損害國權。”魏認為在中國專使在和會上應該強調中國之所以能夠列席和會,“實由我國參加大戰軍事補助而外,又復輸出僑工、供給物資,犧牲大多數之國財民命之購得之結果。”(23)《議員魏斯炅請咨政府對于歐洲會議首先贊成國際聯盟并要求尊重我國之國際平等發言權建議案》,《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6冊,第168頁。
在山東問題成為中國和會外交的焦點之后,國會亦非常關注。眾議員沙明遠在質問政府關于青島及其他中日關系交涉書中,提出六大問題質問政府,“一、兩院議員迭經建議青島及膠濟鐵路應交還中國,政府之主張及訓令各全權委員,是否與人民之希望一致?二、關于山東及青島問題,除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交涉之條約等項外,其他各種密約尚有若干?三、關于順濟、高徐合同,政府一月三日答復山東議員,認為正式合同尚待商定,則前項草合同是否可以取消?四、傳聞日本催訂各鐵路之正合同,有無其事,政府擬如何對付?五、去歲參戰處與日本訂定密約,現在歐戰既終,該密約自當作廢,政府何不提議?六、參戰處向日本借款二千萬元,究竟交過若干,其已交者當即設法還去,其未交者當即勿論,政府有是決心否?”(24)《議員沙明遠質問政府關于青島及其他中日關系交涉書》,《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 6冊,第163頁。
彼時中國在和會上爭取山東權利的最不利因素是“中日密約”,即1918年9月24日中日簽署的《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與《山東問題換文》。條約確定了日本在膠濟鐵路的合辦地位,以及濟順、高徐二鐵路的修筑與控制權,“進一步強化繼承德國權益的法律立場。”(25)唐啟華:《“中日密約”與巴黎和會時期中國外交》,《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眾議員謝鴻燾敏銳地發現這一點,在其領銜的建議案中特別指出,和會外交受挫在于中日二十一條與濟順、高徐路各草案,“此日人所以有繼續德人權利之抗議也。”(26)《議員謝鴻燾等提出關于民國四年二十一條約及順濟高徐路各草案請電歐洲和會否認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3冊,第123頁。參議員魏斯炅也在質問書中尖銳地指出:“中國既參與戰爭,則所有前與德國之脅迫條約,在法自應無效。直接還我舊服,以保主權。”但是最近聽到日本駐華公使聲稱,根據中日密約的內容,日本在山東侵占的原德國權益重新歸于日本所有。魏對此表示不能理解。“國會為人民代表,豈容置若罔聞。”(27)《議員魏斯炅質問政府關于山東地方應自收回之利權是否與他國訂有密約限期答復案》,《參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6冊,第87頁。一些議員還提出了對策與建議。如參議員莊陔蘭也認為中日二十一條及濟順、高徐合同草案均未經國會同意,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屬于無效,“且中國加入協約,德人租借原約根本取消,日人私訂之約豈能繼續有效?”(28)《請電歐洲和會否認私訂之二十一條約及順濟高徐各草約提議案》,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匯編》第1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頁。
隨著和會簽字日期迫近,國會對山東問題的關注進一步加深。6月6日,眾議員曲新卓質問政府對于山東問題另行保留近日有無變更,提到5月20日眾議院曾開會同意政府對于山東問題另行保留的議決,但近日又傳出政府致電陸專使“有萬不得已時,可以酌情辦理。”曲新卓質疑政府立場是否又發生改變。(29)《議員曲新卓質問政府對于山東問題另行保留近日有無變更請明白答復書》,《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4冊,第159頁。6月29日,繼曲新卓質問后的是同為山東籍議員杜惟儉,稱政府關于簽字問題立場矛盾,“答復議員質問,則謂保留一層竟難如愿,即審時度勢決定簽字。批示人民請愿,則允其如不能保留即拒絕簽字之要求。究竟政府對于山東問題萬一不能保留取何方針?”(30)《議員杜惟儉等質問政府對于山東問題不能另行保留時究有若何堅決主張至議員質問之答復與山東請愿團之批示是否政府同負責任書》,《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4冊,第189頁。
此外,還有議員要求政府在和會上對日本的無理要求持抵制立場。如眾議員易克臬等對于日本專使在巴黎議會蔑視我國發言自由權,以及逼迫我方撤回顧維鈞、王正廷兩委員表示不滿,聲稱在和會上,顧維鈞、王正廷贊成威爾遜總統反對秘密外交的立場,引發日本專使的不滿,日本要求中國保持一致立場。“望我政府嚴詞拒絕,并于答復日使及于巴黎會議中,指明該專使反復矛盾違反公意,應請日本政府迅予撤回。”(31)《議員易克臬等質問政府對于日本專使在巴黎議會蔑視我國發言自由權電彼政府迫我撤回議和顧王兩委員是否屬實及若何答復書》,《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1期第 6冊,第158頁。
對和會外交問題的監督,也是國會重要的立法職能,雖然其中摻雜有派系政治因素,但對議員來說,卻是有法可據,《臨時約法》賦予國會針對政府官員的質問、彈劾與查辦權,其中質問權行使多以書面質問書形式,上文多處已經提及。彈劾權行使,主要有眾議員李繼楨提出“彈劾國務員錢能訓違法失職案”。李繼楨聲稱:“國務員錢能訓等違法失職,辱國喪權。”列舉的違法行為包括任命議和專使未經國會批準同意、對日外交政策失措等,而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也成為抨擊對象,“陸征祥庸碌無能,依庇外國婦人以自重(陸的夫人為比利時人);顧維鈞少年輕躁,略善英語;王正廷卑污齷齪,才可傳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輩為專使。此爭名義,彼爭座位,爭議未了,而青島已斷送于人。” 彈劾書最后強調正是政府“昏庸錯亂,輕舉妄動,竟演成今日之失敗。”(32)《議員李繼楨提出彈劾國務員錢能訓違法失職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3冊,第157—159頁。
在五四運動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成為社會輿論攻擊的對象。議員羅正緯等提出“彈劾交通總長曹汝霖賣國嫌疑亟應免職并請查辦案”,居然有46人連署,聲勢很大。羅正緯認為曹汝霖“聲名惡劣,無可諱言。”雖然提出辭職,但是辭職書內容“無非借事邀功,希圖戀棧,倘復任其在位,不獨重違民意,而政府與人民之惡感日積月深……乃其辭呈內僅言個人之私,橫加學生之罪,無一詞片語憐其冒難救國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國。”至于曹在辭呈里強調自己對外借款有功,“是欲借外人之勢力,挾制政府,盤據要津,情詞畢露。”羅正緯要求政府立即將曹免職,從嚴查辦。(33)《議員羅正緯等提出彈劾交通總長曹汝霖賣國嫌疑亟應免職并請查辦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3冊,第155—156頁。同樣地,議員謝鴻燾等也提出查辦案,“查山東利權喪失之故,大都內則由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狼狽為奸,外則由駐日公使章宗祥勾結為鬼為蜮,如高徐、濟順鐵路合同以及各種密約喪權辱國。”謝認為三人涉嫌外患罪,要求總統免職送交司法查辦。(34)《議員謝鴻燾等提出大吏賣國請政府下令查辦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3冊,第161頁。
三、派系利益與和會應對
安福國會在巴黎和會期間的表現,除外來輿論等壓力之外,還與其維護派系利益有關。安福系在國會中原有384人,占議員總數的80%強,后因梁士詒為首的舊交通系從安福系分出,另組僑園俱樂部,剩下純粹安福系議員約有330多人,但仍然超過議員總數的70%,“成為國會的唯一支配者。”(35)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2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64頁。所以,第二屆民國國會又稱為“安福國會”,國會與安福系的利益立場基本是一致的。安福系在處理與政府與研究系的關系上,焦點是和約簽字與外交責任問題。
1919年5月12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在中南海懷仁堂邀請兩院議員召開茶話會,稱外交問題近日非常緊急,特請兩院議員商量辦法,并就和約簽字問題征求議員意見。李繼楨首先發言,聲稱:“昔時政府特派專使,并未經國會通過。現今外交吃緊,及簽字問題欲求國會意見,以備外交或有失敗,即可委過于國會。將來國民激昂,議員實不能代人受過。”(36)《新國會對山東問題之態度》,《申報》1919年5月15日,第6版。多數議員發言主張不能簽字,并責備政府立場搖擺,就連眾議長王揖唐也對李繼楨的意見表示贊同。錢能訓對此只能表示歉意,稱“此事將來即當提交國會征詢意見。”(37)《昨日懷仁堂之外交會議》,《晨報》1919年5月13日,第2版。后來總統徐世昌出面協調也無濟于事,“東海召集議員討論,提出意見。所持論調,對于不簽字之害多,簽字之害少,甚欲國會贊成簽字,而對于輿論之質問,又以不簽字為言,使國會負其咎。安福部議員知其用意,不謀而合,一致反對。”(38)南海胤子:《安福禍國記》,《近代稗海》第4輯,第375頁。
其實早在5月7日,國會一部分議員以此次外交失敗由政府應付失當,對錢內閣提出彈劾案。如李繼楨、光云錦等相繼提出彈劾錢能訓失職違法案。5月9日,參議院議員魏斯炅、眾議院議員王毅又提出質問書。5月16日,安福系開會決定外交除山東問題不簽字外,其余悉聽政府處理。(39)《專電》,《申報》1919年5月17日,第3版。但是政府方面仍然不甘心,繼續尋求國會支持。5月20日,關于和約簽字問題,政府正式咨請國會議決。5月26日,眾議院召開秘密會議,對政府外交方針表示贊成,“惟原約未交難表決,應將原文退回,補提再議。”(40)《專電》,《申報》1919年5月27日,第4版。不久,議員王訥等人聲稱時間已近6月5日,請議長速催政府將巴黎和議全案草約交議。(41)《議員王訥等請議長速催政府將巴黎和議全案草約交議案》,《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4冊,第259頁。
從5月底開始,政府主張簽字的立場開始明朗化。國務院5月24日敬電公開關于山東問題的立場,“第一步自應力主保留,以俟后圖。如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而且“簽字后,仍須國會議決,元首批準,尚不乏操縱余地。”(42)《國務院電曹錕等陳述政府主張歐和草紙簽字理由》,林清芬編注:《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臺北“國史館”2003年版,第46—47頁。6月9日,安福部召開政務研究會,光云錦稱“政府遣派代表赴歐議和,并未交國會同意,實無異專制。議和及外交失敗始提出國會,對于青島主張保留,現又通電各省主張簽字,而謂兩院議長已然同意,意在諉過于同人,萬難承認。”后與會者一致贊成通電否認同意簽字,特別提到“查議會以多數議決為原則,議長不能代表全院意思,且詢請兩院議長對于此層并無若何表示。”(43)《安福部之特別大會》,《申報》1919年6月12日,第5版。6月10日,眾議院曲卓新等向政府提出質問書,要求政府解釋對于山東問題立場是否改變。
6月11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宣布引咎辭職。同日徐世昌以對德和約簽字與南北和會問題為由,咨文向國會辭職。有研究表明,徐世昌的辭職咨文,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政治謀略。當時北京政府未設副總統,徐突然辭職,將會出現國家元首空位,勢必引來各方竭力挽留。“如果挽留其總統之職,就必須支持其內外兩點政策。具體講,必須支持簽署對德和約,必須支持重開南北和會。”(44)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第171頁。果然辭職咨文被國會退回,但是在政治責任問題上國會并未讓步,兩院議長并發表聲明:“查現行約法,行政之組織系責任內閣制,一切外交、內政,由國務院負其責任,大總統并無引咎辭職之規定。”(45)《總統辭職問題昨聞》,《晨報》1919年6月12日,第2版。這明白表示徐世昌可以挽留,但錢能訓必須下臺,6月13日,徐世昌準免錢總理職,特任財政總長龔心湛兼代理國務總理。6月25日眾議院召開院會,山東籍眾議員杜惟儉提出議案,指出政府如果違反輿論貿然簽字,“屆時國會雖仍可否認其簽字無效,然補救已晚。”(46)《山東請愿團之進行》,《申報》1919年6月28日,第6版。經院會議決改為建議案后當天咨送政府。
自4月以來,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接連受挫,北京政府應對失措,五四運動更是表明民意的巨大不滿。在此困境中,政府方面自然希望國會能夠分擔責任。一些皖系要人也傾向政府立場,如段祺瑞就主張和約簽字。5月24日,段祺瑞通電主張和約簽字之利,“歐約如不簽字,國際聯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條件一切放棄,又恐如外蒙宣戰事,借愛國以禍國也”。(47)《段祺瑞致曹錕等剖析巴黎和會簽字與否之國家利害》,《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5冊,第49—50頁。在段祺瑞通電支持簽約的情況下,多數議員仍然不為所動。“很顯然,國會議員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他們是為了更好地服從于自己的利益。”(48)Fung ,Allen Yuk-Lun ,The struggle over the constitution:Chinese politics,1917-1919,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6,p.247.
安福國會作為政治利益集團,從自身利益考慮,反對簽約的起因是對于政府在南北和談中的立場非常不滿。當時北京政府同意在南北和會上討論商談國會問題,“朱總代表(朱啟鈐)與西南會議,居然敢議及國會問題。”當時南方代表在和談中提出八大條件,其中包括恢復舊國會。“此噩電傳來,安福部大嘩。眾議院全體議員,請錢內閣出席質問。錢無詞以對,勉為答曰:‘并非敢議國會,不過討論及之耳。’安福部大不以為然,謂神圣不可侵犯之國會,即討論亦不可。”(49)南海胤子:《安福禍國記》,《近代稗海》第4輯,第376頁。政府在國會問題上的態度勢必危及安福國會的合法性,引起后者的恐懼與憤怒。彈劾錢內閣,其實是表達對徐世昌的不滿,錢的背后是徐,徐企圖以解散安福國會為條件,換取南方對其總統地位的承認。因此,“對于安福俱樂部來說,國會取消與否,這才是切身利益所在,而德約簽字與否,責任在政府,實際上與國會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既然國會與政府關系惡化,國會也就無須出面為政府分擔責任,引火燒身。”(50)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第211頁。更進一步而言,在南北和會的責任問題上,安福系已經飽受輿論批評,所以此時必須在外交問題上表現出與民意一致,以爭取自身的正當性。“民族國家的觀念此時已經成為主流的政治觀念,即使是野心勃勃的軍閥和失意無聊的政客也要標榜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唯其如此,才能贏得民意。”(51)馬建標:《沖破舊秩序:中國對帝國主義國際體系的反應(1912—192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版,第191頁。
結 語
外交權是各國議會行使的重要權力之一。如美國憲法早就明文規定外交權是一項由總統和國會共同行使的權力。一般來說,議會擁有外交領域的人事、宣戰、締約同意權,并且通過立法、監督或者調查等手段,對外交決策進行干預。在民國初年的外交權力制度設計中,國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是《臨時約法》第 35 條,“臨時大總統經參議院之同意,得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
安福國會成立后不久,在審議政府對德奧宣戰案時,就開始重視自身在外交方面的角色。1918年11月1日眾議院開會,克希克圖對政府方面僅派數名一般委員出席表示不滿,指出:“政府提出對德奧宣戰咨請同意追認案,乃極重大之事,按照前國會先例,應由國務總理、外交總長及負責任各總長出席詳為說明。不意本日國務員竟無一名出席。”他認為政府方面對于同意案的態度太不慎重,要求議長立即電話通知國務總理、外交總長等出席,否則本案不能審議。光云錦也認為政府要員不出席,“玩視外交,玩視國會,此實足以引起人民對于內閣不信任。”(52)《速記錄》,《眾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 4冊,第41、43頁。克希克圖的主張獲得在場議員一致同意。后因國務總理、外交總長有事不能出席,于是眾議院當天拒絕審議。次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外交總長陸征祥等被迫到會說明,同意案才以244票多數在眾議院通過。
1919年4月,在中日山東密約相繼曝光后,有議員質問政府陸續宣布各種條約合同何以不交國會追議,指出歐戰以來,政府與各國簽訂的各種契約,如中日軍事協約、二十一條密約、參戰借款合同、軍械借款合同、濟順、高徐鐵道借款合同等,“不特未經國會通過,甚有并未經過國務會議者,在法律上當然不能為有效。然就事實上言之,應審查締約當時有無強迫及詐欺手段,以決定有效與否,此提交國會追議之所以不可須臾緩也。”政府只向報紙公布,而不提交國會審議的做法,有失法治精神。(53)《議員杜棣華質問政府陸續宣布各種條約合同何以不交國會追議書》,《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2冊,第146頁。國務院咨復時辯稱:“查此次宣布各種文件,不盡屬條約性質,且締結在前,法律上既無追認明文,自無從交國會審議。”(54)《國務院咨復議員杜棣華質問政府陸續宣布各種條約合同何以不交國會追議文》,《眾議院公報》1919年第2期第2冊,第199頁。
國會不僅在國內政治場合注意到外交權行使,還有意識對各國發出聲音,表明中國外交立場。一戰甫一結束,何焱森就建議以中華民國國會名義致電法國國會及英美各國國會祝賀歐戰勝利,“本院為代表國民之機關,故特提出此案,既以聯絡感情,尤盼望于國際上取得一位置也。”(55)《速記錄》,《參議院公報》1918年第1期第3冊,第64頁。議案當場獲得全體議員起立通過。巴黎和會召開之后,陳振先等提出兩院議長用國會名義致電出席和會的歐美代表,闡明山東問題立場,“將來山東青島及膠濟鐵路,我國能否直接完全收回,不附其他條件。高徐、順濟鐵路密約能否廢除,將于開議后短時期內決之。我國命運亦將于此短時期內定之。”在當下民族自決主義興盛之際,兩院議長應該以國會名義致電美、英、法、意國領導人,“懇切陳詞,為吾國國民請命,以作全權代表后援。”(56)《請由兩院議長用國會兩院名義電致歐美議和代表主持公理恢復我國山東主權決議案》,《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匯編》第11冊,第231頁。1919年4月4日,國會參眾兩院共同致電巴黎和平會議與美英法意四大國領導人,稱“青島及膠濟鐵路不附帶其他條件,由德國直接交還敝國。又高徐、順濟鐵路所訂官約亦請廢除,以符協約維持公法之宗旨。”(57)《致巴黎平和會議會英首相、法總理、義守(首)相、美總統電》,《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匯編》第12冊,第321頁。
從立法運作過程來看,安福國會不僅以立法、行政監督等方式參與外交事務,而且在外交制度建設上也有所作為,如1919年8月通過《外交官領事官考試法》,被日本學者川島真在專著中特別提及,認為安福國會扎實進行了制度方面的完善工作。(58)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頁。但是在派系政治等因素制約下,當然不能高估安福國會的外交作用與影響,因為即使是在美國,“與總統行政部門相比,國會外交決策顯然處于弱勢地位。”(59)李慶四:《美國國會與美國外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頁。雖然在外交問題上,安福國會有主動進取的表現,但是外來的民意壓力作用與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其在和會外交問題上的實際成效也是有限的,提出的彈劾案與查辦案通常沒有結果,一些重要的建議案在提交委員會審查再也沒有下文。不過,至少在制度形式上,安福國會在巴黎和會時期的表現,仍然不失為近代中國議會外交的初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