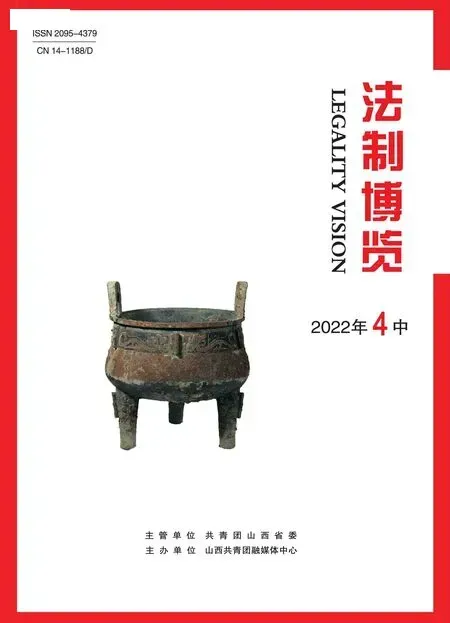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視域下的社會治理
李雪松
廣東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0
一、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指出:“既要立足當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又要著眼長遠,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促進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一)法治思維的內涵
有學者認為,法治思維就是指執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過程。[2]
筆者認為,法治思維是一種思維方式,要求思維主體在進行思維時將法治的要求置于思維框架中,運用法律規則、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基于理性認識、分析、判斷和處理問題的一種邏輯思維方式。
(二)法治方式的內涵
法治方式,就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
法治方式的實現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依據法治思維不做出某些行為;第二,設立行為規范,規制具體行為;第三,運用公權力對相對人實施管理、治理;第四,設置正當程序,保障公權力的正當行使;第五,設置監督和救濟渠道,管控公權力的行使;第六,設置行為的法律后果,對行為進行價值上的引導;第七,對違反程序和法律的行使公權力行為進行追責,保障公權力的合法性。
(三)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
法治思維是一種受到規范的思維方式,因而法治方式表現為受規制的行為方式。這種受規范的思維方式和受規制的行為方式,都指向公平、正義、自由的價值取向。法治思維是規范思維,規則與程序是其顯著特點。法治思維的規范性是通過法律方法來發揮作用的。[3]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統一、互相促進的。[4]筆者認為,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關系如下:首先,法治思維是法治方式的內在驅動和精神核心;其次,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維的外在實現形式;再次,法治思維對法治方式的實現有決定作用;最后,法治方式反作用于法治思維。
二、社會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論述,指明了解決我國當前社會治理面臨問題的方向。國家治理包括社會治理,社會治理的總遵循應當是國家治理的要求和方向。因此,社會治理也應當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
(一)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國家治理是以國家問題為對象的治理,包括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金融、政黨、國防、外交等方面問題的治理。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一環,社會治理應當符合國家治理模式的特征和要求。[5]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我國社會治理提出了要求和方向。
(二)社會治理的主體
對社會治理主體的界定有“一元論”,即政府專屬;“二元論”,即政府與社會組織共享;“三元說”,即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在各自領域行使;“七分說”,即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各司其職、社綜委協調、社會協同、公眾支持與監督、執法與司法保障,等等。[6]
筆者認為,“一元論”過于強調政府的治理主體地位,忽視了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不承認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的法律地位,過于片面。“二元論”雖然引進了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主體,確認了社會組織的社會治理主體法律地位,但是并沒有承認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的法律地位,依然是屬于片面的論斷。“三元說”強調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在各自領域行使治理權,開展社會治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代表性,但其涵蓋面不夠完整,不能涵蓋實踐中的所有社會治理主體。而“七分說”,能較好地表現當下中國的社會治理現狀,較為適合當前的國情。社會治理主體按照“七分說”進行界定,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合理性和完整性。
(三)社會治理的內容
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筆者認為,社會治理的內容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治安秩序方面。社會治安秩序方面的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首要方面。社會治安秩序方面的治理涵蓋了社會秩序、經濟秩序和公共安全等方面。隨著我國現代化的不斷發展,許多新犯罪模式和新問題不斷涌現,社會治安秩序面臨新考驗。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的戰略,為社會治安秩序治理提出了更高目標。
我國社會治安秩序治理水平正穩步提升,并已經步入創新發展的新階段。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國近年來逐步完善了社會治安秩序方面的立法,設立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從立法層面解決了一部分社會治安秩序治理問題。在具體實踐方面,我國治安秩序治理水平已經逐步社會化、信息化、系統化、創新化,治安秩序治理能力不斷提高。
第二,人民內部矛盾方面。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當前社會治理中重要的問題。近幾年的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問題主要集中在基層,表現在基層。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實際,主要是經濟利益的矛盾。如果不及時對經濟利益的矛盾進行有效處理,則會演變成為政治方面的矛盾,從而引起沖突或引起群體性事件。
第三,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的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截至2021年10月,已造成四百八十余萬人死亡。在此次新冠肺炎的風暴中,我國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檢驗,我們經受住了考驗。
在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方面,我國始終堅持生命至上,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堅持及時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加大投入研發疫苗、藥物和快速檢測技術,強化應急物資保障,強化基層衛生防疫。在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法律方面,我國這兩年修改相關法律規范,出臺生物安全法,持續完善公共衛生法律法規體系,為社會公共衛生安全筑牢法律防線。
三、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與社會治理
(一)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解決社會治理問題的重要抓手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符合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如何把社會主義法治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實踐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可以進一步將社會主義法治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都以法治為前提,因此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都遵循法治軌道。在此基礎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夠為社會治理作出指引,使社會治理走在法治的軌道上,并將社會主義法治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促進社會治理。
(二)社會治理需要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社會是一個復雜的構成,社會不是一旦產生就能夠實現其組織的和諧相處的。社會只要存在,必然會出現矛盾和問題,需要進行社會治理。社會治理有許多實現方式,如私力救濟、協商、訴諸司法、信訪等等。這些實現方式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都指向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而解決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最好選擇,就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法的普遍性決定了法治是社會治理的有效手段,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法的普遍性的外化,是人們在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時思維方式的普遍選擇。這又是由法的社會性和權威性決定的。法的社會性是指法的締結和創立是經過社會討論、構建、商議的,全社會所認同。法的權威性是指法在社會治理體系中享有權威的地位。
(三)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促進社會治理不斷完善和創新
社會治理是復雜的,它因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有一些新出現的或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不容易顯現出來,比如“大數據殺熟”“數據算法剝削”等。此時,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有自身的價值取向,并且能以法治為軌道不斷前行。因此,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去探索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思路就得以展開,逐漸形成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路徑。
(四)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不斷發展、豐富和完善的,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而進化。隨著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法治思維會不斷汲取養分,形成新的社會共識和社會理念,從而構成新的法治思維。而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又會衍生出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從而豐富法治方式的實現形式。如“數字法治”“智慧司法”“大數據”等,都是新時代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現的方式。
四、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作用于社會治理的體系化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作用于社會治理中,需要體系化。只有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作用于社會治理的體系化,才能最大限度地釋放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量,作用于社會治理實踐中,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
(一)領導干部應具備法治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在社會治理中有重要作用,決定了社會治理的方向。因此,領導干部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應當首先具備法治思維,實踐法治方式。
就社會治理而言,黨委、政府、社綜委、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領導干部,作為“關鍵少數”,其自身的法治思維要求應當提高標準,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做到以身作則。在實踐社會治理的過程中,領導干部應當首選法治方式實現其治理手段。領導干部只有在實踐中結合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治理的法治化,使社會治理沿著法治軌道不斷發展和完善。
(二)重視領導干部績效考核中的法治考核
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實踐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監督。將領導干部績效考核中的法治考核列為重點,提高一定權重,是直接且有效的路徑選擇。強化領導干部的法治考核,可以促使領導干部在實踐中重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運用,使領導干部養成遇事首先使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習慣,進一步使領導干部形成良好的法治思維,形成更適合解決問題的法治方式。
(三)構建各類社會治理法律法規、規章制度時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社會治理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構建各類社會治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時,應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社會治理工作問題繁多、數量巨大、矛盾龐雜,需要設立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要求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全面性,要求體系化、具體化、完善化。進一步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有利于豐富和完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構建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型社會治理體系。
(四)積極引導各級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社會治理
除了要抓住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之外,各級干部在社會治理體系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要積極引導各級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社會治理,使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各級干部進行社會治理工作時形成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從而使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入心入腦。
(五)社會和公眾也應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參與社會治理
社會協同、公眾支持與監督也很重要。因此,社會和公眾也應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參與社會治理工作,使社會治理沿著法治的軌道運行起來。社會和公眾應當建立相關機制,使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運用得到充分發揮,使各方主體主動、積極、習慣性地使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施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