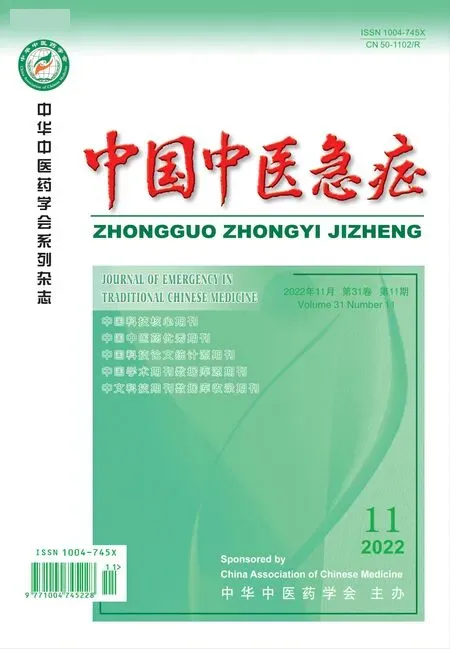《肘后備急方》中疫病用藥的數據挖掘研究*
王曉鵬 林孟柯 梁立新 孫冉冉 丁雪霏 陳騰飛 劉清泉 肖陽春△
(1.北京中醫醫院順義醫院,北京 101300;2.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北京 100010)
中醫藥的發展史是一部與疾病斗爭的實踐史,幾千年來,疫病始終是威脅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中醫在治療疫病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1]。晉代葛洪撰寫的《肘后備急方》雖不是一本中醫疫病專著,但卻不乏對疫病的記載。在該書中對傷寒、時行、溫疫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也指出了“鬼注、尸注”(相當于肺結核一類的傳染病)的低熱、慢性消耗性癥狀以及“乃至滅門”的傳染性[2],在書中列舉了數首“避溫疫”“避天行疫癘”的方劑,如老君神明白散是最早出現的預防和治療疫病的專方,同時也創造了很多空氣消毒預防疫病的方藥,如太乙流金方[3],對后世醫家影響很大。在該書中葛洪最早記錄了天花的癥狀表現[4-5],也最早記載了人工免疫療法,如被狂犬病犬咬傷,用犬腦外敷后不復發[6]。本文通過數據挖掘的方式,探討《肘后備急方》中治療疫病的用藥特色,以期為防治傳染病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納入的方藥均來自晉代葛洪撰寫的《肘后備急方》,研究對象為疫病,主要來自尸注鬼注、霍亂、傷寒時氣溫病、時氣病起諸勞復、寒熱諸瘧方等章節。
1.2 納入和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 主治疫病的方藥,為尸注鬼注、霍亂、傷寒時氣溫病、時氣病起諸勞復、寒熱諸瘧方等章節中的處方;兩味藥及兩味藥以上的處方;內服藥物。必須滿足上面所有條件方可納入。
1.2.2 排除標準 跟疫病無關的方藥;單味藥處方;外治的藥物;在書中提及但未納入藥典中的藥物,如梁上塵、千里流水等。若滿足上面任何一項即可排除。
1.3 數據清洗
為了避免同一種藥物因命名不同而造成錄入分析混亂,在數據錄入前將中藥參照《中藥學》(第2版)進行數據清洗,如將“桑樹白皮”錄入為“桑白皮”;“豉”錄入為“淡豆豉”;“桂”錄入為“桂枝”;“躑躅”錄入為“鬧羊花”;“釜底墨”和“灶突墨”均錄入為“百草霜”等。
1.4 數據分析
本研究分析醫案的軟件選用“中醫傳承計算平臺v3.0”,在研究前從軟件中下載數據錄入Excel表格,由雙人將《肘后備急方》中的疫病方藥錄入到Excel表格,確保數據無誤后,將數據導入“中醫傳承計算平臺v3.0”中逐項進行分析。
2 結 果
2.1 用藥頻次分析
對100張處方進行統計發現用藥頻次排名前10的中藥分別為:甘草、干姜、淡豆豉、附子、黃連、桂枝、常山、大黃、麻黃、黃芩,具體見表1。

表1 頻次前10位的藥物
2.2 四氣、五味、歸經分析
對所用中藥的四氣進行統計發現:寒性藥物最多,占總頻次的35.31%;其次為溫性藥物,占總頻次的28.13%;再依次為熱性和平性,分別占總頻次的15.30%和13.15%;涼性藥物最少,占總頻次的8.11%。對所用中藥的五味進行統計發現:辛味藥最多,占總頻次的35.60%;苦味藥次之,占總頻次的29.42%;再依次為甘味藥和咸味藥,分別占總頻次的27.57%和3.91%;最少為酸味藥,占總頻次的3.50%。
藥物歸經統計發現前5位依序為肺經、胃經、脾經、心經、肝經,見圖1~圖3。

圖2 五味雷達圖

圖3 藥物歸經雷達圖
2.3 藥物功效分析
對納入處方的藥物進行分析,其藥物功效排名前5的依序為解表類、補虛類、清熱類、溫里類、瀉下類,具體見圖4。

圖4 藥物功效統計柱狀圖
2.4 對藥統計
將納入的方藥導入到中醫傳承計算平臺v3.0,在“方劑分析”模塊下進行分析,得到常用的對藥頻次,具體見表2。

表2 常用對藥分析頻次
2.5 角藥統計
將納入的處方導入到中醫傳承計算平臺v3.0,在“方劑分析”模塊下進行分析,得到常用的角藥頻次,具體見表3。

表3 常用角藥分析頻次
2.6 組方規則分析
在“方劑分析”模塊下“關聯規則”對100個處方進行分析,設置支持度為3,置信度為0.7,可得到常見藥物關聯分析,具體見表4,同時也得到藥物規律網絡化展示圖,具體見圖5。

表4 支持度為3,置信度為0.7時藥物關聯分析

圖5 支持度為3,置信度為0.7時的組方規律網絡圖
2.7 聚類分析
通過中醫傳承計算平臺v3.0利用K均值聚類算法(也稱k-means算法)統計出類方核心組合,將K值設定為3,可以將100個處方聚為3類,具體見表5,通過聚類和回歸模擬繪制圖6及圖7;將K值設定為5,可以將100個處方聚為5類,具體見表6,通過聚類和回歸模擬繪制圖8及圖9,具體如下。

圖6 K值為3時方劑聚類分析圖(k-means算法+聚類)

圖7 K值為3時方劑聚類分析圖(k-means算法+回歸模擬)

圖8 K值為5時方劑聚類分析圖(k-means算法+聚類)

圖9 K值為5時方劑聚類分析圖(k-means算法+回歸模擬)

表5 K值為3時類方核心組合

表6 K值為5時類方核心組合
3 討論
在《肘后備急方》中認為疫病多與“癘氣”相關,在書中記載“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耳,而源本小異。其冬月傷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風冷,至夏發,名為傷寒。冬月不甚寒,多暖氣及西風,使人骨節緩墮受病,至春發,名為時行。其年歲中有癘氣兼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如此診候相似,又貴勝雅言,總名傷寒,世俗因號為時行”,《肘后備急方》多處提到用“汗、吐、下”法治療疫病,如在《治傷寒時氣溫病方第十三》載“治傷寒及時氣溫病及頭痛,壯熱脈大,始得一日方。取旨兌根葉合搗,三升許,和之真丹一兩,水一升,合煮,絞取汁,頓服之,得吐便瘥,若重,一升盡服,濃覆取汗,瘥”“又方,取術丸子二七枚,以水五升,令熟,去滓,盡服汁,當吐下愈”,因此當邪氣未深時,可予汗、吐、下法給邪以出路[7]。
本研究納入100張處方,用藥頻次排名前10的中藥分別為:甘草、干姜、淡豆豉、附子、黃連、桂枝、常山、大黃、麻黃、黃芩。其中甘草在《神農本草經》及《本草經集注》中有“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解毒”的功效;干姜有溫中回陽、溫肺化飲的功效,在《神農本草經》中言“主胸滿咳逆上氣”;淡豆豉在《本草經集注》中言“主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惡毒”,具有解表除瘴的功效;附子散寒濕,溫脾腎,在《本草經解》中言其“主風寒咳逆邪氣者”;黃連具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的功效,在《長沙藥解》中述為“清心退熱,瀉火除煩”;桂枝在《雷公炮制藥性解》中言“專入肺經,主解肌發表,理有汗之傷寒”;常山具有化痰截瘧的功效,在《神農本草經》中記載為“主傷寒寒熱,熱發溫瘧,鬼毒,胸中痰結,吐逆”;大黃具有很好的通腑瀉熱功效,在《神農本草經》中言“滌蕩腸胃,推陳致新”;麻黃解表、發汗、利水,在《神農本草經》中云“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汗,去邪熱氣”;黃芩清熱燥濕,瀉火解毒,在《長沙藥解》中還記載“清相火而斷下利,瀉甲木而止嘔,除少陽之痞熱,退厥陰之郁蒸”。綜上發現用藥頻次前10位的中藥多為散寒化濕、溫肺解表、通腑瀉熱、散熱解毒功效。
本研究發現《肘后備急方》中所用中藥多是辛溫藥和苦寒藥,由此可判斷當時疫情寒濕證型比較多,因為苦能燥濕,辛能散能行。藥物歸經前5位依序為肺經、胃經、脾經、心經,在該書中很多疫病初期的主要表現為胸膜咳喘等癥狀,兼有惡心、嘔吐等消化系統癥狀,重癥期則病邪“逆傳心包”,出現胸痛、神昏等癥狀,此時用藥多入心經,因此在用藥功效方面也多解表、補虛、清熱、溫里。
根據關聯規則統計出處方中常用的對藥,出現頻次最高的前兩組對藥為干姜-附子,淡豆豉-梔子。干姜和附子為方劑“干姜附子湯”,最早出自《傷寒論》,附子走而不守,干姜守而不走,二藥合用增強了溫陽散寒的功效[8]。淡豆豉和梔子為方劑“梔子豉湯”,其中梔子清熱除煩,降中有宣,淡豆豉升散調中,宣中有降,兩藥配伍共奏清熱除煩的功效[9]。出現頻次最高的角藥組合為干姜-附子-細辛,3藥配伍增強了溫陽解表散寒的功效。在《肘后備急方》中挖掘治疫病的對藥和角藥不離散寒和清熱兩大類型,因此“寒熱之辨”應為辨治疫病的首辨。
本研究利用K均值聚類算法推算出了處方的核心組合,將K值設定為3時,方劑個數最多的類方核心組合為淡豆豉、甘草、黃連、常山、梔子。該類方組合為梔子豉湯加減,梔子豉湯由梔子、淡豆豉兩味藥物組成。梔子苦寒,為清熱解郁除煩之藥;淡豆豉味輕氣薄,乃宣透郁熱之品,二者相配,清宣相合,治療熱郁胸膈證[10]。方中還有常山配合黃連,可增強清熱燥濕的功效,甘草調和諸藥,用該方治療疫病濕熱證,可以達到清熱解毒,燥濕化濁的目的。將K值設定為5時,方劑個數最多的類方核心組合為淡豆豉、甘草、梔子、麻黃、升麻、葛根。此類方中麻黃、升麻、葛根宣肺疏泄,梔子、淡豆豉清瀉里熱,根據用藥判斷其證型多為“外寒濕內里熱”,在治療疫病的過程中可用此類方達到清郁熱,散表邪的表里同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