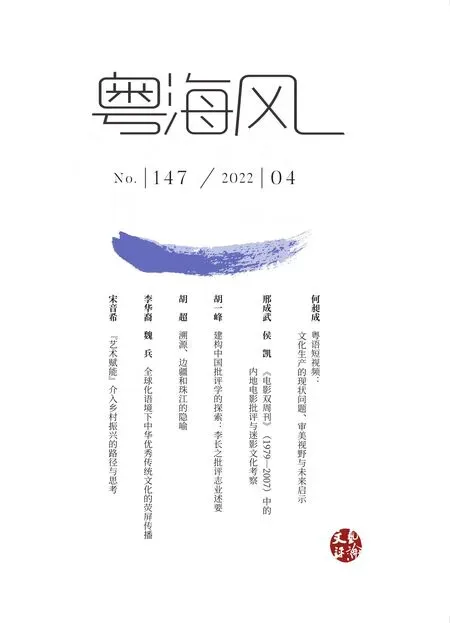未竟的牌局與永恒的人性
——以《海底撈月》為例淺析肖建國(guó)的創(chuàng)作特色
文/楊希
一、濃郁的湘南風(fēng)情
故土對(duì)每個(gè)人的影響都是無(wú)法抹去的。對(duì)于一個(gè)作家來(lái)說(shuō),早期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對(duì)其創(chuàng)作個(gè)性和氣質(zhì)的影響更加深遠(yuǎn),不管是自然風(fēng)貌還是民俗特色,都烙印在其作品中。縱觀文學(xué)史,每一個(gè)有特色的作家都有自己書(shū)寫(xiě)的地標(biāo),比如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山東高密,王安憶的上海……在幾十年城市化的進(jìn)程中,方言逐漸被普通話所替代,城市景觀和生活習(xí)慣也趨于雷同,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學(xué)作品就是在同質(zhì)化的經(jīng)驗(yàn)中開(kāi)辟出獨(dú)特的書(shū)寫(xiě)路徑,豐富感和差異性是其重要的藝術(shù)標(biāo)志。故土不僅可以成為一個(gè)作家專屬的創(chuàng)作資源,也給作品打上了鮮明的風(fēng)格印記,故土的文化特色也由于作家的地域書(shū)寫(xiě)得到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成為一種相互浸潤(rùn)相互滋養(yǎng)的狀態(tài)。
肖建國(guó)生長(zhǎng)在湖南南部小城,對(duì)湘南地帶有著深厚的情感依戀,他的大多數(shù)作品都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與他本身的閱歷、見(jiàn)識(shí)、情感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地理上,湘南地處于兩省交界地,毗鄰廣東,廣西,這里是湖南的“南大門(mén)”,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嶺南的交通要道,到了明清時(shí)期,廣東設(shè)立對(duì)外通商港口,湘南地區(qū)成為物流的必經(jīng)通道,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這里的商品經(jīng)濟(jì)日益繁榮,有了早期城鎮(zhèn)化的景觀。《海底撈月》的第二章用了大量的篇幅來(lái)構(gòu)建真實(shí)立體的小城風(fēng)貌,作家從染坊寫(xiě)到熱鬧的手藝人店鋪一條街,再?gòu)谋遍T(mén)石埠頭,縣城的四個(gè)城門(mén)以及衙門(mén)口寫(xiě)到縱橫交錯(cuò)的古老街巷、騎樓,圍繞小城的是盤(pán)曲的麻地河,蒼翠的城外四面山,山上的東塔嶺,雷公菩薩廟……肖建國(guó)在這里用散文的筆觸逐一撫過(guò)記憶之中的地理風(fēng)物,描繪出一個(gè)富有肌理感的湘南小城。
由于湘南地帶經(jīng)商便利,這里文化交融,人民生活相對(duì)寬裕,性格奔放,形成了以坐歌堂為代表的地方風(fēng)俗和以打麻將為主的生活?yuàn)蕵?lè)。湘南地區(qū)的永州下灌村更是傳說(shuō)中麻將的起源地,在《海底撈月》中可以看到出現(xiàn)頻次極高的麻將牌局,小說(shuō)中作為關(guān)鍵意象的紫檀木盒子裝載的象牙麻將是翠玉的父親專門(mén)從馬來(lái)西亞買回,由此可見(jiàn)湘南小城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fàn)顟B(tài)。小說(shuō)的標(biāo)題“海底撈月”本身就是一種麻將的術(shù)語(yǔ),目錄名也直接取自坐歌堂的唱詞與牌場(chǎng)黑話,小說(shuō)的敘事更是一開(kāi)場(chǎng)便在三天三夜的麻將牌局中展開(kāi),整部小說(shuō)就是一幅鮮活的湘南市井生活圖。
除此之外,小說(shuō)的地域特色還體現(xiàn)在方言的運(yùn)用上。普通話寫(xiě)作無(wú)疑有利于作品的理解和傳播,但在地域描寫(xiě)的文本中就不可避免地被消解了一部分地方特性。方言寫(xiě)作則可以讓一個(gè)地域一個(gè)民族真正立起來(lái)活起來(lái),這是因?yàn)榉窖缘男纬膳c其所在的地理環(huán)境、歷史變遷、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生活習(xí)慣等諸多方面緊密相關(guān),方言匯集了地方文化的特點(diǎn),集中體現(xiàn)出一個(gè)地區(qū)的個(gè)性和特質(zhì),是地區(qū)身份的重要標(biāo)志。《海底撈月》中的湘南方言活潑,粗糲,語(yǔ)義豐富。比如小說(shuō)中經(jīng)常用來(lái)表達(dá)人物心情的形容詞“松快”,不僅有快樂(lè)的意思,還包含著輕松、暢快的多層含義。名詞“毛毛”“小把戲”用以指代嬰兒、幼兒,極富形態(tài)特征,將較為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生動(dòng)化,體現(xiàn)出了湘南地區(qū)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小說(shuō)中大量的動(dòng)詞“搭”“搞”“拼”的使用可以感受到湘南地區(qū)人民的勇猛,利落。人物的名字更直接用了方言化名“細(xì)姥婢”“疤眼皮”“忠良婆”“三道彎”……這些人物名都極具個(gè)性特色,也暗含人物的部分生理和性格特征。可見(jiàn)方言體現(xiàn)出不同地區(qū)的思維方式,它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它更是生活本身。而牌桌上的交流、嬉鬧,牌場(chǎng)黑話的使用,讓麻將桌成為集中表現(xiàn)方言特色和人物個(gè)性的空間。縱觀整部小說(shuō)作品,方言的運(yùn)用使其人物更加原生態(tài),更加貼近土地,貼近真實(shí)生活。并且,方言的表達(dá)特性直接決定了作品整體的語(yǔ)言風(fēng)格,《海底撈月》依托湘南方言所呈現(xiàn)出的語(yǔ)言風(fēng)格就傾向于明快、率真、夸張。
小說(shuō)通過(guò)描寫(xiě)時(shí)代激變之下的湘南地區(qū)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表現(xiàn)出地域文化的強(qiáng)大慣性和內(nèi)在力量,麻將作為其中的具體標(biāo)志,也維系著湘南地區(qū)的文化認(rèn)同。肖建國(guó)的創(chuàng)作以此踐行著他的尋根理念,打造屬于他的創(chuàng)作地標(biāo)。
正如肖建國(guó)自己所言:“要當(dāng)個(gè)作家,就應(yīng)該有個(gè)‘根’。講通俗點(diǎn),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根據(jù)地。不管生活底子是厚是薄,生活面是寬是窄,但總應(yīng)該有一塊這樣的根據(jù)地,并且經(jīng)常有自己獨(dú)特的發(fā)現(xiàn)。沒(méi)有這個(gè)‘根’,就會(huì)是飄的。我的根在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家鄉(xiāng)。”[1]
肖建國(guó)有意識(shí)地在他的諸多作品中書(shū)寫(xiě)湘南的自然風(fēng)光、鄉(xiāng)土人情,為其作品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標(biāo)簽,我們能從其中感受到作家對(duì)故土深沉的依戀和注視,這是肖建國(guó)小說(shuō)的一種獨(dú)特魅力所在。
二、起伏跌宕的情節(jié)
肖建國(guó)的小說(shuō)作品是緊貼時(shí)代發(fā)展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海底撈月》從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初期寫(xiě)到土改運(yùn)動(dòng)、從““文化大革命””寫(xiě)到改革開(kāi)放,人物歷經(jīng)了這些重要的歷史發(fā)展階段,70年的時(shí)間跨度使作品的情節(jié)非常豐富,麻將作為核心意象在小說(shuō)中多次出現(xiàn),已絕非一個(gè)普通的物件,因?yàn)椤八囆g(shù)的生命不是‘物’,而是內(nèi)蘊(yùn)著情意的象(意象世界)”[2]。它與人物的命運(yùn)產(chǎn)生種種關(guān)聯(lián),構(gòu)成了主要的情節(jié)線索。小說(shuō)初始,通過(guò)唱坐歌堂的細(xì)姥婢在李家小姐翠玉出嫁前的一場(chǎng)三天三夜的麻將局中“擔(dān)土”,將主要人物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家境富裕的翠玉姑娘是小城出名的“麻將鬼”,出嫁前,她一心想要自摸“海底撈月”,在最有希望之時(shí),翠玉拈白板的手突然被流彈打中,鮮血直流,這場(chǎng)未竟的牌局成了翠玉一生的轉(zhuǎn)折點(diǎn),也標(biāo)志著這個(gè)偏安一隅的湘南小城的突然解放,故事由此拉開(kāi)了序幕,時(shí)代也進(jìn)入新的歷程。如此難忘的首次牌局的經(jīng)歷,使麻將從此成了細(xì)姥婢人生中的重要內(nèi)容,成功轉(zhuǎn)化為作品敘事的關(guān)鍵要素。
出現(xiàn)次數(shù)不多但貫穿整部小說(shuō)的象牙麻將,是觸發(fā)人物命運(yùn)轉(zhuǎn)折的重要標(biāo)志,它預(yù)示著人物將面臨抉擇,不同的抉擇推動(dòng)不一樣的情節(jié)走向。命途驟變的翠玉姑娘將最珍愛(ài)的象牙麻將托付給年輕的細(xì)姥婢保管,是第一次抉擇。從此,細(xì)姥婢的命運(yùn)便和麻將緊密相連。改革開(kāi)放后,細(xì)姥婢的丈夫水旺忍受不了金錢(qián)的誘惑,將象牙麻將當(dāng)做古董賣掉。細(xì)姥婢面臨第二次抉擇。在女兒三姥婢面對(duì)婚戀選擇之時(shí),象牙麻將再次出現(xiàn),一場(chǎng)牌局讓細(xì)姥婢看清未來(lái)女婿的人品和性格,預(yù)示著三姥婢一生幸福的開(kāi)始。最后,細(xì)姥婢在自己的家庭棋牌室,終于放心拿出象牙麻將與姐妹們分享,以自己的方式紀(jì)念著早逝的翠玉。象牙麻將成為理解細(xì)姥婢命運(yùn)的關(guān)鍵線索,也是整部小說(shuō)中幾次敘事高潮的標(biāo)志。
除了象牙麻將,小說(shuō)中頻繁出現(xiàn)的普通牌局對(duì)情節(jié)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第四章“手氣順時(shí)搏自摸”是細(xì)姥婢前半生中屈指可數(shù)的幸福歲月。細(xì)姥婢與水旺破除萬(wàn)難成婚后,搬進(jìn)了翠玉家的大宅,認(rèn)識(shí)了土保主任的妻子含田婆。經(jīng)歷了聲勢(shì)浩大的土改,小城的生活回歸平靜,細(xì)佬婢終于能再打起麻將,但在麻將桌上的一次胎動(dòng)讓細(xì)姥婢經(jīng)歷了痛苦的難產(chǎn),很快,這種平靜安穩(wěn)的生活就不復(fù)存在了。第五章中,饑荒來(lái)臨,水旺因事入獄,細(xì)姥婢開(kāi)始經(jīng)歷人生低谷,就在眾人擔(dān)心細(xì)姥婢的精神狀態(tài)時(shí),恰是一場(chǎng)麻將牌讓人看到她面對(duì)苦難的勇氣,為后來(lái)細(xì)姥婢做苦力、撿拾腐肉、艱難度日做鋪墊。第七章中,水旺出獄,心情愉悅的細(xì)姥婢邀約翠玉組起了麻將局,也正是在這場(chǎng)牌局中,翠玉第一次將自己對(duì)麻將的心得告訴細(xì)姥婢,使細(xì)姥婢領(lǐng)悟到牌場(chǎng)看人的至高境界,成為細(xì)姥婢以牌局測(cè)試準(zhǔn)女婿的前提。也成為最后,年邁的細(xì)姥婢看淡輸贏、看清人生時(shí)運(yùn)的基礎(chǔ)。
激烈變化的外部環(huán)境和輕松愉悅的牌局交替出現(xiàn),使小說(shuō)在敘事上顯得張弛有度,增強(qiáng)了節(jié)奏感。尤其是從開(kāi)頭的緊張和高潮,到最終章的舒緩和開(kāi)悟,整部作品由牌局始也由牌局終,形成了一個(gè)環(huán)狀結(jié)構(gòu),仿若一場(chǎng)大型的命運(yùn)的牌局。
縱觀肖建國(guó)的寫(xiě)作,在情節(jié)設(shè)置和人物命運(yùn)上的激變與社會(huì)和時(shí)代的變化緊密相連,這種寫(xiě)法深刻揭示出小人物在時(shí)間洪流中被迫裹挾而行的生活本質(zhì),要掌握自身的命,是非常困難的,當(dāng)然,這也就更突顯出小人物身上的堅(jiān)韌品質(zhì)。
三、人物塑造
肖建國(guó)的小說(shuō)總是聚焦于底層平民,所刻畫(huà)的女性平民更能滿足讀者對(duì)于強(qiáng)韌、良善的人性美的期待和追求。《海底撈月》中的重點(diǎn)人物以女性居多,從細(xì)姥婢到翠玉、忠良婆、含田婆、三道彎等,這些湘南地區(qū)的女性生動(dòng)而美好。相對(duì)而言,男性人物的缺陷更加明顯,對(duì)于個(gè)體欲望的處理更缺乏理性,樸素的民間倫理觀念在女性人物身上得到更好的體現(xiàn)。當(dāng)然,小說(shuō)也能直面她們的局限,比如疤眼皮,活潑熱情之余有著自私苛刻的缺點(diǎn)。忠良婆是一位盡職盡責(zé)的母親,但思想傳統(tǒng),冥頑固執(zhí)。最能集中體現(xiàn)作者對(duì)人性期待的是主人公細(xì)姥婢。細(xì)姥婢經(jīng)歷了牌局上的時(shí)輸時(shí)贏,也經(jīng)歷了人生中的種種美好與艱辛,她的性格特征是:直爽真摯、勇敢善良。這是個(gè)有力度的人物,她的韌性和堅(jiān)強(qiáng)撐起整個(gè)家庭在動(dòng)蕩時(shí)代中的穩(wěn)固,她就像不斷生長(zhǎng)的藤蔓,哪怕歷經(jīng)秋風(fēng)和苦寒依然保有茁壯的生命力,甚至更加通透和寬厚,終至成長(zhǎng)為一棵庇佑家人的蔥郁大樹(shù)。除了細(xì)姥婢,小說(shuō)中所有正面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質(zhì)可以概括為三個(gè)方面的道德持守:義、理、情。細(xì)姥婢的性格是在命運(yùn)的歷練中成長(zhǎng)而成,性格的進(jìn)化均在牌局中得到彰顯。正如前人對(duì)參加打麻將的牌手曾有要求:入局斗牌,必先煉品,品宜鎮(zhèn)靜,不宜躁率,得勿驕,失勿吝,順時(shí)勿喜,逆時(shí)勿愁,不形于色,不動(dòng)乎聲,渾涵寬大,品格為貴,爾雅溫文,斯為上乘。正代表性格的修煉過(guò)程和終極目標(biāo)。
細(xì)姥婢身上最突出的,是她對(duì)“義”的堅(jiān)守。她一生信守與翠玉的承諾——保護(hù)象牙麻將。雖然她并不真正了解翠玉,更談不上熟識(shí),但她不以外界評(píng)價(jià)和社會(huì)認(rèn)同標(biāo)準(zhǔn)的變化為基準(zhǔn)去評(píng)判翠玉,始終平等而視。當(dāng)然,這種尊重并非毫無(wú)出處,正是通過(guò)她與翠玉相識(shí)的那一場(chǎng)三天三夜的牌局,細(xì)姥婢認(rèn)定翠玉是純粹的。作為一個(gè)大小姐,翠玉既不關(guān)心家族事業(yè),也不關(guān)注個(gè)人婚姻,終日耽于牌場(chǎng),她對(duì)麻將的癡迷除了是對(duì)娛樂(lè)的沉溺,也有將其視為理想和愛(ài)好的虔誠(chéng)。細(xì)姥婢踐行對(duì)翠玉的承諾,體現(xiàn)出一種任憑世事變遷都堅(jiān)定不移的契約精神,這種精神成為細(xì)姥婢面對(duì)抉擇時(shí)的行事原則。丈夫水旺因非法炸魚(yú)獲刑5年,細(xì)佬婢挺身而出,打各種零工,獨(dú)自撫養(yǎng)4個(gè)孩子,其中艱辛可想而知,但她毫無(wú)怨言,更時(shí)時(shí)處處維護(hù)著水旺。水旺在廣州嫖娼入獄后,細(xì)姥婢放棄了自己心愛(ài)的麻將館,帶著僅有的5000元現(xiàn)金赴廣州保釋丈夫。義氣讓細(xì)姥婢身上不僅有傳統(tǒng)女性充滿堅(jiān)韌和溫情的部分,也有現(xiàn)代女性的獨(dú)立和自強(qiáng)。“義”也是作品中湘南地區(qū)人民集體的價(jià)值認(rèn)同,正面人物身上都有義氣之舉,細(xì)姥婢難產(chǎn)時(shí),含田婆讓丈夫歐土保連夜帶領(lǐng)幾個(gè)年輕人步行將細(xì)姥婢抬去一百多公里外的大醫(yī)院。在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單純的付出靠的正是“義”的支撐。小說(shuō)中的人物在贊嘆對(duì)方之時(shí)常會(huì)說(shuō)“這個(gè)人,好講義氣”[3],可見(jiàn)義氣是湘南地區(qū)眾人稱道的精神品質(zhì),對(duì)“義”的贊美也是對(duì)傳統(tǒng)精神力量的呼喚和回歸。
如果說(shuō)“義”是細(xì)姥婢性格中對(duì)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持守,那么理性精神則是細(xì)姥婢身上的現(xiàn)代部分。細(xì)姥婢在面對(duì)人生際遇中的困惑和選擇時(shí),不是一味的妥協(xié)忍讓,緊隨潮流,而是據(jù)理力爭(zhēng),嘗試主宰自己的命運(yùn),更可以在人云亦云的狀況下做到不參與,不起哄。比如在小說(shuō)第一篇章的解放情節(jié)中,眾人將翠玉視為萬(wàn)惡的階級(jí)敵人時(shí),細(xì)姥婢有自己的判斷,秉持自己的認(rèn)知,不為外界所撼動(dòng),她會(huì)接受翠玉的象牙麻將就證明她并不認(rèn)同對(duì)翠玉的審判。成年后的細(xì)姥婢堅(jiān)決反抗代表傳統(tǒng)思想的母親阻撓自己的自由戀愛(ài)。中年的細(xì)姥婢遭遇““文化大革命””的亂象,面對(duì)被奪權(quán)的熱情沖昏頭腦的丈夫和女兒,以自己理性和溫柔的力量對(duì)他們進(jìn)行感化與勸誡,更在游街途中救下了曾有一面之緣的段碧池。縱然““文化大革命””對(duì)底層平民有巨大的權(quán)力誘惑,細(xì)姥婢卻絕不參與其中。她身上的理性精神來(lái)自父親秋聾子,秋聾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勸誡水旺時(shí)所說(shuō)的話,是為理性精神的一次申辯。肖建國(guó)用了相當(dāng)多的篇幅直呈對(duì)“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顯然,他看到了這場(chǎng)浩劫的本質(zhì),看到了對(duì)于人性的扭曲,雖然依靠人物對(duì)話來(lái)陳述作家所思所想的手法不算高明,甚至稍顯樸拙,但這種真誠(chéng)的理性精神卻是可貴的。作為一個(gè)平民,秋聾子有著深沉的智慧,他尊重女兒的個(gè)人選擇,關(guān)鍵時(shí)刻他能透過(guò)社會(huì)現(xiàn)象看到其本質(zhì)規(guī)律,對(duì)人對(duì)事的看法不被個(gè)人情緒和偏見(jiàn)所左右。小說(shuō)將現(xiàn)代理性融入作品,使人物更具深度。
在經(jīng)歷了種種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人生遭際之后,細(xì)姥婢不斷成長(zhǎng),她的世界觀也如她對(duì)牌局的看法一樣,達(dá)到了另一番境界——情的境界。對(duì)至情至真的參悟使細(xì)姥婢成為一個(gè)成熟豁達(dá),通透達(dá)觀的人。小說(shuō)的后四個(gè)章節(jié),湘南小城在改革開(kāi)放的春風(fēng)下迎來(lái)發(fā)展機(jī)遇,商品經(jīng)濟(jì)迅速崛起,人們開(kāi)始走出湘南,看到更廣闊的世界,也要面臨更多人性的搖擺。金錢(qián)和機(jī)遇,動(dòng)搖了這片土地上最為樸素的價(jià)值觀——“義”。這種轉(zhuǎn)變集中體現(xiàn)在光飛和光雄兩兄弟身上,為了最大程度地獲取利益,兩兄弟不仁不義,不擇手段,侵占和剝奪他人的財(cái)物,完全拋棄了自己的人格尊嚴(yán)。脫離了故鄉(xiāng)水土,常年在外的水旺,也逐漸遺落了本分與義氣,暴露出性格中貪婪的一面,不僅偷偷拿了細(xì)姥婢的象牙麻將轉(zhuǎn)手出賣,還深陷嫖娼風(fēng)波,情感與靈魂都在迅速墮落。作家借此寫(xiě)出了人性的弱點(diǎn),這些都屬于小市民身上普遍存在的缺陷,也許離開(kāi)了鄉(xiāng)土文化和情感的滋養(yǎng),人性中的弱點(diǎn)便會(huì)肆意滋長(zhǎng)。與之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細(xì)姥婢,在經(jīng)歷時(shí)代動(dòng)蕩,生離死別之后,細(xì)姥婢變得溫柔敦厚,她已明白生命最為重要的乃是當(dāng)下的真情。黑格爾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現(xiàn)于感性觀照的一種現(xiàn)成的外在事物,對(duì)這種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來(lái)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較廣泛較普遍的意義來(lái)看。因此,我們?cè)谙笳骼飸?yīng)該分出兩個(gè)因素,第一是意義,其次是這意義的表現(xiàn)。”[4]在小說(shuō)最后的牌局很顯然象征著她的蛻變,這已不再只是一種娛樂(lè)手段了,甚至不再是她的愛(ài)好,而已經(jīng)成為她人生哲學(xué)和生活意義的展示場(chǎng)。
細(xì)姥婢成為麻將高手,牌技與手氣俱佳,但她放棄了靠著麻將館致富的念頭,也放下了牌桌上對(duì)贏的渴望,寧愿一次次輸給自己的姐妹,只為將這牌局一直打下去,將眼前這向好的生活一直過(guò)下去。與真摯的情感相比,財(cái)富或者輸贏是沒(méi)有實(shí)際意義的,是不能帶來(lái)慰藉的,太在乎一時(shí)半刻的功成名就,就像終于自摸海底撈月的一天,那不是開(kāi)始,而是結(jié)束。幸福的真諦無(wú)外乎就是有情有義地活著。
以《海底撈月》為代表的小說(shuō)可以看到肖建國(guó)的創(chuàng)作路徑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透過(guò)人物所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表象對(duì)湘南地區(qū)市民的生存哲學(xué)、人生信仰進(jìn)行追問(wèn)、思考。肖建國(guó)對(duì)故土的深情,決定了其寫(xiě)作是真誠(chéng)的,動(dòng)情的。
湘南人對(duì)生活的期待和認(rèn)知到底是怎樣的,作家沒(méi)有直接陳述,而是借用麻將這一隱喻敘事來(lái)達(dá)到對(duì)其命運(yùn)和精神的認(rèn)知與理解。蘇珊·朗格認(rèn)為隱喻其實(shí)說(shuō)的是一件事物而暗指的又是另一件事物,并希望別人也從這種表達(dá)領(lǐng)悟到是指另一件事物的原理。[5]麻將在小說(shuō)敘事中指代了一種輕松的、愉悅的生活方式,麻將桌提供了一個(gè)釋放內(nèi)心壓力和紓解欲望的空間,在這個(gè)自由輕松的小世界,現(xiàn)實(shí)困境,矛盾糾葛,荒誕亂象都不復(fù)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只是毫無(wú)功利目的的“松快”。麻將是細(xì)姥婢和疤眼皮們?cè)趧?dòng)蕩不安的時(shí)局中的精神寄托,以對(duì)抗平庸、枯燥、麻木。
另一方面,麻將也是時(shí)代命運(yùn)的隱喻。細(xì)姥婢放棄對(duì)結(jié)果的關(guān)注,就是理解了命運(yùn)和時(shí)代。在肖建國(guó)的諸多小說(shuō)中所描寫(xiě)的平民階層均陷入一種困境中——作為大時(shí)代中的渺小個(gè)體,要走出普遍性的困境是困難重重的,人生正像牌局,輸贏是難以預(yù)料的,不可掌控的。本著何種心態(tài),持有什么樣的信念參與其中才是個(gè)體生命應(yīng)該去關(guān)注的,在無(wú)法依靠意志而左右的運(yùn)氣面前,享受過(guò)程,不論結(jié)果。小說(shuō)并無(wú)叩問(wèn)和責(zé)難,也不在深度上過(guò)多地挖掘,只是用本真的善意去啟發(fā)和觸動(dòng)人的靈魂,去尋找一種由內(nèi)而外自省的力量。深刻讓位于溫情,批判示弱于悲憫,這是肖建國(guó)的創(chuàng)作愈加成熟的標(biāo)志。
注釋:
[1]肖建國(guó):《左撇子球王》,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葉朗:《美學(xué)原理》,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頁(yè)。
[3]肖建國(guó):《海底撈月》,深圳:海天出版社,2021年版。
[4][德]黑格爾:《美學(xué)(第二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1年版,第10頁(yè)。
[5][美]蘇珊·朗格:《藝術(shù)問(wèn)題》,滕守堯、朱疆源,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