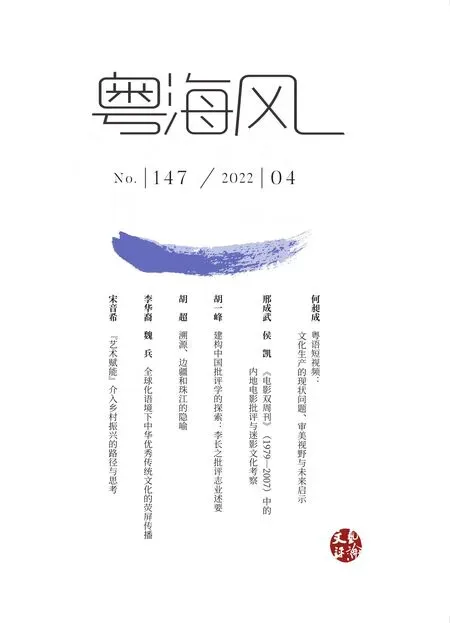近年新主旋律電影中的風景呈現
文/劉暢
風景是近年藝術研究中的關鍵詞。米切爾(W. J.T. Mitchell)將風景看作一種象征體系,認為風景能夠被嵌入到文化傳統之中,激發并重塑意義與價值,因此風景不再僅是供人欣賞的審美對象,也成為一種能夠形塑人們精神的文化實踐。[1]在風景研究的文化轉向中,作為自然物的“風景”不再屬于沉默的大地,而屬于框取風景的社會學的眼睛。電影是以形象進行表達的視覺藝術形式,傾向于以“潛在文本”的方式傳遞內容、形式及精神上的話語。風景正是這樣一種內涵豐富的“潛在文本”,它是影片中“最自由的因素,最少承擔實在的敘事任務,并最能靈活地表達情緒、感情狀態和內心體驗”[2],不僅可以作為敘事的空間背景、情節的引入和過渡出現,起著調整敘事節奏、渲染情緒氛圍的作用,也能夠脫離服務功能,與人物、故事以及影片的生產語境展開有機互動,成為獨立存在的敘事元素。電影中的“風景”不同于“純粹的大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馬丁·列斐伏爾(Martin Lefebvre)認為,風景被視覺裝置框取后可以實現審美愉悅之上的概念超越,即風景一旦成為被再現的對象,就被打上了主體意志的烙印,實現了從自然向文化的邁進,變為一種有意味的文化地理景觀,能夠表達某種文化意義和意識形態訴求。[3]正如Harper與Rayner指出,電影風景不是純粹的現實記錄,它受制于美學處理、技術改進和意識形態的規約,它承擔著容納文化意義、改進視覺審美風格及維護、宣傳民族身份認同的作用。[4]在這一意義上,風景既有視覺上的美學意義,又與故事空間的呈現及文化內涵的生成密切相關,承載著豐富的價值意蘊。
風景歷來是中國當代電影鏡頭表達與影像開掘的重要載體。隨著中國社會與電影生態的變遷,以風景為代表的影像環境也承載了更多的可闡釋空間。主旋律電影是中國當代電影藝術的重要類型,從廣義上說,主旋律電影是“一切匯聚于形成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的輿論力量、價值觀念、文化條件和社會環境的文化交流中的成功之作”。[5]在現代影視語境下,凡是以謳歌真善美、傳遞正能量、弘揚主流價值觀為旨歸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都具有主旋律的色彩。近年來,電影產業化和院線制改革推動了主旋律電影的轉型發展,一種基于“主旋律+”的“新主旋律電影”[6]逐漸占據國產電影的重要份額,創作者以藝術審美與多類型雜糅敘事為媒介,在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追求影片思想性與觀賞性的統一,打破了傳統意義上主旋律電影、藝術電影、商業電影的三分界限。在政治性、商業性、文化性與藝術性交融的新主旋律場域里,風景從傳統意義上人物活動和事件發生的場景背景變為相對獨立的“自主風景”[7],關聯著影片審美空間的建構與文化價值的拓展。本文以近五年來國內上映的新主旋律電影為對象,分析其中“風景”如何通過敘事編碼及影像修辭進入電影文本的復調場域,并以意識形態風景、文化記憶風景與視覺奇觀風景三種主要樣態有效參與到政治、文化與商業場域的建構與運作中。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風景
斐迪南·滕尼斯指出,共同體是“由本質意志推動的,以統一和團結為特征的社會聯系和組織方式,它以血緣、地緣和精神共同體為基本形式”。[8]在自然本性的推動下,以家族、社區和精神為紐帶聯結在一起的族群具有同樣的信仰和需要,以此建立起統一團結的集體,并形成滲透于社會生活和歷史文化各個層面的“共同體藝術”。通過特定的物件、符號、儀式與場面,共同體藝術記錄了一個族群的精神生活,激發、傳達著特定的情感與觀念,傳達共同性、維護共同體團結是共同體藝術的重要功能。在這一意義上,作為國家歷史或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電影也是承載民族精神的共同體藝術形式,民族大義、家國意識、友愛互助等共同體精神歷來是滲透在電影血肉之中的審美追求。[9]作為弘揚社會正能量、傳達主流價值觀的視覺載體,當代新主旋律電影在“意識形態風景”[10]中寄托了形塑國家/民族共同體的期待。肯尼斯·羅伯特·奧維格(Kenneth Robert Olwig)從詞源學的角度考察后認為,當風景與自然、文化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它便具有了隱喻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力。[11]通過建構民族物戀情結的象形符號與展現脫貧攻堅時代成就的影像載體兩種樣態,近年新主旋律電影中的風景發揮了共同體藝術的凝聚作用,因而成為建構民族“想象共同體”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巧妙地縫合了觀眾與影像世界的意識形態在心理或想象關系上的縫隙,促進了民族認知共同體的形成。
(一)建構民族物戀情結的象形符號
在民族危亡、國家危難之際,作為意識形態的風景表現為建構民族物戀情結的象形符號,在戰爭題材的主旋律影片中格外凸顯。弗洛伊德認為,物戀是“被想像為失去了或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涉及主體形成過程中的匱乏、替代和認同。[12]上升到民族層面來說,當一個民族陷入主體性喪失的創傷情境時,意義和秩序的重建與填充需要圍繞某種具有共同體意義的對象,這時符號性、儀式性的行動可以彌合現實的裂縫,風景就充當了這種角色。“物戀”的對象是集體無意識的象征,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文化實踐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隱喻與約定俗成的認知。生死危亡之際,人們需要尋找一種中介物來重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以凝聚民族意識,對于中國人來說,長江、長城、黃河、黃山等風景意象帶有民族認同性,它們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形符號,承載著意識形態的“詢喚”[13]任務,將民族價值觀念進行了實證化和物質化,并且使人們對這些民族價值觀念充滿快感地認同[14],在風景的感召下,“個人”成為“主體”,“家園”變成了“國家”。
戰爭題材主旋律影片有將風景納入國家意識形態表達體系的傳統。《中華兒女》(凌子風,1949)中已經使用富于象征意義的青松、白云高山等風景象征英雄犧牲的崇高和神圣,《上甘嶺》(沙蒙、林杉,1956)也已出現借助風景傳達保家衛國民族情懷的鏡頭語言。《長津湖》(陳凱歌、徐克、林超賢,2021)中風景的呈現繼承了這一歷史認同的傳統,影片利用長城這一風景意象,表達了國家意識形態對主體的詢喚。朝鮮戰爭爆發后,伍千里重回戰場,他的弟弟伍萬里瞞著父母坐上了奔赴戰場的火車。初次入伍的伍萬里不適應組織紀律,在火車上逞強鬧事,伍千里只好將他的授槍儀式取消,叛逆的伍萬里固執打開火車門想要跳下車時,奇觀化的萬里長城映入眼簾,隨著火車的移動,蜿蜒的長城披著朝陽不斷延伸,看著壯美的祖國河山,伍萬里和老戰士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和滿足。萬里轉變了自己的態度,堅定了遵守組織紀律、投身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萬里長城和伍萬里的名字形成了巧妙的對照,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征,長城的職責是守衛祖國邊疆。作為長城的兒女,伍萬里在民族受到威脅時,堅定地選擇守護祖國。長城的出現起到了推進人物成長、推動影片敘事的作用,在長城的感召下,新戰士在成長,民族精神得以凝聚。
(二)展現脫貧攻堅時代成就的影像載體
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作為意識形態的風景更多地成為展現脫貧攻堅時代成就的影像載體。據統計,截至2021年,我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15]城鎮與鄉村的界限逐漸消弭,鄉村不再是城市的對立面,而成為與城市共存的新主體。在近年新主旋律電影中,曾經破敗的農村風景呈現出美好明朗的新風貌,《十八洞村》(苗月,2017)中水墨畫卷般的湘西風光,《又是一年三月三》(馬會雷,2018)中清新質樸的壯族村莊,《我和我的家鄉》(寧浩等,2020)中碧波蕩漾的千島湖、金黃遍地的稻夢空間,《一點就到家》(許宏宇,2021)里綠意盎然的云南茶園,不僅為觀眾呈現了祖國從南到北獨具風情的山川鄉野,也借此贊頌了中國人勤勞奮斗、百折不撓的時代精神。在這些電影中,明亮溫暖的色調、意境開闊的航拍鏡頭、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的融合一同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小康時代影像,潛移默化地宣揚主流意識形態與傳達美好生活理念的內涵。以明麗的風景展現取代直截了當的頌揚式話語體系,讓觀眾在無意間再次體會黨對人民幸福生活的引領作用,增強對國家發展的自豪感和對黨的認同感,也向世界展現了正面積極的中國形象。
《我和我的家鄉》中壯闊秀麗的祖國風光是承載著意識形態的柔性表達策略。作為一部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家鄉》創作的初衷是記錄脫貧攻堅與新農村建設的時代成就,歌頌國家精準脫貧政策的先進性與正確性,但影片另辟蹊徑地將鏡頭投向了祖國詩情畫意的鄉村景觀,讓詩意呈現的風景唱出了生動的贊歌。取景于陜西榆林市毛烏素沙地的《回鄉之路》單元講述的是這一地域防風治沙的生態建設故事,影片首先以灰黃的色調交代了這里過去的惡劣環境,教室里沙塵遍布,窗外是漫天飛舞的黃沙,在沙塵暴的映襯下,孩子們面如土色,毫無生機,暗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關系。在村民的努力下,黃土高坡重新煥發了生機,導演運用明亮的陽光作為畫面的主要光源,營造出寧靜溫暖的色調,將陜西人民煥然一新的生活環境展現得美輪美奐,在大俯拍鏡頭的切換下,筆直的公路與青翠的農田和諧共生,風力發電機、立交橋、火車這些象征著現代化的人文景觀與喜人的綠茵地構成了一幅動人的風景畫,上面寫滿了退耕還林還草、防風治沙建設的時代成就,反映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也奏出了一首熱烈而婉約的家鄉贊歌。
二、作為文化記憶的風景
作為一種文化機器,電影深刻地改變著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影響著人們對于“時間”的記憶。爭取電影對民族特性乃至民族歷史的記錄與“重寫”,喚醒民族記憶與身份認同是發展中的現代民族國家電影理論與實踐的重要主題。[16]作為書寫中國革命與改革歷史的影像載體,主旋律電影是制造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來源,“十七年”與““文革””時期的紅色經典影片創造的經典斗爭記憶更是深深烙印在老一輩人們的腦海中。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潮流為文化領域帶來了傳統價值觀的激蕩,主旋律作品不再執著于創造宏大的集體歷史記憶,而是致力于再現與傳承那些在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中消散的個人與民族文化記憶。
卡爾·索爾(Carl O.Sauer)將風景分為“自然風景”和“文化風景”兩個層面,前者強調風景的自然、物質形態,后者則是風景的社會關系形態,由媒介表達。[17]在新時代文化生態背景下,風景兼具自然風景與文化風景的雙重屬性,關聯著文化記憶的構建與記憶資源的影像化再生產。作為影片的基本元素,風景搭建起了被回憶的物質世界,獨特的影像符號將過去的行為導向與精神情感體驗保存下來,以此展現本民族群共同的生產創造、生活場景與人文歷史等文化記憶,借助影像傳播框架的呈現,風景又被不斷書寫和重構,成為觀眾個人視野中的“家鄉”的文化記憶符號,喚起了儲存在人們心靈深處的記憶編碼,特定的“鄉愁”情緒被再次生產。近年新主旋律電影中以新農村、新民族為題材的作品格外擅長利用臨摹性還原與詩意呈現的風景喚醒文化記憶、重拾心理認同,以“鄉土”與“懷舊”為突破口,風景將地方的山川地貌,人們的風俗習慣、精神信仰和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聯結為共同的“凝聚性結構”[18],從而將不同的時空串聯起來,讓觀眾在不斷回顧過往中感受鄉村與民族傳統文化的變遷,感悟傳統文化的魅力,尋找記憶中的情感點,并通過自我意識、自我記憶與之相關的現實語境關聯在一起,此時,風景喚起的不僅是個體層面上對故土的思念,還自然地上升為群體層面對城鎮化進程中傳統文化衰落、民族文化危機意識的反思,因而形成了對民族傳統與主流價值觀的心理認同。
作為一部“搶救性”民族志電影,《遠去的牧歌》(周軍、阿迪夏·夏熱合曼,2018)以半記錄半虛構的方式講述了新疆哈薩克民族在傳統與現代、游牧與定居、生存與生態之間的矛盾與選擇,記錄民族地區改革開放以來巨大變遷的同時,深描其民族傳統與歷史,在對邊疆自然風貌與風土人情的詩意描繪中構建了哈薩克的“影像民族志”[19]。電影將古老游牧傳統的消亡凝結在四季景色的輪回變化之中,以四季景色變遷暗示時空關系與民族命運的改變,揭示了一個民族消亡與重生的心理變化過程。導演注重選取哈薩克代表性的景觀元素展示“游牧文化”的歷史、人文情懷與豐厚內涵,通過展現自然風景與文化風景的統一,將民族的自然之性與人類之性相融合,也將原始的草原游牧文化基因鐫刻在影像中。航拍下的大俯拍鏡頭呈現出草原的廣袤悠遠與群山茫茫,馬群、駱駝群、羊群、人群在遷徙中的景象配以優美的哈薩克音樂、民歌與舞蹈,深沉而樸素地營造了哈薩克游牧民族原生態的生活質感,這不僅是歷史痕跡的記錄,也是文化流傳的搶救。
新農村題材主旋律紀錄片《中國村落》(夏燕平,2019)通過對中國傳統村落的自然風景、文化歷史與民風民俗的詩意呈現,喚起了人們心中共同的集體記憶與傳承愿望。其中《如畫》篇將自然風光與人文風情有機融合,再現了新疆阿勒泰布爾津縣、江西婺源簧嶺村、安徽黟縣西遞村、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鄉城縣等遺落在現代文明之外的村落風景,并將其展現為中國的文化符碼,在青磚黛瓦、綠水青山的西遞村中,在崇高寧靜、原始浪漫的鄉城縣中,在淳樸自然、沉穩傳統的西灣村里,人與天地同呼吸共命運,耕讀傳家、天人合一、仁義禮智、忠義節孝的傳統價值觀也得到了審美化表達與傳播。在鄉村文明逐漸被現代化進程淹沒的時代中,村落風景搭建起了文化記憶的空間框架,用具象化的符號傳遞著濃濃的鄉愁情感。在這個共同的回憶場所之中,觀眾將個人經歷與影像化的記憶進行疊加,追憶新時代鄉村建設的發展歷程,回憶著自己家鄉的山水,引發了觀眾心底的思鄉情感。
三、作為視覺奇觀的風景
居伊·德波(Guy Debord)認為,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景觀(奇觀)已成為現代社會運行的操縱桿。[20]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 SKellner)進一步指出,媒體奇觀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重要特征,而電影自其誕生以來就是滋生“奇觀”之地,在各種由電影制造的奇觀中,最直觀、最重要的還是“奇觀電影”。[21]由于數字技術對電影的長驅直入,電影對風景的呈現也開始朝奇觀化的方向發展,電影從利用風景,直接變成了表現風景。[22]長期以來,在承擔建構主流意識形態任務的主旋律電影中,奇觀這個帶有電影本質屬性的元素處于缺位狀態,“板著臉、端架子,不鮮活、不自然”成為傳統主旋律電影飽受人詬病的原因之一。新主旋律電影在堅持思想性的前提下,開始兼顧影片的藝術性與觀賞性,風景的呈現向傳統東方審美取“境”(意境),也在商業語境中造“驚”(震驚)。一方面,電影技術的進步與審美觀念的轉變為風景的呈現脫去了樸素的本色,無人機鏡頭、CGI制作、4K高清等數字技術的使用增強了風景的影像表現力,在東方古典審美觀念的滋潤下,具有民族特色的“詩化書寫”使得風景展現出意蘊悠遠而又別具一格的雋永之美;另一方面,糅合了災難、冒險、驚險等商業類型元素的新主旋律電影借助模式化的非真實特效,將風景變為一種視覺消費對象。綜合來說,蓋瑞·特維(Gerry Turvey)對早期境況電影美學追求的界定正契合了當代新主旋律電影中風景奇觀的特點:美麗(令人享受、使人愜意)、有趣(能夠滿足視覺上的好奇)和生動(具有活力的)[23]。對于新主旋律電影來說,審美化、奇觀化的風景呈現不僅是其類型創新的突破口,更隱秘地成為傳播國家意志的一種有效方式。
新主旋律電影通過中國古典韻味的風景影像創造令人陶醉的美麗奇觀,建構影片的藝術審美空間。導演有意識地將風景的展現與故事的內核緊密結合,使用散點透視的鏡頭語言、卷軸式橫移鏡頭、“移步換景”的空間敘事等具有東方藝術美的詩意手法,營造出主客交融、詩畫一體的中國意境。《我和我的家鄉》在回歸紀實美學的基礎上,創新攝影技法、光線運用及意境營造,為影像帶來了豐富的質感與極強的觀賞性。影片開頭便以俯拍大全景的方式呈現了四幅魅力各異的風光圖,從青山茫茫的黔南苗寨、黃沙漫天的毛烏素沙漠到清明澄澈的千島湖、遍地金黃的稻夢空間,處處洋溢著人間溫情與綠色發展交織的祥和氛圍。其中《最后一課》敘事單元運用東方古典文化的寫意手法,從畫面構圖、色彩、光影等方面還原了范老師記憶中的山野村莊,在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中凸顯了濃厚的師生情。這一單元取景于千島湖景區,大量的運動鏡頭與航拍取景塑造出開闊的大空間、大場面。在營造范老師記憶空間時,瓢潑大雨適時而來,沖淡了影片的彩色調,湖光山色、青竹荷花、溪水潺潺以寫意手法與中和之美將中國傳統美學的含蓄與靜穆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以“主旋律+災難”、“主旋律+冒險”為題材的新主流電影中,出其不意、變幻莫測的風景奇觀提升了影片視聽觀感的真實性,在短時間內不斷刺激觀眾的神經系統,帶給觀眾早期“吸引力電影”[24]的“震驚”體驗,進而與商業性、大眾化接軌。《中國機長》(劉偉強,2019)以快速利落的剪輯風格、震撼人心的聲音效果及好萊塢式驚險刺激的奇觀畫面呈現了時而壯麗時而危險的風景。飛機飛行過程中風景的三段式變化構成了影片視覺風格的美學傳達,也是推動敘事的重要元素。飛機平穩起飛時,視野開闊的山水風光是高潮前的鋪陳,飛機遇險時激烈的電閃雷鳴則將影片推向敘事的高潮,當飛機平穩迫降時,窗外出現了肅穆崇高的雪山之巔,敘事節奏重新歸于平靜,風景的奇觀化呈現與影片敘事節奏的跌宕達成了和諧一致。
圍繞影片建構的種種奇觀風景不僅是電影技術與商業市場的成功,更是一次意識形態場域的勝利。“不論電影被視為是一種藝術形式、政治工具還是商業性企業,電影都旨在訴諸于盡可能多的觀眾,必須打入社會集體成員的意識中,利用集體潛意識,電影的商業功能、意識形態功能和審美功能才能奏效”[25]。審美化、奇觀化的風景是新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表征,其直接抓住了觀眾的審美趣味,吸引觀眾紛紛走入影院,從而為主旋律的政治宣傳與理念輸出提供受眾基礎,這也正是主旋律電影利用風景粘合政治、商業與藝術的機制所在。
結 語
風景深刻影響著電影視覺風格與精神文化價值的建構。近年新主旋律電影通過不同形態風景的呈現,將“家園”變成“國家”,將“空間”化為“地方”,將“自然”變為“奇觀”。在新主流的語境下,主旋律電影中的風景不僅能夠作為意識形態風景參與國家形象認同的建構,也具有文化記憶風景的樣態,發揮著“影像民族志”的獨特作用,又能化身為視覺奇觀風景,為觀眾帶來持久的審美享受與感官震驚,由此風景從傳統意義上敘事的背景變為具有豐富意味的景觀式存在。在多聲部風景話語的共同作用中,新主旋律電影的政治性、商業性、藝術性、民族性被縫合在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因而實現了影片外在畫面表象與內在文化意蘊的融合。在面臨價值多元化嚴峻挑戰的當下,以主旋律電影作品為載體,用中國方式表達中國話語,為中國電影樹立民族文化形象,展示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以及中國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國際觀,是未來新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方向,而風景作為一種電影藝術中穩定呈現的因素,能夠在其發展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
注釋:
[1][美]W.J.T.米切爾編:《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2][俄]C.M.愛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富瀾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 年版,第316頁。
[3]Martin Lefebvre(ed.),Landscape and Film,London :Routledge,2006,p. xv,pp. 19—60
[4]Graeme Harper and Jonathan Rayner,“Introduction:Cinema and Landscape”,in Graeme Harper and Jonathan,eds,Cinema and Landscape,Bristol/Chicago :Intellect,2010,p.22.
[5]滕進賢:《增強責任感,為提高影片的思想藝術質量而努力——在 1989 年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當代電影》,1989年,第2期。
[6]作者注:“新主旋律電影”是新階段主旋律電影的特定發展樣貌。新世紀以來,主旋律電影越來越明顯地趨于轉向創作類型化和市場運作商業化,“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開始相互融合。近年來,“新主流電影”說法使用較多,在打破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藝術電影三分的語境下,“新主旋律電影”基本相當于新主流電影。
[7]Martin Lefebvre,“Between Setting and Landscape” in Landscape and Film,Martin Lefebvre e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23.
[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版,第65頁。
[9]蒙麗靜:《電影理論中的共同體美學淵源》,《當代電影》,2020年,第6期。
[10]作者注:張英進將以宣傳政權為中心的意識風景稱為“意識形態風景”。見張英進、鄭煥釗:《民族文化,個人視野,多地記憶:當代中國電影的真實風景》,《文藝理論研究》,2011年,第3期。
[11]Barbara Bender,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Oxford :Berg Publishers,1993:p307—339.
[12]張京媛編:《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頁。
[13]作者注:阿爾都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指出,對主體的詢喚(interpellation)是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功能與運行機制。意識形態是抽象的,而以概念、觀念、形象等形式存在,是阿爾都塞所說的“隱而不露的神秘角色”。只有在詢喚下,個人成為主體,服從于意識形態所需要的物質實踐,意識形態才能發揮作用。
[14]厲梅:《論抗戰文學中風景的物戀性》,《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0期。
[15]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第002版。
[16]張頤武:《歷史/記憶/電影:時間之追尋》,《當代電影》,1992年,第3期。
[17]邵培仁:《媒介地理學:媒介作為文化圖景的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頁。
[18]作者注:“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它起到的是一種連接和聯系的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兩個層面上:社會層面和時間層面。凝聚性結構可以把人和他身邊的人連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讓他們構造一個 ‘象征意義體系’……它將一些應該被銘刻于心的經驗和回憶以一定形式固定下來并且使其保持現實意義,其方式便是將發生在從前某個時間段中的場景和歷史拉進持續向前的‘當下’的框架之內,從而生產出希望和回憶。”見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19]喬慧:《〈遠去的牧歌〉:民族心志與歷史宏圖的詩意言表》,《新疆藝術(漢文)》,2020年,第4期。
[20][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21][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當代美國社會文化透析》,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22]周憲:《論奇觀電影與視覺文化》,《文藝研究》,2005年,第3期。
[23]TURVEY G.Panoramas, Parades and the Picturesque: The Aesthetics of British Actuality Film,1895—1901[J].Film History,2004(1):p9—27.
[24]作者注:愛森斯坦將電影對觀眾產生一種類似窺探癖式的感官效應稱之為“吸引力”,它的本質是表現主義的。湯姆·甘寧在對早期電影的考察中發現這一階段電影的獨特之處是為了讓“形象變為可見”,由此他稱這些尚未成為敘事藝術載體的電影為“吸引力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s)。在他看來,吸引力電影強調震撼或驚懾的直接刺激,并不關注敘事本身。
[25]吳瓊:《當代中國電影的類型觀念》,見楊遠嬰主編《中國電影專業史研究(電影文化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