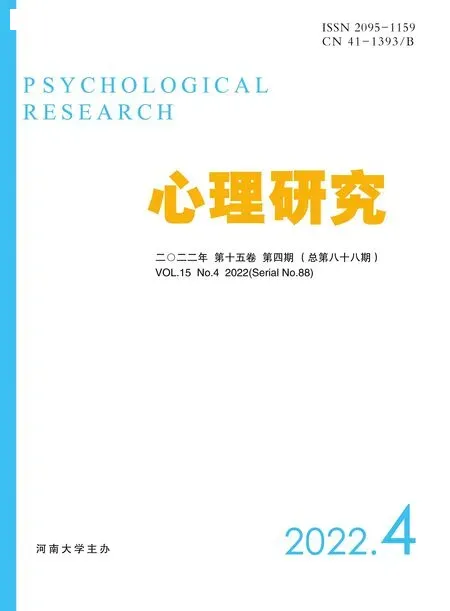轉換與堅持:低階層者有效應對健康困境的心理策略
饒婷婷 喻 豐 李 凱 張君君
(1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心理學研究所, 西安 710049;2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 武漢 430072;3 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西安 710049)
1 引言
推進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在近年來受到政府、學界和公眾的一致高度重視。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指出, 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而隨著國家和人民對健康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大家也逐步認識到,實現“健康中國”的目標不僅是醫學界的任務,它還有賴于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進步。 這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就是那些相對較為貧困的低階層群體的總體健康水平并不樂觀, 在很多身心健康的指標上都與相對較高階層者存在差異(鄧子謙 等, 2020)。這種健康不平等的現象對我們推進“健康中國”戰略,實現國民更高水平的健康與發展帶來了挑戰(朱慧劼,風笑天, 2018)。
過往的很多研究已經發現, 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客觀與主觀差異普遍存在(Stephens, Markus, &Phillips, 2014)。 除了所擁有的物質資源、認知風格以及社會態度上的差異外, 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健康水平也存在較大差別, 這種現象被學界稱為健康的階層差距(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health; 尤瑾 等, 2016)。更多研究進一步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健康的階層差距普遍存在(尤瑾等, 2018; Sepúlveda & Murray, 2014)。 因此,探討這一問題的發生機制及其改善思路也已成為心理學、社會學、公共衛生等不同學科共同關注的研究焦點。
研究者們首先從社會環境、心理機制、生理機制等不同層面研究了健康的階層差距形成的原因(胡小勇 等, 2019)。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們還基于上述原因,積極探索能夠打破健康貧富差距、提升低階層者在逆境中的健康狀況的策略。 特別是近年來有研究者提出的轉換—堅持策略 (shift-and-persist strategies),被認為是能夠有效改善低階層者諸多健康風險的心理學策略(Chen & Miller, 2012)。 鑒于此, 下文將在簡要回顧健康的階層差距及其發生機制的基礎上, 闡述轉換—堅持策略對于改善致病生理機制的積極作用, 并探討轉換—堅持策略對于低階層個體的健康產生積極作用的內在機制, 最后對該領域未來研究方向做出學理展望。
2 健康的階層差距
與高階層者相比, 低階層者的多方面健康指標都呈現出較低水平。 以往研究發現,無論是死亡率、疾病患病率、 一年內的急診部重復造訪次數和重復住院次數等客觀健康指標, 還是如自我報告的健康指標數據和心理疾病等主觀健康指標, 低階層者都與高階層者存在顯著的差距 (胡小勇 等, 2019;Rubin & Stuart, 2017)。
健康的階層差距可以從社會和生理兩個層面來解釋。從社會層面上來看,低階層群體因為處于資源缺乏的困境,他們所擁有的居住環境、社會資本、家庭教養方式、家庭情感支持等都不盡如人意,這樣的社會環境更容易導致健康狀況下降(洪巖璧, 華杰,2020; Motley, et al., 2017)。 此外,資源劣勢容易造成心理劣勢,一部分低階層者壓力敏感性高、消極情緒多,更容易做出健康風險行為,長此以往易導致較差的健康狀況 (李小新 等, 2019; Lago et al.,2018; Tan et al., 2020)。
與社會因素相比, 生理機制是與健康狀況聯系更緊密和直接的一環。從生理上來看,低階層者的生活壓力導致慢性疾病產生的生理機制與認知、 情緒及各項生理指標都有關系。 當對壓力情境進行評估時,由于資源的匱乏,低階層者往往感知到更高的風險,他們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和交感神經系統就被激活,釋放出如皮質醇、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等激素, 與激素的受體結合的細胞遍布身體的各個組織, 如果反復持續暴露在高水平的激素當中,這些組織的結構和功能都會發生改變,并逐步發展成致病過程, 最終引發慢性疾病(McEwen& McEwen, 2017)。 此外,童年貧困的生活環境會導致多種激活腎上腺軸和交感神經系統的壓力。 有研究表明,與高階層家庭的兒童相比,低社會階層的兒童在健康方面始終有著更高的風險 (Kramer et al., 2017)。 那些童年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人,即使長大以后經濟條件得到改善, 他們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依然更大(Anda et al., 2009)。可見,由于過多暴露于壓力之下而引起的應激激素分泌過量, 是低階層面臨更高健康風險的主要原因。
3 轉換—堅持策略對健康的積極作用
轉換—堅持策略是人們面對壓力情境時的一種心理應對策略。 研究表明轉換—堅持作為情緒調節應對策略對于生理健康至關重要, 而且也與一系列的積極心理健康指標呈正相關關系 (Chen &Miller, 2012)。關于轉換和堅持二者的內涵和外延,下文將會具體闡述。
3.1 轉換策略
轉換(shifting)是指在個體面對困境和壓力時,通過接納現實和認知重評(cognitive reappraisals)的調節策略,以調適自我、適應環境(Chen & Miller,2012)。轉換策略的使用可以有效促進身心健康。 如調整關于某一事件的威脅觀念可以預測人們對此情境更少的錯誤認知, 使人們在壓力和威脅的挑戰中更多保持相對的理性平和 (And & Moskowitz,2004)。 而轉換策略之所以能夠有效促進身心健康,主要就在于轉換策略包含了接納現實和認知重評兩層含義。
首先,轉換包含了接納現實,對無法改變的現實的接納會降低不利處境對健康的影響。 根據控制感的雙過程模型(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人面對困境有兩種控制方式, 一是初級控制(primary control)即努力改變外界環境,二是次級控制(secondary control)即接納現實(Morling & Evered, 2006)。 一般而言,首要控制是人的基本動機,但是當外界情境不允許被改變時, 接納現實就成為更好的選擇, 它能夠幫助人們保留在未來實施首要控制的動機和可能性, 因此這一策略能夠幫助個體更好地維護個人控制感和自尊水平, 進而預測更好的健康結果(Milligan et al., 2016)。 許多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一論證,如研究發現,那些執著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有著夸父追日式理想主義的低階層者,與不那么執著于掌控的個體相比,血壓更高,血管外周阻力更高,患高血壓的風險也更大(Wright et al.,1996)。而放下無法實現的抱負能降低身體的炎癥水平,包括降低C 反應蛋白的等級(Miller & Wrosch,2007)。
其次,轉換還包含著認知重評的含義。認知重評是一種調節情緒的先行關注策略 (antecedent-focused strategies), 也就是說它發生在情緒反應趨勢形成之前, 是為了減少客觀情境引起的壓力情緒反應,而對于引發情緒的事件進行重新認知與解構,以改變自己認知、舒緩自身情緒的調節策略(程利 等,2009)。 在多種情緒調節策略中,認知重評是運用相對普遍且效果相對更好的一種方式。如研究表明,相對于情緒抑制等情緒調節機制, 認知重評能夠更好地減少心血管對急性實驗室壓力源(acute laboratory stressor)的反應;面對嚴峻壓力時,成人和兒童對威脅更加良性的評估都能夠減少血壓的反應, 也能夠降低青少年在日常社交中的動態血壓 (Chen et al., 2007; Gross, 1998)。 而對于其他心理問題如應激傷害(安獻麗, 陳四光, 2016)、抑郁癥(張闊等, 2016)等,認知重評也都表現出了顯著的干預效果。
3.2 堅持策略
堅持(persisting)是指在逆境中不斷尋找生活意義、維持樂觀、心懷力量、忍受困境并保持穩定自我的應對方式(Chen & Miller, 2012, 2013)。 堅持的目的在于實現自我需求,并且用尋求意義、保持樂觀等方式忍受暫時的困境, 這本身是一種首要控制的應對方式,能夠幫助人們調和現實困境,并調和自我與世界的沖突, 使人們即使身在逆境中也能看到生活的價值(Landau et al., 2015)。 由此,堅持策略是幫助個體對抗健康困境的有效策略。
一些采用生理指標的研究表明, 堅持策略可以有效改善健康困境。 例如,研究發現,越樂觀的人日常生活中越不容易出現高血壓, 體外自然殺傷細胞的細胞毒素更強(感染病癥的一種預防反應),全身炎癥水平更低(Roy et al., 2010);頸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進程更慢,患冠心病的可能性更小,冠心病恢復的機會更大(Chaves & Park, 2015)。 同樣的,報告生活中有重要意義和目標的人皮質醇和促炎因子分泌更少, 疾病導致的死亡率更低 (Boyle et al.,2009)。 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也顯示,對意義的追求是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 心理幸福感不僅強調快樂與積極的情緒, 也同樣重視個人成長與生命意義的實現(羅雪峰, 沐守寬, 2017)。 發展精神病理學領域的研究顯示, 對意義的尋求是脆弱兒童應對挑戰的重要方式, 對個人創傷以及如恐怖襲擊這樣的集體創傷的應對都有益處 (Updegraff et al.,2008)。此外,面對逆境時能夠尋找人生意義、保持樂觀的精神和展現自己的力量, 也是許多處境不利群體崇尚的重要品質, 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度過困境(李占宏 等, 2018; 張晶 等, 2020)。
總之,無論是生理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的研究,都支持了堅持策略是改善健康困境的有效手段。 而無論是接納現實的轉換還是認知重評的轉換, 都能夠有效降低壓力帶來的負性影響, 減少困境對身心健康系統的破壞。因此,轉換—堅持策略對于低階層群體來說,有著更重要的意義。
4 轉換—堅持策略對低階層者健康的影響
研究發現,相對于高階層群體而言,轉換—堅持策略對低階層群體的健康改善具有更大的作用。 由于轉換—堅持能夠提升控制感(Morling & Evered,2006),因此,它對于那些由控制感缺失導致的心腦健康問題、憂慮、抑郁等身心疾病的作用更大(Chen& Miller, 2013)。 而研究顯示低階層恰恰相對缺乏控制感(Mao et al., 2020)。 因此,對于低階層群體而言,轉換—堅持策略可以有效地調節他們的情緒,從而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積極影響(Troy et al.,2016)。 具體來講,轉換和堅持兩者既可以獨立預測低階層者的健康水平, 又可以作為一種整合策略來預測低階層的健康水平。
4.1 轉換與堅持可分別獨立預測低階層者健康水平
轉換策略能夠顯著改善低階層群體的健康水平。 如發展精神病理學對促進心理韌性的因素的研究顯示,兒童能在逆境中發展較好,關鍵特點之一就是調節自我的能力強, 包括控制自己對壓力情境的理解及對壓力的情緒和行為反應 (Luthar, 2006)。特別是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中, 更好的自我調節能力與更少的問題行為和更積極的心理結果相聯系(郭永玉 等, 2017)。
堅持策略同樣能夠很好地預測低階層者的健康水平。如研究發現:低階層群體中對生活目標有著更高的堅持水平的成人身體中的白細胞介素-6(全身炎癥的標志物,能預測心血管疾病)的含量更低。 然而,在高階層群體中,對生活的堅持水平與身體中白細胞介素-6 的含量高低無關 (Morozink et al.,2010)。對樂觀(堅持策略的指標)的研究發現了同樣的模式, 低階層的中年婦女中悲觀的人的動態血壓和患高血壓的風險顯著高于樂觀的人, 也顯著高于高階層的婦女。 而低階層中樂觀的婦女與高階層婦女在動態血壓和患高血壓的風險指標上相近(Grewen et al., 2000)。 這些研究表明堅持策略本身也能夠保護低階層免受健康風險的傷害。
4.2 轉換與堅持整合策略預測低階層者健康水平
轉換或堅持都能對低階層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到積極作用。 不僅如此,已有研究還表明,轉換和堅持的整合策略更加能夠對低階層群體的健康指標有良好改善效果。換言之,堅持與轉換的效用還可以相互促進, 轉換與堅持整合策略的一并使用可以更為顯著地正向預測低階層者的健康水平。 有研究(Kim & Kim, 2012) 對被試童年時期的家庭背景環境、轉換和堅持(接納現實和認知重評)策略的使用以及被試身體的24 項共包含7 大系統的生理指標進行了測量。結果發現,在童年階層、轉換分數、堅持分數三者間存在交互作用: 轉換和堅持的分數能夠交互預測擁有低階層童年背景成人的健康水平,但對高階層童年背景的人沒有預測作用; 擁有低階層童年背景的成人中, 在轉換和堅持量表上得分都高的人的健康水平是最好的。 這一研究有力直觀地揭示出: 綜合運用轉換與堅持策略對于低階層者而言是最好的應對方式。
此外, 對患哮喘的兒童及其臨床數據的研究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有研究(Chen et al., 2011)以積極的認知重評作為轉換的指標, 而以樂觀作為堅持的指標, 同時對被試群體體內哮喘相關的炎癥指標和六個月內的其他臨床預測因子進行了監測, 結果表明, 轉換—堅持策略與階層之間有著顯著的交互作用,在轉換—堅持策略上得分較高的低階層者,體內炎癥水平比組內平均水平更低; 同時他們在接下來的6 個月內遭受的臨床損害(clinical impairment)更少,與高階層者并無顯著差異;而在轉換—堅持策略上得分較低的低階層者則表現出總體更差的臨床狀況。 這一研究再次表明了轉換—堅持策略對于減輕低階層者的患病風險、 提升其健康表現具有重要的預測作用。
綜上, 轉換—堅持策略能夠幫助個體在困境條件下抑制壓力應對的應激生理反應,延緩致病機制,有助于減少慢性疾病患病風險。 而由于低階層者生活在選擇權較少、社會限制較多的貧困環境中,使得其更重視接受壓力、調整自己適應環境的能力,以及憑借樂觀主義、 意義尋求的力量來面對困難的應對方式。 相反,高階層者擁有較多資源,可以即時解決困境,這使得他們更重視主動解決問題、直接消除壓力來源(Manstead, 2018)。因此,轉換—堅持策略對低階層群體健康水平的改善要更為有效, 是值得低階層群體和處于困境中的人們運用的一種方便簡易卻效果明顯的心理應對策略。
5 小結與展望
近些年來, 我國在幫助貧困群體脫貧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 在物質脫貧上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 然而,對于低階層群體身心健康改善的幫扶工作還有更多值得投入的空間,需要社會各界進一步給予關注和研究(胡小勇 等, 2019)。 國外大量研究已經表明了堅持—轉換的應對策略對個體身心健康有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于缺乏物質資源、處于逆境條件的低階層群體來說,轉換和堅持不僅能夠各自獨立預測他們的身心健康,還能作為一種整合策略,顯著減緩壓力對低階層健康的不良影響。 因此,未來中國本土學者需開展更多立足于我國國情的實證研究來檢驗這一效應的穩定性, 同時要深度進行更具生態效度的挖掘和探討,并且加強干預與應用研究的開展。
5.1 更細化地探索轉換—堅持策略的具體效應
轉換—堅持策略對低階層的健康會產生影響,但許多問題仍未得到清晰結論。 例如, 有研究者提出, 不同社會階層對不同應對策略的價值評判可能有所不同(Chen & Miller, 2013)。 照此觀點,有些應對策略產生的影響還需做出更為細致的劃分和探究,但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一觀點還暫無實證研究的支持。 再如轉換—堅持策略在理論上更為強調的是個體童年期家庭階層水平與應對方式對其健康的交互影響(Chen et al., 2015),那么兒童的壓力感知是直接從階層環境而來, 還是他們從父母身上習得的? 單一的積極成人榜樣是否足以教會兒童應對生活中各領域的壓力, 某些領域是否需要特殊的成人榜樣來教會兒童壓力應對策略? 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索。此外,雖然過往該領域的一些研究也曾采用縱向設計,但追蹤時間較短,難以長期監測低階層兒童習得的應對策略對健康狀況改善的長期軌跡。所以未來需要開展更多時間跨度更長的研究,來檢驗堅持—轉換策略對低階層群體身心健康的長效影響及其發展規律。
5.2 開展更具生態效度的研究
為了更具生態性地揭示低階層者的健康困境及其應對方式的效應, 未來研究應建立更靈活且更具整合性的模型。 雖然通常人所處的社會階層終其一生不會有太大變動, 但是總有部分人所處的社會階層會經歷較大的改變(Simandan, 2018),未來研究需要厘清人在經歷了階層變動后是否需要某一套不同的心理社會特點來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況。另外,人與自身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也是不斷變動的, 環境會塑造人的行為, 人也會依照自己的人格特點來選擇自己的環境, 或通過某些社交模式來固化自己的信念,從而無意中塑造了自己的環境。 因此,未來的研究需要考慮建立更多層次、 更靈活的人與環境之間互動模型,來預測個體的健康。
5.3 加強實踐應用研究
低階層群體的身心健康問題仍然是當今社會發展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Tan et al., 2020)。 未來需要加強關于轉換—堅持策略的實踐應用研究,特別是探討如何培育低階層者更好地習得和運用轉換—堅持策略。 既然研究已經反復支持了轉換—堅持對于低階層身心健康的積極影響, 那么基于兒童成長時期,開發專門的心理培訓程序,以提升處境不利兒童青少年在這方面的心理調節能力, 是研究必須要關注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 這方面的研究還較少。未來研究者可立足于本土社會文化,發展出相應的干預課程, 使得上述基礎研究結論能夠更多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治理與教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