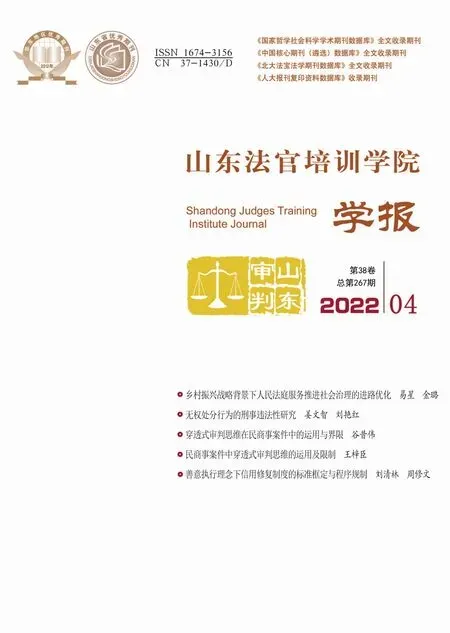民商事案件中穿透式審判思維的運用及限制
王梓臣
引 言
傳統民商事案件的裁判思維是三段論推理邏輯。三段論模式中,成文法是大前提,案件事實是小前提,案件裁判結果是結論。大前提中蘊含結論,即成文法中蘊含著案件裁判結果。這就要求,大前提確定,小前提真實,兩者高度契合。但是,在大量疑難復雜案件之中,運用三段論式時遭遇困境,不僅作為大前提的成文法難以確定,而且,小前提是否真實亦需要探尋,甚至兩者之間如何契合也需要論證。面對這樣的案件,穿透式審判思維就有了用武之地。
“穿透”一詞,幾乎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使用,不必過多的探討。但是,穿透式思維卻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而穿透式審判思維則更加不容易理解,至于其在審判中應該如何運用,就需要認真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了。然而,目前對此命題的研究深度還遠遠不夠。在為服務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司法保障和推動審判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深入研究穿透式審判思維這個重要命題,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穿透式審判思維的一般原理
穿透式審判思維體現了審判思維方式由事物表象向事物本質的切入,由規則探討向實踐理性的轉變,也契合了當代社會哲學話語由純粹思辨走向生活世界的理論旨趣。①參見武建敏:《實踐法學的哲學思考》,載《理論與現代化》2007年第3期。關于穿透式審判思維的概念和范疇,“不能把它們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和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釋”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頁。。
(一)實現案件審理的實質正義
“穿透式”概念的提出,與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密切的聯系。2014年,在金融監管領域出現“穿透式監管”的概念;2015年,其影響力逐步擴張;2016年,成為行政監管中接受的概念;2017年,在金融監管領域中大量使用;2018年,“穿透式監管”出現在央行等聯合發布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簡單來說,穿透式監管是指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核心原則,在提升市場透明度的理念指引下,甄別金融領域相關業務的性質,根據業務功能和法律屬性明確監管規則。
“穿透式審判思維”概念,是中國的審判經驗及審判智慧。2019年7月,在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講話中指出,對金融創新業務,要按照“穿透監管”要求,正確認定多層嵌套交易合同下的真實交易關系。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其中出現了“穿透式審判思維”的提法,這是司法文件正式明確這個概念。
《九民紀要》簡明扼要地描述了穿透式審判思維的目的,即“注意處理好民商事審判與行政監管的關系,通過穿透式審判思維,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探求真實法律關系”。正如有學者主張的“商法應與民法共享同一種方法論”③參見韓強:《關聯公司間法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載周江洪、陸青、章程主編:《民法判例百選》,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頁。,筆者認為,穿透式審判思維的概念和內涵不應局限于涉金融審判案件領域,亦不僅限于“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探求真實法律關系”,還應該進一步挖掘和拓展其在所有民商事案件審理中的應用價值,故而可以對其做這樣的概念界定:穿透式審判思維是一種穿透紛繁復雜的民商事訴訟案件表象,采信承載案件真相的證據,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揭示被遮蔽的民商事法律關系,適用符合案件本質的法律,通過明智簡約的論證說理,對案件作出正確裁判,最終實現司法實質正義的思維方式。
(二)契合“奧卡姆剃刀”原理
“奧卡姆剃刀”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原理。它的提出者是十四世紀邏輯學家、圣方濟各會修士威廉,因為他來自英格蘭薩里郡的奧卡姆鎮,故而得名。這一原理的含義是,只承認一個確實存在的東西,凡干擾這一具體存在的空洞的普遍性的概念都是無用的累贅和廢話,應當一律取消。簡而言之,就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
在自然科學領域,這一原理最常見的形式是:當你有兩個競爭的理論能得出完全同樣的預測時,簡單的那個更好。厄思斯特·馬赫提倡“奧卡姆剃刀”的一個版本,稱為“經濟原理”:“科學家應該使用最簡單的手段得出結論,并排除一切不能被認識到的事物”。該原則引入經濟學后表述為KISS原則,“不要將簡單的模型同‘天真模型’混淆,總而言之,應當遵循的是KISS原則(Keep It Sophisticatedly Simple)”,即“保持明智的簡約。”①參見李富成:《構建明智簡約的添附制度新體系》,載《河北法學》2005年第8期。
筆者認為,“奧卡姆剃刀”原理為穿透式審判思維提供了理論基礎。可以把穿透式審判思維看作是“奧卡姆剃刀”原理在民商事審判領域的一個創新版本,或者說是一個創新表述。法官審理的案件,是過去發生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歷史。其審判思維,應該穿透案件歷史的重重迷霧,直達案件的本質。在撥開歷史迷路去發現案件本質的過程中,智慧的法官拿起“奧卡姆剃刀”,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剃除那些干擾因素,把復雜的對象剃成最簡單的對象,務實高效地實現司法的實質正義。
(三)揭開審判人員的“思維之幕”
思維科學領域的“思維之幕”指的是,人們通過思維來認識世界,可最終又被思維與真實的世界隔開了。思維像一個幕布,反過來阻礙著人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②參見夏正林:《思維與邏輯講義——人應該如何講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頁。對于法官來說,審理案件需要思維,但有時會被像一個幕布一樣的錯誤思維,隔離在案件真實世界之外。穿透式審判思維,則能夠揭開這個幕布,或者說,穿透式思維之下,不存在思維之幕的問題。穿透式審判思維,本質屬性上屬于認識論范疇,是一種真理性認知手段,是一種理性思維,能夠排除非理性因素的不利影響,在對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考量與衡平過程中,具備切入點和方法論的積極作用。
目前的問題在于,穿透式審判思維不是每個法官都已經具備的功能。每個法官都工作在思維之中,但并不一定知道思維在我們的審判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一個特定案件的解決或者裁判的作出必定依賴于一定的審判思維,反過來,審判思維的選擇又往往影響著解決的效果或者實質正義的實現程度。長期以來,受機械思維、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的影響,以及直覺、經驗、習慣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擾,有時候法官難以認清案件本質,不能發現隱蔽的真實世界。
從法教義學角度看,穿透式審判思維有利于法官作出正確裁判,樹立司法權威,務實高效地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在我國民法典頒布實施以后,遇到疑難復雜的民商事案件,法官本來就不應該,現在更加不應該抱怨成文法不完善,而是應該恰當地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立足于案件本身、當事人合法權益,同時關注社會發展趨勢、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
二、穿透式審判思維的“理想類型”① 筆者之所以將其稱為“理想類型”,是因為包括筆者在內的法官思維永遠無法涵蓋現實案件的復雜性,只能類型化地把案件進行分類討論。這有點像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核心概念之一的“理想類型”,即其是依據價值關聯所建構的一種思想圖式,是一種思維的邏輯產物,將給描述提供明確的表達手段。它的作用是助于對現實世界的研究,從而把握行動者的主觀意義,解釋社會行動。參見張輝:《韋伯法律社會學中的理想類型及其困境》,載《學術交流》2016年第1期。
概念沒有類型是空洞的,類型沒有概念是盲目的。②參見申衛星:《期待權基本理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穿透式審判思維的“理想類型”,是從民商事審判實踐經驗現象中,抽象概括形成的基本思維模型。不同的案件需要運用穿透式思維的環節可能不盡相同,形成不同的案件穿透類型,如證據審核穿透型案件、事實認定穿透型案件、論證說理穿透型案件、法律適用穿透型案件,當然有時也許會在好幾個環節同時需要穿透式思維。
(一)穿透式審判思維下的證據審核——避免機械適用證據規則
審判實踐中,在法官面前展現的只是經過證據材料還原的事實,而證據材料往往帶有主觀傾向甚至虛假表象。它必須經過法官的思維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穿透式審判思維要求,在案件證據承載的信息存在多種理解的時候,法官不是消極地、被動地聽取當事人的主張,簡單地選擇一種字面或表面上的理解“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必然有選擇性和創造性的行為”③[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李紅勃、李璐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代譯序”部分第11頁。。選擇的過程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法官應當心中永遠充滿正義,目光得不斷往返于事實與證據之間,通過穿透式審判思維,避免機械適用證據規則,選擇相對更值得法律保護的權益,實現司法的正義性、安定性與合目的性。
案例一:④本文案例,除“南京彭宇案”外,均系筆者主審或參與討論過的案件,經過技術性處理后納入本文作為典型案例使用。在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案件中,賈某向張某個人經營的砂石料場購買沙子,向張某說買沙子若干方。張某送貨到目的地后,賈某向張某出具欠條,但欠條署名處簽字內容為“見證人:賈某”。后賈某拖延付款,張某訴至法院,要求判決賈某付款,證據只有欠條一張。賈某辯稱,自己僅是見證人,沙子并不是自己購買,但是,其始終沒有提供出購買者的信息。
機械適用證據規則,會拘泥于“見證人”三字的字面意思,認為該證據并非欠條,得出原告張某證據不足的結論,進而駁回其訴訟請求。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則會認定,案涉欠條符合證據的法定形式,具有證據效力,應予采信,能夠證明賈某就是買賣合同當事人。張某作為買賣合同的出賣人,已履行交付沙子的義務,其享有的收取貨款權益應予以保護。賈某雖主張其是見證人,但其在購買沙子時,未向張某表明購買者另有他人,應認定其為購買人,其應當承擔向張某支付貨款的義務。
(二)穿透式審判思維下的案件事實認定——發現符合司法價值追求的案件真相
案件事實并不自帶法律標簽,需要法官將具有法律意義的因素,重新排列組合形成審判視角下的案件事實。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通過法官思維重現爭議案件的歷史,重新定義案件的事實,這也就是所謂的“法律真實”。穿透式審判思維要求,在分析民商事法律行為,特別是市場交易行為時,法官應該考慮歷史發展階段,著眼于促進經濟社會更高質量發展,從整體上考慮如何使得社會的資源和財富更多,衡量當事人各自的權益保護價值,調整當事人之間的權益分配,最終實現個體權益與社會整體權益的衡平發展。
案例二:甲租賃乙的房屋,雙方約定租期五年,租金年初支付,并約定租房目的是經營甲家祖傳的特色美食。簽訂合同的當日,甲支付了第一年度的租金。十一個月后,甲得了重病住院,決定不再租賃房屋,書面通知乙解除租賃合同。遭到乙拒絕。雙方爭執不下,訴諸法院。雙方當事人都不肯放棄自己的權益,特別是在法律關系中屬于遵守合同約定的乙。
傳統的審判思維會這樣認定事實,即房屋租賃合同合法有效,甲存在違反合同約定的事實;乙已履行了自己交付房屋的合同義務,有權要求甲履行支付租金,甲應繼續履行房屋租賃合同約定的支付租金的義務。穿透式審判思維則認為,司法應該著眼于發揮物的最大效用,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案的事實應從更大視野分析認定,合同解除以后,乙仍然可以出租房屋,發揮房屋的最大效用,促進經濟發展;合同如果不解除,甲無法經營,房屋閑置,造成經濟上的浪費,亦給重病在身的甲平添債務壓力,與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的“友善”亦有相悖之處。甲因為重病導致事實上已經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實現其合同目的,即經營自家祖傳特色美食已經不能再實現。此時,甲有權解除合同。
(三)穿透式審判思維下的論證說理——剔除不必要的累贅和廢話
民商事審判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發揮論證說理的功能作用,以提升裁判結果的社會公眾接受度。穿透式審判思維要求,法官在論證說理時,將尋求法律真實的來源從理性的自我轉向外部世界,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法律關系的確認從原因轉向功能,通過社會需求認識司法本質,以明智簡約的論證說理回應社會需求,實現法律維護社會正義的目的。“社會正義是包括各種社會道德、正義觀念、公共政策在內的多元、復雜且不斷變化的混合體。……司法必須將自身與社會正義緊密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司法的目的和功能。”①[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李紅勃、李璐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代譯序”第18頁。很多時候,對于案件當事人之外的人民群眾而言,裁判文書“本院認為”部分的論證說理,或許比裁判“主文”更能體現社會正義。
案例三:在眾所周知的“南京彭宇案”的二審中,彭宇承認與他人相撞,卻說不清楚與何人相撞;警方提供了彭宇陳述兩人相撞情況的筆錄照片,盡管筆錄原件丟失,但當時做筆錄的警官確認了筆錄的真實性,再結合雙方當事人其他陳述、相關的案件事實,可以確信彭宇撞到老太太的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而且,事實上,彭宇本人也曾承認當時確實與老太太發生相撞。
從穿透式審判思維來看,該案一審法官在裁判文書的論證說理時,不顧及社會公眾對法官的期待和要求,違背了“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奧卡姆剃刀”原理,沒有穿透式地作出與裁判結果直接相關的分析論證,而是自以為是地論證:如果彭宇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應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后自行離開”等等。這樣一來就引起全社會的反感:扶人理由就不能是做好事?!做好事就不能幫著把傷者送醫嗎?!法官在錯誤思維下的論證說理,將本來屬于道德領域的社會話題紛爭,引入到司法裁判領域,帶來了非常不好的社會效果,嚴重影響了司法的形象。
(四)穿透式審判思維下的法律適用——追求法律精神的準確落實
法官對民商事案件的證據、事實及法律關系作出分析認定之后,最終的一環還是要選擇適用法律條文。在穿透式審判思維之下,可以采取剝筍式的分析,層層推進,一邊揭開掩蓋事實真相的遮蔽物,一邊援引相關的法律條文。
案例四:在一起勞務合同糾紛案件中,原告馮某訴請被告韓某支付勞務費20萬元。馮某提交了韓某出具的欠條作為證據。該欠條載明:“今欠馮某勞務費20萬元,工程款到賬后支付。”作為被告的韓某主張“工程款到賬后支付”是支付勞務費所附條件,目前所附條件未成就,所以不應支付勞務費。
法官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對法律適用的分析過程如下:
第一,在雙方當事人事先沒有對支付勞務費的期限有約定的情況下,馮某履行完畢提供勞務的義務之后,有權要求韓某支付勞務費,韓某應當及時履行支付勞務費的義務(援引《民法典》第579條)。
第二,意思表示真實是民事法律行為有效的必備要件之一。本案中,根據雙方當事人的陳述,并結合涉案欠條系韓某單方面出具,馮某曾到社保機構投訴的事實,可以認定所附條件并非馮某真實意思表示的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不滿足民事法律行為有效的意思表示要件(援引《民法典》第143條)。
第三,合同具有相對性,韓某與馮某之間關于勞務費的約定,對案外人無約束力,不應以韓某收到案外人款項為前提條件,且馮某無從知曉韓某是否收到案外人款項,所附條件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援引《民法典》第7條、第119條)。
最終,法官認定馮某主張韓某應向其支付勞務費,合法有據,應予支持;支付勞務費所附條件不具有合法性,依法不成立,對當事人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當屬無效。
三、對穿透式審判思維運用的衡平限制
穿透式審判思維并非沒有約束,它也需要一定的衡平與限制。否則,權力有可能假借穿透式審判思維之名肆意妄為,不但起不到為服務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司法保障的積極作用,反而可能會適得其反,作出錯誤的裁判,阻礙正確發揮審判職能作用。
(一)司法正義理念的指引
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應以司法公正理念為指導。法官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公正裁決案件是其價值追求,這也是法官的特殊身份決定的。關于案件的所有解釋意見、裁判方案,都必須接受公正性檢驗,只有符合公正性、能夠達成公正裁判的意見和方案,才是正確的和應當采取的。①參見梁慧星:《裁判的方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48-349頁。
案例五:在一起離婚案件中,A與B雙方本系夫妻,當A身患重病住院時,雙方協議離婚,將全部財產都分給了B。A經治療后出院,但身體構成三級殘疾。A主張撤銷離婚協議關于財產分割部分的條款,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財產。B辯稱,雙方自愿離婚,不同意重新分割財產。
機械的審判思維產生了這樣的認識:A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離婚協議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A、B兩人均應按約履行,且雙方已經辦理了離婚手續,離婚協議中財產分割部分已經實際履行完畢,不應予以撤銷。
之所以說上述思維機械,甚至錯誤,是因為其背離了根本的社會正義理念。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則認為,一方面,A出院后身體殘疾,沒有生活來源,夫妻共同財產全部歸乙所有,明顯不公平;另一方面,A身患重病之時,對生活乃至生命的看法,必然受到影響,夫妻本應互相關愛,此時協議離婚,B有利用對方處于危困狀態、缺乏判斷能力的嫌疑。應適用《民法典》第151條,支持A撤銷財產分割協議的主張,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財產。
(二)語言文字固有含義的規范
法律規范都是從相關的法律文本中抽象而來,而法律文本是由語言文字構成的,因此,語言文字是法律規范的構成單位。我們并不否認,紙面上的語言文字本身具有局限性。立法者如果認為有必要,完全可能通過艱苦的努力、縝密的思考、冗長的定義,對他們作出所有可能的列舉式的說明,并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就是說,使法律規范具有極端的明確性。但立法者沒有這樣做,這樣做在技術上是困難的。①參見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頁。這也是為什么需要進行法律解釋的根本原因。不過,我們更不應該否認,無論怎么進行法律解釋,無論怎么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都不能脫離語言文字規范的本身。否則,法律的安定性、可預測性等基本屬性將無法得到保障,將陷入法律虛無主義的迷途。
案例六:丁某和劉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約定:丁某將自己的一處房屋賣給劉某,劉某在五年內分期付清購房款100萬元,劉某支付第一期購房款20萬元后,就辦理房屋所有權過戶手續,但房屋所有權仍然歸丁某所有。雙方按照約定履行,劉某支付了第一期購房款20萬元,丁某協助將房屋過戶登記至劉某名下。其后當地舊房改造拆遷,涉案房屋拆遷補償款數額180萬元。丁某起訴主張合同約定房屋所有權未轉移,該補償款歸其所有,并稱其愿意退還劉某的購房款,并支付利息。
上述案例就不能適用穿透式審判思維,不能認為按照意思自治原則而認定房屋所有權未轉移。因為這個時候,我們要尊重《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即第116條規定“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第209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雙方當事人之間關于房屋所有權保留的規定,因與之相悖而無效。從語言文字規范來看,《民法典》關于不動產物權轉讓的規定非常清楚,語言通俗易懂,涉案房屋過戶登記至劉某名下后,已發生所有權轉移的效力,丁某的主張沒有法律依據。
(三)外觀主義規則意識的約束
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要慮及外觀主義的具體規則。外觀主義主要應用于交易行為的領域,且在遇到當事人的意思、權利等因素表里不一,兩方當事人的意思、權利相沖突,不能兩全時,只得按照外觀主義規則,保護對該外觀有理由地產生信賴的一方當事人的權益。②參見崔建遠:《論外觀主義的運用邊界》,載《清華法學》2019年第5期。當然,我們需要注意,司法實踐中,外觀主義所適用的領域本身也有其限制,即其一般適用于因合理信賴利益外觀或意思表示外觀的交易行為。但是,這并不妨礙外觀主義規則意識對穿透式思維的限制作用。我們在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的時候,要有外觀主義的規則意識,保持與外觀主義之間的適當張力。
案例七:在杜某(實際施工人)訴乙公司(承包方)、甲公司(發包方)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中,甲公司已分三筆向乙公司支付完畢全部工程款,其中的第三筆110萬元是由乙公司委托黃某領取,黃某拿到工程款后不見蹤影。杜某訴請由乙公司向其支付110萬元,乙公司提供乙公司、杜某、黃某三方協議:乙公司與黃某合作涉案工程項目,乙公司與杜某沒有債權債務關系,乙公司、黃某之間關于涉案項目的其他債權債務另行結算,黃某、杜某之間的債權債務自行解決;另外,又提供杜某向乙公司的承諾書:杜某與乙公司合作的所有工程項目已全部履行完畢雙方的權利義務,雙方無任何債權債務糾紛。
一審、二審法官不當適用了穿透式審判思維,沒有考慮意思表示外觀而導致合理信賴的情節。一、二審判決均認為,杜某實際施工了涉案工程,涉案工程已竣工驗收合格,乙公司在從甲公司領取工程款后,有義務將所領款項付給杜某,于是判決乙公司向杜某履行支付工程款的義務。考慮到意思表示外觀產生的合理信賴,再審法官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三方協議和承諾書,系杜某、乙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對杜某、乙公司均具有法律約束力,乙公司沒有向杜某支付工程款的義務。
結 語
審判思維不是憑大腦器官先天決定的,而是通過后天培育而發展完善的。為服務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司法保障,必然要求民商事審判思維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同時,民商事審判思維的發展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審判工作自身也在進入新發展階段。然而,法官面臨“創造性的因素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大道之側有著許許多多的岔路口,而路邊的指示標牌也很不完整”①[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長》,李紅勃、李璐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1頁。“法官不一定要固守先例,換一種思維方式,探索新的方法,將是法官一生不斷進取的動力源泉”②馬軍:《法官的思維和技能》,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擺脫審判思維上的不成熟狀態,對審判思維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研究,找出規律性和可復制性,為今后的工作提供審判思維方面的參考和指引,將有力促進審判工作高質量發展。總之,審判思維的發展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