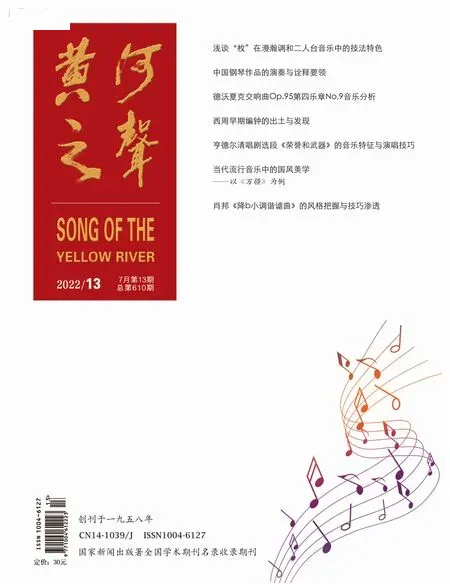古詞粵韻
——無伴奏合唱作品《望月懷古》音樂分析
吳開華
一、作品介紹與曲式結構
《望月懷古》是以韶關籍唐代大詩人張九齡的名詩為歌詞。作曲者為葉方婷,創作于2018年,其為華南理工大學藝術學院舉辦的原創合唱作品音樂而生。其音樂動機來源于詩詞的粵語音調,旋律悠長深遠,并通過富于變化的復調手法力,求展現“海上生明月”的悠遠意境。
(一)“懷古”與“懷遠”的對比
《望月懷遠》是唐代詩人張九齡原詩的名字,而無伴奏合唱作品《望月懷古》是作曲者采用詩詞里的內容做成為作品題目。在此,我們應該思考一下,為何作曲者不按照原來的“懷古”作為作品的名字,轉而采用“懷古”呢?對此,筆者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詩人采用“懷遠”表達的是人物處于古代情景下的心理,即二者相隔千里卻又聯系不上心中人的思念與盼望,因而是懷念遠方的他;然而現作曲家的“懷古”是用音樂的形式懷念古人及其作品。兩者的目的都在于“懷”,但目標對象卻大不相同。這大概就是“懷遠”和“懷古”的區別。
(二)作品曲式結構
作品的結構為帶有引子、縮減再現的單三部曲式結構,B段重復一次,轉調性結構。音樂開始為g小調,引子由兩部分組成,1-9小節為引子1,9-13小節為引子2。A段(14-27小節)可分為a、b兩個樂句,調性一直沿用前調;B段(28-39小節)分為c和c1兩個重復樂句,調性從原來的g小調轉為?B大調;隨后在40小節開始通過主題聲部的改變而進行B段的主要材料重復,為B1段(40-57小節)。A1再現段(58-68小節)為縮減再現,通過聲部的和聲填充與其b句的后半部分采用念白形式來代替音樂材料的形式來呈示再現段。
二、《望月懷古》的形象單元與形象連接
《望月懷古》作為帶有縮減型的單三部曲式,則帶有三個不同的形象單元。其構成三個主題形象的基礎條件如下:a.引子的“形象單元”,其速度為Andante(?=55),調性為g小調;b.A樂段速度為Andante(?=55),調性由?B大調轉向g小調;c.B樂段速度為Animato(?=100),調性轉向?B大調。最后重復A樂段速度與調性都得以回顧則不再贅述。
通過三個主題的速度與調性的對比差異可以觀察出其中的個性不同:
引子形象:主題音調以長音符為主,通過向下行跳進再向上行級進作為動力之一。其動力之二:在聲部安排上只采用了女聲聲部,通過多次使用節奏切分來打破四拍子的強弱規律,從而推動音樂的進行。女高聲部旋律開始于d1音,經過四拍后在女中聲部以純四度的音響出現并和女高聲部形成補充聲部。無論是從內部節奏運動還是聲部之間的交互進行都可以很好地避免音樂的停滯不前,從而創造出一種遠方海上霧氣茫茫,海面卻又在不斷涌動的動靜結合之像。
A主題形象:其音調平穩,以四度內的進行為主。A段材料先以女高聲部沿用引子主題材料以pp的力度出現,意在延續引子部分中的“迷霧”形象,使得后面的音樂材料得以延續發展。隨后男高、女中和男低聲部分別出現,和聲逐漸豐滿起來,意在使得聽者的思緒從遠處的迷霧中慢慢地拉近到海邊上的“情人”的內心世界。音樂情緒富于起伏,多次的漸強漸弱就像是“情人”內心等待的焦慮與翻涌的思念,最后歸于一聲無奈嘆息。樂譜中的一處漸弱后漸強在于“怨”字的表達上,集中地表現了人物內心思念的不斷積蓄到底,從而釋放對長夜漫漫的幽怨。該樂段整體處于弱的力度中,其漸強和漸弱都應該是在其框架里有分寸地適度處理,過分地漸強容易破壞主題形象,但過于漸弱又容易失去人聲的把控。
B主題形象:此時調性通過從25小節的g小調的屬和弦到導和弦就開始做出轉換成?B大調的準備,同時完成了速度從?=55變成以二分音符為一拍,每拍50的轉換即?=100。本段體現了中西元素結合使用,該主題主要采用了復調的寫作手法,通過不同聲部的進出與不同聲部音色對比的配合來描寫“情人”在房間里的情景及清晰,描寫了其行為的不安與環境氛圍,曲調中帶有一定的戲曲元素,如戲劇當中的音調及拖腔等。此段力度以mf為主,最后通過非常規和弦與高疊置和弦的使用和f力度的配合將本曲推至高潮。演唱時應該注意各部分mf內容的表達,指揮應合理安排不同內容的mf力度值,避免隊員一律唱成同樣的力度,從而失去音樂色調的對比。
連接不同形象單元的材料稱為形象材料連接,三個不同的主題形象單元的連接是具備了不同的形象連接的。如第一處出現的引子與A樂段的延續性連接。
引子主題作為全曲最先出現的音樂形象,其擔任著奠定全曲基調的作用。為了避免引子與呈示段的斷裂,引子主題過渡到A主題形象是通過A主題在女高聲部延續了引子主題的材料,通過11小節處的小三和弦進行到大三和弦,同時也通過12小節的大三和弦進行調性的轉換,使g小調變成?B大調,也使和聲從柔變亮,從而將海面景象拉回人物內心作出鋪墊,從而顯得前后邏輯嚴謹。
主題A與主題B是屬于對置型連接。主題A在27小節通過休止的自由延長與速度從每每拍55變成100來形成對A主題的對比,其從作曲手法和材料內容也完成了呈示段與對比段的對置。
三、各段音樂材料分析
對于任何音樂作品來說,單純地從其表面淺顯分析其速度和段落是指揮工作的第一步,而分析其作品內的細部音樂材料則是最關鍵的一步。《望月懷古》在其復調與和聲的運用上體現了古今技法的融合與展示。
(一)引子材料
引子1由女高聲部的“d2”、“b1”、“c2”、“g1”四音組而成,通過延留、顯現等方法來打破傳統的四拍子節奏規律。女中聲部在此也進行了長音式的襯托,前兩小節通過使用二重輔助音來推動音樂,第5~6小節通過下屬功能組進行到主功能,以此將音樂延伸至引子2中。引子2開始也是通過下屬功能進行到主功能,同時將不同的聲部進行疊加,音樂停留在主七和弦上,七音的加入讓和聲更加豐滿且七和弦極其不穩定需要解決從而引出A段。
(二)A段音樂材料
A段分為不對稱的上下兩句(5+8),采用主復結合的方式寫作。四聲部的進出各有不同,a句女高聲部從正拍開始唱出引子1的核心四音組,而男高則兩拍后唱出本段的主題樂思,從而形成了典型的對比性復調。女中聲部在17小節第二拍以男高聲部上方四度平行的和聲性聲部的方式短暫出現,到19小節(b句)第二拍男低聲部出現與男高聲部為一組,而女聲聲部則為另外一組對比聲部,直至25小節剩男聲聲部。a句主要采用復調寫法,較難分析其和聲,b句和聲清晰可見,22-25小節通過Ⅱ7-Ⅳ7-Ⅴ7-Ⅰ6-Ⅳ7-Ⅴ結束在屬七和弦(缺五音)。最后通過一聲輕嘆與自由延長結束A段。
(三)B段音樂材料
B段材料由不對稱的兩句構成,其中包括B段重復了一次并進行了擴展,調性通過對置轉向?B大調。其最大的特點是在寫作中對主旋律在不同聲部的穿插進行重復表達。c句(28-34小節),新的主題樂思第一次出現于女中聲部,采用三音組進行,兩拍后男低聲部以下方四度,對其前兩個核心音進行模仿,第二次主旋律來到女高聲部,此時男高聲部則是對主題三音組材料的展開。經過一小節后女聲聲部以平行四度形成節奏同步的主調性聲部進行,此時第三次主旋律到了男低聲部,材料依舊是來自主題,此后兩聲部形成了長音式的襯托最后再把主旋律交給女聲聲部。
d句以和聲性寫作為主,和聲通過下屬功能組與主功能組進行為主,主旋律先在女聲聲部出現,兩小節后女中聲部的三度平行旋律交織于男低聲部,形成了女高男低的十度平行進行。
B1段采用對比復調寫作,c1句可以分為兩個樂匯。第一個樂匯(40-41小節)由女高音擔任主旋律,兩個內聲部以長音襯托為主,男低聲部以主題動機變形,一字兩拍不斷地向前發展。第二個樂匯(42-45小節),主旋律交給了女中聲部,此時女高音的旋律來自引子1的音樂材料,男高聲部以一字三、二拍的規律出現。d1句以女聲、男聲間隔一拍的卡農形式出現。和聲通過在50小節處的?B大調的Ⅵ級和弦作為g小調的中介和弦進行轉調,并在54小節由Ⅴ7進行到Ⅵ,形成阻礙進行但沒有解決。
(四)再現段音樂材料
其再現段為縮減動力性再現,通過對A段a句女中聲部缺失的補充而形成動力性再現,b1句則是對后面樂匯的省略,以念白的方式交代唱詞,最終旋律停留在g小調的導音上與女中聲部形成空五度,使音樂產生一種調性的模糊不清。在音樂的聽覺中,若作品最后得不到解決,便會使聽者得不到聽感上的滿足,從而產生一種對音樂繼續發展的渴望。
四、古詞粵韻
《望月懷古》取詞于唐代大詩人張九齡的《望月懷遠》,而唐代的古體詩在其韻律中又與廣東話(粵語)發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曲者運用跨越型旋法創作,其根據廣東話的發聲聲調進行音樂的創作,將語言、旋律與音樂形象有機地聯合起來,旨在更好地貼近粵語發聲的特點和展示音樂形象。
(一)入聲字的使用
唐宋詩詞人的吟詩填詞是有一定的章法可循的,如五言絕句或七言體的詩歌,它們都要求要押韻。因而,古代便有兩種韻書作為吟詩填詞的依據。一類是以吳、閩、粵語系為主的《切韻》、《廣韻》;另一類韻書,是以普通話或官話區域的語系為根據。前者韻書,字音分平、上、去、入四聲,為唐宋人作詩填詞選韻的標準,即使是北方普通話地區的,也不例外地以此為據。①
入聲是古代漢語的一種聲調,屬仄聲,指一個音節以破音/p/t/k/作結尾,發出短而急促的子音。現將《望月懷古》中的入聲字標注出來并與普通話讀音作對比②:
海上生明月(yuè),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xī)起相思。
滅(miè)燭(zhú)憐光滿,披衣覺(jué)露滋。
不(bù)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普通話的四聲調將粵語的入聲調歸入其中,但其聲調值卻是大有不同。如:上陰入聲調值為5(燭zug1)、下陰入聲調值為3(覺gog3)和陽入聲調值為2(月yud6、竟jig6、滅mid6)。而普通話中的陰平調值為55、陽平調值為35、上聲調值為214、去聲調值為51。通過對粵語與普通話的聲調發音對比,若采用普通話的四聲調來朗讀或演唱會使其平仄既不同,音韻亦不協調。原因在于粵語九聲調中的入聲調符合了唐詩作詞的音律平仄關系,而音調值得更加豐富也賦予了音律創作的便利。
(二)跨越性旋法的使用
意在更好地將語言特點通過旋律表達出地道的語言味道,跨越型旋法大部分作曲者使用的創作手法之一。通過詞作品的語言聲調來配合其旋律寫作,如第一句歌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海hoi2”、“上soeng6”、“生seng1”、“明ming4”、“月yud6”、“天tin1”、“涯ngai4”、“共gung6”、“此qi2”、“時si4”。其中“生seng1”和“天tin1”為陰平,調值為55、“海hoi2”和“此qi2”為陰上,調值為35、“明ming4”、“涯ngai4”和“時si4”為陽平,調值為11、“上soeng6”、“共gung6”和“月yud6”為陽去、陽入聲,調值為22和2。若以陰平聲調(55)為軸,其聲調值與旋律安排以A段主題第一句為例如:“海”(?b1,35)、“上”(g1,22)、“生”(d2-c2-d2,55)、“明”(f1-g1,11)、“月”(g1,2)、“天”(c2,55)、“涯”(g1,11)、“共”(a1,22)、“此”(c2,35)、“時”(f1)③,其旋律與其聲調值的走向是基本一致,而全曲也很明顯地運用了這樣創作手法來闡述作品與語言的關系,使音樂更富于本土氣息。
結 語
《望月懷古》作為粵語合唱作品與古體詞作品的結合,其在粵語聲調與音樂創作上有其自身的特點。在粵語聲調與音樂形象的構造上,其通過聲調的高低來描繪旋律線的同時能準確地表達情景。如“海上生明月”中的“生”字處于該句聲調的高點也是旋律的高點,描繪出一種明月慢慢升上的情景,使畫面生動起來。作品大量使用七和弦,通過下屬七和弦與其非常規的解決作為推動音樂的發展手法之一。七和弦與高疊和弦的不解決是古典作品中不常用的,而該作品在傳統的復調寫法中也得到很好的體現,傳統復調與非常規和弦的結合也是本作品的特點之一。■
注釋:
① 黃素芬.唐詩與廣東話[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04):57-60.
② 下劃線文字為粵語入聲字,()內為普通話拼音。
③ 括號里第一個為旋律音高,第二個為該字的粵語聲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