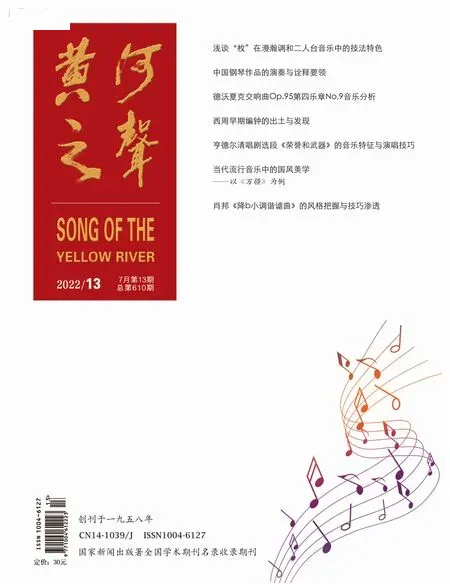赫哲族現代民歌《山水醉了咱赫哲人》音樂結構及特征闡析
趙 媛
一、赫哲族現代民歌《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創作背景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是著名音樂家郭頌創作的一首典型赫哲族民歌,從年代來劃分屬于現代民歌。這首作品具有鮮明的現代抒情特征,但是又忠實地反映了赫哲族民歌的傳統特征,該作品描述了赫哲人生活中常見的哲羅魚、梅花鹿、大山、河水等自然物,烘托了赫哲人對自己家鄉無比的熱愛,也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樸素的自然主義理想,為我們呈現了美輪美奐的生活世界下的音樂畫卷。總體看,《山水醉了咱赫哲人》這首現代民歌建立在赫哲族民間音樂素材的基礎上,曲調的運用和節奏的選擇都具有強烈的傳統風格,在伴奏織體等方面的處理則更具現代民歌的特性。
二、《山水醉了咱赫哲人》曲式結構特征分析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是F宮調式作品,曲式結構為再現三段曲式,整首歌曲由三部分構成,A段+B段+A段,共有58個小節。
大多數赫哲族民歌都屬于宮調五聲類作品,選用傳統的三段曲式結構進行創作。尤其在現代民歌中,民歌思想的表現內容與題材的選擇方面往往具有“宏大敘事”的特點,主要是將篇幅較長的神話故事、英雄史詩、童話故事和長篇愛情故事的某一個片段拿來進行創作。因此,像《山水醉了咱赫哲人》這類作品的曲調選擇往往與這些傳統觀念息息相關。從《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曲式結構來看,反映了赫哲族傳統的音樂語言習慣和特點,作為一個標準的三段曲式結構的現代民歌,作曲創作中運用了典型的赫哲族傳統民歌素材,將曲調的方式進行了稍微偏“漢式”變化,其核心目的是要把赫哲族的音樂傳統在多民族文化這種環境中融合,以這種三聲部的形式開拓赫哲族傳統音樂旋律的表現空間。這其實才是創作者的最終美學追求。《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將赫哲族口弦琴、嫁令闊音樂的自然表現精神與漢族嚴格的五聲曲調形式相結合,既保留了中國傳統音樂的線性特征,又讓赫哲族傳統音樂的旋律得到了新的拓展。這無疑是赫哲族傳統民歌的創新手法的典范應用。
從具體的曲式形態來看,《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F宮調式與赫哲族的其他民歌類型一樣,均為五聲調式,且有變化音出現,再現部旋律也主要為上五度或下五度關系的近關系音程為主,曲式結構的選擇烘托了抒情性與敘事性相結合的現代民歌特點,有時候抒情性特征反而更加明顯。
六小節前奏過后進入A段(7-30),A段共有六個大樂句,形成方整性樂段結構,遵循了傳統的“鋪墊、承接、轉折、回歸”邏輯進程,結構大氣工整,符合民歌的一貫曲式風格。B段(41-58)仍然是F宮調式,共有四個大樂句,每個大樂句各有四個小樂句,結構非常工整,但是旋律、和聲等與A段對比明顯,反差較大。B段以敘事為主,是對A段抒情內容的展開,節奏中運用了大量的休止符,增強了頓挫感,彰顯敘事的魅力。再現段是對A段的再現,從D.S.標記可以看出是完全再現了A段,發揮了作品曲式的概括功能,進一步烘托主題,讓這首現代民歌的主題實現升華呼應,最后的四個延長小節結束在主音上。
三、《山水醉了咱赫哲人》調性特征分析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在赫哲族傳統民歌基礎上采用再現調性音樂形式,比如“賦格”,但是作者沒有完全機械地套用這種發展模式,而是根據赫哲族傳統民歌調性特征進行了少許變動,例如增加了齊奏聲部的五聲調性音階,這樣一來,作品的線性音響更加飽滿,不會單調乏味,反映了現代民歌的調性創作理念,突出了赫哲族傳統民歌的旋律“流動性”意味,烘托了明朗、歡樂的氣氛。《山水醉了咱赫哲人》旋律主要由do、re、mi、sol、la五音作為骨干音。這種調性音符的選擇與漢族民歌非常類似,區別在于調性的寫法上。一些研究者認為《山水醉了咱赫哲人》不能算是赫哲族傳統的五聲調性作品,最多算是一首增加了弱fa、弱si的七聲音調作品,而且認為著說作品的音程結構不夠嚴密,組織功能不強。但是本文認為《山水醉了咱赫哲人》應該是典型的五聲調性作品,準確地說是帶有現代特征的赫哲族民歌。
從調性分布來看,《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眾多小樂句之間都是傳統的“五度結構”,結構布局符合傳統民歌的五聲調式體系,無論是赫哲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民歌中,“五度結構”十分普遍。例如A樂段第三樂句落點音為羽音,第四樂句落點音為商音,二者組合成一個完整的五度結構。
從旋律結構來看,B段的第二句尾音與第三句的起音的銜接中,選用了傳統的“魚咬尾式”創作技法,這種技法形成的旋律結構更加完整統一,具有很強的律動感,赫哲族的其他民歌如《共產黨救了咱赫哲人》也選用了這種旋律技法。
從音程進行來看,大量的“大跳”音程增強了旋律的波動范圍,讓旋律更加自由奔放,符合赫哲人的性格特征,充滿一種熱情豪邁的情緒。例如9、27小節的五度大跳,19小節的八度大跳,20小節的六度大跳,提高了旋律走向和情感表達的豐富性,比傳統民歌的音程進行更加大膽,情感更加飽滿。這種處理方式凸顯了《山水醉了咱赫哲人》調性風格,突破了傳統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會產生一種“游離感”。實質上《山水醉了咱赫哲人》是典型的五聲調性作品,無論是音程大跳的豐富變化還是五度結構的穩定輸出,讓這首作品在繼承傳統民歌的調性特征基礎上,情感的釋放更加大膽、激烈,具有很強的“進攻性”。
四、《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和聲特征分析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和聲特征十分明顯,既突出了傳統的線性織體特征,又適當地借鑒了西方和聲色彩表達技法。《山水醉了咱赫哲人》音域十分寬廣,大多以八度平行的方式帶給人一種和聲線條的簡潔流暢之感,色彩變化也與赫哲族人性格自由奔放非常接近,民歌的和聲色彩極具開放性,再加上器樂伴奏更是增添了這種色彩的獨特性。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中的和聲不像西方傳統和聲那樣重視功能和聲,作者顯然沒有將重點放在了色彩的運用中,沒有使用三度疊置的和聲結構,而是使用了大量的色彩和弦。例如“F—A—C—bE”的進行模式中,這里的“bE”音初看很突兀,好像打破了慣有的和聲結構,色彩也不是很鮮明。但是我們發現緊接著的樂句卻發生了快速的線性運動,于是就形成了一動一靜的對比效果。同樣,作者也沒有應用五聲音階的和聲縱向疊合,目的是保持和聲色彩的多樣性和靈活性。藝術具有通感,這在嫁令闊、依瑪堪等說唱音樂當中有著典型的表現。《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和聲空間布局與演唱的時間流動氣韻通過線條運行與和聲變化達到了高度融合。又例如,《山水醉了咱赫哲人》中加入了許多分裂八度和聲,這些和聲的走勢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那種向上進行,作者將它們反向設計,達到八度和聲向下進行的效果,故意和主流的音響效果發生沖突,產生色彩差異,同時又加入了口弦琴的自然音色韻味,凸顯赫哲族民歌的和聲伴奏風格。眾所周知,西方和聲體系中單音作為獨立音存在,就像一個字母一般,一個具體的和聲就是靠不同的獨立音組成的,每一個單音組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和聲。作者很顯然站在了傳統少數民族民歌的和聲創作立場上,他認為單音必須要在整個的音樂運動過程當中體現出來,而不能作為獨立的存在。一個音可以被分作為“音頭、音身、音尾”,如果離開這種視角,那么就會破壞赫哲族民歌的和聲色彩功能。所以要想理解《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和聲特征,就必須深刻理解每一個音的表現意義,將每一個音放在整支曲子里去體驗其和聲色彩。
還有一大亮點在于作品56小節中。56小節的伴奏織體選用了反向八度低音和分解和弦,尤其是反向八度是現代民歌和聲伴奏中十分罕見的,也是郭頌創作的作品中為數不多的一次嘗試。反向八度低音與西方復調創作手法十分相近,但是區別是它造成的旋律線流動呈現反方向,張力更加明顯。整首作品此處的旋律線不僅僅是相互襯托的作用,還有一種“有秩序的排斥”作用。25小節的伴奏織體選用了琶音,目的是提高作品的情緒感染力。琶音的出現讓情感更加細膩,旋律線條更加優美自然,同時充滿音樂空間想象力。兩小節過后,27小節開始琶音變為分解和弦,進一步提升了旋律的流動感,速度也開始加快,仿佛漁人劃船越來越快,心情愈發喜悅。
五、《山水醉了咱赫哲人》聲韻特征分析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具有鮮明的聲韻特征。《山水醉了咱赫哲人》與傳統的說唱民歌具有相通性。
一方面,《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節奏感、力度等具有高超的聲韻特征。作者通過音樂語言、力度、速度等處理,讓作品敘事的節奏產生鮮明的層次感,不同的聲部形成變化,讓聽眾產生聲線粗細、節奏長度、和聲色彩濃淡等不同的聲韻體驗,這些聲韻表達形式又與整體曲式結構布局形成更大的空間張力。音程變化、節奏的變化、力度的強弱變化、不同的演奏技巧相互組合,這些都可以讓音樂作品產生整體的聲韻效果。聲韻的融入可以讓這首作品有著不一樣的時間感體驗,反映了作者對這首作品獨特的個人韻味理解。這種韻味體現在作者的特殊創作嗜好當中,例如作者傾向于在一些樂句旋律的細節方面留下個性化的特征,尤其在滑音、顫音的標記方面做特殊處理。不同的處理方式表達了不同的韻味。由于《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具有鮮明的說唱意味,許多細節的處理都強調即興發揮,不拘泥于固定形式,強調現場性。《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就是體現了赫哲族傳統說唱音樂的聲韻特征。
另一方面,《山水醉了咱赫哲人》通過器樂配合突出聲韻。赫哲族善于吹奏口弦琴,這是赫哲族一種傳統器樂,在嫁令闊和依瑪堪音樂中經常可以見到。口弦琴的演奏技法較為簡單,主要充當伴奏功能。《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當中有一些旋律片段由口弦琴進行伴奏。例如為了表達音的拖曳與顫動,口弦琴伴奏中可以緊跟音符進行,通過滑音和刮奏增強音色。演奏時不能單純地靠指尖波動,當一個旋律音出現后,利用顫動產生音的余味,而不是等待它自然消失。雖然這種技巧在西方音樂當中也十分常見,但是區別還是很大。在西方音樂當中,像顫音、滑音等技巧一般都是作為裝飾音存在的,而赫哲族《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當中的口弦琴的拖曳音、顫音不僅僅是一種裝飾的技巧,質言之它們有著更深刻的民族音樂味道。口弦琴將這種“裝飾音”作為本真的音來對待和處理,如果不作這樣的處理就不能叫做演奏。所以口弦琴的每個音幾乎都需要拖曳和顫動來處理。又例如利用按音來改變音高,通過口弦琴的左手按音發聲,然后移動手指從而改變音高,其實這也是一種特殊的裝飾音技法,其音色細膩柔美,余音繞梁三月不絕。
六、《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審美特征分析
《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反映了赫哲族傳統民歌說唱中的一貫審美風格。作者結合自身生活經驗和體會,將赫哲族傳統審美旨趣融入作品中,表達了“自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審美價值觀。這種審美價值觀不僅體現在傳統民歌當中,還體現在赫哲族美術、建筑、文學、舞蹈、工藝制作當中。《山水醉了咱赫哲人》作為一首現代民歌,集中體現了這種美學方法論的價值。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赫哲族對家鄉山水的熱愛,引申出赫哲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和諧穩定快樂生活的憧憬。
作為一首現代民歌,《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的傳統審美價值觀與現代審美價值觀也有許多重合之處。它的旋律線條的律動感、音樂畫面空間的疏密結構、樂句落音的主次輕重,自由即興的說唱表達,都與現代音樂創作規律十分相近。同時,這首作品的主題立意與新時代民族文化事業發展高度重疊,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十分吻合。
結 語
綜上所述,《山水醉了咱赫哲人》作為一首現代民歌,沿襲了赫哲族傳統的嫁令闊、依瑪堪等音樂形態的曲式、調性、旋律等特征,同時在意境和聲韻方面又有所創新。因此不能從傳統民歌的角度去觀察和分析這首民歌作品,因為結合新時代審美視角才能更好地把握這首現代民歌的音樂結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