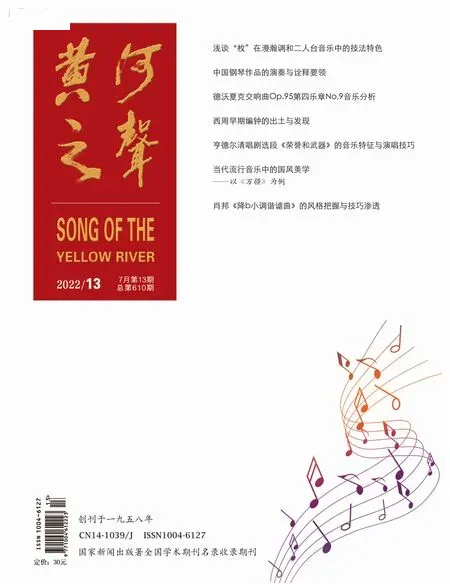“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歌詞藝術特點分析
李凌子
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臺灣青年一代以學生為主要成分的知識分子中掀起了一股木吉他風潮。如今“臺灣現代民歌運動”已成為固定用法,“專指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臺灣的年輕知識分子尤其是學生當中,興起的一種以‘唱自己的歌’為口號,自己作詞作曲并用木吉他自彈自唱的音樂形式。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打破長久以來在臺灣樂壇中被西方音樂及以‘時代曲’為主流的壟斷局面。這種音樂形式通過借助文藝界的力量,以及演唱會、唱片、電臺、電視臺的傳播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也使流行音樂的大部分傾聽者由成年人轉為青年學子。”①
一、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歌詞創作主題中的藝術性
(一)唯美鄉村頌歌式的仁民愛物
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最早投入到田園生活風格創作中并且最擅長此類風格創作的人是被稱為“鄉間田園歌謠始祖”葉佳修,可以說這類田園風開創了臺灣校園民謠的全新風格,同時也影響了一批填詞人的作品,如莊奴《踏浪》、侯德健《捉泥鰍》、三毛《夢田》。
筆者將鄉土鄉情田園歌分類為“頌歌”有特殊的理由:一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觀念,對于思鄉、懷舊則有著一脈而承理想化“頌”的色彩;二是由于近代以來華人移民的特殊歷史,涌現出了眾多東南亞、華人歌者,他們的創作中不乏許多思鄉愛國主題。這些歌曲在中國內地廣為流傳,甚至類似于愛國頌歌,傳播渠道也往往是政府機構的宣傳鼓勵,例如《我的中國心》,第一次在內地出現便是在1987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由臺灣歌手張明敏演唱呈現。“長江”“黃河”“黃山”“長城”這些來自中國的意象成了海外游子的精神符號,也作為文化象征成為他們身份認同的必不可缺,西洋和聲與樂器包裹下“中國心”的意義建構,讓民族文化的核心得以血脈相承。
因此,筆者把這類田園歌曲歸類為思鄉之歌,也可稱為愛國頌歌,葉佳修也有相關詞作《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童安格《把根留住》以及余光中的詩作《鄉愁》,這些作品描寫了土地與人的情感,但無法脫離“頌”的本質,體現了民歌運動時期時代的需求,它們的表現形式以及文體都隨著主題不斷變化。
在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鄉間小路》和《外婆的澎湖灣》是葉佳修最為大眾耳熟能詳的作品,其中,《鄉間小路》為e小調調式,結構為再現三段體,即“A—B—A”,A段為典型的起承轉合,極具民歌的民間風味。到了歌曲B段,歌詞采用直抒胸臆的表達方式,由兩個相似的樂句構成,從全曲最高音向下二度模進,搭配單純直白的歌詞寫作方式,表達對田園生活的無限熱愛以及歌頌宣揚。
葉佳修創作的《外婆的澎湖灣》歌曲調式為G大調,曲式結構為兩段體,即“A—B”,A段第一句旋律級進為主,第二句在音區上直接比第一句跳進一個八度,上揚的旋律態勢給予了旋律輕快的感情,而三、四句則更類似于美國鄉村民謠,平鋪直敘白描澎湖灣的風光,B段副歌結構則由一完整句子構成,巧妙創造出了極為吻合的歌詞旋律,四度五度的音程跳進也極容易讓聽者進入音樂情緒,抒情效果極佳。倒數兩句節奏型則頻繁變化,八分音符到四分音符休止再到四分附點音符,時值由短到長,旋律從活潑過渡到悠遠,可謂抑揚頓挫。總之,葉佳修身為詞曲雙修的音樂家,善用音樂語言來刻畫人物形象或是描繪景物,并糅合美國60年代民謠的手法和中國傳統民歌元素。吉他作為主奏樂器的伴奏形式也極具民謠感,旋律的簡單悅耳更使其作品傳唱程度甚高。
(二)吟游四方白描式的自由想望
作家三毛的歌詞是她一生的寫照,也是她身為作家在音樂的時代洪流中發出的光與熱。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大量對原生態的自然本色與日常生活進行白描而不假雕琢,三毛的作品抒情色彩濃郁,透露著女性對自由與愛情的向往。她所提倡的“鄉土”精神,與民歌時代所追尋的自我認同、本土尋回之理想不謀而合。
從三毛作詞的《橄欖樹》歌詞來看,其憧憬烏托邦的自由精神展現無遺,故土情結也在她的文字之中涌動,透露出臺灣人尋根的渴望與身份認同。關于《橄欖樹》的歌名,傳言本名為“小毛驢”,后被齊豫改為《橄欖樹》,而原標題更能說明三毛熱衷于白描,并從生活原始素材中提取文學意象的審美取向。象征性意象在詩歌與歌詞中因其自身的模糊性很難說清楚,這首歌的“橄欖樹”則是作者想要建構的象征,而后加以情景的烘托與發展。在一連串意象例如“小鳥”、“小溪”、“草原”之后點出“橄欖樹”,歸結于此包容一切的象征性意象中,這個象征并無明確所指,卻有因為先前意象而累積起來的情緒感——夢中家園的具象代表。三毛用獨特的來自異國的風格手法讓歌詞極具文學性,“流浪”與“橄欖樹”所指代的顛沛與精神歸屬則是一組對立修辭,可看出她所提倡的對故土充滿眷戀,但同時心靈得以解脫并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
三毛主張的思想類似于中國古代道家的美學觀“滌除玄鑒”,含義為洗去主觀欲念、成見與迷信,澄凈之心忘懷古往,明察之態品讀事物②。三毛對漂泊的贊賞、對心無旁騖寧靜致遠的追求,以靈魂救贖的吶喊來抒情便充斥“滌除玄鑒”之意味。三毛的可貴之處,也正是此種她所提倡的人與自然的建構模式。除卻這些靈魂深處的夢想白描,三毛的歌詞風格也極具“個人性”。1979年三毛的丈夫荷西潛水遭遇事故不幸身亡,三毛悲痛欲絕,寫下作詞作品《今世》,歌詞搭配齊豫凄厲的泛美聲演奏方式,輔以弦樂以震音演奏不和諧音程,搭配鋼琴密集如雨的伴奏,表達了詞作者個人無法抑制的激烈情感。如此呼喚式語句,敘述了一個私人化的、凄美哀絕的故事。
二、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歌詞創作手法中的藝術性
(一)呼應——歌詞最本質的結構特征
文章向來講求起承轉合,小說故事不可避免起因,經過,結果的敘事結構,歌詞的基本格局則是呼應。呼應是建構歌詞的基礎,也是嚴格歌詞形式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這種容易廣為傳唱的寫作手法可謂在民歌運動時期廣為應用。如余光中作詞,羅大佑譜曲的《鄉愁四韻》,整潔而簡單的曲式一唱三嘆,每一段首行與末行旋律相似,首尾呼應,四個樂段相互獨立又反復演奏,形成一種回環復沓的音樂節奏,主題思想得以不斷深化,蕩氣回腸。
侯德健作詞的《龍的傳人》中,句間相互呼應,類似于連續問答但并非問答的形式,其呼應結構較為復雜隱蔽。問句并非提問,而是引出進一步解釋的語句,如此形成了巧妙的呼應。這種樸素整飭的結構形式是七○年代所熱衷的,特點是穩定規整,易于推進情緒,但也容易形成八股套路而不利創新。
(二)押韻——追求音韻回環的穩定美感
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在押韻上沒有太大突破,仍然推崇規整穩定的一韻到底,合轍押韻的節奏感適合表達校園歌曲的音樂美從而表情達意,王夢麟作詞的《雨中即景》采取隔行押韻的模式,韻腳“了”“跑”“好”“到”押“遙條韻”。葉佳修作詞的《鄉間小路》則一律江陽韻,幾乎每句都押韻且韻腳明顯。一韻到底與韻腳的反復出現,營造出一種極為傳統且易于傳唱的美感,并給人以富有規律的停頓感,如南方二重唱《想你的夜》采取“先天韻”。嚴格押韻的曲例不勝枚舉,成為七○年代歌曲的審美取向。
但歌詞用韻的方式很多,一韻到底的歌詞在結構上以內容情感展示音樂線索,而韻腳的變化則常常藏著情感的路線,會呼應出相應的音樂情感。例如席慕蓉作詞的《出塞曲》主歌前兩句為“姑蘇韻”,到了三四句即轉為“懷來韻”,而后邊則是“江陽韻”,韻腳由閉口音逐漸轉換為開口音,韻腳的改變形成了一種天然的轉折,要求音樂旋律以同樣的轉折相呼應,但這樣的作品仍是少數。
民歌運動中,許多選擇現代詩入詞的歌詞則不如純歌詞押韻,詩歌的形式更為自由,押韻并不是必須,席慕蓉《出塞曲》便是如此。再如三毛的歌詞便沿襲了詩歌這一押韻自由的模式,除《橄欖樹》與《軌外》外,其余作品均無明顯的韻腳或直接放棄押韻,如《曉夢蝴蝶》。由此可見,在追求押韻美感的同時,歌詞的選用更為自由。縱然口語化、律動穩定的歌曲在民歌運動中被大量創作普及,但歌詞也漸漸更重視表達完整獨立的詞意句意,而非完全依附音樂。
(三)句式結構整飭——鐘情于利用排比對偶的從容敘述
當今流行歌曲的歌詞字數長短錯落,再不像律詩一般整齊劃一,這更利于創作復雜多變的旋律與節奏。但現代民歌運動中的作品似乎更傾向于均等整齊的歌詞結構,在長短句的交錯中保持著規整的節奏。例如羅大佑作詞的《船歌》與賴西安作詞的《月琴》,相比于押韻,結構的整飭更為當時的創作者們所追崇,兩首歌詞韻腳明顯,在段落上運用對偶或排比的句式,段落之間字數相等、結構方正。另外在余光中《鄉愁四韻》《江湖上》等作品中此手法也被頻繁使用。如此的歌詞結構能夠不慌不忙地、連續地敘述一層統一含義,以追求一氣呵成娓娓道來連綿的美。在作曲上也方便寫作利于記憶的旋律,在重詞輕曲的現代民歌時代廣為運用。
(四)文本互涉——獨特的創作者構成
由于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大量引用文人作家的詩詞、散文作品入歌,遂無法避免歌詞中有與作家散文間狹義的文本關聯。法國后結構主義批評家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最早提出“文本互涉”的概念,指“不同文本之間進行結構或故事的互相模仿、也包括主題的相互關聯與暗合及引用”散。本節無意從廣義“互文”的領域探討三毛歌詞與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關系,僅指出三毛歌詞與其所作散文間狹義的文本關聯。
例如三毛的“自傳性”文字創作一直延伸到歌詞中,她的歌詞與散文一致,極具個人特色,其歌詞對于故事的二次敘述比散文更加凝練,情感爆發得更為熱烈。自傳性的歌詞濃縮了三毛回憶里最為精彩的片段,三毛發表的散文《惑》中“我”看了電影《珍妮的畫像》,不斷夢到“珍妮”,“我”十分渴望去找到珍妮,希望她帶“我”去那個空無一物的虛幻世界里,同時又想要逃離“珍妮”的縈繞。而電影中“珍妮”哼的歌曲,和三毛《橄欖樹》“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有著諸多相似。文本挪用的例子在三毛的作品中還有很多,如歌曲《沙漠》中三毛錄音的念白“那時,沙漠不再只是沙漠。而化為一口水井,井里,一雙水的眼睛”。該句念白化用自三毛偏愛的法國作家圣·艾克蘇佩里《小王子》。而三毛在《說給自己聽》文案中所寫的“寫到這首歌時只想到一條蛇,可以將我送去彼岸的蛇。”也是受到《小王子》故事的影響。歌曲《謎》講述了三毛童年時期的心靈對話,《七點鐘》《飛》則講述了她的初戀,相似的內容可以追溯到三毛的書作《雨季不再來》。《曉夢蝴蝶》《沙漠》《遠方》等關于德國未婚夫荷西以及沙漠的鄉愁訴說,則可在書作《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駱駝》中尋見。幾乎每一首歌都能在作者的演講、小說、散文中得到對應內容,這來源于現代民歌時期創作者構成成分的特殊性。雖為“民歌運動”,但創作人依然以高校學生、知識分子為主,他們最初接觸的文體并非歌詞,而是散文、詩歌與小說此類表達形式,遂文本互涉成為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歌詞的一大特點。
結 語
雖然最終因為臺灣官方文化的干預性治理,以及所謂“本土”并非真正閩南本土,而是借助了遙遠中華意象的原因,臺灣民歌未逃脫僵化的命運,但其精神內核仍有可取之處。本文通過歌詞的角度,分析了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時期的創作手法與藝術特征,望能引起更多人對臺灣現代民歌運動專題研究的關注,豐富對于中國臺灣音樂發展的認知。■
注釋:
① 重返61號公路.遙遠的鄉愁——臺灣現代民歌三十年[M].新星出版社,2007:3.
② 朱立元.美學大辭典[M].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③ 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