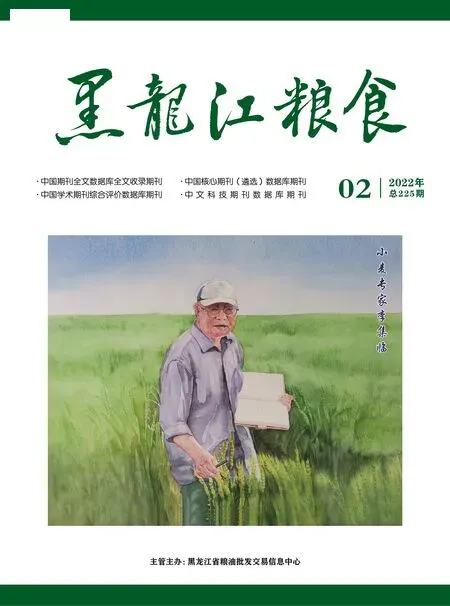加強(qiáng)生物安全是保障“大國糧安”的重要內(nèi)容
□ 丁聲俊
一、為什么必須高度重視生物安全問題
迄今,人們對生物安全問題還認(rèn)知甚少,對其嚴(yán)重危害性也認(rèn)知甚淺。然而,從全局和深遠(yuǎn)的視角出發(fā),生物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問題,已不單純是對人體健康、經(jīng)濟(jì)與科技的表面影響問題,而是已提升到攸關(guān)政治安全、經(jīng)濟(jì)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的戰(zhàn)略層面上至關(guān)重要的大事。當(dāng)下,必須高度重視生物安全問題,把加強(qiáng)生物安全提升為保障“大國糧安”的重要戰(zhàn)略地位。
所謂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現(xiàn)代生物技術(shù)開發(fā)和應(yīng)用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各種災(zāi)害或潛在威脅,以及對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預(yù)防和有力控制的措施。鑒于生物技術(shù)發(fā)展有可能產(chǎn)生多種負(fù)面影響,人們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由于在一般情況下,人類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要素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可以維系經(jīng)濟(jì)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的安全狀態(tài),因而使人們往往忽視生物安全的隱性風(fēng)險,成為包括經(jīng)濟(jì)、軍事、生態(tài)環(huán)境在內(nèi)的國家安全的一個重大隱患。致使生物安全已成為一個攸關(guān)世界安全與發(fā)展的基本問題。如今,許多國家和地區(qū)都把生物安全納入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乃至國家整體安全戰(zhàn)略。加之生物安全直接關(guān)系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發(fā)生和蔓延,關(guān)系天下蒼生與糧食安全,已成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一個重大因素,引發(fā)廣大民眾普遍關(guān)注。
隨著全球化進(jìn)程的加快,以及生物技術(shù)的進(jìn)步,生物安全的范圍越來越廣,其內(nèi)容主要包括:危險性病原物與人類身體健康安全,外來有害生物與生物多樣性減少及轉(zhuǎn)基因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安全和生物防恐等。其中每一項內(nèi)容都可擴(kuò)展為一個宏大的課題,如基因技術(shù)的安全性、遺傳資源的保護(hù)與利用、生物武器的控制、外來生物入侵、重大突發(fā)性疾病的防控,以及轉(zhuǎn)基因生物的跨國越境轉(zhuǎn)移等,都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體健康產(chǎn)生潛在的重大影響。當(dāng)然生物安全風(fēng)險首當(dāng)其沖的是會對農(nóng)業(yè)和糧食產(chǎn)業(yè)產(chǎn)生嚴(yán)重的負(fù)面效應(yīng)。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大國的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既是國民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產(chǎn)業(yè)和民生產(chǎn)業(yè),也是生態(tài)產(chǎn)業(yè)和風(fēng)險產(chǎn)業(yè)。這就意味著,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必然更多、更易遭受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范與化解重大突發(fā)性公共生物安全風(fēng)險,對于保障大國糧食安全和國家總體安全,是一項重之又重的大事。
然而,值得關(guān)注的是,我國面臨生物安全風(fēng)險的挑戰(zhàn)越來越嚴(yán)峻。在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豬瘟等動物烈性傳染病頻頻發(fā)生,給畜牧業(yè)生產(chǎn)造成嚴(yán)重?fù)p失和威脅。目前在我國流行或散發(fā)的動物疾病有200余種,各類疫病造成的直接經(jīng)濟(jì)損失每年超過1000億元。此外,農(nóng)業(yè)有害生物帶來的危害也非常嚴(yán)重。廣義地說,農(nóng)業(yè)有害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乃至病毒。像危害植物的各種害蟲、有害動物(蝸牛、螨類等)、病原微生物(真菌、細(xì)菌、放線菌病毒和線蟲等)和寄生性種子植物(菟絲子、槲寄生、桑寄生、列當(dāng)?shù)龋L镩g雜草因具有對栽培植物的侵害性,往往也包括在內(nèi)。全世界常年發(fā)生農(nóng)業(yè)有害生物1700余種,每年因有害生物給全球農(nóng)業(yè)糧食造成巨大損失。根據(jù)FAO的統(tǒng)計,因蟲害、病害和雜草危害造成的損失占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37%。其中,蟲害占14%;病害占12%;雜草占11%。目前,我國農(nóng)業(yè)糧食領(lǐng)域面臨的生物安全形勢也十分嚴(yán)峻,對農(nóng)業(yè)有害生物亟待加強(qiáng)管控和提高治理能力。我國必須大力加強(qiáng)對包括農(nóng)業(yè)糧食在內(nèi)的生物安全風(fēng)險的防范和監(jiān)管。
二、生物風(fēng)險給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造成危害的嚴(yán)重教訓(xùn)
生物安全風(fēng)險是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的重大隱患。它一旦暴發(fā),就必然對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帶來毀滅性災(zāi)害。一個多世紀(jì)以來,在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生了數(shù)以百計的嚴(yán)重生物安全事件,嚴(yán)重威脅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安全,威脅人類生活、生產(chǎn)和生存,乃至影響人類文明進(jìn)程,造成了重大歷史性災(zāi)難。
(一)誘發(fā)嚴(yán)重疫病,導(dǎo)致大量農(nóng)業(yè)勞動力喪失
農(nóng)業(yè)勞動力是指能參加農(nóng)業(yè)勞動的人力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農(nóng)業(yè)勞動力是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最活躍、最積極的要素和發(fā)展力量的源泉。它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因受自然、社會、經(jīng)濟(jì)等各種因素影響而處于不斷變化中。一個多世紀(jì)以來,在歐洲乃至世界歷史上疫情致使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口死亡,這意味著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勞動力的嚴(yán)重?fù)p失。且不說自古以來,在世界上暴發(fā)過一連串的瘟疫,造成無計其數(shù)的人口喪生。僅在1347—1353年,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就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無獨有偶,肆虐兩個世紀(jì)之久的黃熱病,造成美洲、非洲及歐洲部分地區(qū)的人口大量死亡,社會活動趨于癱瘓。19世紀(jì)的霍亂肆虐,橫掃全球,僅印度就有超過3800萬人死亡。1918年暴發(fā)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萬—4000萬人死亡,全球患病人數(shù)在5億以上。大量人口的死亡,不僅是眾多家庭的悲劇,而且使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慘遭厄運:大批農(nóng)業(yè)勞動力被瘟疫吞噬和奪走,致使廣袤的土地由于無人耕種而淪為不毛之地,農(nóng)業(yè)糧食生產(chǎn)凋敝,社會民眾掉進(jìn)饑荒的深淵。
(二)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嚴(yán)重破壞,直接危害農(nóng)糧生產(chǎn)
生態(tài)環(huán)境也是生產(chǎn)力。這一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chǎn)力理論的新發(fā)展。其精髓在于:一是糾正理論偏頗。強(qiáng)調(diào)發(fā)展與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相輔相成,在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中培育新產(chǎn)能。這是對以征服與改造自然為主旨,在“斗爭”中彰顯生產(chǎn)能力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力理論的糾偏。二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強(qiáng)調(diào)資源、環(huán)境、生態(tài)并重,意味著將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生產(chǎn)要素和內(nèi)生動力納入生產(chǎn)力范疇。這是對生產(chǎn)力理論的新發(fā)展。三是強(qiáng)調(diào)與民生相融合。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優(yōu)良,成為生產(chǎn)力健康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生動力。這是對生產(chǎn)力內(nèi)涵的新拓展。把上述集中到一點就是,生態(tài)環(huán)境也是重要生產(chǎn)要素。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保護(hù)生產(chǎn)力;損害生態(tài)環(huán)境就是破壞生產(chǎn)力。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則農(nóng)業(yè)糧食興;生態(tài)環(huán)境劣,則農(nóng)業(yè)糧食衰。進(jìn)入近代以來,產(chǎn)生的環(huán)境污染直接對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發(fā)展帶來了嚴(yán)重負(fù)面后果。
(三)外來入侵物種導(dǎo)致生物多樣性減少
外來物種是指那些出現(xiàn)在過去或現(xiàn)在的自然分布范圍及擴(kuò)散潛力以外的物種、亞種或以下的分類單元,包括所有可能存活、繼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體。目前,世界上外來物種入侵或傳入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人為有意引進(jìn)。包括人們出于農(nóng)林牧漁業(yè)生產(chǎn)、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生態(tài)保護(hù)、觀賞等目的有意引進(jìn)某些物種。二是人類無意傳播。主要包括隨交通工具帶入,像豚草隨農(nóng)產(chǎn)品的國際貿(mào)易帶入;像假高粱隨進(jìn)口糧食夾帶傳入;隨動植物引種帶入,像毒麥隨進(jìn)口種子傳入等等。三是通過自身繁殖擴(kuò)散和風(fēng)力、水流、動物等途徑進(jìn)行的自然擴(kuò)散。外來入侵物種具有生態(tài)適應(yīng)能力強(qiáng)、繁殖能力強(qiáng)和傳播能力強(qiáng)等“三強(qiáng)”特點。與此相對照,被入侵生態(tài)系統(tǒng)擁有可供利用的資源但又缺乏自然控制機(jī)制,因而形成外來物種入侵頻率高現(xiàn)象,對本土生物形成嚴(yán)重威脅,甚至成為公害,人類的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在自然界長期的進(jìn)化過程中,生物與生物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協(xié)調(diào),并將各自的種群限制在一定的環(huán)境和數(shù)量范圍內(nèi),形成了穩(wěn)定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但當(dāng)一種外來生物侵入并在脫離了人為控制后,就會在當(dāng)?shù)氐臍夂颉⑼寥馈⑺旨皞鞑l件下野蠻擴(kuò)散,形成大面積“單優(yōu)群落”,從而打破原有的生態(tài)平衡,造成極大的負(fù)面影響。迄今,外來物種的入侵已經(jīng)成為一大危害。
這里,以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維多利亞湖失去生態(tài)平衡為實例進(jìn)行簡要分析。這座湖地處坦桑尼亞、烏干達(dá)和肯尼亞交界處,是這三個非洲人口大國的“母親湖”,也是非洲土地最肥沃、電力最充足的地區(qū)。湖中生長魚類品種多達(dá)600余個,絕大部分屬獨有品類。后來遭尼羅河羅非魚和鱸魚,以及巴西水葫蘆(鳳眼蓮)等兩大物種入侵,使維多利亞湖生態(tài)鏈遭到難以挽回的破壞:魚類減少80%,物種滅絕60%,鳥類滅絕35%。湖水面積從百年前的6.9萬平方公里縮小到5.9萬平方公里,縮小了1萬多平方公里。本土魚類被滅絕的多達(dá)500余種,連甲殼軟體類動物和鳥類也難逃一劫。
(四)轉(zhuǎn)基因食品安全性潛存風(fēng)險
轉(zhuǎn)基因食品指的是利用轉(zhuǎn)基因生物技術(shù)獲得的轉(zhuǎn)基因生物品系,并以該轉(zhuǎn)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或為原料加工生產(chǎn)的食品,均稱為轉(zhuǎn)基因食品。根據(jù)轉(zhuǎn)基因食品來源的不同,可劃分為植物性轉(zhuǎn)基因食品、動物性轉(zhuǎn)基因食品與微生物性轉(zhuǎn)基因食品。目前,世界上涉及轉(zhuǎn)基因食品或轉(zhuǎn)基因食品原料的有:轉(zhuǎn)基因大豆、轉(zhuǎn)基因玉米、轉(zhuǎn)基因番茄、轉(zhuǎn)基因油菜、轉(zhuǎn)基因馬鈴薯等。如今轉(zhuǎn)基因食品已經(jīng)逐步進(jìn)入一些國家民眾的日常生活。因為食品與人類健康息息相關(guān),所以人們對于轉(zhuǎn)基因技術(shù)在農(nóng)業(yè)糧食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極為關(guān)注,尤其是轉(zhuǎn)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為廣大消費者關(guān)注的熱點。
迄今,世界上對轉(zhuǎn)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沒有定論。支持者推崇轉(zhuǎn)基因食品是解決糧食安全的“突破之路”;但是反對者特別是廣大百姓對轉(zhuǎn)基因食品的潛在危險性始終存在疑慮。許多專家學(xué)者以事實論證,轉(zhuǎn)基因生物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體健康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一是轉(zhuǎn)基因生物既對害蟲和病菌發(fā)揮抑止作用,也對非目標(biāo)生物、有益生物等產(chǎn)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危害;二是轉(zhuǎn)基因生物會增強(qiáng)目標(biāo)害蟲的抗性;三是轉(zhuǎn)基因生物可能造成雜草蔓延;四是轉(zhuǎn)基因生物危及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環(huán)境;五是轉(zhuǎn)基因生物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威脅。2001年7月9日,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也公開承認(rèn),轉(zhuǎn)基因食品可能會破壞生態(tài)平衡。有關(guān)轉(zhuǎn)基因食品的潛在危險和安全性的許多問題,有待于進(jìn)一步研究才能下結(jié)論。
正是由于轉(zhuǎn)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沒有定論,所以迄今世界上大量國家不接受這種有爭議的作物,即采取禁止種植轉(zhuǎn)基因作物。日本民眾非常強(qiáng)烈地反對種植轉(zhuǎn)基因食品作物,在日本的國土上至今沒有種植轉(zhuǎn)基因的種子。在愛爾蘭,所有轉(zhuǎn)基因食用作物都被禁止種植,對含有轉(zhuǎn)基因原料的食品實行標(biāo)簽制度。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希臘、保加利亞和盧森堡等國禁止轉(zhuǎn)基因食用作物的種植和銷售。有一些國家通過禁令,不得種植轉(zhuǎn)基因作物或者飼養(yǎng)轉(zhuǎn)基因動物。有些國家雖然允許種植部分轉(zhuǎn)基因作物,然而公眾普遍不信任。更有許多國家法定對轉(zhuǎn)基因食品必須加標(biāo)識。鑒于上述,我國對轉(zhuǎn)基因食品一定要保持科學(xué)態(tài)度,要提高消費者知情度和消費自由度。
三、我國農(nóng)業(yè)糧食面臨生物風(fēng)險的嚴(yán)峻挑戰(zhàn)
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農(nóng)業(yè)糧食生產(chǎn)大國、貿(mào)易大國和消費大國。在看到我國具備多種優(yōu)勢條件的同時,還必須清醒認(rèn)識我國糧食安全隱伏的風(fēng)險,正視面臨的嚴(yán)峻形勢,即堅持底線思維。從中長期看,我國作為糧食大國還存在系統(tǒng)性、結(jié)構(gòu)性問題,集中表現(xiàn)出“八大挑戰(zhàn)”:一是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壓力呈加重態(tài)勢;二是人均耕地、淡水資源數(shù)量趨減,資源承載壓力越來越沉重;三是全國人口逐年增長和消費剛性增長的趨勢,使中長期的糧食供求呈“緊平衡”態(tài)勢;四是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處于成本上升期,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基本上都高出國際市場價格,減弱了在國內(nèi)外市場上的競爭力;五是糧食比較效益較低,糧食生產(chǎn)和農(nóng)業(yè)收入占農(nóng)戶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較低,導(dǎo)致農(nóng)民生產(chǎn)糧食的意愿不高、生產(chǎn)積極性下降;六是農(nóng)民組織化程度低,小農(nóng)生產(chǎn)者占絕大部分,不僅其規(guī)模效益低下,而且抵御自然災(zāi)害的能力薄弱;七是農(nóng)業(yè)糧食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弱,尤其是作為農(nóng)業(yè)糧食生產(chǎn)“芯片”的優(yōu)良品種的培育處于劣勢,必須急起直追;八是外來入侵有害生物造成多種危害,威脅農(nóng)業(yè)糧食可持續(xù)發(fā)展。
關(guān)于我國農(nóng)業(yè)糧食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已有多種深入的論述。本文著重闡述人們關(guān)注不多的生物安全、特別是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的挑戰(zhàn)。生態(tài)系統(tǒng)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間內(nèi),生物與環(huán)境構(gòu)成的統(tǒng)一整體。在這個統(tǒng)一的整體中,生物與環(huán)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并在一定時期內(nèi)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動態(tài)平衡狀態(tài)。保持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是攸關(guān)農(nóng)業(yè)糧食興衰的要舉。當(dāng)前,多種干擾壓力導(dǎo)致我國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系統(tǒng)嚴(yán)重退化、沙化和鹽堿化。與此相伴隨,必然帶來一系列消極影響:生態(tài)功能減弱或喪失;生態(tài)效益和社會效益降低;生物多樣性降低;生產(chǎn)力下降;基本結(jié)構(gòu)和功能破壞或喪失,以及“抗逆”能力下降。特別是對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帶來嚴(yán)重禍患,包括土地、草原、森林和水域等主要領(lǐng)域的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受到多種干擾壓力而失衡,構(gòu)成國家糧食安全的隱患。
(一)作為農(nóng)業(yè)糧食基礎(chǔ)資源的土地,生態(tài)系統(tǒng)趨于退化
土地生態(tài)系統(tǒng),也稱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耕地是國土中的精華,是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的基本要素。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嚴(yán)重的環(huán)境污染、劇烈的氣候變化,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與田間管理方法,造成我國耕地資源稟賦趨于劣化:土地面源污染蔓延,土壤肥力趨于下降,酸化和鹽漬化面積大幅擴(kuò)展。為片面追求農(nóng)業(yè)糧食高產(chǎn),過度不合理使用化肥和田間除草劑、殺蟲劑等農(nóng)藥。然而,我國化肥肥料利用率低,使用結(jié)構(gòu)不合理,造成巨大浪費。所謂肥料利用率是指當(dāng)季作物從所施肥料中吸收的某一養(yǎng)分占肥料中該養(yǎng)分總量的比例。肥料利用率是衡量施肥效果的主要指標(biāo),目前我國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氮肥、磷肥和鉀肥當(dāng)季平均利用率分別為33%、24%、42%。其中,小麥氮肥、磷肥、鉀肥利用率分別為32%、19%、44%,水稻氮肥、磷肥、鉀肥利用率分別為35%、25%、41%,玉米氮肥、磷肥、鉀肥利用率分別為32%、25%、43%。目前我國主要糧食作物肥料利用率水平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這表明我國在化肥利用領(lǐng)域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我國當(dāng)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的肥料利用率是多少?》,《微生物肥料圈》,2018年9月9日)。眾所周知,我國耕地總量占世界第三位,然而化肥和農(nóng)藥的使用量長期保持世界首位,兩者的使用總量占全世界使用總量的30%以上。這不僅造成嚴(yán)重浪費,而且是我國面源污染的主要根源。
由于化肥、農(nóng)藥等化學(xué)物的過量使用形成的有害殘留物快速積累,加速了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與物種滅絕,從而引起食物鏈斷裂和農(nóng)作物病蟲害暴發(fā)幾率的提高。上述種種危害,不僅使我國耕地資源稟賦退化,而且也使土地面積明顯減少。目前全國人均耕地面積已縮減到1.5畝以下,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的一半。
(二)作為重要國土資源的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普遍退化
草原是重要的國土資源,也是現(xiàn)代畜牧業(yè)基礎(chǔ)條件。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以各種草本植物為主體的生物群落與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環(huán)境構(gòu)成的功能統(tǒng)一體。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在其結(jié)構(gòu)、功能過程等方面與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它不僅是我國重要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基地,而且是重要的生態(tài)屏障。長期以來,由于對草地的掠奪式開發(fā),亂開濫墾、過度樵采和長期超載過牧,導(dǎo)致全國草原嚴(yán)重退化。其主要表現(xiàn)包括:一是草原植被疏落,產(chǎn)草量下降;二是牧草質(zhì)量劣化,可食性牧草減少,毒草和雜草增加,使牧場的使用價值下降;三是草原退化、沙化,導(dǎo)致氣候惡化,許多地方的大風(fēng)日數(shù)和沙塵暴次數(shù)逐漸增加;四是草原牧區(qū)鼠害加劇,使草場慘遭破壞而失去使用價值。鼠害的發(fā)生,既是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失調(diào)的惡果,也是造成草原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一步惡化的原因之一。草原退化、堿化和沙化,氣候惡化,以及嚴(yán)重的鼠害等一系列生態(tài)問題,都嚴(yán)重?fù)p害了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的生物安全。這是對草原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生態(tài)惡果。
(三)作為“地球之肺”的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明顯退化
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一個復(fù)雜的巨系統(tǒng),具有以下特征:生物種類豐富,層次結(jié)構(gòu)較多,食物鏈較復(fù)雜,光合生產(chǎn)率較高,所以生物生產(chǎn)能力也較高。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分布在較濕潤的地區(qū),在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具有調(diào)節(jié)氣候、涵養(yǎng)水源、保持水土、防風(fēng)固沙、消除污染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被稱為“綠色水庫”、“地球之肺”。
在新發(fā)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實施林業(yè)發(fā)展和生態(tài)建設(shè)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效:森林總量持續(xù)增長,森林質(zhì)量不斷提高,天然林穩(wěn)步擴(kuò)大,人工林快速發(fā)展。然而,在一定的自然因素、人為因素或兩者的共同干擾下,會發(fā)生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表現(xiàn)出如下消極現(xiàn)象:服務(wù)功能減弱或喪失;生態(tài)效益和社會效益減小;生物多樣性降低;生產(chǎn)力下降;基本結(jié)構(gòu)和功能破壞或喪失;穩(wěn)定性和“抗逆”能力減弱等,導(dǎo)致森林生態(tài)功能嚴(yán)重弱化。
一是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面臨的挑戰(zhàn)巨大。我國總體上仍然是一個缺林少綠、生態(tài)脆弱的國家。森林覆蓋率遠(yuǎn)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積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森林資源總量不足、質(zhì)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
二是嚴(yán)守林業(yè)生態(tài)紅線面臨的壓力巨大。隨著城市化、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加速,生態(tài)建設(shè)的空間被不斷擠壓,嚴(yán)守林業(yè)生態(tài)紅線,維護(hù)國家生態(tài)安全底線的壓力日益加大。
三是森林產(chǎn)品供求矛盾巨大。目前,我國現(xiàn)有用材林中可采面積僅占13%,可采蓄積僅占23%,可利用資源少,木材供需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很突出。同時,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脆弱、森林生態(tài)產(chǎn)品短缺的狀況依然突出,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四)廣闊水域系統(tǒng)功能日益退化
所謂水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是指在水域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環(huán)境共同組成的、以水為基質(zhì)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它與人類生活、生產(chǎn)息息相關(guān),是整個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發(fā)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長期以來,在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干擾下,我國水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漸失平衡,即逐漸退化。先說前者自然因素,例如湖泊富營養(yǎng)化促使水質(zhì)變壞,藻類過度生長產(chǎn)生毒素,以及藻類殘體分解時消耗大量溶解氧,導(dǎo)致魚類及其他水生生物死亡。再說后者人為因素,像在魚類洄游通道上攔河筑壩、使魚類無法溯河或降海產(chǎn)卵繁殖等。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又往往互相結(jié)合、互為因果、共同干擾,導(dǎo)致水域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其主要表現(xiàn)包括:
一是數(shù)量萎縮。據(jù)第二次湖泊調(diào)查,近50年來,我國湖泊數(shù)量減少了243個,面積縮減9606平方千米,約占湖泊總面積的12%。最新一次濕地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近10年來,全國濕地面積減少了3.4萬平方千米,減水率達(dá)8.82%,儲水量銳減。湖泊和濕地面積持續(xù)縮減,成為我國近期面積喪失速度最快的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
二是水質(zhì)惡化。我國水污染的廣度、深度和頻度表明,水域污染屬于嚴(yán)重類型。例如,五大淡水湖,除了洞庭湖目前處于中營養(yǎng)水平外,其他鄱陽湖、太湖、洪澤湖和巢湖均處于富營養(yǎng)化狀態(tài)。在遼闊的西北部的湖泊,普遍呈咸化、堿化,水質(zhì)趨于劣化。
三是稟賦下降。湖泊和濕地,與森林、海洋并稱為世界三大生態(tài)系統(tǒng)。與水域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相對照,其稟賦也不斷減退,湖泊魚類資源種類減少、數(shù)量縮小、生物多樣性下降。
(五)大量外來有害生物入侵造成極大危害
中國是幅員遼闊、自然條件復(fù)雜的國家,又是農(nóng)業(yè)、糧食、牧業(yè)和漁業(yè)大國,因而是全球生物物種特別豐富的國家,占世界第八位,在生物多樣性保護(hù)行動中舉足輕重。我國國土上蘊藏著的豐富生物資源,是大自然的寶貴財富,對生物多樣性的開發(fā)利用具有極大的經(jīng)濟(jì)和科學(xué)價值。隨著國際貿(mào)易和人員往來日益頻繁,以及旅游業(yè)和物流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外來物種入侵我國的數(shù)量不斷增多,范圍越來越廣。特別是農(nóng)業(yè)糧食有害生物侵入并擴(kuò)展各地,危害加重。迄今全國34個省(區(qū)、市)均有外來入侵生物,可以說已經(jīng)遍及全國。據(jù)生態(tài)環(huán)境部發(fā)布的《2020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狀況公報》,全國已發(fā)現(xiàn)660多種外來物種入侵我國。其中,有71種對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已造成或具有潛在威脅并被列入《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69個國家級自然保護(hù)區(qū)已有219種外來入侵物種,其中48種被列入《中國外來入侵物種名單》。
外來物種入侵已經(jīng)給入侵地區(qū)帶來嚴(yán)重?fù)p害:一是外來入侵物種會改變侵入地的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降低物種多樣性,進(jìn)而對當(dāng)?shù)厣鐣⑽幕犬a(chǎn)生消極影響。二是外來物種對人類健康可能構(gòu)成直接威脅。一個典型實例是豚草花粉,成為人類變態(tài)反應(yīng)癥(過敏性)的主要致病源之一,所引起的“枯草熱”,對許多國家的人體健康產(chǎn)生了極大危害。三是外來入侵動植物直接危害當(dāng)?shù)剞r(nóng)林等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它們會對農(nóng)田、園藝、草坪、森林、畜牧、水產(chǎn)等造成直接危害。四是外來生物入侵會改變當(dāng)?shù)厣鷳B(tài)系統(tǒng),給當(dāng)?shù)厮痢夂虻葞硪幌盗胸?fù)面影響,還會導(dǎo)致各種間接損失。五是外來入侵物種帶來直接和間接的經(jīng)濟(jì)危害。《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報道顯示,在歐洲,每年外來物種的入侵造成至少12億歐元的損失。而外來入侵物種專家小組(ISSG)的主席皮耶羅說,12億歐元的數(shù)字偏低,因為這個數(shù)字不包括外來物種對本地物種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大量事實表明,農(nóng)業(yè)糧食有害生物入侵已成為世界的公害。
(六)整個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弱化。
綜上所述,自然環(huán)境是環(huán)繞人們周圍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如大氣、水、植物、動物、土壤、巖石礦物等。它們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基礎(chǔ)。通常把這些因素劃分為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巖石圈等五個自然圈。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nèi),依靠自然調(diào)節(jié)能力維持的相對穩(wěn)定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如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海洋生態(tài)系統(tǒng)等。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可以分為:水生生態(tài)系統(tǒng),即以水為基質(zhì)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陸生生態(tài)系統(tǒng),即以陸地土壤或母質(zhì)等為基質(zhì)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常常趨向于達(dá)到一種平衡狀態(tài),這是靠自我調(diào)節(jié)過程來實現(xiàn)的。不過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是有限度的。由于人類的強(qiáng)大作用,絕對未受人類干擾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已經(jīng)沒有了。這意味著生態(tài)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遭破壞,功能受阻礙,甚至整個系統(tǒng)崩潰,生態(tài)平衡失調(diào)。由此產(chǎn)生的危害是廣泛而深重的,值得人類高度警惕。
事實敲響了警鐘。我國土地生態(tài)系統(tǒng)、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水域生態(tài)系統(tǒng),出現(xiàn)了普遍性退化,加之大量外來有害生物入侵造成的嚴(yán)重危害,致使我國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嚴(yán)重減弱,造成了系統(tǒng)性、頻發(fā)性、普發(fā)性生態(tài)危害和生態(tài)災(zāi)難:一是危害資源。首當(dāng)其沖造成農(nóng)業(yè)糧食生產(chǎn)的稀缺資源(如耕地等)或永久性喪失、或稟賦降低。二是破壞森林。森林被亂砍濫伐,林地大面積縮減,致使我國仍然處于“缺樹少緑”狀態(tài)。三是干旱頻發(fā)。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導(dǎo)致干旱災(zāi)害頻發(fā),土地沙漠半沙漠化現(xiàn)象嚴(yán)重,其面積快速擴(kuò)展,甚至暴發(fā)危害極其嚴(yán)重的沙塵暴。四是水土流失。在水流作用下,特別是人類錯誤行為嚴(yán)重破壞了坡地植被后,由自然因素引起了地表土壤破壞和土地物質(zhì)移動,即普遍發(fā)生的水土流失。五是大氣污染。形成酸雨危害農(nóng)田,同時有毒氣體危害大氣,引起人們呼吸道疾病,危害人類生命健康。六是水域污染。江河湖泊水質(zhì)變劣,甚至江河斷流干枯,危害水生物生長等。七是危害生物生長。致使生物多樣性減少。八是固體污染物成災(zāi)。有害生活垃圾和農(nóng)業(yè)白色垃圾不僅污染生活環(huán)境,而且破壞土壤結(jié)構(gòu)和功能。這些不可忽視的問題警示人們:是時候了,必須從戰(zhàn)略高度大力加強(qiáng)生物安全建設(shè)。
四、加強(qiáng)生物安全系統(tǒng)現(xiàn)代治理和保障能力
面對“兩個大變局”和疫情大沖擊的嚴(yán)峻形勢,當(dāng)今中國確保“大國糧安”格外艱巨復(fù)雜,也格外重要和必要。歷史的教訓(xùn),嚴(yán)峻的挑戰(zhàn),敲響了長鳴的警鐘!聲聲警示人們:在糧食安全有保障、形勢好時,要堅持底線思維,化挑戰(zhàn)為動力,補(bǔ)短板增實力,切戒放松糧食安全之“弦”,加強(qiáng)實施糧食戰(zhàn)略定力,推動生物安全建設(shè),促進(jìn)生態(tài)發(fā)展、綠色發(fā)展,更高質(zhì)量、更高水平、更有把握地確保“大國糧安”。另外,從憂患意識、底線思維出發(fā),在客觀看到我國是糧食大國、并具有多種優(yōu)勢的同時,還必須正視我國農(nóng)業(yè)糧食“大而不強(qiáng)”、以及存在多種“短板”的狀況,尤其是面臨嚴(yán)峻的生物安全風(fēng)險。為保障“大國糧安”,必須從建立和完善制度入手、切實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生物安全現(xiàn)代治理和保障能力。
(一)提高思想認(rèn)識是先導(dǎo)
思想決定行動,行動決定結(jié)果。強(qiáng)化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生物安全建設(shè)要以“思想建設(shè)”為先導(dǎo)和保證。面對“兩個大變局”和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嚴(yán)峻挑戰(zhàn),建立并完善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系統(tǒng)現(xiàn)代治理和保障體系是重要新舉措,也是一項重大新任務(wù)。為此,必須“提高思想,強(qiáng)化認(rèn)識”,即提高對保障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重要戰(zhàn)略意義的認(rèn)識。隨著全球化進(jìn)程的加快,以及生物技術(shù)的進(jìn)步,生物安全已成為一個攸關(guān)世界安全與發(fā)展的基本問題,涉及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科技、文化和社會等多領(lǐng)域。我國是一個有著14億多人口的大國,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風(fēng)險,始終是一刻也不可放松的大事。保障生物安全對于保障國家總體安全而言,占有重要戰(zhàn)略地位和作用。要站在保障“大國糧安”、保護(hù)人民健康、維護(hù)國家安全和長治久安的戰(zhàn)略高度,進(jìn)一步深化對保障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系統(tǒng)戰(zhàn)略意義的認(rèn)識,并有針對性地采取必要措施,堅持農(nóng)業(yè)糧食高質(zhì)量發(fā)展,堅持生態(tài)發(fā)展、綠色發(fā)展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歸根結(jié)底,要把糧食安全新戰(zhàn)略“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科技支撐,擴(kuò)大產(chǎn)能,適度進(jìn)口”,以及新舉措“黨政同責(zé)”貫徹落實好。
(二)制定頂層設(shè)計和規(guī)劃是關(guān)鍵
從國家總體安全的角度出發(fā),制定好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控和治理頂層設(shè)計和規(guī)劃,是重要關(guān)鍵。這就要求整體統(tǒng)籌,綜合運用新技術(shù)、新理念和新模式,特別是要著力加強(qiáng)數(shù)字化治理和能力,形成與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相適應(yīng)的智能感知、精細(xì)管理、科學(xué)決策、高效服務(wù)的數(shù)字化治理能力和便捷化服務(wù)能力,支撐生物安全建設(shè)。
鑒于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的來源多、時空廣、頻譜全,必須多管齊下應(yīng)對挑戰(zhàn)。包括從國家戰(zhàn)略高度進(jìn)行整體謀劃,全盤考慮,全域防御,進(jìn)行系統(tǒng)性、全譜性的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控和治理的戰(zhàn)略設(shè)計和戰(zhàn)略規(guī)劃。對其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問題進(jìn)行戰(zhàn)略部署,明確維護(hù)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的路線圖,為其風(fēng)險防控和治理提供行動指南。同時,整合國家各方面的力量,加強(qiáng)對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的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和布局,建立科學(xué)高效的風(fēng)險應(yīng)對計劃和應(yīng)急機(jī)制;堅持平時和戰(zhàn)時結(jié)合、預(yù)防和應(yīng)急結(jié)合、科研和防控結(jié)合,提高體系化對抗能力和水平。加強(qiáng)戰(zhàn)略謀劃和前瞻布局,完善生物安全防控預(yù)警、預(yù)測機(jī)制以及應(yīng)對舉措。
(三)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是根本
為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體系的目標(biāo),必須采取重要措施,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第一,加強(qiáng)國家集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鑒于健全和完善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體系防控和治理,涉及部門多、領(lǐng)域廣,攸關(guān)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等多個方面,具有多學(xué)科、多領(lǐng)域交叉的特點,所以必須加強(qiáng)集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第二,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制度建設(shè)。包括決策咨詢制度、應(yīng)急預(yù)演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進(jìn)出口的安全風(fēng)險防范與控制制度、生物安全的國家報告制度等。第三,建立健全預(yù)警監(jiān)管機(jī)制。完善的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預(yù)防、評估和預(yù)警機(jī)制,能降低和減少生物安全事件發(fā)生的突然性。為此建立預(yù)警監(jiān)管機(jī)制是必要措施,主要內(nèi)容包括:預(yù)防預(yù)警生物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成災(zāi)等態(tài)勢分析,預(yù)測預(yù)警措施以及篩選優(yōu)化應(yīng)對策略;健全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的審查和監(jiān)管機(jī)制,從源頭上預(yù)防和化解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第四,健全完善防控和監(jiān)管體系。重點包括兩方面:一方面要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控和治理的裝備技術(shù)體系。當(dāng)前要大力提高科技在維護(hù)糧食生物安全中的作用,為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控和治理提供強(qiáng)大的技術(shù)支撐。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管控體系。主要包括建立生物安全防控管理組織結(jié)構(gòu),完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提高生物安全防范支撐條件,提供生物安全設(shè)施裝備和配套設(shè)備,加強(qiáng)生物安全監(jiān)督,以及建立和加強(qiáng)突發(fā)事件應(yīng)對能力。總之,要積極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體制和創(chuàng)新機(jī)制,并充分發(fā)揮其優(yōu)勢,從根本上確保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
(四)推進(jìn)科技創(chuàng)新是強(qiáng)大動力
21世紀(jì)是生物學(xué)的世紀(jì)。方興未艾的生命科學(xué)、生物科技等領(lǐng)域發(fā)展迅猛,但離不開強(qiáng)大的科技實力的支撐。同樣,筑牢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防線,科技創(chuàng)新手段必不可少。也就是說,推進(jìn)科技創(chuàng)新,筑牢包括農(nóng)業(yè)糧食在內(nèi)的國家生物安全防線具有極大必要性和迫切性。當(dāng)前,首先要優(yōu)化科技創(chuàng)新模式。通過政府引導(dǎo)投資、各類型企業(yè)融合等方式加大對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領(lǐng)域的投入,引進(jìn)高新技術(shù)人才,開展戰(zhàn)略前瞻性研究,培育壯大生物安全科技企業(yè),提升其核心競爭力,搶占國際生物技術(shù)制高點。其次要培育專業(yè)科技人才隊伍。要從基礎(chǔ)教育入手,培養(yǎng)、儲備一批生物安全領(lǐng)域的人才,并廣納海內(nèi)外英才,造就一支高素質(zhì)隊伍,讓中國成為生物技術(shù)人才培養(yǎng)的新高地。再次要加強(qiáng)科研攻關(guān)。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重大科技成果,是確保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體系之重器。從加強(qiáng)能力建設(shè)入手,大力進(jìn)行科研攻關(guān)。與此相應(yīng),要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科研攻關(guān)體系和能力建設(shè),完善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攻關(guān)的創(chuàng)新型體制和機(jī)制,加快推進(jìn)生物安全領(lǐng)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相關(guān)領(lǐng)域國家重點科研體系;加快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攻關(guān),以科技創(chuàng)新為動力,筑牢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防線。總之,要從保護(hù)人民健康、保障國家整體安全、維護(hù)國家長治久安的全局高度,有力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糧食生物安全現(xiàn)代治理能力的科技支撐。
(五)建立健全法律法規(guī)體系保障
從保護(hù)人民健康、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維護(hù)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出發(fā),必須盡快制定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gòu)建包括農(nóng)業(yè)糧食在內(nèi)的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guī)體系、制度保障體系。要立足于國內(nèi)和國際“兩個實際”,明確立法目的、主要內(nèi)容和適用范圍;加強(qiáng)體制協(xié)調(diào)、確立基本原則;構(gòu)建法律制度體系、創(chuàng)新法律機(jī)制,設(shè)計法律責(zé)任,以及公眾參與和社會監(jiān)督,促進(jìn)國際生物安全的交流和合作、促進(jìn)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shè)、促進(jìn)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當(dāng)前需要加快構(gòu)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guī)體系和制度保障體系,
從國家糧食安全的戰(zhàn)略高度,加強(qiáng)糧食的科學(xué)、規(guī)范、高效的生物安全法律防線。第一,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進(jìn)程,構(gòu)建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的完備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第二,建立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的管理制度體系,包括監(jiān)測預(yù)警體系、標(biāo)準(zhǔn)體系、名錄清單管理體系、信息共享體系、風(fēng)險評估體系、應(yīng)急體系以及決策技術(shù)咨詢體系等。第三,加強(qiáng)保障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能力,加大人、財、物的投入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第四,強(qiáng)化源頭管控,嚴(yán)防外來有害生物“偷渡”入境。要按照底線思維、源頭預(yù)防、綜合治理、全民參與的原則,抓好防控工作。強(qiáng)化源頭管控,把好外來物種引入、國門防控、國內(nèi)調(diào)運檢疫三大關(guān)口。第五,在全社會普及生物安全及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安全體系基礎(chǔ)知識,培養(yǎng)公眾維護(hù)生物安全、要從自身做起的意識,養(yǎng)成良好、科學(xué)的工作和生活習(xí)慣。還要時刻關(guān)注外來生物對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和公眾健康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第六,強(qiáng)化法治保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嚴(yán)格依法管理,堵塞漏洞,防止生物技術(shù)被濫用,將生物安全風(fēng)險降至最低。
五、結(jié)論
面對“兩個大變局”和疫情大沖擊的嚴(yán)峻形勢,當(dāng)今中國確保“大國糧安”格外艱巨復(fù)雜,也格外重要和必要。它緊緊關(guān)系國家經(jīng)濟(jì)安全、乃至國家整體安全。然而在歷史進(jìn)入到21世紀(jì)的今天,包括社會、經(jīng)濟(jì)、科技與大自然在內(nèi)的客觀環(huán)境發(fā)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需要站在新時代的高度,把生物安全建設(shè)提上重要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物安全建設(shè)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然而,包括農(nóng)業(yè)糧食的生態(tài)體系在多種干擾壓力下趨于退化,以及多種外來有害物種入侵,使得保障“大國糧安”也面臨著新風(fēng)險和新挑戰(zhàn)。當(dāng)前,傳統(tǒng)生物安全問題和新型生物安全風(fēng)險相互疊加,境外生物威脅和內(nèi)部生物風(fēng)險交織并存,致使生物安全風(fēng)險呈現(xiàn)出許多新情況和新特點。新時代在呼喚,生物安全關(guān)乎“大國糧安”,關(guān)乎國家長治久安,關(guān)乎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它已成為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把加強(qiáng)生物安全建設(shè)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其現(xiàn)代治理體系,提高其現(xiàn)代治理能力,以牢牢穩(wěn)住我國糧食安全“壓艙石”。
面向未來,我國必須大興生態(tài)革命,促進(jìn)綠色發(fā)展和持續(xù)發(fā)展;大力加強(qiáng)國家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shè),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包括農(nóng)業(yè)糧食產(chǎn)業(yè)在內(nèi)的國家生物安全屏障。具體包括:盡快制定和實施生物安全法;確立保障生物安全的體制機(jī)制;建立風(fēng)險監(jiān)測預(yù)警、風(fēng)險調(diào)查評估、信息共享等基本制度,構(gòu)建起生物安全風(fēng)險防控的“四梁八柱”。同時,要大力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和科技攻關(guān),系統(tǒng)提升保障我國生物安全的科技支撐能力。采取這些重要措施,將會有力推動我國提高農(nóng)業(yè)糧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治理能力,對于立足現(xiàn)階段、貫徹新理念、構(gòu)建發(fā)展新格局,以及確保“大國糧安”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