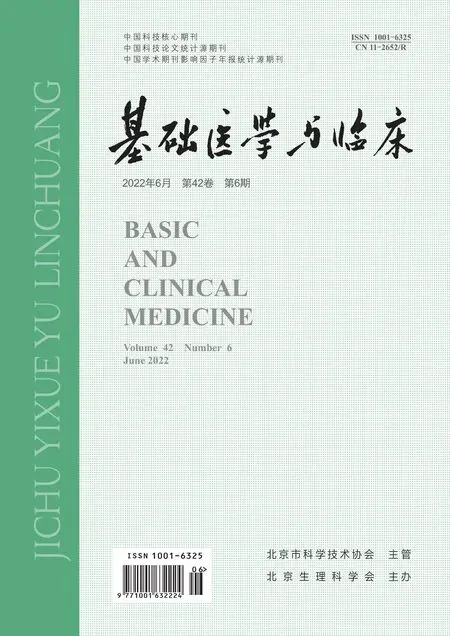飲食作用的腸道菌群-免疫軸與高血壓相關性的研究進展
王振花,李潮生
(深圳市寶安區人民醫院 心血管內科,深圳 518000)
高血壓(hypertension)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險因素之一,受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飲食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環境因素。腸道菌群(gut microbiota)是指人體胃腸道內存在的數量巨大的微生物的總稱,其數量高達380萬億個,所攜帶的基因數量約為900萬個,猶如一個置于宿主腸道內的“微生物器官”。飲食對腸道菌群結構及功能的影響,以及與人體健康的關系是研究的熱門領域。越來越多研究證實腸道菌群與高血壓密切相關,腸道菌群可能在飲食調控血壓中起關鍵作用。近10年來,免疫反應在高血壓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得到證實,基于腸道菌群在調節人體免疫穩態的重要作用,飲食調控血壓的機制可能與腸道菌群調控免疫有關。本文就飲食作用的腸道菌群-免疫與高血壓發生發展的關系的最新研究進展進行闡述。
1 腸道菌群與免疫
隨著無菌動物與菌群移植動物模型的應用,腸道菌群調節免疫的相關研究陸續開展。無菌小鼠腸道黏固有層缺失輔助性T細胞(T helper cell 17,Th17),結腸固有層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比例明顯下降, 初步揭示腸道菌群可能在調節免疫系統中發揮關鍵作用。將脆弱芽孢桿菌移植給無菌小鼠后, 發現小鼠脾臟T細胞數量增加及淋巴器官生成[1]。在嚙齒類動物中,腸道菌群中的分節絲狀菌可以誘導Th17細胞產生,而將人類腸道中的雙歧桿菌移植給小鼠后同樣可以誘導小鼠腸道內Th17細胞產生,由此可見,Th17細胞的產生依賴于特定腸道菌群的存在[2]。Treg細胞主要存在于結腸黏膜,在調節免疫穩態中發揮重要作用。梭狀芽孢桿菌是定居于小腸數量最多的革蘭陽性菌之一,其菌簇Ⅳ和ⅪⅤa在結腸最為豐富,可以促進Treg細胞產生,其機制可能與短鏈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誘導腫瘤壞死因子β(tumor necrosis factor β, TNF-β)生成有關。由此可見,特定的腸道菌群及其相應代謝產物可以調節Th17和Treg細胞的分化,維持免疫穩態[3]。
2 高血壓與免疫
近10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免疫系統參與血壓調節。RAG-1-/-小鼠(缺乏T細胞和B細胞)在灌注血管緊張素Ⅱ(angiotensin Ⅱ, Ang Ⅱ)和醋酸去氧皮質酮(desoxycorticosterone acetate, DOCA)鹽后,未出現明顯血壓升高,當將T細胞(而不是B細胞)過繼轉移到RAG-1-/-小鼠體內后,出現血壓升高和血管功能障礙,首次證實了T細胞在高血壓中的作用[4]。眾所周知,CD4+T細胞分為輔助性T細胞和調節T細胞(Treg細胞),在適應性免疫中發揮關鍵作用。在Ang Ⅱ誘導的高血壓模型中,發現Th17細胞數量增加[5]。Treg細胞能拮抗效應T細胞的作用,參與自身耐受和維持免疫穩態,同樣與高血壓密切相關。Ang Ⅱ誘導的高血壓小鼠淋巴細胞亞群檢測,發現高血壓小鼠Treg細胞明顯減少,且Treg細胞與血壓負相關[6]。而采用過繼轉移Treg細胞治療Ang Ⅱ 及醛固酮誘導的高血壓小鼠,均發現Treg細胞可以下調血壓。上述研究分別在多種不同的高血壓動物模型,利用不同實驗方法干預,均證實了免疫系統參與高血壓發病。
3 腸道菌群與高血壓
近年來,隨著高通量測序、微生物關聯分析等新技術的應用,人們發現腸道菌群在不同個體及不同疾病狀態存在差異[7]。最初通過各種高血壓動物模型[自發性高血壓大鼠、Dahl鹽敏感大鼠、Ang Ⅱ誘導的高血壓大鼠、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高血壓大鼠及DOCA小鼠][8-10]進行腸道菌群分析,與正常動物對比,均發現腸道菌群豐富性、多樣性、菌群間比例發生改變,且與血壓變化相關。后續進一步通過菌群移植動物模型明確腸道菌群與高血壓的因果關系。將正常血壓患者及高血壓患者的糞便分別移植給無菌小鼠,10周后小鼠腸道菌群出現與人類供體相似的變化,且移植高血壓患者糞便的小鼠出現血壓升高[11]。缺失腸道菌群的無菌小鼠注射Ang Ⅱ后,與普通小鼠對比,未出現明顯血壓升高及血管功能障礙,且血管內超氧化物酶和骨髓單核細胞浸潤減少,炎性因子基因表達下調。因此,腸道菌群參與血壓調節,其機制可能與調節免疫炎性反應有關。目前臨床研究也證實腸道菌群與高血壓密切相關。健康對照人群、正常高值血壓患者、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分別進行了全面宏基因組測序,發現正常高值血壓組和高血壓組的普里沃菌和克雷伯氏桿菌比例增加,而類桿菌和雙歧桿菌比例下降[12]。眾所周知,女性在絕經前血壓與動脈硬化程度均較男性低,其原因在于存在免疫系統差異,而腸道菌群多樣性變化與女性高血壓患者動脈硬化呈負相關[13],高血壓發病的性別差異可能與腸道菌群調節免疫有關。
4 代謝產物在腸道菌群調節免疫中的作用
腸道菌群不僅以食物為底物為機體提供能量和營養,還產生多種代謝產物,調節機體代謝。隨著腸道菌群代謝產物調節免疫炎性反應在疾病發生發展的研究陸續開展,發現腸道菌群組成的變化及相應細菌代謝產物有助于理解腸道菌群調節免疫反應的機制。
4.1 短鏈脂肪酸(SCFAs)
SCFAs是由腸道內的厭氧菌群代謝膳食纖維產生的有機脂肪酸,主要包括乙酸、丙酸、丁酸等,可以維護腸道穩態,調節免疫炎性反應維持機體健康。一項隨機對照臨床干預試驗顯示低鹽飲食可以增加循環中SCFAs,降低血壓[14]。丙酸鹽可以調節免疫細胞、減輕炎性反應從而調節血壓,給予載脂蛋白E敲除小鼠和NMRI野生型小鼠注射AngⅡ誘導動脈粥樣硬化與高血壓小鼠模型后,均隨機用丙酸鹽和0.9%氯化鈉溶液干預,結果發現丙酸鹽可顯著改善兩種動物模型的血壓,而且丙酸鹽減輕了小鼠全身炎性反應,脾臟Th17細胞數量減少[15]。丁酸也可以通過激活Treg細胞、抑制炎性細胞因子的生成而改善機體代謝。SCFAs主要通過激活G蛋白偶聯受體(G-coupled protein receptors, GRCRs)、嗅覺感受器受體Olfr78和抑制組蛋白乙酰化參與調節免疫炎性反應。其中GPR41、GPR43、GPR109A在闌尾、脾臟和骨髓等免疫組織中高表達。SCFAs不僅通過與結腸上皮細胞上的GPCRs結合及抑制組蛋白乙酰化,增加Treg細胞數量減少炎性反應,還可以轉化成乙酰輔酶A,進入三羧酸循環,激活mTOR信號通路誘導Th1和Th17細胞產生[26]。另外,SCFAs還可以作用于樹突狀細胞,調節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達,影響T細胞分化。由此可見,SCFAs不僅可以增加Th17細胞促進炎性反應,還可以增加Treg細胞數量發揮免疫耐受,在維持免疫穩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4.2 氧化三甲胺(trimethylamine oxide, TMAO)
腸道菌群代謝食物中的膽堿、卵磷脂和左旋肉堿等物質生成TMAO,TMAO是動脈粥樣硬化的重要風險因子。TMAO與高血壓密切相關。TMAO與低劑量Ang Ⅱ聯用可以延長Ang Ⅱ的升壓效應[17]。OSA大鼠予以高鹽飲食建立高血壓大鼠模型,與對照組相比,腸道菌群分析顯示擬桿菌增加,乳酸桿菌減少,且循環TMAO水平升高,Th1/Th2細胞失衡,給予鼠李糖乳桿菌干預治療后TMAO水平下降、免疫炎性反應減輕,血壓下降[18]。隨著TMAO在其他研究領域的應用,發現TMAO在免疫調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9]:1)TMAO可以促進巨噬細胞清道夫受體的表達;2)可以促進IL-1、IL-6、細胞間黏附分子-1等炎性因子表達;3)可以激活PKC/NF-κB 信號通路,增加單核細胞黏附;4)觸發氧化應激并激活NLRP3炎性小體。雖然TMAO與高血壓密切相關,但TMAO在血壓調節中的免疫機制仍需進一步探討。
4.3 其他代謝產物
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發現多糖A (polysaccharide A, PSA)、吲哚等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可以調控免疫炎性反應進而影響血壓。高鹽飲食可引起小鼠腸道乳桿菌明顯減少,小鼠大便樣本中吲哚代謝產物減少,Th17細胞增加,給予小鼠補充乳桿菌后可以增加吲哚代謝產物,下調Th17細胞,血壓下降[20]。而將脆弱芽孢桿菌移植給無菌小鼠后,可以產生PSA,增加脾臟T細胞數量、維持Th1/Th2穩態和促進淋巴器官生成,而移植脆弱芽孢桿菌的突變體(不產PSA)不會出現上述免疫系統變化[1]。給予小鼠口服純化的PSA,可以增加CD4+T細胞數量并激活CD4+T細胞產生相應細胞因子。
5 以腸道菌群為靶點,調節免疫炎性反應的膳食干預
腸道菌群與高血壓均受飲食因素影響,飲食是影響腸道菌群結構與功能的重要環境因素,相似的飲食結構其腸道菌群組成更接近。不同膳食結構可以改變腸道菌群,影響代謝產物,誘發免疫炎性反應,參與高血壓發生發展。
5.1 高鹽飲食
給予C57BL/6J小鼠及Dahl鹽敏感大鼠喂食高鹽飼料,與正常飲食組對比,發現高鹽改變了腸道菌群組成及循環代謝產物,高鹽作為影響血壓的重要飲食因素,腸道菌群可能在高鹽調節血壓中起關鍵作用[21-22]。采用16S rRNA鑒定普通大鼠及高鹽誘導的高血壓大鼠的糞便微生物菌群,同樣發現高鹽飲食改變了大鼠腸道菌群組成及代謝產物,將高鹽誘導的高血壓大鼠的腸道菌群移植到普通大鼠后,出現血壓升高[23]。12名健康男性增加鹽攝入后可以降低乳桿菌屬細菌的存活,同時Th17細胞增加和血壓升高,證實高鹽調控血壓的機制:與腸道菌群調控宿主免疫系統有關[20]。將145例未經治療的高血壓患者隨機分為低鹽組與正常飲食組,結果顯示低鹽飲食增加了循環中SCFAs,進而降低血壓、改善血管順應性,首次通過隨機對照干預研究證實了人體內鹽攝入量調節血壓與腸道菌群有關[14]。
5.2 西方飲食
西方飲食是一種高脂肪、低纖維攝入的飲食結構,與代謝綜合征和高血壓明顯相關。有研究比較小鼠喂食西方飲食和普通飲食對腸道菌群結構的影響,發現西方飲食組小鼠厚壁菌門明顯增加[24]。由此可見,西方飲食可以調節腸道菌群,參與高血壓進展。小鼠喂食西方飲食后,引起全身炎性反應,飲食結構調整為普通飲食后,炎性反應消失,而且西方飲食可以誘導髓系祖細胞基因組重編程從而激發先天性免疫,其機制與激活NLRP3炎性小體密切相關[25]。一項大型橫斷面研究顯示攝入高脂肪飲食可引起機體持續炎性反應,從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病風險。由此可見,腸道菌群可能在西方飲食調節機體免疫炎性反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而且西方飲食作用的腸道菌群-免疫軸已在炎性腸病及代謝綜合征等領域得到證實[26]。然而其在血壓調節中作用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5.3 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是以蔬菜、水果、魚類、豆類和橄欖油為主的飲食風格,可以有效減低心血管事件,尤其可改善患者的血壓和動脈硬化[27]。地中海飲食可以增加SCFAs,其產生與厚壁菌門和普氏菌明顯相關,該研究首次為地中海飲食、腸道菌群和相應代謝產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提供了證據[28]。后續針對老年人進行為期12個月的地中海飲食干預,進行腸道菌群及代謝組學分析,發現44種細菌豐度增加,包括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等,同時45種細菌豐度下降,包括瘤胃球菌等,代謝組學分析顯示SCFAs增加、次級膽汁酸降低,且與老年人認知功能及炎性指標(C反應蛋白和IL-17)密切相關[29]。
6 問題與展望
大量研究證實腸道菌群與高血壓密切相關,且腸道菌群在飲食調節血壓中發揮關鍵作用。鑒于免疫系統在高血壓中的作用及腸道菌群的免疫調節作用,綜合分析飲食、腸道菌群、免疫之間的相互作用及與高血壓發生發展關系的研究開始被探索,并提出高血壓發病的新機制:“飲食作用的腸道菌群-免疫”軸。腸道菌群有望成為治療高血壓的新方向和靶點,膳食干預及益生菌調節腸道菌群可能成為高血壓綜合管理的新策略。但該領域的研究仍處于初步階段,基礎與臨床研究上尚存在一些不足:基礎研究仍較少,更多集中于高鹽飲食-腸道菌群-免疫軸,缺乏其他膳食結構的研究證據,且分子機制方面闡述仍不明確。而在臨床研究方面,多為觀察性研究,缺乏大規模的隊列研究及臨床干預研究證據支持,同樣缺乏白大衣高血壓、隱匿性高血壓等高血壓表型腸道菌群特征的證據,以及從不同性別角度詮釋腸道菌群與免疫在血壓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