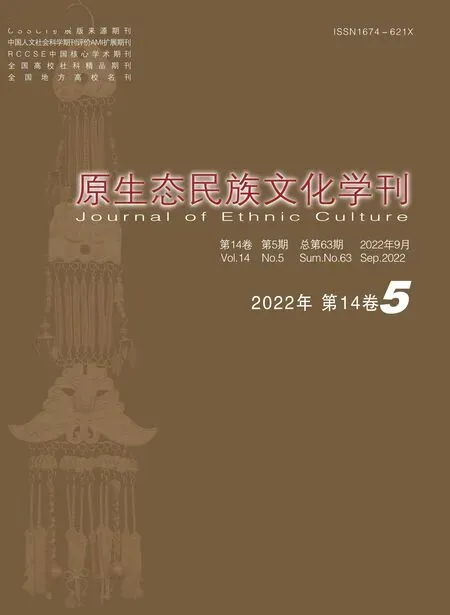宋以降靖州飛山神變遷再探
馮博文
飛山神是宋以降出現(xiàn)于靖州、并于湘黔界鄰地區(qū)廣泛傳播的區(qū)域性神明,后世宗族、研究者多將其與靖州楊氏祖先“飛山公”楊再思等一視之。一般認(rèn)為,楊再思是五代飛山蠻首領(lǐng)及今湘黔界鄰地區(qū)楊氏人群的祖先,死后受封為神;飛山蠻是五代北宋前期活躍于今湘西南靖州、綏寧一帶的地方人群,楊氏在其中扮演領(lǐng)袖角色,自稱誠、徽州刺史。熙寧九年(1076年)溪洞誠、徽州歸順,元豐四年(1081年)后,宋廷改誠、徽州為經(jīng)制誠州和蒔竹縣,元祐六年(1091年)廢為羈縻州,崇寧二年(1103年)再置靖州。飛山蠻、飛山神與“飛山公”,是宋以降湘黔界鄰地區(qū)的核心政治、文化現(xiàn)象[1]。
既有研究大抵由清代譜牒與方志出發(fā),將三者聯(lián)系起來,形成以下敘述:五代時(shí)期,蠻酋潘全盛(或作潘金盛)據(jù)飛山,遣其黨楊承磊進(jìn)略武岡,楚王馬殷討伐潘、楊,楊承磊族人楊再思?xì)w附馬殷;北宋前期,楊再思已由人成神且具有一定影響力,宋廷通過敕封“飛山公”楊再思來達(dá)到實(shí)現(xiàn)國家文化大一統(tǒng)的目的;宋元時(shí),“飛山公”又被屢屢加封至“威遠(yuǎn)廣惠王”,成為區(qū)域性神明。祖先歸附、由人變神、朝廷敕封,乃是獲得地方人士與論者普遍認(rèn)可的飛山蠻首領(lǐng)成為飛山神或曰“飛山公”的敘事體系。①相關(guān)研究著述可參見李紹明:《從川黔邊楊氏來源看侗族與土家族的歷史關(guān)系》,《貴族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楊再思氏族通志》,黔東南日?qǐng)?bào)社印刷廠印,2002 年,第11-12 頁;魏建中:《神山與山神——飛山神信仰探微》,《民族論壇》2017年第2期。論者進(jìn)而指出:“飛山公”楊再思對(duì)中央王朝而言是地方社會(huì)代言人,中央王朝出于將權(quán)力植入地方社會(huì)的目的,樹立楊再思作為地方的保護(hù)神形象。他由楊姓祖先及地方社會(huì)代言人逐步演變?yōu)榈胤缴衩鳎灰跃钢轂橹行挠鷣碛鷱V泛的地域內(nèi)人們信奉和祭祀[2]。這一變化是隨著區(qū)域開發(fā)進(jìn)程,由王朝力量主導(dǎo)及地方社會(huì)精英努力推動(dòng)的、向某種可以稱之為“正統(tǒng)”或“標(biāo)準(zhǔn)”不斷加以創(chuàng)制和改造的結(jié)果[3]36-64。亦有學(xué)者持不同意見。謝國先認(rèn)為集楊氏祖先和誠州刺史兩個(gè)身份于一身的楊再思,是宋代以來?xiàng)钍先后w在家族傳說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精神領(lǐng)袖和宗教形象,這個(gè)形象又被歷代地方官員利用并不斷粉飾,最終演化為今人熟悉的飛山公楊再思[4]。吳湘曾簡(jiǎn)要提到飛山公信仰從山神向祖先神轉(zhuǎn)變的過程,但未展開論述[5]。
晚唐五代以降,長江以南的沅資流域土著人群“紛紛崛起,斥逐官吏,割據(jù)州縣”[6]236。北宋神宗、徽宗時(shí)期,宋廷在沅、資、酉、辰、渠流域建置州縣,開啟對(duì)湘西地區(qū)的控制整合過程。論者在區(qū)域歷史進(jìn)程中考察“飛山神”信仰變遷,從王朝國家整合邊緣地區(qū)社會(huì)文化的脈絡(luò)里界定地方信仰變遷的意義,是一種可取的考察理路。然論者多以方志、譜牒和田野口碑資料討論明清時(shí)期“飛山公”信仰之面貌,較少利用宋元文獻(xiàn)分析飛山神信仰的早期特征。若將宋元飛山神與明清“飛山公”楊再思等一視之,便會(huì)得出飛山神即“飛山公”的固定印象,將飛山神信仰嬗變和靖州楊氏家族的祖先建構(gòu)等多個(gè)階段的歷史過程合而為一。因此,本文試圖分析宋元文獻(xiàn),并謹(jǐn)慎使用明清時(shí)期相關(guān)材料,在宋世開拓誠、徽州蠻的區(qū)域歷史脈絡(luò)中檢討飛山神之起源以及飛山神與楊再思的合流過程。
一、早期飛山神及其受封背景
南宋靖州錄事參軍謝繇于1184 年所撰《飛山神祠碑記》,是官方敕封飛山神的最早記載[2]。《碑記》如下:
飛山之神,自有靖州以來,已著靈跡。元豐六年賜廟顯靈,三十年封威遠(yuǎn)侯[按志,宋淳祐間已加為英惠公,此祀作于前,故只稱侯,特為表之],血食此土,福庇一方,于今八十余年。歲時(shí)水旱祈求,驗(yàn)如影響。正廟在飛山絕頂,一州之民凡有禱祀,皆登陟于高峰之上。舊有行祠,建于刀弩營前。紹興二十五年,崔守移置于方廣寺門之左。乾道六年,詹守復(fù)移置于寺側(cè)之西,然皆一時(shí)草創(chuàng)。淳熙三年,來威中洞姚民敖作過,朝廷調(diào)發(fā)江陵駐扎統(tǒng)制率逢源提兵收捕,密禱于神。既與賊戰(zhàn),覺空中飛沙飄石,奔風(fēng)急雨,賊皆股傈,望風(fēng)而退,由此獲捷。率乃答神之貺,增修行祠,易以竹瓦,添置泊水,覆以茆茨。日月逾邁,風(fēng)雨飄飄,上漏下濕,神像幾暴露矣。九年正月,淦陽孫公國傳來守是邦,下車之初,百廢俱舉,始修學(xué)宮、備器械、整官舍。至于倉庫、場(chǎng)務(wù)、犴獄之屬,修葺一百余間,悉覆以瓦,其勤可謂至矣。公嘗語于眾曰:“備員于茲,雨暘時(shí)若,年谷屢豐,賴神之力居多。茲及不遠(yuǎn),而神祠弊漏如此,倘不能有以報(bào)之,是誰之責(zé)?”乃出己俸,鳩工市材,取新去故,易小以大,重建堂殿、泊水、門屋七間,增置廚房一間,易茆以瓦,□之以墻,涂以丹雘。匪雕匪斫,不侈不陋,尺櫞片瓦,不擾于民。廟貌尊嚴(yán),棟宇綸奐,結(jié)始于次年□□之朔,告成于季冬既望,乃舉酌而祀之曰:飛山之神,功德兼隆;福庇一州,廟食侯封。八十余年,遠(yuǎn)彌欽崇;自惟不才,符分虎銅。二年于茲,自春徂冬;所祈必應(yīng),有感必通。雨暘應(yīng)候,時(shí)和歲豐;民安盜息,皆神之功。何以論報(bào),第竭恪恭;修神之祠,與國無窮。①文中有“按志,宋淳祐間已加為英惠公,此祀作于前,故只稱侯,特為表之”一句,洪武《靖州志》所收碑記無此句,光緒《靖州直隸州志》有此句。道光《靖州直隸州志》中“按志”二字作小字夾注,且在文首以小字注明此碑由明參將金章重刻。據(jù)此,該句或?yàn)榻鹫轮乜檀吮畷r(shí)所注,道光志收入該文時(shí)一仍其格式,光緒志據(jù)道光志抄入時(shí)竄入正文。參見(清)覺羅隆恩等修,汪尚友等纂:《靖州直隸州志》卷一二《藝文上》,成文出版社2014年影印道光十七年續(xù)修刻本,第2257頁。
據(jù)此,其時(shí)靖州有一飛山神正廟,位于飛山之頂;有一飛山行祠,位于刀弩營前。元豐六年(1083 年),飛山廟受賜廟額“顯靈”。紹興二十五年(1155 年),飛山行祠被移至飛山方廣寺西側(cè),淳熙三年(1176年)有過一次簡(jiǎn)單增修,淳熙九年復(fù)被知州孫國傳修葺一新。②從碑記描述來看,翻新后的飛山祠似乎仍與方廣寺在一起,并且南宋《輿地紀(jì)勝》只記載了“飛山寺”,洪武《靖州志》謂“飛山方廣寺”,頗疑即飛山祠和方廣寺合稱。參見(宋)王象之撰,趙一生點(diǎn)校:《輿地紀(jì)勝》卷七二《荊湖北路·靖州·景物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1835 頁。至明初,方廣寺已廢。今飛山頂建筑群仍以方廣寺為核心建筑,僅在寺側(cè)一小亭內(nèi)置有楊再思塑像。《宋會(huì)要輯稿》謂:“飛山神祠在靖州渠陽縣。神宗元豐六年十月賜廟額‘靈惠’。高宗紹興三十年四月封威遠(yuǎn)侯。”[7]禮二〇之山神祠1036此當(dāng)為《碑記》所謂飛山行祠。同書又謂:“顯靈廟,廟在靖州渠陽縣飛山。威遠(yuǎn)侯,淳熙十五年五月加封威遠(yuǎn)英齊侯。”[7]禮二一諸神廟1097此當(dāng)為《碑記》所記飛山正廟。《碑記》謂元豐六年賜廟“顯靈”,《宋會(huì)要》“山神”條所載“靈惠”當(dāng)為“顯靈”之誤。飛山正廟位于靖州城西飛山頂,似是元豐六年(1083年)賜廟額“顯靈”或之前所建。宋軍進(jìn)入誠徽州地區(qū)前,“誠徽州蠻”及周邊地域內(nèi)存在地方人群信祀的山、溪等自然神。洪武《靖州志》記有福湖山,“中有神洞,以祀山之神,夷人畏鬼,平時(shí)不敢樵采”。③洪武《靖州志·山川·山》“福湖山”條,不分卷,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洪武《靖州志》又載“黃溪大王廟”“靈溪大王廟”,當(dāng)同為土著人群所祀神祇。與誠州緊鄰的沅州,有“明山神”。飛山當(dāng)如福湖山、沅州明山一般,存在土著人群信祀的自然神。謝繇《碑記》對(duì)“飛山之神”并無人格化描述,宋代飛山神當(dāng)屬自然神,尚未與具體人物或特定人群相關(guān)聯(lián)。
熙寧六年(1073年),章淳經(jīng)略南江蠻,于沅州明山“以兵事禱之,得吉卜,既而蠻人田元猛果降,因奏封順應(yīng)侯,賜廟額”[8]卷65辰州府·祠廟2882,進(jìn)而在新辟之地修筑懿州城,并將既有之明山神定為懿州新城主山神[7]禮二〇之山神祠1033。因此,沅州明山神受封為順應(yīng)侯,乃宋軍經(jīng)略南江蠻、籠絡(luò)土著人群的文化手段。元符二年(1099年),涇原路經(jīng)略使章楶收復(fù)天都山,修筑秋葦川、灑水平、南牟會(huì)等城寨,因天都山“本漢唐故地,久陷異域,今復(fù)歸中國。林木茂潤,氣象雄偉,神靈所宅,實(shí)鎮(zhèn)西土”,加之“方出塞進(jìn)筑,有禱必應(yīng)”,奏建天都山神祠。銀川城柏株山之部臺(tái)神,“徽宗崇寧三年復(fù)故地,筑州城及龍泉新寨畢,封褒順公廟”[7]禮二〇之山神祠1037。明山神、天都山神、部臺(tái)神的賜封皆與北宋新辟疆土或新筑城寨關(guān)系密切,表明祭祀土著人群之神明并加以賜封,乃是北宋開拓新疆時(shí)的慣用文化策略。熙寧九年(1076年),溪洞誠、徽州歸順。宋廷于元豐四年(1081 年)修筑貫堡等寨,五年改貫堡寨為渠陽縣,六年移渠陽縣于州治。誠州城寨、建置至元豐六年(1083 年)始具規(guī)制,而飛山神受封“顯靈”恰與此同年。據(jù)此推知,宋廷為飛山廟賜廟額“顯靈”的直接原因是其在宋軍開拓誠、徽州的過程中發(fā)揮靈驗(yàn)或籠絡(luò)功能。同年,誠州官員亦因伏波將軍“素為夷狄畏信”,奏請(qǐng)為伏波將軍加爵,其用意與封飛山神相近,同為鎮(zhèn)撫誠徽州蠻。①洪武《靖州志·總類·祠廟》“昭靈忠顯廟”條,不分卷。據(jù)《宋會(huì)要》禮二〇之《歷代帝王名臣祠》,元豐六年十月為渠陽縣屈原祠賜額“昭靈”(第1002 頁),然洪武《靖州志》卻載“(元豐)六年,昭靈廟即系伏波將軍”,有所抵牾。頗疑元豐六年,誠州官吏將土著的屈原祠改為伏波廟。因此,建飛山正廟與敕封飛山神,乃宋軍在湘黔界鄰地區(qū)建立直接統(tǒng)治的文化表征。
元豐以后,飛山神分出一行祠,位于刀弩營前。元豐年間,誠州剛剛進(jìn)入版圖,民丁不足,無從招募土丁防守,故元豐七年十月“詔湖南邵州武岡縣減將下防托弩手二百,以其錢糧募土人入溪峒”[7]蕃夷五之西南溪洞諸蠻9892。所以,其時(shí)誠州尚無刀弩營。元祐年間,宋廷罷廢誠州,崇寧二年(1103 年)復(fù)于其地置立靖州。政和七年(1117 年),始于辰、沅、靖諸州置刀弩手。史載“湖北辰、沅、靖、澧州刀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為之,授以閑散,而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九千余人。”②(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八甲集《兵馬戎器舟車·湖北土兵刀弩手》,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影印本,第7冊(cè),第12a頁。又曹彥約《辰州議刀弩手及土軍利害劄子》謂:“政和七年,因都鈐張察所奏,召募土丁,給受田土,置立將校,彈壓夷猺,當(dāng)時(shí)得防,即與依奏。”參見(宋)曹彥約撰,尹波、余星初點(diǎn)校:《曹彥約集》,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8頁。刀弩營兵源來自三州土丁,職責(zé)是“彈壓夷猺”。飛山行祠位于刀弩營前,當(dāng)與刀弩手存在一定關(guān)聯(lián);其創(chuàng)置年代當(dāng)在兩宋之際,其功能與刀弩營“彈壓夷猺”頗相仿佛。洪武《靖州志》謂靖州延壽寺“所有寺基,概為軍營”,所謂“軍營”或指刀弩營。③洪武《靖州志·古跡》“延壽寺銅鐘”條,不分卷。州志又謂南宋曾修筑自州城西門通往“飛山行祠”之道路,行祠在州城西,與今靖州城關(guān)西的飛山廟方位大體相合。④洪武《靖州志·城池》,不分卷。
南宋時(shí)期,湘黔界鄰地區(qū)動(dòng)亂頻發(fā),宋軍相當(dāng)看重飛山神的戰(zhàn)時(shí)靈應(yīng)功能。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淳熙三年(1176年),靖州先后發(fā)生楊再興、姚民敖之亂;紹興三十年、淳熙十五年,飛山神兩次受封。兩次“瑤亂”與飛山神加封的時(shí)間,存在一定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姚民敖起事,江陵駐扎統(tǒng)制率逢源因飛山神在大戰(zhàn)之中顯靈,主動(dòng)增修行祠,此事見于謝繇《碑記》。靖州通判胡份墓志載有相近之事,志謂:“郡犬牙蠻獠,儲(chǔ)粟寡一,被圍則乏。軍興,公經(jīng)營,増其廩入,無倉卒憂。歲旱,盜且萌蘗,與郡將齋禱飛山之神,雨隨車至。”[9]卷18祭文99胡份祭祀飛山神,是因靖州干旱無糧,無以應(yīng)對(duì)“蠻獠”圍困。嘉泰二年(1202年),知州呂松年專門修葺從西門到飛山行祠的道路,⑤洪武《靖州志·城池》,不分卷。亦表明飛山行祠對(duì)宋維持在靖州之軍政統(tǒng)治頗具意義。神祇靈驗(yàn)是宋代封神的必備條件[10]278,飛山神在宋軍鎮(zhèn)壓地方人群過程中的靈驗(yàn)效果乃是飛山神受封、祠廟增修及得到特殊待遇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論,飛山神在元豐六年(1083 年)之前缺乏史料記載,或是土著人群信祀的自然神;飛山神受封,與熙、豐年間經(jīng)略“誠徽州蠻”的軍事行動(dòng),尤其與元豐六年誠州置立直接相關(guān)。元豐六年后飛山神的受封、加封與飛山祠廟的創(chuàng)置、增修,是宋廷在湘黔界鄰地區(qū)建立軍政統(tǒng)治的文化象征。
二、元明之間飛山神身份的再詮釋
楊再思一般被認(rèn)為是“飛山蠻”領(lǐng)袖楊承磊之族兄。據(jù)稱,楊再思“常有功于郡”,故而屢被加封[11]卷3祠廟328。然宋元之時(shí),靖州官方認(rèn)可的地方名宦序列中并無楊再思此人,在靖州沿革中不具備相應(yīng)的政治紀(jì)念意義。南宋靖州曾撰多次修撰圖經(jīng)志書,州教授陳公顯所撰《靖州志》沿革序中未提及楊再思,僅謂“太平興國四年,誠州十洞酋楊通蘊(yùn)款附;五年,楊通寶來貢,以為誠州刺史,誠州通中國自此始矣”。①洪武《靖州志·歷代沿革》,不分卷。據(jù)此,楊通寶納土入貢與“誠州通中國”在靖州沿革史中具有標(biāo)志意義。元人所撰《宋史·誠徽州蠻傳》亦僅述及楊通蘊(yùn)和楊通寶[12]卷494蠻夷二14197,洪武《靖州志》將楊通寶列為本州首位“名宦”,并無楊再思之名。②洪武《靖州志·歷代沿革》,不分卷。概言之,楊通寶乃宋明間朝廷與靖州官方推崇的“飛山蠻”楊氏第一人。此一時(shí)期,飛山神與楊再思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可能性頗為有限。
后世楊氏族譜中錄有一份宋皇祐六年(1054 年)加封楊再思為“飛山威遠(yuǎn)廣惠王”的封誥,謂:
敵王所愾,世選爾勞,有功于民,死當(dāng)廟食。以爾西秦望族,當(dāng)代元?jiǎng)祝首有找暂o朝廷,鳩家眾而鼓忠勇。偏州坐鎮(zhèn),五省蒙庥;屢世宣猷,百年不墜。自非素以忠義固結(jié)民心者不能及。身既歿矣,猶思造福于民,故禱雨祈晴、御災(zāi)捍患,默佑一方,叩之無不響應(yīng)。雖前賜爾侯封,謚爾廣惠,僅足酬廣石柳慶、比沙渠之功也。今部者以闕典請(qǐng)爾王號(hào),特封飛山威遠(yuǎn)廣惠王。汝其益赫厥靈,勿昧尊主庇民之志,欽哉![13]368
若該封誥屬實(shí),則是最早出現(xiàn)楊再思之名且說明宋代靖州楊氏已經(jīng)形成楊再思認(rèn)同的史料。不過此“封誥”頗具疑點(diǎn)。其一,封誥時(shí)間有皇祐六年、元祐六年(1091年)、延祐六年(1319 年)之說,③依次參見《楊再思氏族通志》,第33頁;《楊氏歷代源流事實(shí)》,收入向零、余宏模、張濟(jì)民主編:《民族志資料匯編》第9集《土家族》,第370頁;《楊再思?xì)v史文化考察報(bào)告》,收入朱衛(wèi)平主編:《五溪之神:楊再思?xì)v史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可知該文本衍生自某一祖本族譜文本,編纂者重在傳述“廣惠王”之名,時(shí)間并不重要。其二,明初以前,飛山神被加號(hào)至“威遠(yuǎn)英濟(jì)廣惠英惠公”,然目前所見明代各地飛山廟通以“飛山廟”“渠陽廟”“威遠(yuǎn)侯廟”“英惠侯廟”為名,所謂“廣惠王”之說在明代尚未成形。④一份楊氏族譜指出萬歷四十年時(shí)銅仁知府稱楊再思為“飛山公威遠(yuǎn)廣惠王”,參見《民族志資料匯編》第9 集《土家族》,第374頁。其三,文本措辭有疑:(1)“以爾西秦望族,當(dāng)代元?jiǎng)住笔侵妇钢輻钍峡ね陉P(guān)中,乃宋朝元?jiǎng)祝凰螘r(shí)楊再思并無此種政治意義;⑤據(jù)《楊再思氏族通志》所收楊氏通名支系族譜舊序中,康熙舊譜序尚未提及楊氏郡望弘農(nóng),乾隆舊譜序始云楊氏出自弘農(nóng)。參見《楊再思氏族通志》,第60頁。(2)“五省蒙庥”,然宋代無“省”之稱謂,元代靖州屬湖廣,與之毗鄰的并無四省;(3)以“欽哉”結(jié)尾,非宋代制敕用語,宋代封嘉嶺山神為威顯公之詔文可資對(duì)比,詔云:“崛彼靈峰,寔(推守)〔惟宋〕祀。遘梯沖之內(nèi)侮,興雨雪而外凌。闇冥之交,髣髴有覩。狂寇驚潰,堅(jiān)壘妥安。捍民成功,蒙福斯厚。而名爵未著,牢具不豐,非所以重依人、尊受職也。宜加封號(hào)威顯公。”[7]禮二〇之山神祠1033因此,該文本的出現(xiàn)年代理應(yīng)存疑。
擱置此“封誥”,最早提及“楊再思”的史料是洪武九年(1376年)《靖州志》。該志是靖州知府王尚文在南宋紹定《靖州志》基礎(chǔ)上抄撮增補(bǔ)而成,故載有兩份祠廟名目。前一份為明初靖州現(xiàn)存祠廟,其中有“飛山廟”,“去州西五里”。后一份為“本州已廢廟宇”,應(yīng)是南宋紹定《靖州志》所載、至明初已廢祠廟,其中有“飛山正廟”,“舊在州城外西飛山上”。據(jù)前揭《宋會(huì)要輯稿》與《碑記》,南宋有飛山正廟與飛山行祠,分別位于飛山頂與刀弩營前。洪武九年,飛山頂?shù)恼龔R已廢,州城西五里的飛山廟仍存(今址仍在),應(yīng)即淳熙九年知州孫國傳增修的飛山神祠。紹定《靖州志》中雖載有飛山廟,卻極可能并未解釋飛山廟主神身份;洪武《靖州志》錄有已廢之“飛山正廟”,謂“或言其神即故誠州刺史、楊氏之祖諱再思者也”,口吻極為謹(jǐn)慎。①洪武《靖州志·廟宇》“飛山正廟”條,不分卷。所謂“或言”,應(yīng)是作為外來官員的王尚文訪于當(dāng)?shù)仃壤希缘胤饺耸靠谥蝎@知飛山廟所祀乃楊氏之祖楊再思。倘若此一推測(cè)勉能成立,則飛山神至遲于明初已與靖州楊氏人群發(fā)生聯(lián)系,飛山神即楊再思之說在一定程度上獲得靖州知府認(rèn)可,但仍存疑。因此,洪武《靖州志》所謂“或言”,表明洪武九年以前亦即元明之間的靖州飛山神出現(xiàn)變化:靖州楊氏人群已形成楊再思祖先認(rèn)同,將飛山神認(rèn)定為其祖楊再思,并試圖將此說向官方意識(shí)層面推介。
“楊再思”的出現(xiàn),當(dāng)是靖州楊氏人群借追溯始祖以構(gòu)建宗族之結(jié)果。回到宋軍開拓誠、徽州蠻的歷史過程即可獲知,靖州楊氏的宗族化與“楊再思”之出現(xiàn)并非突然出現(xiàn),而是有其文化脈絡(luò)可循。楊氏作為誠徽州蠻區(qū)勢(shì)力最大及與官府接觸最為密切的土著人群,具有接受儒學(xué)教育的領(lǐng)先地位。北宋熙寧年間,楊光僣“與其子日儼請(qǐng)于其側(cè)建學(xué)舍,求名士教子孫”,宋廷為其專置誠州教授[12]卷494蠻夷二14198。元祐元年(1086年),湖北都鈐轄、轉(zhuǎn)運(yùn)司奏報(bào):“誠州地林等溪峒一千四百五十四戶,惟楊族一姓補(bǔ)充班行,其姚、石、龍、盧、吳家數(shù)姓亦大族,頗懷觖望。”[14]卷377哲宗元祐元年五月9164這表明楊氏在與官軍溝通中獨(dú)占優(yōu)勢(shì)。政和年間,宋廷準(zhǔn)許楊光僭之孫以歲貢入太學(xué),這不僅是宋廷對(duì)楊光僭之優(yōu)待,亦表明楊光僭子孫接受儒學(xué)教育之領(lǐng)先。紹興十四年(1144 年),“靖州乞依舊置新民學(xué),教養(yǎng)溪洞歸明子弟,以三十人為額。”[15]卷151紹興十四年二月丁亥2425南宋以后,文臣取代武將出任靖州主官,如知州吳順之墓志銘所述:“異時(shí)守皆武臣,文法闊略。公初以文臣臨之,下車語僚屬曰:‘蠻夷荒忽,不威制則玩,不靜治則擾’。”[16]303—304歷任靖州知州均注重興文教和教化溪洞蠻酋子弟,不斷由官府設(shè)立書院和民學(xué)[17]。靖州土人田生為貶謫到靖州的文士程子山建造“踈亭”(此亭后成為靖州一景),表明其文化素養(yǎng)頗高,故與中原文士具有交游之誼。②洪武《靖州志·亭臺(tái)》“踈亭”條,不分卷。康熙《靖州志》卷六《藝文·觀亭記》作“觀亭”。然在接受教育的蠻酋子弟之中,唯有楊光僭后裔楊立中嘗擢為甲第,①康熙《靖州志》卷六《藝文·作新書院記》,第391頁。可知楊氏尤其是楊光僣子孫在靖州地方人群中保持儒學(xué)教育優(yōu)勢(shì)。南宋以后,靖州雖時(shí)而發(fā)生“瑤亂”,舉事領(lǐng)袖已多非楊氏,而是吳氏、姚氏、林氏等族姓[7]蕃夷五之西南溪峒諸蠻9903。楊氏人群被納入王朝國家直接統(tǒng)治后,迅速向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靠攏,并取得一定文教優(yōu)勢(shì),當(dāng)率先具備宗族建構(gòu)的意識(shí)與能力。
同一時(shí)期,飛山廟成為靖州民眾禱告之場(chǎng)所,即如謝繇《碑記》所謂“歲時(shí)水旱祈求,驗(yàn)如影響”,“一州之民,凡有禱祀,皆登陟于高峰之上”。②(清)勞銘勛纂,吳起鳳修:《靖州直隸州志》卷十一《藝文》,第5a、5b頁。自此時(shí)起,飛山神成為靖州官民共同崇信的地方神明,從而具備與靖州土著人群接觸的可能。元至明初,楊氏從曾是土著人群“飛山蠻”領(lǐng)袖的歷史資源出發(fā),以楊再思祖先記憶為手段凝聚自身認(rèn)同,實(shí)現(xiàn)靖州楊氏的宗族化,并以楊再思以誠州刺史身份保境安民的祖先敘事向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靠攏,適應(yīng)著湘黔界鄰地區(qū)從羈縻向州縣轉(zhuǎn)型的進(jìn)程。
三、“飛山公”:楊再思與飛山神的合一
據(jù)前揭洪武《靖州志》,明初靖州知府對(duì)飛山神即楊再思之說尚存疑慮,然飛山神傳至黎平時(shí)與楊再思確定關(guān)聯(lián)。洪武十九年(1386年)建飛山廟于黎平,《寰宇通志》謂黎平府飛山廟:“在府治東,祀靖州楊再思,五代梁時(shí),再思為誠州刺史,死而有靈,土人祀之,祈禱有應(yīng)。宋奉為英惠公,廟在靖州飛山。國朝洪武十九年建于此。”③(明)陳循等纂:《寰宇通志》卷一一四《貴州·黎平府·祠廟》飛山廟條,天津圖書館藏明景泰七年刻本,第39冊(cè),第12b頁。“洪武十九年建于此”,嘉靖《貴州通志》作洪武十年,驗(yàn)之較早的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當(dāng)以洪武十九年為是。參見(明)沈庠修,趙瓚纂:《貴州圖經(jīng)新志》卷七《黎平府·古跡》,巴蜀書社2016年影印貴州省圖書館影寫弘治刻本,第79頁。洪武十八年置五開衛(wèi),十九年筑衛(wèi)城,永樂十一年始建黎平府治于衛(wèi)城西,弘治八年遷建府治于衛(wèi)署之南,故黎平府自永樂十一年起便與五開衛(wèi)共治一城。《寰宇通志》成書于景泰年間,所謂“府治”實(shí)指五開衛(wèi)城,因此,黎平飛山廟實(shí)際與五開衛(wèi)城同時(shí)營建于洪武十九年。明軍立足靖州,征討亮江流域諸土酋,設(shè)置衛(wèi)所;黎平飛山廟與五開衛(wèi)城建于同年,可知黎平飛山廟或是來自靖州的衛(wèi)所移民所建。因此,飛山神與楊再思已于明初合而為一,并隨著衛(wèi)所移民進(jìn)入黎平,在湘黔界鄰地區(qū)傳播。元明鼎革之際,靖州楊氏將飛山廟歷史緣起的解釋權(quán)歸為己有,作為外來統(tǒng)治者的明朝官員,只能被動(dòng)接受楊氏對(duì)飛山廟淵源和飛山神身份的解釋。
在苗亂頻發(fā)的背景下,明代黎、靖等地修建飛山廟和編纂地方志,對(duì)鎮(zhèn)撫苗夷的楊再思形象予以確認(rèn)。作為飛山神信仰起源地,靖州與通道縣在明初時(shí)皆有飛山廟,④洪武《靖州志·廟宇》,不分卷。明代時(shí)便已“靖屬通祀之”。⑤同治《綏寧縣志》卷十七《祠廟》“飛山廟”條,國家圖書館藏同治十一年刻本,第22頁。《寰宇通志》載:“威遠(yuǎn)侯廟,在(靖州)州城西。侯名再思,誠州刺史楊氏之祖。宋紹興間封威遠(yuǎn)侯,立廟祀之;淳熙間,加號(hào)英濟(jì)。后廟毀,國朝正統(tǒng)十一年(1446 年)間重建。”①景泰《寰宇通志》卷六十《靖州·祠廟》飛山廟條,第21冊(cè),第3b頁。吳湘曾據(jù)《大明一統(tǒng)志》認(rèn)為,原飛山神的封號(hào)與楊氏之祖掛鉤不會(huì)晚于明正統(tǒng)十一年(1446年),這一估計(jì)顯然過晚。參見吳湘:《唐宋時(shí)期飛山蠻研究》,第101頁。黎平所屬土司多有飛山廟或楊再思祠,如“亮司署左有二侯祠,并祀英惠侯楊再思”,“王寨、洪州所均有飛山廟”。②光緒《黎平府志》卷二下《祠廟》楊公祠條,國家圖書館藏光緒十八年刻本,第35頁。英宗、代宗之后,飛山祠在各地官員的支持下興建起來。弘治以前,飛山廟出現(xiàn)在思州府,當(dāng)?shù)毓賳T強(qiáng)調(diào)“夷人有災(zāi),禱之屢應(yīng)”。③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卷四《思州府·祠廟》,第51頁。正德年間,銅仁土官李椿在銅仁建飛山祠[18]卷6祠廟179。飛山神的新內(nèi)涵顯然得到思州、銅仁土人與土官普遍認(rèn)可。
楊再思鎮(zhèn)服溪洞苗夷、保境安民的形象,與前史所謂飛山神威服蠻夷的靈應(yīng)故事相承接,此為飛山神的自然神內(nèi)涵被靖州楊氏具化為祖先楊再思的重要背景。嘉靖十六年(1537 年),倪鎮(zhèn)所撰靖州《重修飛山神祠碑記》云:“吾郡之飛山神,生以威德服溪峒苗夷而民受其福,終則精爽不昧,民立祠以祀。凡水旱災(zāi)厲,有禱克應(yīng)。雖深山窮谷中,莫不有廟。……越嘉靖丙申,實(shí)今清平云崖金公分守之。明年一夜,夢(mèng)神素服白馬相謁。問其姓,答曰木姓也。及謁廟,宛如所夢(mèng)。因悟楊從木從易,是為神姓。見其傾圮,捐俸修之。”④道光《靖州直隸州志》卷一二《藝文上》,第2261頁。嘉靖年間,飛山神姓楊并由土人立祠祭祀的說法已經(jīng)在靖州流布,楊再思的地方形象基本確定。鄧鐘所撰黎平《二王廟碑記》云:“萬歷庚子春,值郡苗猖獗,戕我官軍,奪我囤房,毀我廟宇,盡人神共憤久矣。……時(shí)值大兵未集,駐營郊外飛山廟址在焉,因憶興師之夜,夢(mèng)三神自云中夾山而飛……比謁飛山二神,恍如夢(mèng)中所見。”所謂“飛山二神”,其一便為楊再思。清人就指出“有明之世,逆苗猖獗,時(shí)著威靈,是誠能為民御災(zāi)捍患者也”。⑤光緒《黎平府志》卷二下《祠廟》楊公祠條,第36a頁。地方官樂于承認(rèn)楊再思保境安民、威服苗夷和禱應(yīng)必靈的形象。從飛山之神到祖先神楊再思的變遷,既是靖州地方人群將作為統(tǒng)治象征的神明改造為祖先神的過程,亦是其向王朝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不斷靠攏的過程。
“飛山公”傳布至湘黔界鄰地區(qū)后,各地土人對(duì)其身份做出多元化解釋。據(jù)鄧鐘《二王廟碑記》,黎平飛山廟祀有二神,當(dāng)?shù)仃壤现^其中一神,“吳其姓,有戰(zhàn)功,與楊公結(jié)為關(guān)張”,指明此飛山廟中祀有吳、楊二人,吳氏失其名。⑥光緒《黎平府志》卷二下《祠廟》楊公祠條,第36a頁。黎平府亮寨土司有“二侯祠”,清初以前僅祀楊通蘊(yùn)、楊通寶二人,亮寨土司龍氏始祖配享;清初,土司龍文炳恐“祀孫而忘其祖,于禮未協(xié)”,始增設(shè)楊再思與諸葛武侯木主,可見亮寨司祭祀楊再思乃后起之事[19]242。據(jù)此,黎平飛山廟并非僅祀楊再思一人,而多與吳、龍等湘黔界鄰地區(qū)其他大姓人群領(lǐng)袖同祀。此外,亮寨二侯祠祀楊再思始于清初,此前僅祀楊通蘊(yùn)、楊通寶,這與宋元史籍所見北宋誠州沿革恰恰相合。黎平府二侯祠與二王廟中的楊再思與其他姓氏同祀現(xiàn)象,當(dāng)是此地土人、土司依據(jù)自身歷史與社會(huì)情境進(jìn)行的改造。⑦北宋時(shí),楊氏便是湘黔桂界鄰地區(qū)主導(dǎo)性人群,姚、石、龍、盧、吳諸姓從屬之,但“頗懷觖望”。
康熙年間,賀國賢在銅仁建造飛山廟,土人多認(rèn)為“飛山公”是楊業(yè),賀氏則專門指出是楊再思。論者指出,“楊姓人群在建構(gòu)祖先傳說故事過程中有著不同的歷史知識(shí)來源”[2]120,而官員賀國賢卻將楊再思視作“飛山公”的標(biāo)準(zhǔn)身份。康熙《靖州志》纂者云:“威遠(yuǎn)侯楊公再思,其為五代時(shí)溪洞君長無疑,說者以令公二字指謂朱梁時(shí)之楊師厚,遂有梁朝加贈(zèng)尚書之聯(lián);或又以為則天時(shí)高麗舞之楊再思,荒誕不經(jīng)。”①康熙《靖州志》凡例,第280頁。此說反映出靖州土人對(duì)“飛山公”存在五代楊師厚、武周楊再思等多種解釋,而方志編纂者卻堅(jiān)持認(rèn)為“飛山公”即楊再思。晚清黎平人楊秀之指出:“郡城內(nèi)外,并立有飛山祠,而其中所塑之像,皆以劇本所傳楊業(yè)父子省之”[13]365。此外,亦有將“飛山公”和沅江流域水神楊公相混淆的情況[3]198-233。在以賀國賢為代表的地方官員看來,“飛山公”的正統(tǒng)身份即為納土歸附、保國守土的溪洞蠻酋和誠州刺史楊再思,各地土人亦依據(jù)自身歷史情境或歷史知識(shí)對(duì)“飛山公”做出多元解釋。概言之,各地人群對(duì)“飛山公”存在顯著的差異化認(rèn)知,②靖州以外在接受飛山公楊再思是所謂誠州刺史同時(shí),開始和靖州爭(zhēng)奪楊再思出生地與“誠州”位置,如城步、黎平。參見楊再思?xì)v史文化研究課題組:《楊再思?xì)v史文化考察報(bào)告》,收入朱衛(wèi)平主編:《五溪之神楊再思?xì)v史文化研究》,第7頁。但在諸多認(rèn)知之中,只有作為溪洞豪酋、誠州刺史的楊再思是獲得官方認(rèn)可的“飛山公”標(biāo)準(zhǔn)身份。“飛山公”雖由元明之間的靖州楊氏人群主導(dǎo)建構(gòu),它的標(biāo)準(zhǔn)身份卻是由明清地方官員賦予和強(qiáng)化的,此為“飛山公”在地方人群與王朝國家互動(dòng)中漸次標(biāo)準(zhǔn)化的過程。
四、余論
既有研究將后世湘黔界鄰地區(qū)成熟的“飛山公”信仰與宋元時(shí)期靖州的飛山神直接等同,認(rèn)為靖州飛山神即楊氏祖先或曰“飛山公”楊再思。本文則試圖揭示宋代以降靖州飛山神信仰變遷中的更多細(xì)節(jié),核心問題在于早期飛山神身份以及靖州楊氏祖先記憶與飛山神如何合一。經(jīng)過考述,可以認(rèn)知:北宋前期的飛山神或?yàn)橥林巳盒澎氲淖匀簧瘢槐彼卧S六年,宋廷置立誠州,并敕封飛山神、創(chuàng)置飛山廟;南宋,飛山神開始與靖州地方人群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元明之間出現(xiàn)飛山廟祭祀楊氏祖先楊再思的說法;明前期,飛山神已與楊氏祖先楊再思合而為一,演化為后世習(xí)知的“亦祖亦神”的“飛山公”。盡管湘黔界鄰地區(qū)土人對(duì)“飛山公”始終存在多元解釋,誠州刺史楊再思卻是唯一受官方認(rèn)可的“飛山公”標(biāo)準(zhǔn)形象。要之,自宋以降,飛山神的身份內(nèi)涵歷經(jīng)土著人群自然神、王朝國家敕封神明與靖州楊氏祖先神的變遷及交錯(cuò)過程。
飛山神的身份內(nèi)涵變遷,為認(rèn)識(shí)湘黔界鄰地區(qū)進(jìn)入王朝國家控制體系及其與周邊區(qū)域的歷史進(jìn)程差異,提供了一種解釋路徑。湘黔界鄰地區(qū)乃是云貴高原東端及武陵山區(qū),宋代以前皆具有濃厚的土著文化色彩。自晚唐五代始,湘西諸蠻酋“紛紛崛起,斥逐官吏,割據(jù)州縣”。北宋開拓沅水流域溪峒蠻以來[20],沅水中上游的湘西北、黔東南、湘西南地區(qū)逐漸形成頗具差異的歷史軌跡:湘西北與黔東南地區(qū)自元明以降,維持長期的土司自治(當(dāng)然,兩地的土司政治結(jié)構(gòu)并不相同),湘西南的靖州地區(qū)則再未脫離王朝國家直接控制,并成為明初經(jīng)略清水江流域乃至貴州地區(qū)的跳板之一。那么,靖州地區(qū)自宋時(shí)進(jìn)入王朝國家版圖的社會(huì)機(jī)制如何?由本文考述可知,飛山神身份內(nèi)涵的變遷大體分為兩階段:宋時(shí)在靖州建置州縣、砦堡,建立軍政控制,飛山神遂成為王朝國家統(tǒng)治湘黔界鄰地區(qū)的文化表征,并在南宋鎮(zhèn)撫地方人群叛亂中發(fā)揮靈應(yīng)作用。元代以降,王朝國家逐漸以鄉(xiāng)里區(qū)劃取代峒團(tuán)組織,深化其對(duì)靖州地區(qū)的社會(huì)控制;①大德元年至三年(1297-1299 年)之前,靖州會(huì)同縣有“廣德鄉(xiāng)”。參見(元)揭傒斯著,李夢(mèng)生點(diǎn)校:《揭傒斯全集》卷六《記·靖州廣德書院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頁。與此同時(shí),靖州楊氏將其追溯始祖的宗族化努力與飛山神身份的再詮釋相結(jié)合,在意識(shí)形態(tài)層面向王朝國家主動(dòng)靠攏。然則,原本服務(wù)于王朝國家軍政控制的威權(quán)神明,在王朝國家與地方人群的互動(dòng)之中,成為官方與地方宗族、土人共同接納的區(qū)域性神明。飛山神的身份內(nèi)涵變遷,反映著宋以降湘黔界鄰地區(qū)的地方人群被納入王朝國家控制體系的文化整合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