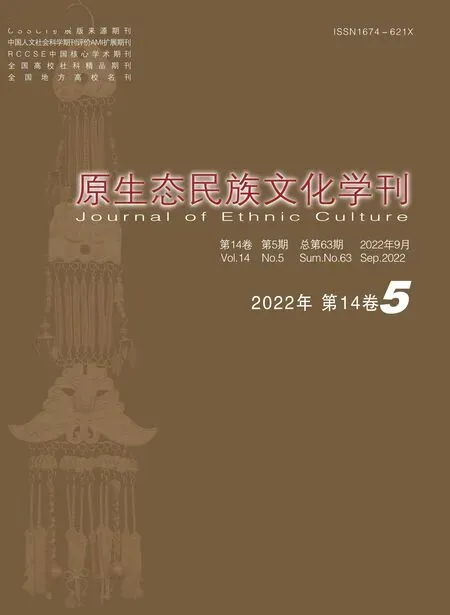儀式治療困境與多元醫療體系的建構
——以涼山彝族“斯色那”治療實踐為例
李小芳,羅木散
1965年,毛澤東主席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1],西方醫學體系逐漸進入中國的廣大農村。自此,我國大部分地區形成了中醫、西醫和少數民族傳統醫學共存的多元醫療體系。目前,國內學者關于多元醫療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多元醫療體系共存的原因,以及在多元醫療體系背景下重點研究基于民間信仰的儀式治療、多元醫療體系之間的相互關系和運行狀態等。首先注重對儀式治療過程中的“神藥兩解”進行分析,例如龍開義[2]、陳媛媛[3]、劉志揚[4]等的研究。其次,人類學也開始關注不同醫療手段之間的互動,以及當地人的求醫邏輯和原則。這些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有:余成普對侗族村寨的多元醫療研究[5];和柳對納西族村落的疾病與治療研究[6];徐君與李沛容對木里藏族的研究[7];段忠玉、李東紅對西雙版納傣族村寨的多元醫療模式共存現象的研究[8];孫金菊對甘肅回族民俗醫療體系的研究[9];王志清對蒙古族慢性病老人群體的民俗醫療手段研究[10];劉詩謠和劉小珉對鳳凰縣苗族醫療體系的研究[11];張有春對漢族鄉村治病過程的人類學解讀[12]。從這些研究來看,尋求多元化的醫療實踐路徑,不僅是一個關乎世界性的宏大的傳統醫學或現代醫學相結合的醫療問題,同樣也能在微觀的地方傳統治療實踐中找到具體案例。
“斯色那”是涼山彝族社會中常見的疾病類型,是一種地方性疾病認知理念,具有較為多元和豐富的內容:其一,外顯的疾病癥狀,例如嘴歪眼斜、四肢酸痛、關節腫痛等,最為常見的“斯色那”是風濕病;其二,一些在地方具有“污名化”的疾病,例如艾滋病,這一劃分方式主要在布拖地區常見;其三,一些治療難度較高的病癥,例如精神類疾病,這些病癥被稱為是十分嚴重的“斯色那”。這三種情況時常交叉在一起,但歸根結底都是彝人在應對相關疾病時的策略。當地人認為“斯色那”只能被畢摩(彝族社會中的“祭司”)主持的“斯色畢”儀式治愈,治療過程也絕不僅僅是單一的治療策略,其中包含著傳統植物藥運用、心理慰藉、社會救助、飲食禁忌等諸多措施。然而,儀式治療雖在應對“斯色那”疾病時曾發揮重要作用,但在當下也面臨著諸多困境。同時,涼山彝族社會逐漸構建起多元醫療體系,也給了當地人更多的求醫選擇。
2019年6月和2021年7月,本文兩位作者先后兩次到布拖縣城進行田野調查,追蹤當地“斯色畢”儀式主持者拉比畢摩的“斯色那”治療儀式,發現儀式治療曾在當地醫療實踐中形成的權威——“斯色畢”專職化畢摩的產生,以及在地方現代醫療體系的不斷完善中儀式治療不斷面臨困境。2021 年10 月進入美姑縣洛覺村,在當地的醫療發展變化中,發現多元醫療體系正逐漸在彝族鄉村得到建立和完善。結合這三次田野所獲資料,本文將探討彝族社會中儀式治療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多元醫療體系在國家力量參與下逐漸被建構的過程。
一、“斯色那”治療儀式“斯色畢”
“斯色畢”是專門用以治療“斯色那”的各類儀式的統稱。“斯色畢”根據患者病情的輕重緩急產生了相應的治療儀式,常見的有“斯色阿曲畢”“斯色德伙畢”“斯色爾覺畢”“斯色嘎開”等。一般情況下,輕微的病情用“斯色阿曲畢”治療,嚴重者(例如癱瘓)用“斯色爾覺畢”治療,根據病情由輕變重,儀式過程由簡單到復雜。無論舉行哪一種治療儀式,病人痊愈后都必須舉行“斯色嘎開”儀式,以示阻斷病人與“斯色”之間的聯系。其中,“斯色阿曲畢”是最典型和常見的“斯色畢”儀式,其儀式過程如下。
儀式開始前畢摩或主人家需要準備儀式用物。包括豆腐花污、白酒、泥團①泥團:指用來塑泥偶的泥團。斯色畢儀式中的泥偶數量龐大,形象生動,既有人也有動物,既有君臣也有民眾,儼然一個濃縮的世界。、爆蕎花②爆蕎花:彝語音譯稱為“恩補”。苦蕎籽放進燒燙的鍋中翻炒爆開而成,也就是苦蕎做成的爆米花。、牛羊油①牛羊油:指斯色畢儀式過程必須用到的物品山羊、綿羊、黃牛等動物油。也可以用其他的動物油替代,但是禁止用過年豬的豬油。、響竹②響竹:彝語音譯稱為“馬若”。它是畢摩常用的一種臨時性法器。取一節長約80cm 的竹竿,一端剖為5瓣或7瓣或9瓣,握住另一端搖動則發出聲響。、線③線:指“斯色畢”儀式過程使用的線。通常用婦女自己捻的羊毛線,用時染成黑、白、花三色,如果找不到毛線也可用普通的紅、藍、黑線替代。、柳樹枝④柳樹枝:“斯色畢”儀式通常用柳樹枝做神枝。、柴火、接骨草、干辣椒、貫眾、野櫻桃、鵝屎、馬屎等。儀式正式開始時,畢摩念誦著《泥塑擦拭口頭經》,并且拿起泥團在病人身上順時針方向擦拭了3圈,又在病人頭上順時針方向轉3 圈后,用手指在泥團上戳了一個深陷的洞,讓病人往里哈氣3次,最后迅速捏合洞口(疾病轉移),泥團放好備用。助手(通常為患者近親)用鋤頭在空地上挖出一個泥坑,泥坑的四方各辟一條水溝,稱之為“斯色之路”。水溝上方兩側用黑色神簽⑤黑色神簽:指未削皮的神簽。斯色畢儀式通常都用柳樹枝做神枝。設兩道關隘“格疊”,其上設一個除穢架“伙古”⑥除穢神枝:彝語音譯為“伙古”。指兩根神叉插在地上,上面搭上一根神枝,形似一道門。,剩余三條水溝盡頭各挖一個泥坑與之相連接,且在每個泥坑的兩邊都用黑色神簽設一道關隘“格疊”。助手在神座下方燒一堆火,稱為放煙火⑦放煙火:彝語音譯為“母古此”。畢摩做儀式之前一項必須的儀禮,夾火碳放入草把(有時必須用莊稼桿)使燃放出煙火,以示通報神靈,并請天地間的各路神靈前來幫助畢摩,增加畢摩神力。,并在火里放入幾個大石頭燒著。布插完神座后吉克畢摩一邊念經一邊塑泥偶。
畢摩需為儀式塑9 個泥偶:獨腿雄性神怪祖“斯阿普希茲”、獨臂雌性神怪妣“斯阿媽洛茲”、斯色豬偶“斯維色維”、斯色馬偶“斯木色木”、禿頭土鬼偶“得俄勒”、土葬斯色子“地木斯惹”、土葬斯色女“地木斯阿木”、地下界斯色“得斯得色”,穿地斯色“斯布色布”。畢摩每捏好1個泥偶,病人就抓1把爆蕎花先擦拭全身,向爆蕎花哈3口氣,再把爆蕎花塞在泥偶的嘴里、手中、腳上等。神座的4 個泥坑里都先墊上一個圓形的餅狀泥塊,作為泥偶的底座。泥偶塑好后有些直接放在坑中泥塊上,有些則放在泥坑之間的水溝里或是放在坑的洞口。泥偶中有形形色色的殘肢斷臂的“人物”形象和豐富多樣的“動物”形象,整個場景好像是對現實世界的模擬,儀式畫面頓時變得生動起來。畢摩戴上神笠,莊嚴地念誦《斯色畢畢體》經語,仿佛正與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另一個世界在對話與交流。
完成上述工作后,病人在脖子上、手腕上和腳上分別戴上白色、藍色、紅色的線,畢摩念誦《斯色來源口頭經》。在念經過程中,畢摩偶爾用響竹敲打患者身體幾下,一會兒敲打背部、一會兒敲打手臂或腳。病人認真地聆聽著他念誦的經文,不時從面前的袋子里抓起一把爆蕎花擦拭身體各個部位后從頭上順時針方向轉過一圈再丟進面前的泥坑里。約半小時后,助手從火堆里夾起幾塊燒得滾燙的大石頭,放在泥坑中,然后把接骨草、干辣椒、貫眾、野櫻桃、鵝屎、馬屎等幾種“藥物”混合搗碎后,放在燙石上面,泥坑里頓時煙霧四起,病人坐在邊上,埋著頭,把臉對著泥坑里冒出的高溫煙霧熏蒸。助手用羊毛披氈把病人圍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這時畢摩站起來一邊快速念經,一邊用響竹敲打病人身上。煙霧逐漸減少時,助手舀一盆水從下面掀開披氈澆在燙石上面,煙霧量又增加,病人則繼續接受煙霧的熏蒸,這樣重復三四次,直到煙霧量不再增加為止。
“藥物”熏蒸的整個過程,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的時間,但是病人在披氈里一直不停地叫喚著,里面的高溫和復雜氣味似乎讓病人難受不已。熏蒸完后掀開披氈時,病人已全身冒汗,助手迅速填埋泥坑。此后,助手在剩下的3 個泥坑里都放上1 塊燙石,燙石上面都放上羊油,煙霧從泥坑中升起時香氣四溢,燒烤味頓時彌漫開來。病人站起來,從袋子里一把接一把的抓起爆蕎花,先擦拭身體,然后丟進泥坑中,嘴里念念有詞。畢摩念著有關藥物的口碑經,從袋子里抓起一把食粉“匝別”①食粉“匝別”:畢摩在儀式過程中祭祀神靈的時使用面粉或蕎子等物。撒進泥坑里。病人在畢摩的指引下,先走到左邊的泥坑旁,并從袋子里抓一把爆蕎花擦拭身體后丟進泥坑中,然后把洞口的泥偶放進泥坑里,取下戴在腳上的線纏繞在泥坑中的泥偶上,最后含一口酒噴灑向泥坑,再從泥坑上跨過,助手迅速填埋泥坑。病人用同樣的方法再跨過剩下的2個泥坑。總的來說,病人依下、左、右、中的次序跨過4 個泥坑后,助手從火里夾起一個燙石放在上方的水溝里,在燙石上面澆點水,冒出蒸汽時,病人從燙石上跨過,表示除掉了身上的污穢。病人從上方水溝中間走到除穢架時,把上面的神枝拿開,等病人通過除穢架后,畢摩口誦《除穢口頭經》立即封鎖關隘,以示隔斷病人和“斯色”之間的關系,“斯色”不再作祟于病人。最后,畢摩搗毀神座用物于原地,“斯色畢”儀式到此結束。
畢摩作為“斯色畢”儀式的治療者,在為患者治病時,要將前人在治療實踐中創造和積累的醫療方法和經驗加以應用。為提高治病療效,“斯色畢”儀式治療過程除了使用念祝詞、巫術儀式外,還涉及地方性的植物藥知識。畢摩熟悉和了解當地人的疾病特征、體質、飲食習慣、氣候特征、民風民俗等,能更好地把握病人的心理,并在儀式過程中使用病人熟悉的病因解釋和治療方法,強化病人對自己醫術的信賴和對治療效果的認同,從而達到幫助病人解除病痛的目的。畢摩一方面不斷繼承和總結前人的醫療實踐和經驗,另一方面又不斷加以探索和實踐,他們親自采集和使用各種動植物藥,了解它們的藥性和功能等。同時摸索、積累了多種行之有效的醫療術,并將其融入儀式治療過程中,如蒸療、熏療、敷療、針刺、沸油洗身、吹傷口、噴酒等。在“斯色畢”治療過程中,畢摩除了展示其儀式技巧外,還在治療實踐中通過“草木浴”“熏蒸”療法等方案來緩解患者的病癥。
二、儀式治療的短暫春天:出現專職化治療者
在傳統彝族社會中,畢摩通曉地方各類知識,長期以來擔負著治病救人之責。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畢摩群體內部都未出現明確的醫療分工,每一位學有所成的畢摩幾乎都可以在儀式治療的路徑下應對諸多疾病,這也使得當地人的醫療實踐長期處于“巫醫”結合的狀態,通常只能被歸入到文化實踐的范疇。同時,基于多年的“求畢”經驗,當地人普遍認為不同家庭和患者都有其合適的畢摩,因此某位畢摩即便被認為是治療“斯色那”的高手,有時候也不一定能治好所有患者的病癥。這些文化觀念限制了畢摩在某個儀式或治療領域的專業化發展。當然,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當地人還是會根據畢摩在應對疾病時的表現和治療效果,形成“某個畢摩擅長應對某類疾病”之類的話語共識。然而,布拖縣拉比畢摩在過去許多年曾是治療“斯色那”的專職畢摩,他在自家院子而非前往患者家中舉行儀式。他的院子就像一個儀式治療的“診所”,由患者自行前來接受治療,然后支付一定的報酬。
(一)鬧市中的“斯色畢”儀式
傳統的“斯色畢”儀式主要在河邊舉行,這符合當地人對“斯色”這一致病怪靈的認知(認為其多來自河流或沼澤)。畢摩、患者和家屬通常選擇人跡罕至的河邊空地,迅速搭建儀式空間,并心無旁騖地治療“斯色那”。而在布拖縣城,拉比畢摩的“斯色畢”儀式顯然與其他畢摩有所不同,多年來他深居城市,已很少外出,在車水馬龍與鋼筋混凝土的鬧市中等待慕名而來接受儀式治療的“斯色那”患者。在這里,儀式治療已被打上深深地“現代”烙印,無論是患者所患病癥,還是畢摩的治療方式,都明顯超出了傳統的“斯色那”疾病與治療范疇。原本被認為是十分重要的儀式地點,在這里逐漸被忽視;那些看似不太符合傳統“斯色那”病癥的患者,也被送來接受儀式治療;接二連三的患者可以在同一天同一塊場地接受相同程序的儀式治療。從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到,疾病或儀式治療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已經具有超越傳統的意義和內涵。鬧市中的“斯色畢”并非只是簡單的治療身體上的傷痛,也暗含著當地人對某種疾病的束手無策,同時也是他們應對社會危機的生存或生活之道。
據拉比畢摩稱,每到臨近適應舉行儀式的吉日(布拖地區認為狗日、虎日、馬日最佳),都會有患者家屬提前打電話聯系他。儀式中常見的“斯色那”包含各類疾病,有風濕病、腦梗、腦膜炎、精神疾病、艾滋病等,其他各類病癥倘若符合“斯色那”內容,也順理成章需要舉行“斯色畢”儀式。拉比畢摩從不為患者占卜(“斯色那”疾病判斷大都由畢摩進行占卜),在他看來自己占卜并自己舉行治療儀式顯得沒有說服力,因此找他主持“斯色畢”儀式的患者和家屬都是自行尋找其他途徑占卜確定為“斯色那”后才來找他治療。倘若患者接受儀式治療后病情無明顯變化,當地人通常也會將其歸咎為占卜有誤而非儀式無效。正因如此,拉比畢摩的名聲在那些被治愈的案例中不斷被傳播向各地,許多家屬開車載著無法站立行走的患者從涼山各地趕來,只為能夠找尋一種減輕病痛的途徑。鬧市中的“斯色畢”儀式,顯然多了一些治療“城市疾病”的意味,許多近幾十年來才頻發的病癥已遠遠超出涼山彝人的傳統疾病認知范疇。因此,“斯色畢”專職畢摩的產生,既是城市彝人不斷增加后地方社會對儀式治療的渴求,也是當地人在遭受諸如艾滋病等“城市疾病”傷害后的應對策略。當地人需要通過儀式治療來減輕社會對自己可能造成的進一步傷害——避免疾病帶來的社會污名,獲得一定的心理慰藉。
(二)“生意”漸少的儀式治療“診所”
隨著縣城內艾滋病防治措施和醫療水平的不斷加強,拉比畢摩的病人數量逐年下降,特別是艾滋病患者已很少接受儀式治療。2019年,第一次進入布拖縣城參與拉比畢摩主持的“斯色畢”儀式時,還能接觸到一些前來接受儀式治療的艾滋病患者。等到2021 年再去時,這類患者已經沒能再遇到。拉比畢摩的“生意”也不再如往年那般興旺,到適合舉行儀式的吉日時,原本門庭若市的場景如今有些蕭條,通常只有一兩位患者前來,全然沒有了當年少則三四個、多則近十位的盛況。
拉比畢摩將“斯色那”患者數量的減少歸咎為當地彝人對現代醫學的依賴,以及對快速生活的追求。這一解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說明當地人對現代醫學的認知和信任越來越深。此外,近些年來地方政府通過強有力的艾滋病防治措施,不僅使現有患者得到了優質的醫療資源,也有效遏制了艾滋病的傳播,更讓當地人對艾滋病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
據布拖縣政府醫療衛生發展報告顯示:
截至2021 年,全縣感染者/病人治療覆蓋率、病載檢測率、治療成功率從2017 年前的52.11%、86.8%、62.6%分別提升至97.01%、97.03%和95.96%,母嬰傳播率由最高的7.9降至3.6%,單陽家庭配偶陽轉從9.99/百人年降至0.9/百人年,感染者/病人新報告人數顯著下降(2017年度新報告958人,2021年1-9月新報告267人)。
這些數據表明:首先艾滋病疫情增長態勢在布拖縣境內已經得到了有效遏制;其次,政府對艾滋病患者的管理和服務措施愈加完善;最后,無論是政府工作人員還是普通民眾,當地人對艾滋病的認識越來越成熟。
針對“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當地衛生部門制定了多項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建立鄉鎮家庭醫生團隊,定期到所負責的鄉鎮衛生院開展技術指導、業務培訓、診療和巡診,帶動鄉鎮衛生院服務能力提升;提高家庭醫生服務率和貧困人口免費健康體檢覆蓋率;規范慢性病的防控工作,擴大慢性病篩查和宣傳覆蓋面,促進慢性病患者規范化管理,降低慢性病患者費用報銷程序和費用負擔。筆者遇到的患者們在談及治病難問題時,均表示近些年已經“住得起院、看得起病”,“對醫院和醫生越來越了解了”。這些措施表明地方政府正在直接介入到鄉村醫療衛生發展和民眾的身體健康問題,從而讓國家醫療衛生的發展成果惠及底層民眾。同時,醫療資源和醫學知識也逐漸滲透到了廣大農村地區,將極大改善當地人的就醫環境,完善當地人的醫療認知。
綜上來看,“斯色畢”專職化畢摩在布拖縣城內產生,與當地艾滋病問題、醫療衛生發展狀況、社會經濟水平、個體或家庭疾病經歷等諸多因素有關。當地彝人對“斯色畢”儀式的需求,既是對文化信仰和傳統醫療認知的實踐,也是因為他們在遭受現代頻發的各類疾病時,限于多方面的條件約束而不得不選擇的治療路徑。隨著國家、政府力量在鄉村醫療領域的直接介入,以及醫學常識的廣泛普及,民眾的現代醫療認知將不斷得到完善,儀式治療的“萬能性”和曾經的治療權威會不斷被減弱。同時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當地人對疾病分類的認識不斷提升,“斯色那”的疾病范疇也將進一步被縮小——至少艾滋病這類疾病將逐漸被移除。
三、儀式治療的現實困境:儀式簡化、重程序輕藥物
涼山彝人的一生都與儀式有著密切聯系,生時有各類治療疾病的儀式,面對死亡時需要通過“尼木措畢”儀式來應對生命危機、整合集體力量[13]。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約束,儀式治療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涼山彝人解決疾病問題的首要選擇,而在彝區社會的快速轉型中儀式治療也凸顯困境。一些畢摩在儀式治療過程中只注重儀式本身,而忽視了植物藥、儀式與身體之間存在的聯系,也無法理解儀式過程對患者的社會文化意義。這些問題反映出的是,畢摩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傳承和發展中遭遇了諸多困境,其中尤為明顯的是畢摩的知識傳承問題。原本世襲相傳的畢摩,即便今天打破這一血緣枷鎖也已很難找到合適的畢摩衣缽繼承者。新興的畢摩群體對傳統知識越來越缺乏系統化的學習過程,造成許多畢摩已無法全面掌握地方性知識,包括醫藥地理知識、儀式儀規知識、歷史經文等。例如,“斯色畢”儀式治療過程中,畢摩的植物藥使用本是十分關鍵的儀式環節,然而,對于年輕一代的畢摩來說,他們只關注儀式和經文,而忽略了祖先傳下來的植物藥知識。這也造成今天的畢摩儀式治療只能起到慰藉患者心理或改善患者社會關系的文化價值(這一價值甚至也沒有被一些畢摩意識到),逐漸失去了其本身具備的生物或藥學價值。
(一)不斷簡化的儀式過程
從布拖和美姑地區幾十場“斯色那”治療儀式中不難發現,儀式過程正不斷被簡化,其簡化方式包括減少儀式時間、儀式材料、經文內容等。美姑縣被認為是目前涼山傳統畢摩文化保存最為完整的地區,境內有上千名彝族畢摩,成立了“中國彝族畢摩文化研究中心”,是研究畢摩文化的前沿陣地,每年都會有諸多學者慕名而來。就當前的實際狀況來看,這里的畢摩文化氣氛雖十分濃烈,但當地的畢摩也承認儀式過程已經不斷被改變或簡化。例如洛覺村的類類畢摩在儀式過程中遭遇大雨后,直接跳過多段經文,把儀式結尾草草做完,他的解釋在于只要有這一心意和行為,經文念誦多少并不重要。在布拖縣城,拉比畢摩自豪地說他曾在一天時間內完成12 場“斯色畢”儀式,從早到晚不停歇。這一數據是驚人的,因為每場“斯色畢”儀式從準備各類材料、布置儀式空間到儀式結束,最少需要兩個小時,倘若不是儀式環節和內容的簡化,即便不吃不喝,一天時間也無法舉行12 場儀式。儀式過程簡化,既是當代畢摩做出的改變,也符合彝人在快速社會變遷和生活節奏中的文化實踐需要。一方面,畢摩在快節奏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自己的其他工作需要完成,他們無法專注于只做畢摩事業。例如達果畢摩雖是美姑縣畢摩文化協會主要負責人,被稱為是當地最有權威的畢摩之一,但是他還經營著其他諸多產業,包括畜牧養殖、農業種植等,在當地他也是致富代表。另一方面,許多彝族家庭也希望畢摩儀式能夠快速結束,不要過于復雜。他們在回憶曾經的儀式時,總是抱怨時間過長,“一到后半夜孩子大人都困得不行,不知道那時候為什么儀式時間那么長”。原本神圣的儀式,現在只被作為一項不得不遵從的“傳統”,并且如今也需要考慮儀式的經濟和時間成本。
當地人在逐漸失去理解畢摩文化的能力、并無法形成新的文化共識后,儀式的力量在應對疾病危機時或許將大打折扣,而畢摩文化活動最終也只能被認為是一種“迷信”行為。當然,即便是不斷簡化的畢摩儀式,如今也是在彝族社會文化不斷受到現代性沖擊后,當地人所能保留和參與的為數不多的文化實踐方式。
(二)本土藥物知識“失傳”
涼山彝區有著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特別是美姑縣,境內屬低緯度高原性氣候,立體氣候明顯,四季分明,年均氣溫11.4℃,常年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十分有利于各類動植物的生長。據官方資料顯示,美姑縣野生動物和野生藥材種類繁多,野生動物有187 種,分屬62 個科;受國家一類保護的動物大熊貓等5 種,二類保護的有獼猴、小熊貓、白腹錦雞等27 種。野生藥材主要品種有103種,其中名貴藥材有天麻、貝母、蟲草等。僅在洛覺村內,我們便發現了30 多種具有藥用價值的植物。例如當地的珠芽蓼,就是一種傳統的中藥藥材,藥用部位為根狀莖,具有抑菌、抗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臨床上主要用于止瀉,尤其對腸炎、細菌性痢疾、嬰幼兒腹瀉屬大腸濕熱者,具有較好療效。當地的一些彝族老人還能夠掌握多種植物藥功效,特別是祛風利濕、止痛消炎類植物他們更是如數家珍,這也是他們對所處自然環境的生存反應。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這些老人經常隨手摘下幾片葉子,然后告知我們這類植物的藥用價值。然而,具備這類地方知識的當地人已經屈指可數,如今這些老人大都已經70 歲以上,等到他們離開人世,這些知識將有面臨“失傳”的可能。老人們也經常感慨祖輩留下的植物藥知識現在已經無人問津。
“巫醫”結合一直以來是畢摩儀式治療的主要特點,二者被視為同等重要,因此畢摩也是彝族藥物知識的重要傳承人和實踐者。然而,近些年來,許多畢摩對儀式所需藥物已無法完全掌握,儀式過程重“巫”輕“藥”,大多數時候都抱著“只要有一些就可以”的態度。“斯色畢”儀式中運用了大量本土植物藥,盡管當地人更強調儀式治療的文化和社會意義,但是這些藥物曾以文化實踐的方式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健康。而在當下的儀式治療中,植物藥大多數時候只被作為一種儀式道具,畢摩、患者和家屬更在意其象征意義,而很少去關注它們的藥用價值。在拉比畢摩主持的“斯色畢”儀式中,“熏蒸”所用藥物少則只有五六種,多則八九種,找不到某類藥物時,也可以用其他外形相似的物品替代。例如,蛇皮是某些“斯色畢”儀式中常用的藥材,但是一到秋冬季節蛇皮難覓,無奈之下,有些畢摩便讓主人家準備一根相似的繩子替代,他們很少認為這一替代會影響治療效果。洛覺村的達果畢摩則十分清楚這些藥物的價值,認為畢摩的儀式治療倘若沒有任何藥物知識做支撐,不可能堅持到今天,“以前優秀的畢摩都很清楚山上的這些藥物,有時候都有自己獨特的秘方”。目前年紀較長的畢摩(特別是美姑縣的畢摩)即便無法完全掌握,也還能運用一定的藥物治療方法,而下一代畢摩還能否具備這類知識已是無法預料之事。當然,誰愿意和誰能成為下一代畢摩已經是文化傳承面臨的首要困境。
(三)成為下一代畢摩:誰愿意,以及誰能?
彝族畢摩文化在官方話語體系中早已得到承認,如今擁有“尼木措畢”祭祀、畢摩繪畫、畢摩音樂等三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涼山畢摩文獻一項國家級檔案遺產名錄,以及畢摩剪紙、畢摩泥塑、“吉覺”彝族譜等若干項省、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也有了一定數量的實錄音像、搜集整理、翻譯注釋、田野調查、調查研究等各方面的成果。然而,這一包含著彝族諸多優秀內容的文化綜合體,如今也面臨著誰愿意、以及誰能成為下一代畢摩的現實困境。這些困境直接影響了畢摩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在畢摩傳承這一問題中,誰愿意成為下代一畢摩是擺在彝族社會的首要問題。傳統彝族社會,畢摩作為一種重要的職業,很少面臨誰愿意成為畢摩的問題,那些具有畢摩血緣的男性,都被認為擔負著傳承畢摩文化、守護一方安寧的職責。而在當下,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畢摩已經不再是村落中必須有人從事的職業,新一代年輕人甚至不承認這是一種可以謀生的職業。以洛覺村為例,目前全村近30名畢摩,年齡結構偏大,90后年輕人不愿意繼承父輩的畢摩事業,紛紛投身其他行業。畢摩原本需要將自己的畢生所學傳授給下一代,但如今他們也不愿意自己的兒子首選畢摩作為職業,他們在培養自己的孩子時,更愿意將其培養成國家“干部”,而非畢摩。只有那些學習成績較差,又無其他生存技能的孩子,老人們才會建議他們成為畢摩。與其他生活和發展路徑相比,成為畢摩在當下已經顯得毫無誘惑力。
年輕一代彝人不愿意成為畢摩反映出他們深受現代生活和職業觀的影響,已經很難將畢摩視為出人頭地的成長途徑。同時,彝族社會之間的流動性也越來越強,美姑的畢摩到西昌或西昌的畢摩到美姑主持儀式已經不是很難實現的事情。然而,深入了解畢摩文化的內容和傳承機制就能發現,成為畢摩并非易事,在“不愿意成為畢摩”的背后同樣有“誰有能力成為畢摩”這樣深刻的問題。一名合格的畢摩,應該掌握經卷文獻、法器法具、泥塑草偶、犧牲用物等基本儀式技能,而優秀的畢摩還要理解畢摩文化中包含的彝族哲學思想、社會歷史、語言文字、天文歷算、歷史地理、人倫規范、法規約定、文學藝術、風俗禮制、征伐戰事、農業畜牧、醫藥衛生、彝族譜牒等綜合性知識。這些知識的學習過程需要花費諸多時間和精力,甚至要為此付出一生,當地人認為這比在當下的教育體系中培養一名大學生更有難度,倘若現在的年輕人有他們當年學習畢摩文化的恒心,并將其付諸當下的學校教育中,那么也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大學生或是受人尊重的“干部”。因此,村子里有能力的年輕人通常認為在大致相同的時間、精力和經濟付出下,成為榮耀家族的大學生和國家“干部”,遠比成為一名畢摩更具有意義,更能在當下社會獲得承認。而對那些不思進取者,即便他們愿意成為畢摩,最終無法成為或只能成為一名主持簡單儀式的畢摩。隨著當前彝族社會對個體成才的評價體系和職業觀的變化,那些具備天賦的年輕人也最終只能被埋沒于學校教育中,錯過了學習畢摩的最佳年齡。
四、地方醫療發展中的多元求醫路徑
“斯色那”的儀式治療過程十分復雜,個體在其中有著一定的參與感與主體性,并且能夠在當地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產生互動效應,進而使患者成為整個村落的同情與幫助對象。因此,現代醫學雖已經成為涼山彝區最為重要的醫療路徑,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的儀式治療方式在今天受到了當地人的“冷落”。作為一種對現代醫學的補充,儀式治療在人們無法完全被現代醫學治愈的情況下,仍發揮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也使其成為傳統文化與現代醫學之間有效互動的重要橋梁。然而,儀式治療在彝區盛行的原因不僅在于文化和信仰實踐,還是因為當地存在現代醫療資源缺乏、醫學常識不夠普及等問題。同時,隨著現代各類新型“城市疾病”逐漸超出當地人的認知范疇,畢摩的傳統儀式治療已難以獨立為當地人提供求醫需求。在此現狀下,如何讓當代彝人在遭受各類疾病問題時獲得多元醫療路徑,顯得尤為重要。
(一)儀式治療作為一種補充
涼山彝人在日常生活中遇見疾病時,去醫院還是請畢摩從來都不是個難題。他們往往根據生活經驗選擇“最佳”的治療方式,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發病第一時間立即去醫院就診即可痊愈,例如一些急性疾病,腸胃炎、呼吸道感染等。第二,發病第一時間先去醫院接受治療,待病情穩定后請畢摩在家中做儀式,兩者結合效果最佳,例如車禍、刀傷等意外傷害。彝人認為,外傷第一時間在醫院處理病情會馬上得到控制,不會加重傷口感染,但手術之后往往疼痛難忍時需要做儀式治療,可使疼痛得到減緩,也能祛除身上的“晦氣”。第三,發病第一時間請畢摩做儀式治療,如果先去醫院,將導致疾病終身不愈;例如“斯色那”,當地人認為只能由畢摩“斯色畢”治愈,如果去醫院打針或是輸液就終身不愈,嚴重者可能會導致癱瘓。對現代醫學的懷疑態度在當下的涼山社會依舊存在,有些患者選擇去醫院反而是一種“無奈之舉”,是他們在接受儀式治療無效后的擇醫行為。因此,彝人對儀式治療有效性的認可與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以及彝人在尋求現代醫學時的失敗經歷交織在一起,他們有時候會認為可以求助于現代醫學,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已經失去對本土儀式治療手段的信任。這種復雜情緒的根源從當地有限的醫療資源中能夠看到一些端倪。
美姑縣的醫療資源在長期一段歷史時期內都處于相對匱乏的境地,能夠治療的病癥十分有限。在醫院提供的近幾年住院統計單子中,列出了51種病例,其中患有支氣管肺炎、肺部感染、急性支氣管炎、慢性胃炎、肺炎等5類疾病的患者數量最多。具體統計如下。
2017 年全年,住院病人總數1 7471 人,其中支氣管肺炎2 124 人,肺部感染833 人,急性支氣管炎558人,慢性胃炎482人,肺炎444人;這5類約占25.4%。2018年全年,病人總數量14 949人,其中支氣管肺炎1 959人,肺炎485人,肺部感染473人,急性支氣管炎348人,慢性胃炎307人;這5類約占23.9%。2019年1月到2019年8月,病人總數量11 096人,其中,支氣管肺炎 1 264 人,肺部感染 480 人,肺炎 299 人,急性支氣管炎 232 人,慢性胃炎 174 人;這 5 類約占22%(此數據由美姑縣醫院提供)。
這些統計數據表明,無論是在鄉衛生院還是在縣城醫院,住院就診的病例中并無包含在“斯色那”范疇內的病癥。這種現象既與當地醫療資源短缺相關,同時也表明當地人認為現代醫學對“斯色那”的諸多病癥無從下手,因此很少求助于它。更為重要的是,“斯色那”的相關病癥實際上都是慢性疾病,以現代醫學目前的發展還無法完全根治,這也進一步將患者推向了儀式治療。據當地醫生介紹,近些年來在國家“精準扶貧”的政策支持下,外來專家對口幫扶縣醫院,極大提高了他們的治療水平,但設備條件落后、缺少藥物,使得他們在面對許多疾病時仍束手無策。例如風濕類疾病,縣醫院除了必要的止痛藥外,無其他藥物可以提供給患者,并且這類藥物往往價格較高,當地人限于財力很少能求助于醫院。即便人們能夠獲得藥物,但這類病癥無法完全被生物醫學治愈,時常會復發,使得當地人在面對“斯色那”時越發傾向于成本較低、但具有一定療效的“斯色畢”儀式。
目前,國家的醫療體制呈現出多個不同的醫療體系并存的局面,而并非純粹地混合在一起[14]。同樣,在地方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美姑縣,多元化的病因解釋和治療方式正逐漸得到當地民眾乃至醫生的認可。當地醫院的漢族醫生見到彝族患者時,首先會用彝語問,“怎么樣,哪里不好,發燒嗎,病了幾天,頭痛嗎?”,進而問患者,“你是不是得了‘冉’?”(“冉”是彝族人對某類疾病的認識和理解,很多當地彝族人其實也不一定知道這是什么病)。遇到風濕類疾病,周醫生會問,“來醫院之前有沒有做‘斯色畢’儀式,沒有的話回去了還是做一場”。他認為,“疾病的治療三分靠藥物,七分靠心理因素和個人體質”。可見,民間的儀式療法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當地醫生所認可。當地方醫療活動能夠被納入解釋病因或治療疾病的多元醫療體系中時,本身就證明了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從涼山彝人不斷在儀式治療和現代醫學之間“周旋”的案例可以看到,多元醫療體系之間的互動不僅意味著人們在求醫過程中有了更多的選擇,還表明不同醫療體系下的治療者也希望患者獲得多元治療方式。這樣的醫療格局能夠給我們的啟發是:彝區醫療體系的建立不應僅僅只是依賴于西醫,還要借助傳統儀式治療的社會文化力量和本土彝族醫藥的發展才能較為全面地服務于當地人的醫療實踐過程。畢摩可以成為現代醫學的參與者,而醫生也可以借助畢摩的許多話語和文化手段來傳播醫學知識、反思醫患關系、關注患者疾痛問題。近些年來,彝族本土醫藥和現代醫學的同步發展,讓我們看到了多元醫療體系在涼山不斷得到完善的可能。
(二)彝族醫藥初步發展
不同于藏藥、苗醫等民族醫學的發展進程,彝族醫藥起步較晚且發展較為滯后,目前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族醫藥較有代表性,而涼山彝族醫藥仍處于起步階段。關于云南楚雄彝族醫藥的發展進程,高金榮和楊本雷的研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和總結[15]。在楚雄彝族醫藥不斷發展的同時,2014 年9 月,西南民族大學首屆中藥學(彝藥)專業招生,標志著彝族醫藥開始被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中,為培養專業性彝醫人才奠定了基礎。截至2021 年,西南民族大學彝族醫藥專業共招收253 名學生,其中四川223 名,貴州29 名,云南省2 名(本數據由西南民族大學藥學院提供)。這些彝族醫藥專業學生,一部分在畢業后得到了繼續讀研深造的機會,將成為這一領域的重要后備力量。相比于楚雄地區,涼山彝族醫藥仍有一定發展差距,但近些年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也獲得了一些發展機遇。在社會各界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2021年3月,涼山州中西醫結合醫院正式掛牌為四川省彝醫醫院,與此同時,涼山州9 個彝族縣建成的“中彝醫醫院”以及西昌彝醫藥研究所、涼山州彝醫藥研究所等醫療和科研機構不斷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獲得了一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此外,據涼山政府統計顯示,截至2021年,當地擁有藥用植物2448種,藥用動物有91種,中藥材資源蘊藏量占四川省總量的20%,其中優勢中藥材品種有川續斷、重樓、附子、艾草等,且中藥材標準化種植基地近14萬畝。近些年來,在“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中,一些地方政府抓住機遇,開始利用涼山獨特的自然環境種植植物藥,發展醫藥產業,在不斷完善地方醫療體系的同時,也帶動了新興產業經濟的崛起。
隨著各類科研成果不斷出現,彝族醫藥也在實踐中得到了檢驗。劉圓、阿子阿越等彝族醫藥研究者深入到涼山彝族聚居區進行田野調查,訪談村子里的老彝醫家,收集彝族民間傳統醫藥經驗與常用動、植、礦物標本1 000 多份(“斯色畢”儀式所用植物藥幾乎都包括在其中),秘方1 000 多個。他們將這些收集到的秘方及動植礦物藥反復進行科學分析、整理、藥物制劑工藝改進、動物實驗、臨床驗證,從而探索與積累了一些對痛風、風濕類風濕、面癱、脫發、乳腺小葉增生、急慢性咽喉炎、淋病、皮膚病、骨病等各種疑難病癥的治療經驗與特效處方。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他們治愈了個別權威醫院未治好的某些疾病,如不孕不育癥、生殖器疾病、性病、骨傷、痛風、風濕、類風濕、乳房包塊、急慢性咽喉炎等,其中最多的是痛風、風濕、類風濕病患者最多[16]。而這些他們提及的被彝族醫藥治愈最多的病癥(痛風、風濕、類風濕病),都屬于本文所關注的“斯色那”范疇,這表明“斯色畢”儀式所用植物的“有效性”在彝族醫藥的治療實踐中得到了初步檢驗。
從涼山彝區“斯色畢”案例中不難發現,在民俗醫療儀式過程中,“求藥”和“求巫”通常被認為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巫、藥并用是民俗醫療療效得以實現的重要方法。隨著彝族醫藥理論在生物科學視野下獲得發展,并嘗試在醫院中治病救人,表明曾經“巫醫”結合的傳統治療方式如今也開始被納入現代醫療體系中。與傳統醫療不同的是,弱化儀式過程而注重對傳統醫藥知識的動態傳承和科學運用,如今已成為彝族醫藥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共識,并被認為是彝族醫藥能夠在現代多元醫療體系中獲得長足發展的主要路徑。當然,彝族醫藥的發展任重道遠,還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理論構建、理論與現實結合以及人才培養等問題。
(三)鄉村醫療快速發展
從美姑縣的醫療發展資料中,可以發現地方政府針對鄉村醫療問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特別是在貧困人口救助、健康體檢以及疾病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現代醫療資源向鄉村傾斜,并幫助當地人獲得新的醫療認知和醫學常識。
首先,實施貧困人口醫療救助扶持行動,確保所有人獲得就醫機會。具體救助人數與資金投入如下:
2016 年- 2019 年衛生扶貧基金救助貧困人口6 541 人次,救助金額281.48 萬元,2020年1 - 10 月衛生扶貧基金救助貧困人口19 358 人次,救助金額969.10 萬元;2016 年- 2019年四川省醫藥愛心基金救助貧困人口47人次,救助金額16.84萬元,2020年1月至今四川省醫藥愛心基金救助貧困人口631 人次,救助金額54.54 萬元;2020 年政府資金兜底救助貧困人口5 521人次,兜底救助金額415.082萬元。2021年1月-2021年8月,衛生救助11 373人次,累計949.1 萬元。始終確保貧困人口縣域內住院維持治療醫療費用個人支付占比均控制在5%以內(這些數據由美姑縣政府提供)。
涼山彝人依賴儀式治療并不意味著他們不愿意接受現代醫學,而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患者無法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特別是面對一些重大疾病時,他們更加束手無策。因此,面對那些無能為力的疾病,他們只得求助于儀式治療,并寄希望于此。當他們與現代醫學之間的鴻溝逐漸被拉近后,到醫院就診治療將成為一種常態。
其次,推進貧困人口免費健康體檢,引導當地民眾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問題。在涼山彝人的傳統疾病認知中,預防疾病通常是一種文化觀念和行為,而非關注人體的生物變化。這也導致長期以來彝人在生活中樂于“占卜”預知自己的身體問題,而很少有意識去醫院接受健康體檢。因此,當地政府實施免費健康體檢的意義,不僅在于提供公共福利,還有利于引導當地人關注身體的生物變化,從而及時發現可能面臨的疾病問題。
最后,培訓貧困地區健康管理員,對慢性疾病或重大疾病患者進行管理服務。健康管理這一理念在彝族鄉村社會長期以來存在,在進行儀式治療時,畢摩通常會在約束患者的日常飲食習慣方面發揮著作用;同時,患者家屬或其他社會關系,也會就患者的疾病形成一定的共識,時刻提醒患者注意自己的行為。當患者的疾病通過儀式治療得到社會關注后,社會的集體約束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健康管理角色。如今,健康管理被納入行政體系中,其約束力和服務能力將呈現出專業化、規范化特征。當地政府每年培訓20 名健康管理員,采取各類干預策略,對重點人群和性病患者進行分類干預和管理。例如開展風濕病、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壓、糖尿病患者、高原性心臟病患者管理,制定相應管理服務規范,開展針對性防治知識宣傳。
在“精準扶貧”的各項政策支持下,鄉村醫療設施、人才培養、健康管理、醫學常識普及等方面均有了明顯改善。當求醫之路變坦途后,當地彝人在多元醫療路徑中,從注重儀式逐漸轉變為求醫為先。與此同時,自2019 年底開啟的疫情防控工作,促使行政力量和現代醫療資源進一步深入涼山鄉村,雖暫時影響了鄉村醫院對民眾的疾病治療工作,但也讓鄉村醫療條件在這兩年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機會。
五、結語
醫學人類學在分析同一社會中的不同求醫選擇時,提出了“多元醫療模式”(medical pluralism)的概念,認為這一模式能更好地說明人類對待疾病的態度與策略。這一模式在解釋當代彝族社會的醫療實踐時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多種醫療體系和醫療資源在涼山實現了共生、共存。所不同的是,在探索多元醫療路徑時,涼山彝人最初持有注重儀式治療、現代醫學為輔的態度。在圍繞“斯色那”疾病形成的醫療認知和治療實踐中,彝人認為疾病被治愈是因為儀式,而藥物很少被認識和強調。與此同時,由于儀式治療在面對一些疾病時展示出一定的社會意義,使得專職化儀式治療者在涼山嶄露頭角。在行政力量的干預下,隨著地方醫療資源的快速發展、醫學知識的普及,涼山彝人的醫療認知不斷得到完善,在多元醫療路徑中注重“求醫為先”成為新模式。
可以預見的是,涼山彝族社會中諸如“斯色畢”之類的儀式治療并不會因為現代醫學的快速發展而迅速消失,而是作為一種輔助性治療方法,發揮其社會與文化意義的作用;同時,在具體的疾病治療中,科學的藥物治療將更受到彝人的青睞。這些藥物,不僅來自西方醫學,而且來自各類中國傳統醫學,例如彝族醫藥也將在醫療實踐中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