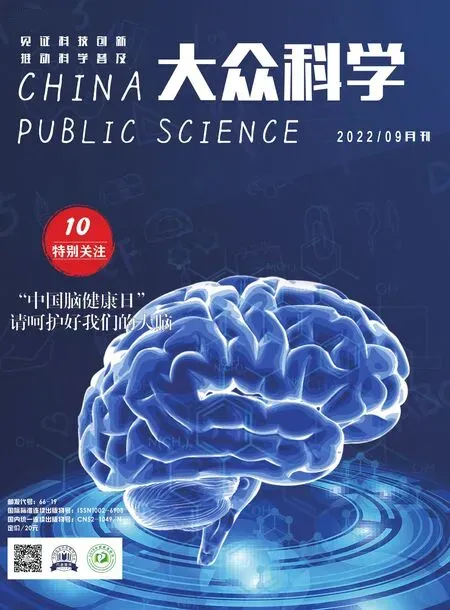腸道和大腦之間也有“交流”
早在十年前,有人告訴你肚子里的細(xì)菌可以影響你的心情和你的行為,你可能認(rèn)為這個人在忽悠。而最近五年,人們改變了這種看法。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腸道微生物通過腸-腦軸調(diào)控大腦的功能和行為。腸道也稱作人的“第二大腦”。
大量的動物和人體實驗證明:腸道菌群與大腦通過自主神經(jīng)、腸神經(jīng)、免疫系統(tǒng)、腸內(nèi)分泌信號、神經(jīng)遞質(zhì)、支鏈氨基酸、膽汁酸、短鏈脂肪酸、脊髓、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肽聚糖等途徑和介質(zhì)進行雙向交流,腸腦和大腦可以相互影響。
通過大人群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消化性潰瘍疾病和其他胃腸道疾病都可能與重度抑郁癥存在顯著聯(lián)系。胃腸道疾病的四種消化表型(PUD,GORD,PG M和IBS)與抑郁癥狀、重度抑郁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神經(jīng)質(zhì)以及失眠等神經(jīng)性疾病存在正相關(guān)。
這個結(jié)果證明了神經(jīng)系統(tǒng)與胃腸道疾病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這兩類病可能具有遺傳相似性。
研究也再次證明了,菌群參與多種神經(jīng)相關(guān)疾病。不僅僅是疾病、情緒和欲望,也和腸道菌群相關(guān)。胃腸道疾病可能會引起患有抑郁癥的風(fēng)險,反之亦然。服用引起嚴(yán)重抑郁的相應(yīng)藥物可能會導(dǎo)致胃腸道疾病的發(fā)生。同樣,如果腸道疾病好了,相應(yīng)的抑郁癥狀也會跟著改善。
腸道和大腦的相互影響受多種因素調(diào)節(jié),環(huán)境、飲食、遺傳、壓力等因素都能影響菌群-腸-腦軸。所以,在將來,用藥物治療身心疾病將不是解決病痛的唯一途徑,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再加上腸道菌群或許將是人們需要重新思考的影響因素。
腸道菌群可以調(diào)節(jié)機體的情緒、認(rèn)知、記憶等,并且與焦慮、抑郁、自閉癥、多動癥、阿爾茨海默病等神經(jīng)疾病存在密切關(guān)聯(lián)。
動物研究表明,腸道菌群還能影響后代大腦健康。無菌飼養(yǎng)、使用抗生素治療或其他環(huán)境因素都能造成母體微生物組或出生后的早期微生物組改變,可能會導(dǎo)致子代的大腦免疫、血腦屏障通透性、大腦結(jié)構(gòu)和神經(jīng)回路在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元的產(chǎn)生、特性和成熟方面出現(xiàn)異常。這些影響會持續(xù)到成年,并易導(dǎo)致長期的行為缺陷。
也就是說,在神經(jīng)發(fā)育的關(guān)鍵窗口期4歲之前,維持微生物組平衡至關(guān)重要。那么腸道菌群是如何影響腸道與大腦之間的交流呢?
途徑1:免疫系統(tǒng)
腸道菌群與腸道免疫系統(tǒng)之間存在密切的互作。包括代謝產(chǎn)物(例如短鏈脂肪酸 SCFAs)和膜成分(例如多糖 A)在內(nèi)的微生物組成分均可影響免疫穩(wěn)態(tài),形成促炎或抗炎的局部免疫反應(yīng)。
腸道菌群還可以調(diào)節(jié)位于大腦的免疫細(xì)胞——小膠質(zhì)細(xì)胞的發(fā)育、成熟和功能。
在神經(jīng)炎癥的背景下,血腦屏障通透性的改變,可促進微生物組分通過這一屏障,以及外周免疫細(xì)胞對腦實質(zhì)的侵襲。中風(fēng)等疾病引起的大腦炎癥會改變腸道菌群的組成,從而導(dǎo)致惡性循環(huán)——腸道菌群失調(diào)進一步加劇神經(jīng)免疫反應(yīng),從而加重了大腦病理的嚴(yán)重程度。
途徑2:內(nèi)分泌/循環(huán)系統(tǒng)
微生物和代謝物,如次級膽汁酸、吲哚衍生物和 SCFAs,可以通過腸道內(nèi)分泌細(xì)胞(EECs)和腸嗜鉻細(xì)胞(ECCs)發(fā)出信號,從而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肽的分泌,例如可調(diào)節(jié)食欲的激素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和神經(jīng)調(diào)節(jié)劑(如激素和神經(jīng)遞質(zhì)血清素)。此外,某些腸道細(xì)菌可以直接合成和釋放神經(jīng)遞質(zhì)和神經(jīng)調(diào)節(jié)劑。比如羅伊氏乳桿菌、長雙歧桿菌等。
途徑3:神經(jīng)途徑
微生物組分、微生物調(diào)節(jié)激素和微生物依賴性免疫介質(zhì),可直接與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及其支配的迷走神經(jīng)和脊髓傳入神經(jīng)相互作用。產(chǎn)生的局部信號可通過感覺神經(jīng)回路傳遞到參與認(rèn)知、情緒、恐懼/焦慮、軀體感覺和/或進食行為的大腦區(qū)域。
反過來,迷走神經(jīng)和脊髓傳出神經(jīng)會傳遞信號至腸粘膜,并直接(如通過脊神經(jīng)衍生信號調(diào)節(jié)寄生蟲入侵)或間接(通過與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影響胃腸穩(wěn)態(tài)。
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信號或微生物相關(guān)分子調(diào)節(jié)腸道內(nèi)神經(jīng)元的活動,最終可影響胃腸道生理、局部免疫功能和腸道菌群的組成。
菌群-腸-腦軸其中的免疫、內(nèi)分泌、系統(tǒng)和神經(jīng)通路是高度復(fù)雜和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