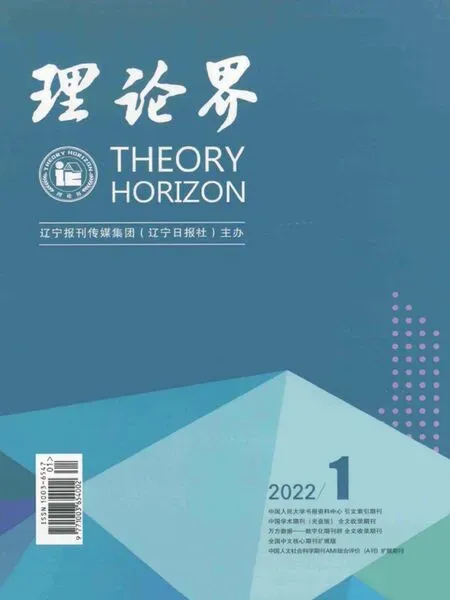淺析“天人合一”的三個層面及其悖論
丁 虎
“天人合一”觀念源遠流長,被看作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內容極其龐雜,自古及今社會各界學者對之有著不同的認知。一般認為,“天人合一”是談人和自然的統一問題,也有人認為是言自然理性和道德理性、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統一的問題。但無論怎樣理解,首先它們的結論是建立在承認“天人合一”合理合法性基礎上的。不過,“天”究竟指何種意義上的天,“人”是何種意義上的人,這是對“天人合一”進行分析甄別的前提,因為作為“天人合一”的關鍵,古代的“天”“人”都有著非常特殊的概念,它們各自有多重內涵。例如“天”有自然的天、意志的天、物質世界的天(自然界)等,由此又衍生天道、天理、天命、天心等相對應的觀念。而“人”也有自然的人、精神世界的人等區別。這樣不同意義上的“天”“人”組合是不是“合一”?如何“合一”?它們“合一”的理論根據何如?“天”“人”關系在古人看來是不是都是“合一”?或者說,“合一”的內涵究竟有沒有統一的標準?是在什么意義上的“合一”?有沒有相反的觀點?“天人合一”就其理論的實質而言,不過是對“天”“人”關系問題的一種解釋或認知。“天”“人”之間關系究竟如何,這需要我們用史實與邏輯推理做進一步討論。
一、自然哲學的“天人合一”及其悖論
較早從自然角度論述天人關系的是老子,《老子·二十五章》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從此處可以看出,在宇宙中“天”“人”與“道”“地”之間單從存在的角度看,它們是并列關系,如果從邏輯的角度看,它們又是逐次依存的關系,因此,“天”“人”的存在更具有統一性與多樣性,并非“合一”。從構成物質性“氣”的角度論述天、地、人之間的關系較早出現在《淮南子·天文篇》:“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2〕天地皆“氣”構成,不過是清濁而已,但兩者是何關系,并未寫明。《管子》一書中則直接說:“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為人。”〔3〕從構成物質性的根源方面看,它們實際都明確了“天”“地”生“人”,“天”“地”“人”應合為一體。而在《呂氏春秋》中這樣說道:“始生之者,天也。”〔4〕又說:“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4〕“天”是萬物的本源和起點,陰陽造乎于“天”,而人則由陰陽而化之。因此從生成論的角度證實了“天”“人”的“合一”。而莊子亦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又說“通天下一氣耳。”〔5〕從邏輯推理上進一步證實了“天”“人”的一“氣”,或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人應是“合一”的。東漢直至明清時期,天地氣化理論作為一條討論天人關系的路徑就一直延續下來。如東漢的王充說:“說《易》者曰:‘元未氣分,混沌為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為天,濁者為地。’”〔6〕并且認為“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6〕王充盡管不承認社會實踐中“天人合一”,卻贊成陰陽家和儒書上的結論,認為“氣”是構成“天”“地”“人”三者的根本物質。魏晉時期,嵇康認為:“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7〕唐代的柳宗元也提到了“龐昧革化,惟元氣存”的思想,認為宇宙在最初時期只有元氣。到了宋朝,張載則這樣認為:“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8〕這實際上肯定了天地人與萬物的一體性。可見,古人認為“氣”為天、地、人構成的基本元素是沒有問題的,不管這里“氣”的性質如何。
不過,即使承認了“天”“人”皆是“氣”構成,但并不代表承認客觀事實上“天人合一”。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9〕并且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9〕可見,與“天”相比較,“人”貴于“天”,而非與“天”一致。更不是與“天”“合一”。在“人”與“天”的相互作用中,前者更處于主動的地位,體現“人”的主體性。宋朝的邵雍則反對以“氣”為基礎的天人合一論。他在《觀外物篇》中說:“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氣為神,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10〕就是說天、地、人之間的關系是對等的,而不是統一的,它們構成的基本元素也是不一樣的,而人在三者之中為萬靈之本,是最為貴者。而在元代伊世珍所著的《瑯嬛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姑射嫡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
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
曰:“既有毀也,何當復成?”
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
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
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蛔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之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之開謝,寧有既乎?”〔11〕
顯然,這一段對天、地、人關系的表述是把人和天地分開、天地和宇宙分開,而且天、地、人都是有限的,都有成有毀,而宇宙是無限的,天地不過是人生活著的世界,它們之間并沒有構成方面實質上的聯系。因此,古人在物質層面的“天人合一”只是“天”“人”關系的一種說法,與之相對應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亦同時存在,后者對于破除人對天的迷信,更加科學認知天人關系發揮著積極的導向作用。
二、道德哲學的“天人合一”及其悖論
從道德層面看,古代的“天人合一”更具有審美的意蘊和人格理想性質,甚至是人存在最美好的一種境界。莊子在《齊物論》中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顯然這里的“一”不是物質性的合一,而是人精神境界上的“一”,因為天地與“我”的關系是并生,而不是“合一”,真正“合一”的對象是萬物,并且“合一”需要一定的條件,那就是“心齋”的功夫。何謂“心齋”,莊子的解釋是:“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于聽,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5〕實際是通過人的理性努力,排斥外在的干擾,凈化內心的雜念,以此來與自然交接,達到心靈與大自然的合體,實際是說,在現實生活中天、地、人的區分依然存在。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12〕孟子的“盡心”是盡其本然之心,“知性”知的是本然之性,人的本心、本性與天命是一致的。而人心是通向天性不假外求的自知,因此他接著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實踐中,存養不過是修道的功夫,至于生命的長短是由天命決定的。也就是說,理性的實踐并不能達到行道的圓滿,天人之間在實踐中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與區別。天人之性的相通只是理論上可能,是人們“存心”“養性”“事天”的一種教言,是提升人品無限接近而又無法達到的最終理想。由此張載對孟子此說解釋道:“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8〕張載所謂的“大心”“不以見聞梏其心”強調的是不受外界干擾的自然本心,由其心觀天,則可實現心性與天人一體,即“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8〕。而其“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人能盡性知天”與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以及《禮記·禮運》的“人者,天地之心”,皆體現了人在對天認知的主觀能動性。其“為天地立心”則更是人為地給冥頑無知的自然之天貼上目的性的標簽。馬一浮對之的解釋似更能說明這一點:“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謂之天;就其稟賦言之,謂之命;就其體用之全言之,謂之心;就其純乎理者言之,謂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謂之理;就其發用言之,謂之事;就其變化流形言之,謂之物。”〔13〕天人之間在客觀上并沒有直接的聯系。當然,他們“盡性知天”是建立在“性即天道”基礎上的,不是毫無根據的漫天遐想。
精神上的“合一”并不代表事實如此,例如莊子就認為與人相比,“無為為之之謂天”。《淮南子》更說:“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目差智故,曲巧偽詐。”〔2〕兩者天人之別顯而易見,天道無為,而人道則是有為的。王充在繼承《莊子》《淮南子》 論“天”的基礎上說:“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6〕王充再次延續了“天”無為的實然與“人”有為的應然的客主之別。唐代的劉禹錫在《天論》中則指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14〕實際指出“天”“人”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相分的關系,而“天”“人”發生關系時,人處于主導地位,這樣劉禹錫就把“天”“人”相分的觀念提到較高的水平。
由上可以看出,“天”“人”之間本是相分的,人與自然之天的“合一”只是人主觀心理的合,是通過人至誠盡性知天,窮神達化,指向人心理上精神上的最高境界。如《老子·十六章》所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1〕只有使心靈的虛靜達到極點,人才能夠復歸于生命的自然,實現精神上與天合一。也就是說,這個層面的“天人合一”是有條件的。而現實世界人心能否真正做到“致虛極,守靜篤”,或者說能達到何種程度都是值得思考的。因此,道德上的“天人合一”,心是最根本的條件,換句話說在“天”“人”之間,“天”“人”實際是相分的,人在其中占據著主動性或主體性。
由此看來,“天人合一”不過是認識的主體人對天道和人道的統一作出的一種獨特性規定而已,通過“天”“人”之性的邏輯聯系,指出“人”可以盡人之性,達到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終極關切,體現了古人特別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士人在精神層面的一種理想或需求,有了如此的精神境界,人類免不了將這種宗教情懷引向真善美的大道,這是“天人合一”在道德價值層面的最高指歸。但是,正如杜維明所說:“天道和人道絕對統一的觀念是有片面性的,天道和人道的統一并不意味著人道即天道,更不能以人道取代天道。”〔15〕對于個體而言,在實踐中“天人合一”思想境界體現的是個體的一種體知,一種審美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不但作為常人很難達到,即使是圣賢也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而已。簡言之,道德層面的“天人合一”人們只能在努力中無限地接近而無法真正實現“合一”。
三、政治哲學的“天人合一”及其悖論
社會意義的“天人合一”涉及人與自然交往過程中“天”“人”之間“人”的外在感知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因此,“天人合一”更具有情感與意識形態的色彩。從先秦的孔、墨到漢代的董仲舒,直至唐代的韓愈,都認為“天”是有意志的神,是宇宙的主宰者、百神之大君,不但管理著天上的各位神靈,而且主宰著人間的一切。在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是其代表。他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16〕首先他把人和天在精神和價值層面的統一看作“合一”。又把皇帝比作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地上的各種災異現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現,是天子沒有遵從上天的意志而發出對天子的警告。其次董仲舒從生理方面來證實“天”“人”同構與“合一”。他說:“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16〕他把人體結構和外在表象與天地萬物聯系起來,得出“以類和之,天地一也”。副數與副類構成了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具體環節。最后,董仲舒從情感和道德方面來論述天人之間的同一性。他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16〕將人的喜怒哀樂與天的春夏秋冬相比附。他還認為:“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16〕把天看作道德的化身和來源。
從董仲舒“合一”的理論看,首先體現了他的君權神授理論,其中包括兩個意圖:一是屈民而伸君,二是屈君而伸天。前者強調君主至上對百姓的絕對統治,后者雖表現為“天”對君主的實際控制,亦體現了人民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換句話說,“天”對“人”可以進行警告,人也能與天地相參。但無論是君主還是百姓在“天”仍是處于被動地位,無所謂“合一”。其次他的“天”“人”生理同構,只是從“天”“人”之間有著相似的地方進行比附,而忽略了不同的地方,用特殊代替了一般,用部分代替整體。最后,他提出的“天”具有人間的道德作為前提,那么人間的惡,“天”也有嗎?如果有,天既然指導統治人間,其本身應該是全善。這樣人的惡從何而來?實際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不過是為政治目的張本,邏輯上缺乏科學依據。
宋代的程頤則從理、性、命三者關系的角度論述“天人合一”。他說:“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17〕天命、社會統治之理、人的自然之性,三者實際是相一致的,之所以有了區分,主要在于人心,提出“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即使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也認為“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明王陽明也有類似的論述:“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18〕無論他們在表述上有何區別,但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天人合一”為仁道原則的立論依據,運用理性思辨來為社會運行秩序和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尋求根據,在凸顯人的主體性與理論合理性的同時,也為不同聲音的產生留下了張力。
其實自“天人合一”觀念產生以來,就有人提出質疑和反對,天人相分、天人對立、天人對等的思想與之同時存在、并行發展。孟子和其學生有這樣一段對話: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12〕
這段話雖是孟子回答萬章堯、舜禪讓作出的一種解釋,也比較符合信史的實證邏輯,但顯然他把“天”看作王天下至高無上合法的絕對權威,“天有完全獨立的認知能力和運作意愿,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的,因此樂天、畏天、敬天、事天是人的本分”。〔19〕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天”對“人”體現出絕對的統治,兩者之間本身不存在“合”,“合”也只是人有目的“合”于天。當然孟子除了“敬天、事天”,他還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且引用《太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12〕把人間許多事情的決定權或主導權放在人民身上,認為天命是民意的反映,上天的旨意是以民意為指歸的。天聽而不自我聽是難以使人相信的。因此,孟子在“天”“人”關系問題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強調天的威嚴,另一方面強調人的重要性,兩者在實踐中實際上是相分、相對應的關系,盡管這并不能完全代表孟子哲學“天”“人”關系意涵的全部。
同時代的荀子則觀點明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9〕認為天有著自我的運行和變化規律,與人事沒有任何關系:“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9〕天人之間相分而不“合一”。因此,人在天面前不應該是被動的,因此,他提出“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9〕,否認天對人的統治,強調了人在天中的主體性地位。
東漢王充的《論衡》實際是對董仲舒“天人感應”的一種積極回應,他否認天的意志,認為天和地一樣都是物體,只不過天在高空幾萬里,它并沒有意志,更不會和人產生精神層面的感應。他用客觀現實來駁斥董仲舒“天人感應”的矛盾和種種荒誕。他說:
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后若一。
他還舉例說:
“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年〕,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圣主寬明于上,百官共職于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6〕
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6〕唐代的柳宗元在王充的天道觀的基礎上指出,天不過是一個“有形之大”的自然物,古人說君權神授都是愚弄欺騙百姓的,天和人間的福禍沒有任何的直接關系。
總之,從政治層面上看,“天人合一”論帶著明顯的意識形態的色彩和階級傾向,理論比較膚淺,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此,往往被反對者發現其漏洞進行駁斥或回擊。
四、結語
從古至今,作為有意志、主宰義的“天”和作為自然含義的“天”的雙重內涵始終存在,這就造成了天人之間復雜的邏輯和事實上難以準確辨別的關系,正如李澤厚所說:
“天”和“人”的關系實際上具有某種不確定的模糊性質,既不像人格神的絕對主宰,也不像對自然物的征服改造,所以,“天”既不必是“人”匍伏頂禮的神圣上帝,也不會是“人”征伐改造的并峙對象。從而“天人合一”便既包含著人對自然規律的能動的適應、遵循,也意味著人對主宰、命定的被動地順從崇拜。〔20〕
可見,“天人合一”觀念無論從積極或者消極方面看,不過是強調“人”必須與“天”保持一致性、協同性及統一融合性。換言之,“人”對“天”而言,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是處于相對的狀態,而“人”則處在被動地位。特別是人還沒有脫開“天”是自然人格神的宗教或迷信,以及對自然規律的認知還不能解釋生產生活中出現的難題時,這種理想性與現實性的矛盾會永遠存在。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人實際起著主導性作用,不但不是天主宰著人,而且是人主宰著天。但從另外的角度看,特別是當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或重大社會矛盾時,許多學者卻從主體性的人轉向天。因此,從這兩方面看,天人之間不但不是“合一”,而且是對等的。“天人合一”理論的價值在于:一是重新審視天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以后,人們在用科學技術革命改變、主導著自然時,發現人與自然還有著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雙向引力。天道和人道的統一是以兩者存有的連續性和有機的整體性為基礎,人與天的關系應該是互動、和睦、統一而不是對峙、沖突的,更不是主動與被動的存在,換言之,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是工業革命初期人對自然的無限征服、破壞,而是物質發展與自然恢復與保護的平衡。二是外在的天與人之內在的天在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等層面的交融下,人生境界得到極大的升華,生命的理想獲得了極高的境界,這種“天人合一”常常能夠使得人們在紛亂繁雜的社會中安靜下來,人性的魅力與人格的尊嚴在這個時候在自身上獲得滿足,彰顯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修養。當然,“天人合一”觀念的罅隙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天”的自然與命定、主宰的雙重內容和含義關系的模糊性,給今人理解“天人合一”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對它的認知不能再以古人的“順天”“委天數”思想為根基,而應該對“天”有著科學的認知和態度,必須以自然人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否則“天人合一”觀念就會滯后于現代社會的發展。二是就人化的自然來說,“天人合一”境界正如上述所說是一種靜態,這常常會使人缺乏一種沖出解決矛盾甚至沖突、斗爭羈絆的心境,缺少打破寧靜、奮力向前的內在動力,容易使人精神頹廢、消極。因此,只有把這種靜觀與現代社會生產生活相結合,與科技發展相應景,形成與現代社會發展一致的自覺韻律,成為推動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活力,才能克服古代“天人合一”的內在矛盾,才能吸收傳統“參天地,贊化育”的精華,實現現代意義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