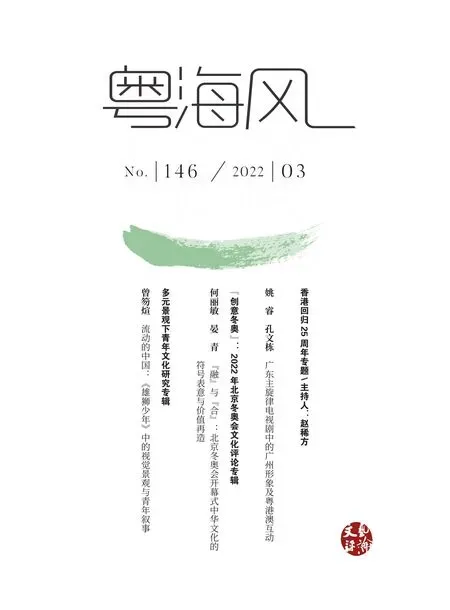香港音樂文化巡禮(1997—2022)
文/麥瓊
引 言
香港,素有東方之珠美譽。自開埠至今,從一個荒蕪的小漁村成長為國際大都會,作為世界金融和貿易中心,一直是世界矚目的地方。如果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驛站,顯然不能擔當東方之珠的稱譽,城市的品格往往更充分地體現在文化上。歷經180年風雨洗禮的香港,在世界城市文化歷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存在。而香港的文化版圖中,音樂,尤其是半個世紀以來的流行音樂,無疑是香港文化中最為亮麗的色彩。回歸祖國之后,香港迎來新的發展變化,各行各業都呈現新的情勢。音樂文化亦然,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對其做一番考察巡禮和思考,自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一、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其音樂傳統建立
香港作為現代都市和華人社會的特殊性,首先體現在它曾經的被殖民歷史。由于英國政府對香港一直秉持“統而不治”的政策,文化上是一種放任的態度。因此,香港文化的傳統根基是廣府文化,并在時代的變遷中融入了閩系文化、客家文化、海派文化,當然也有歐美文化等。自然生態下,其主體性自覺力量的不足,以至于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識長期處在一種模糊狀態,甚至落入一種自卑的殖民心態,只求短期利益的過客心態,甚至將家國視為逃難、寄居的地方。也就是說,真正的香港人身份自覺和認同有著漫長的歷史過程。二戰之后,香港的社會相對穩定,使得人口急劇增長。[1]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的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韓國)之一,是最具移民吸引力的地方。伴隨著工業、商業上的矚目成就,“香港出品”成為世界水平的認同,其中自然包括香港的文化。然而,存在一種有明確屬性的香港文化嗎?殖民帶來商業的繁榮、物質生產的成就和都市的現代化,是否也在侵蝕著被殖民者對于自身歷史的切實敏感和自尊呢?這是人們面對香港社會的崛起和特殊地位而時常露出的疑問。
這就要看香港的現代化透露出哪些精神特征和價值堅守了。香港的現代化道路由多種因素促成,譬如歐美工業技術和資本向亞洲的轉移,自由貿易港的區位優勢,國際金融中心的逐漸建立等。但是,這些只是客觀外因素,其中一定是通過香港社會的內因而產生作用的。社會結構的二元性,體現為統治者的殖民意志和普羅大眾的生存意愿的博弈與妥協。不同的勞動生產階層又體現出對社會結構的觀念和利益訴求。所以,香港有的議會中以功能界別來分配議席,以體現其正當性和平衡性。社會結構的合理性,使得工業時代的香港獲得各行各業蓬勃發展的機會。同時讓市民的謀生有了更多的機會和希望,年輕人通過拼搏,追求理想是基本生活邏輯。生存靠自己的奮發,機遇靠自己努力爭取,還要有幾分運氣,是大眾的一般共識。其實這也就是一種庶民精神的崛起,自然地支撐了工商業的持續繁榮和現代化。作為香港人的身份開始有了自發的意識。由求生存到尋求富足,從故土情懷到向心香港,這不是政府主導的結果,而是香港人冷暖自知的身份自然轉變。沒有官方的文化導向,民間的音樂文化呈現出自然的生態。一則容易產生共情,二則利于通過商業途徑傳播。加之活躍的、雄厚的資本聚集,對世界文化資源的吸引,香港流行文化的繁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具體地說,香港文化的主體性得益于工商業在七八十年代的騰飛,“香港制造”的推出隨之有了主體性的品格。影視、文創、武俠小說、粵語歌曲等隨著經濟的繁榮,經過現代傳媒的發酵和輻射,在商業利益驅動和市場力量作用下,向嶺南地區、東南亞,直至全球的華人世界輸出港式文化產品,成為香港人引以為豪的價值體現,從而塑造了香港人的文化精神,即香港性(Hongkong-ness)。與此同時,電視臺、電臺、電影、電視、唱片、卡拉OK等文化工業為“香港制造”推波助瀾。文化工業主要以粵語為主,既是市場的自主選擇,也體現了作為市民文化的主體性要求,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逐漸有了內在的自覺并獲得外部的確認。黃霑對此的論述很真誠:這“顯示了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移民起初戰戰兢兢,努力向高質素的外來文化汲取養分,美國的、上海的、臺灣的都兼收并蓄,然后才慢慢鞏固了自己信心。香港流行音樂對母語的觀念,是和香港人自我意識的建立同步的。到香港人開始明白,自己不再是過客,而是以此為家的地道港人,流行音樂才開始切實反映這種心態,才有真正算得上是代表香港的獨特聲音出現。”[2]也就是說,“我系我”的信心建立是以文化的形式逐漸鞏固的。從祖國內地改革開放之初,港人回鄉的待遇和心情就充分體現了這種身份的重要性和獨特性(時代傳奇色彩)。回歸祖國之后,“一國兩制”的進一步落實,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又面臨著新的文化心態調整,這也是需要正視的一個事實,自然是深刻影響香港將來的文化發展的關鍵因素。
因此,體現香港文化的聲音形式非流行歌曲莫屬,而作為文化上的“東方之珠”標簽則由鄭國江與羅大佑創作的同名歌曲確立,這也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高光時刻。《東方之珠》既是對香港在商業文明上的成就的肯定與歌頌,也是情感上對即將回歸的香港親切呼喚,帶有昵稱的意味。當然,對于思想精神上的文化認同,必須滲透于香港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鳴。這種文化特質的表現,存在于類似羅文的《獅子山下》(顧家輝曲,黃霑詞)、甄妮的《奮斗》(顧家輝曲,黃霑詞)那樣的發自內心的真摯情感,牽連每一個人的真實生活的深情歌唱,寄托了人們對現實的關切,對未來的希望。而且在一代代歌手和音樂人的努力下,編織了屬于香港的、以粵語流行歌曲為主的文化圖景。既有許冠杰唱出的《浪子心聲》(許冠杰曲,許冠杰、黎彼得詞)、《半斤八兩》(許冠杰曲、詞)那種從內容到氣質反映普通香港人的真實生存狀態,又有像梅艷芳、張國榮、譚詠麟等唱出的《愛在深秋》(李鎬俊曲,林敏聰詞)、《有誰共鳴》(谷村新司曲,小美詞)、《似水流年》(喜多郎曲,鄭國江詞)等,對濃郁都市浪漫情愫的散發,以及Beyond樂隊唱出的《真的愛你》(黃家駒曲、詞)和《光輝歲月》(黃家駒曲、詞)等具有人文情懷的吶喊。當然還有傳統粵劇在影視、電臺、唱片、舞臺等媒體的交融與共榮。
音樂文化的身份確立固然在于對外的產品輸出,也在于行業制度的建立。這種自覺的標志性事件是“香港詞曲作家協會”和“亞洲作曲家聯盟”的成立,為業界樹立了文化的職業身份。并主辦了“香港藝術節”“華人音樂家音樂節”等權威性的音樂活動,全面樹立自主性的全球化文化形象。也就是說,回歸前香港的音樂文化生態經歷了文化品格的形塑,有著主體性穩定且內容多樣的生態。而其中以流行音樂為主流,既綜合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時代曲、60年代的臺灣時代曲和歐美流行曲的元素,更是在粵曲、粵劇的曲調、詞韻上的創新,這些與小眾生態的嚴肅音樂及傳統的戲曲、曲藝道,形成帶有極強煙火氣的、具有獨特美學品格和文化能量的音樂文化傳統。
二、回歸后的香港音樂巡禮
香港是世界自由港,經濟發達。1997年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2.43萬美元,與內地相比,是屬于想象級別的距離。香港的順利回歸,開啟了新的時代,“一國兩制”保證了香港的繼續繁榮。25年的歷程,香港的社會變化始終與祖國的崛起同命運共呼吸,根本體現在文化上的一脈相連。文化的香港給人的直接觀感是國際化、嶺南基因,卻在近百年的發展中形成獨特的品格。音樂文化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也是影響力外溢最廣的領域。
(一)傳統音樂
1. 戲曲音樂(粵劇)
粵劇在香港的堅實基礎乃是因為語言。殖民時期,香港的官方語言是英語,而社會交際語言主要是粵語。作為廣府文化的代表——粵劇,自然是傳統音樂的主要表現。因為戲曲的傳統在香港有著普遍的民間基礎,藝人也相對集中,在演藝和創作上,香港一度是粵劇藝術的高地。京劇、昆曲、黃梅戲也有零散的聲音,但是在香港的市場份額相對逼仄,確實有“客居”的意味。
粵劇之于香港,或者香港之于粵劇,有著獨特的意義,粵劇是維系傳統最為重要的文化形式,這是歷史造成的。而最為特別的是,香港自覺地擔當了對粵劇的保護和傳承,經歷了粵劇的興盛繁榮和歷史滄桑。在流行文化尚未興起的時代,粵劇就是香港人的文化主食。粵劇現代的榮光也是在香港寫就,各路老倌、大咖如:白駒榮、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任劍輝、白雪仙、唐滌生、南海十三郎等無不是以香港為大本營。雖則近半個世紀以來,粵劇在香港與內地各自依循不一樣的發展路徑,內地是以官方體制為主,香港則以民間松散的市場需求為主。人口基數的問題和受到流行音樂的沖擊,香港的粵劇從業者像是靈活的職業身份,常常利用發達的茶座、電臺、影視、唱片、演唱會等,并建立起粵劇、粵曲(元素)與流行音樂的共生共榮。因此,盡管香港21世紀以來并不怎么誕生新的粵劇作品和較少專職的粵劇演員,但是粵劇的聲音卻從來不曾缺失。
回歸后,香港粵劇的一個明顯變化是與內地連成了一個文化板塊,是名副其實的地方文化,即大灣區文化的組成部分。粵劇的表演、創作、研討等文化活動,一般是很難分辨其來自哪里,這個圈子基本上已經融為一體。創作上,廣東省是比較活躍的,演出的市場集中在城鄉,在香港則具有高端文化的功能與意義。2004年5月設立的粵劇發展咨詢委員會,為粵劇的推廣、保存、研究等提供政策支持。在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演藝學院和民間粵劇組織,如八和會館等機構和熱心人士的努力下,香港的粵劇劇迷人數中在最近十幾年有了客觀的增長。另外,粵劇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后,官方對粵劇的文化價值更為重視,放出很多大手筆,解決了回歸前一直掣肘粵劇發展的瓶頸。譬如2012年九龍油麻地戲院和2019年西九龍戲曲中心的落成,為香港的粵劇文化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設施。尤其是后者,無疑是粵劇圣殿般的存在。未來西九龍文化區多功能的設施和高質量的室內外環境,將是弘揚中國戲曲的一個文化高地。
此外,世紀粵劇有了另一片天地,就是音樂課堂中的粵劇傳承與普及。香港教育部門在學校音樂課程中引入粵劇與樂曲,2003年小學開始實施,2009年中學開始實施,為此培養了大量的音樂師資。這可以看作是傳統文化的回歸和價值肯定,也是基礎教育對美育的修正和進步。粵劇的專業教育(香港演藝學院和社會組織的訓練班)與通識教育并駕齊驅,是粵劇文化得以傳承的基本保證。
2. 廣東音樂
廣東音樂是與粵劇、粵曲同一血脈的文化,而作為依靠器樂的藝術形式,廣東音樂曾經比粵劇和樂曲的傳播更為廣泛。但是香港的人口基數不大,粵曲和廣東音樂似乎難有廣泛的民間基礎。茶樓依然存在,但是茶樓的音樂表演式微,已經沒有了廣東音樂的生存空間,音樂的元素依賴“熟食”(互聯網音樂),而且都是早期保存的經典。香港的學者對廣東音樂一直保持著熱忱,畢竟廣東音樂曾經的輝煌是香港創造的。可惜的是,廣東音樂在發展過程中兼收并蓄的同時,逐漸也迷失了自己的身份與品格堅守,隨著民間自發力量的削弱,自然也就逐漸萎縮了,沒有創新的內在要求和動力,自動地走入博物館。回歸后,香港人玩廣東音樂,顯然是很難成為一股文化的,從香港官方到民間都被視作最為孤寂的香港小眾文化。但有一個現象令人甚為欣慰,就是廣東音樂的元素常常作為香港專業作曲家的創作營養被寫進交響樂、室內樂,不知道該不該竊喜。
(二)流行音樂
香港近百年對世界商業文化的貢獻中,流行音樂應當算是一項突出的成就。可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香港的流行音樂幾乎不成氣候。四五十年代一些南來藝術家,為香港的流行文化帶來改變;直至七八十年代,香港成長起來的獨特的流行文化,居于華人流行文化的中心地位,傳輸了獨特的香港精神和風格。粵語歌曲的繁榮,從無心插柳的商業電臺廣告歌開始,逐漸找到一片生存的天地,并由幾代極具才華的藝人淬煉成創作方法與美學上自成一格的“文化產品”。以國語時代曲的曲調為基礎,借鑒歐美樂隊的伴奏技術,加上粵語生動而又接近現實的通俗表達,成就了香港流行音樂文化。頒獎禮、流行榜、打歌榜、演唱會、歌迷會,層出不窮的流行形式,將現代社會的文化功能從刺激、肯定到鞏固,得以一一實現。這是香港的獨特經驗,也是將這種流行文化推向高峰的根本作用力。以唱片為例,幾乎所有的世界著名唱片公司如EMI、Universal、PolyGram、Warner、Sony、BMG等均進駐香港,并在競爭中催生本地的唱片公司:英皇娛樂、金牌大風、華星唱片、東亞唱片等等,可謂洋洋大觀。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的數據顯示:1996年香港的唱片銷量是1800萬張,16.91億元。這是在張國榮、許冠杰、梅艷芳等歌星退出和盜版市場猖獗的情形下統計的,無不銘記了那個時代的傳奇。作曲、編曲與制作等創作環節的分工合作,是典型的工業化流程,營銷和推廣更是農業時代不能比擬的商業模式。生產制作的歌曲,通俗而不庸俗,結構不大,經濟簡潔,符合商業邏輯。為商業服務,讓價格倒逼價值,勢必讓許多有才華、有創意的音樂人進入這個行業。也就是說,由粵劇和粵曲衍生,融合國語時代曲、歐美流行曲而成香港流行音樂,是一股文化的熱潮,既有產品借商業力量行銷世界,也在接受者的內心形成了一種群體性的文化認同。
回歸后,香港流行音樂對內地的影響從廣東迅速發展到全國,尤其是北京的音樂舞臺和市場。不再是零星的、個別的像奚秀蘭、張明敏80年代象征性地參與內地的節目,而是現象級地、全方位地與內地的融合,在廣泛的合作中建立起互信與優勢互補。尤其是中國加入WTO,與世界的接軌為文化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市場,隨之而來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的協議中納入廣告、視聽、娛樂等行業。無論是對市場的拓展,創作空間的開拓,技術手段的多元,藝人歌手的展示途徑、與內地資源的合力等方面,在世紀之交的香港有著巨大的想象空間。像那英、王菲演唱的《相約九八》(蕭白曲,靳樹增詞)、葉倩文演唱的《我的愛對你說》(李海鷹曲,陳潔明詞)就是非常成功的范例。但是,原有的香港流行音樂資源輸出逐漸出現更新換代,尤其是黃霑、梅艷芳、張國榮的離世,算是這個蜜月期的結束。這種轉折,既有生機勃勃的市場的誘導,也有文化轉型的陣痛。出現了與上一輩文化觀念和藝術質素不同層次的承接力量,倒逼香港音樂的創新性發展,卻又由于缺乏市場的支持,而沒有順利接棒。若換一個角度看,根本就不可能“接棒”,因為文化的發展是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而生長。年輕人已經在社會的轉型中改變了審美的價值核心,旋律、節奏、韻味、精神內涵,也許在年輕人的感知中有了新的解釋,只是這些很難讓目前尚在實踐中的人們來論述。
當然,21世紀以來香港流行音樂融入內地綜藝文化的同時,也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語言上。從歌詞的寫作上看,以黃霑、鄭國江、林振強、林敏聰、黎彼得等詞家為代表的傳統派,他們或寄情于傳統故事、武俠言情,或反映都市生活、借古諷今等題材,文字講究與古典詩詞的承接。但是,這種具有鮮明風格、偏向詞性的典雅俏皮,又體現詞韻美感的審美趣味逐漸被拋棄,代之以新人林夕、黃偉文、潘源良、陳少琪、周耀輝、周禮茂等新潮派。他們一般是愛情題材壓倒一切,歌詞猶如內心的喃喃自語,在藝術性上有大膽創新的意味。例如,林夕的歌詞是有所超越的,寫意很深,表現手法多樣。他有較好的傳統文學訓練,承接黃霑時代的文脈,但有文化氣質上的區別,也有個人的詞風品格,代表著時代的轉折。歌詞在內容上追求的是個性化表達,觸及社會問題和個性心理描寫。同時注重人文深度的挖掘,諧謔的意味比較普遍,反映高速發展的都市社會給年輕人帶來的情感困惑、對未來的彷徨等精神癥候。尤其是在王菲、陳奕迅等實力唱將的演繹中釋放了新世紀的文化氣息。但是,在新舊的交替中,這種美學沒有得到深耕,卻在資本的加持中逐漸剝離對傳統審美需求的依賴。天馬行空的肆意,導致了胡思亂想的結果。多數年輕詞作家的創作被詬病為“題旨空泛、不知所謂”。表現在:修辭手法奇特、怪異,表達晦澀,情感基調暗灰,意象迷離,沒有邏輯的單純堆砌。甚至于不自覺地將粗言穢語納入其中,這是行業的自損行為。尤為嚴重的是,在對傳統詩詞美學的拋離后,作品結構方式散亂。急切的表達,堆砌的意象對于審美消化是有障礙的。音樂如果沒有強大的結構力和足夠的美感,就難免顯得費解、難聽。音樂是訴諸聽覺的,一聽即明,一聽則喜,是流行歌曲的文化屬性,也是其獨特的藝術價值,即使是工業流程生產的流行歌曲,也應當保證一定的藝術價值含量。否則很難得到傳唱,是走不遠的。
在音樂旋律的寫作與配樂方面,21世紀的香港流行曲不再依賴江南小調、廣東音樂、粵曲,而是有著較為自由的旋律寫作勇氣。配器上保持主調旋律的流動,在樂器的色彩表現上下功夫,有其合理和超越的一面。譬如陳奕迅演唱的《浮夸》(2005年,黃偉文詞,江志仁曲),音樂有開闊的發展思路,旋律飄忽,有一定的輕搖滾的元素,對原來小調式音樂結構有所突破。又譬如同為陳奕迅演唱的《富士山下》(澤日生曲,林夕詞),演繹上有聲音技巧的發揮,既能鋪陳長歌詞的宣敘婉轉美感,又能讓歌唱與器樂的膠合非常和諧,尤其是鋼琴的運用是之前華語歌曲配器中沒有過的奇妙和功能表現。另外,在挖掘歌手的聲音特點,賦以音樂特質的理念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如將薛凱琪甜美聲線結合可愛的氣質、鄧紫棋渾厚的聲音與開闊的音域而形成個性化的唱腔,這些都是粵語流行曲創新的亮點。但是整體上新生的創作群體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成績單,是人們的普遍觀感。
(三)專業音樂
目前,香港有六大團體,代表著高雅文化。包括香港管弦樂團(港樂)(1974年正式職業化),香港中樂團(1977年成立),香港小交響樂團(1990年成立),香港芭蕾舞團(1979年成立),城市當代舞蹈團(1979年成立),香港舞蹈團(1981年成立)。以世界性眼光看,這個數量的專業隊伍不算太起眼。但是,對于只有700多萬人口的香港,在藝術音樂相對后發的亞洲城市是相當可觀的,而且就其團隊的建制、人才和職業化管理而言,是遠超內地城市的。專業音樂在香港可能受眾上僅為極少數,但是其職業化建設令西方同行也刮目相看。就拿香港管弦樂團和香港中樂團來說,幾十年來利用國際化都市的優勢,有著良好的待遇和運行管理機制,吸引眾多高階的演奏家和指揮家加盟合作。它們有自己成熟的樂季、創作培育計劃和賞樂群體,也敢于嘗試演繹推廣香港的現代音樂。當然這些集中發生在香港回歸之后。其中港樂的演繹水平在世界著名指揮家艾杜·迪華特(Edo de Waart)和梵志登(Jaap van Zweden)的長期調教下已經成為世界水平的管弦樂團,每一個樂季的曲目安排都有變化,而且涉略幾百年來最有代表性的、包括高難度的作品,是樂迷欣賞最高階音樂嚴肅音樂的窗口,對內地的古典音樂文化發展有積極的影響。
有著職業化水平的樂團,便有利于嚴肅音樂的創作。香港的專業音樂創作與流行音樂相比,顯得聲量微弱,起步也較遲,但卻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文化力量,可以說是華人音樂文化的一個亮點。專業音樂創作中,前輩作曲家林聲歙、黃友棣、林樂培、陳培勛、葉純之等,與內地的音樂教育淵源較深,沿襲對西方古典技法的借鑒和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改造。“九七”之后,創作比較活躍的作曲家群體中,陳永華、曾葉發、陳慶恩、盧厚敏等,則較多具有海外留學的經歷,音樂創作具有國際視野,探索新的音樂語言和技法。當然,他們在音樂精神上仍然關照中華文化和香港特質。九七香港回歸祖國,作為一個世界矚目的歷史節點,曾經產生了不少頗具分量的作品,吸引了包括本港和海內外的作曲家參與,那當然也是屬于香港的文化。譬如盧厚敏的管弦序曲《融》、陳錦標的《九七引》、陳偉光的《1997交響幻想曲:匯》、陳永華的交響大合唱《九州同頌》等。像曾葉發、關乃忠、陳能濟聯合譜寫的組曲《香江新篇》(《普天樂》《安晴》《火樹銀花沐香城》),音樂運用了廣東音樂素材,是難得一見的大部頭創作。他們是新世紀藝術音樂創作最為活躍的代表人物。當然還有更為年輕的一代,像鄧樂妍、伍卓賢、楊嘉輝、陳仰平等,他們的創作在世界水平的展演和比賽中常常獲得驕人的成績,展示了華人的音樂才華。很難說他們已經形成“香港樂派”的影響力,也沒有鮮明統一的音樂美學宗旨,但是他們具有世界視野,探索的路徑是非常開闊的,有非常新銳的技法,在交響樂、室內樂、歌劇和大型合唱等方面有數量可觀的成就。而且,據筆者的觀察,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在音樂的精神內涵的探索中設法回歸中華文化,無論采取中樂團還是西樂團編制,都將中國的樂器諸如琵琶、胡琴、嗩吶、古箏、笛子、古琴、塤等作為重要的主奏樂器,體現中國的聲音,試圖讓中國的聲音煥發民族的自信。
事實上,藝術音樂在香港回歸之后,聲量是越來越高的。有音樂天賦的本港青少年常常很早就留學歐美,在世界舞臺上發出聲音的才俊近年有不錯的表現。張瑋晴、沈靖韜、黃家正等,當然也包括移居來港的世界級大師郎朗,反哺香港的嚴肅音樂文化。尤其是從1973年開始的“香港藝術節”,2003年開始的“香港國際——亞太現代音樂節”等大規模的藝術展演、比賽,成為世界級的文化盛事,頂級音樂團體和著名演奏家紛紛被邀請前來舉行音樂會。這些都是香港作為大都會不可或缺的文化格局和高端文化需求。
以上是筆者基于個人視角和有限的信息來源而做的香港近25年來音樂文化發展的觀察管窺。對于香港的文化發展,港英政府時期一直采取放任態度,一方面體現了殖民者的傲慢心態,同時也不上心,不重視香港社會的前途。結果是,香港的文化受制于管制當局對在地文化的漠視,更多的是自生自滅,呈現出官方與民間的相對隔閡。從治理香港的施政報告中也能體現出香港文化身份的轉變。“九七”之前,港督一直將“康樂”“文娛”作為市政局(Urban Council)的次等項目來管理,“香港文化”的概念是從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施政報告中才獨立出現,并委任文化委員會(2000年)制定文化發展策略,由香港藝術發展局(Hongkong Art Development Council)負責具體的職能工作。由此,從宏觀的政策規劃,文化活動的撥款資助到文化藝術教育才逐漸顯示香港的主體性。即如施政報告中所描繪出香港的文化——國際文化中心、世界都會特色,媲美倫敦和紐約,“紐(約)倫(敦)(香)港”的三足鼎立——的藍圖。
三、問題與思考
(一)香港音樂文化的獨特性價值
本杰明說:“在漫長的歷史周期中,人的意識感知能力是隨著人類總的生存模式一起變化的。人的意識感知能力的組織方式,實現這種意識的感知能力所借助的媒介,不僅是由大自然決定,還是由歷史環境所決定的。”[3]中國社會的近現代化歷程緩慢而復雜,艱辛中飽含屈辱。辛亥革命后文化上的近現代化同樣在尋求出路,希望與世界接軌和交融。而香港、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承載了中國近代歷史的沉浮與苦難,也作為一扇窗口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藝術與商業的結合,是推動文化革新的核心力量。從文藝復興的佛羅倫薩,工業革命的倫敦,18、19世紀的維也納和巴黎的藝術商人,到20世紀的好萊塢,都說明了一個現象:現代城市的強大吸引力可以聚集商業力量和藝術家,形成大規模的生產與消費,完成一次次文化革新。對于華人文化的期望也許不是顯性的,香港被歷史性地選擇成為這種革新的起點,尤其落地于流行音樂。同時,高度國際化的都市文化中,專業音樂是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抓手,也成為融入世界潮流的通道。雖然不見得在民眾中引起對流行文化那樣的社會關注,卻一直潛在地影響和塑造著香港文化的精致與獨特價值。
通俗文化的精致化。粵曲、南音本身就有這種素質,對遣詞造句、音韻協律有著典雅的內在追求。在粵語歌曲的黃金時代,如《順流逆流》《幾許風雨》《有誰共鳴》《男兒當自強》等廣為傳唱的作品,不是一般的通俗性可以解釋的。學界有這樣的基本認知,粵語保留中原文化中高雅的音韻特質,有著非常獨特的文化特征和審美魅力。而在香港,粵語依托充分的傳媒環境以保證其民間準官方意味,除了電臺、電視等聲音語言的傳媒途徑,報紙、雜志也是相當完善的粵語文字體系,這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地區是比較通行的。但是作為文字的傳播,一旦超出粵語方言區就很難行動,其局限性很大,哪怕是電影這么具象的視覺藝術,將粵語翻譯成普通話之后,語言的原始魅力衰減是非常明顯的。然而,相對于歌曲仍有著天然的優勢。像徐小鳳、林子祥、羅文、陳慧嫻、王菲、李克勤等,他們在演唱上具有較高技術、藝術水平,在粵語的咬字、唱法、感情投入、舞臺表演等方面,是千錘百煉出來的藝術格調,非一般的工業流程可以包裝成功。這種獨特的美學體現在多種結構元素的和諧:歌調(旋律+節奏)、歌詞與伴奏三方的緊密結合。當然,三者不是被動的撮合,而是一種主動的靠攏,缺一不可。旋律的地方性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港味,區別于上海時代曲的江南風格,又不是純粹嶺南廣府南音的悲情調式,而是五音為主的七聲性,夾雜著歐美和東洋曲風。節奏則是來自粵語的、民間音樂的輕松、樂觀的節奏。這些在西洋樂器的伴奏中得到加強,有樂隊演奏技術和音色對歌唱的共時性加持,掙脫了傳統音樂的粗糲,蛻變出一種屬于城市節奏的聲音來。溫拿、Beyond、達明一派、太極、草蜢,在香港的都市夜空,曾經是不敢小覷的聲量。
論及香港流行音樂的價值,可以有很多表述角度。香港文化的精神實質,商業固然是香港音樂的精神,但是人文性的追求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日常香港流行音樂給人的印象是娛樂工業的產品,不無道理,但也是片面的觀感。在流傳較廣的經典歌曲中,其實并不缺少人文精神訴求。舉一個例子,Beyond樂隊的《光輝歲月》,在幾十年來的流行榜單中從來沒有被冷落過,在唱片的銷量中居然獨占鰲頭,超出其他音樂作品一大截。黃家駒的一批音樂,其人文訴求哪怕是在世界流行樂壇,也是得到相當的尊重的;更不要說,前文提及的“刻苦耐勞、勤奮拼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的獅子山精神了。時任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曾經在本世紀初訪港時,在大會上專門朗誦《獅子山下》的歌詞:“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以鼓舞香港人對未來的信心,令人動容。香港粵語時代曲的共情力可見一斑,不愧為悠悠香江的不朽名句,也是其獨特性價值所在。
(二)面向未來的努力支點
21世紀已經過去20余年,世界在變化,香港當然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近年有一股悲情籠罩在香港的文化天空,“香港流行音樂已死”是圈中人對現狀的感慨。如果固守原來對流行音樂輝煌時代的觀念和思維,自然會產生今不如昔的落差。不管是圈中人的自省,還是行外人的觀感,香港的流行文化都必須面對變化,而且未來的音樂文化發展,一定是一種更加國際化,更加開放、容納的文化。香港仍然不失中華文化交流的橋頭堡功能,而且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文化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很難做既定的預期。但是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作為藝術創作,創作理念和技術層面的問題必須得到重視。
首先,對于題材、表達內容,固然是每一個時代都有其內容訴求。但是作為藝術形式的手段和技術問題,就需要符合藝術規律。流行音樂的前輩對后來者的歌曲創作表示悲觀,主要也是對后者的音樂素質和技術上的不足有著深刻的觀察。前輩在寫作中自覺履行代言人的角色,自己的意思表達是以大眾的接受為目標的。因此黃霑的詞,較為明朗,反映大眾化的心聲。雖說娛樂也有瘋瘋癲癲的時候,但商品屬性是第一要求。同時,人文追求上有對本土文化身份的訴求,有著集體主義的理想和積極樂觀的精神追求。即使是個性化的形式,也應當是順應時代的、有著價值追求的內容表達。
其次,關于填詞的獨門秘訣。香港的音樂創作為了大眾的接受程度,通常是依曲填詞,鍛造歌詞的音樂性和獨立性,同時保證音樂旋律的動聽,以保證音樂旋律的動聽。對于音樂來說,旋律是靈魂,無需論證。粵語流行曲創作人大多采用“先曲后詞”的方法,詞曲的質量往往更容易得到保證。這是經驗總結,也是香港流行歌曲常見的創作方法,是否因為粵語的九聲六調之故,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研究,但這是香港歌曲創作的一大風景,是很獨特的。說起來,填詞本來也是中國傳統戲曲創作、詩詞創作、學堂樂歌的基本方法。譬如李叔同填詞的《送別》(約翰·龐德·奧特威原曲)就是典型范例。但是現代的歌曲創作,尤其是藝術歌曲的創作,一般采取依詞譜曲的方式。內地的流行音樂創作中,先詞后曲的做法相當普遍,與香港的做法各異其趣。黃霑認為:“歌詞是寫來唱詠的,供聽眾聽的。協韻就令歌詞唱出來的時候,既易于記憶,也有聲韻之美。……歌詞創作人不但不能放棄用韻,更應努力鉆研用韻的方法,萬不能因為一己文字功夫不足,把我國韻文優良傳統……”[4]可見前輩詞人深諳這個道理,也非常努力研習粵語的詞韻特點。因此,才有鄭國江填詞的《漁舟晚唱》(古曲)、黃霑填詞的《男兒當自強》(廣東音樂)、《星》(谷村新司曲)、林振強填詞的《千千闕歌》(近藤真彥曲)這些填詞極佳的歌曲,從中可以體會到香港音樂的另一種智慧與價值。
此外,作為流行文化的觀察,常常會不自覺地找尋音樂劇(Musical)的身影。流行音樂幾十年來的持續繁榮,卻沒能夠發展出香港的音樂劇市場,自張學友的《雪狼湖》之后,就沒有了后續的音樂劇故事,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之所以有這樣的提問,主要是基于這樣的邏輯:香港的商業音樂是相當發達的,而且有充足的資源,如演出場地、制作團隊建設、市場營銷等成熟的機制,音樂劇的出現應當是水到渠成的,就如同倫敦的西區和紐約的百老匯。這里似乎存在一個有趣的相悖現象,又或者是螺旋性發展的必然,有待以后的觀察。
(三)大灣區的音樂文化融合與想象
從文化根性看,粵港澳本為一家,即廣府文化。香港的特殊地位,尤以香港文化的表現最為突出。既歷經歐風美雨洗刷,也更能體現嶺南文化的韌性,淬煉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素質和文明內核。我們必須珍惜這種價值,而且這種價值認同具有普遍性,其中共情力最強的便是音樂文化(語言與聲音)。因此,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香港的文化發展必然融入珠三角,乃至國家發展的新格局,并成為新的文化動力與擔當。
在面對回歸之后香港音樂發展道路的困惑的同時,回望廣東流行樂壇如今的式微、寂寥,對比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流行音樂的蓬勃之勢,所謂“白頭宮女話天寶舊事”,難免發生與對香港流行音樂現狀一樣的感嘆。其實,這也客觀上反映了區域性文化發展中共同的周期性困境。當然,筆者不太贊同以下這種觀點,即“隨著內地的崛起,香港的產業不可避免的受到擠壓,加上港府的政策不力,民生問題日益突出。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廢青’們就把矛頭指向了內地。”[5]這存在著對香港社會和文化的片面認識,香港在經濟上與內地確實存在競爭,但更多的是合作,或者是合作框架下的競爭(如CEPA),沒有擠壓的故意和事實。文化上更不存在香港市民明顯地將“矛頭指向內地”的敵意。
生活中的音樂文化,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形成同一體這是沒有懸念的。“大灣區文化藝術節”自2019年開始,將珠三角地區的優質文化資源從互動過渡到一體化的運作模式。而作為大灣區文化共情力最強的文化形式——粵劇,早就開啟了一體化模式。譬如始于2003年的“粵劇日”(每年11月最后一個星期日),用政府職能部門的力量推廣粵劇文化的普及。2006年5月和2009年10月由廣東、香港和澳門聯合申報的粵劇項目,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遺產目錄”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就是一種新型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文化融合。粵港澳的文化優勢互補,在新編粵劇、音樂劇、多媒體音樂制作等方面,已經有了積極的探索并初見成果,相信未來的大灣區文化繁榮一定是超乎想象的。
結 語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是一個歷史性的時間節點,恰逢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十四五”規劃開局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頒布之年。香港的社會發展與內地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文化從親緣到一體化是必須面對的事實,也是香港越向更高臺階的基本格局。當然,文化具有自身的演化規律,需要面對的課題不比經濟和政治來得輕松。譬如有香港學者說的:“20世紀末以來的全球化發展,文化藝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將越來越顯著,若不留神,香港文化藝術會不知不覺地被全球化吞噬了去。”[6]這樣的憂慮,是對現實深刻觀察之后的肺腑之言。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索的問題,是香港文化在新時代的發展迎來的戰略性問題,也是最為迫切的現實問題。在被殖民時代,這是不需要考慮,也是無從考慮的問題。如今的“一國兩制”樹立起香港的未來和信心,是自主性文化發展的良好開始。但是如何建構21世紀香港的文化精神,讓音樂取得更開闊的發展道路,向世界輸出香港品牌,是有巨大挑戰性的任務。香港過去沉淀的價值不容輕視,25年的艱難轉型也是非常好的經驗和歷練。香港有光輝的歲月,“東方之珠”不僅是過去的香港,更是將來的香港,而這東方之珠的光環中一定不會缺少音樂的色彩。
注釋:
[1]1945年至1950年,香港人口從50萬急劇增長到220萬,之后也是快速增長。至1980年錄得人口是510萬。
[2][4]黃霑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2003年。
[3]轉引自[英]彼得·霍爾:《文明中的城市》,王志章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864頁。
[5]張昕冉:《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71502564474911.
[6]劉靖之:《香港音樂史論》(文化政策·音樂教育)序,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