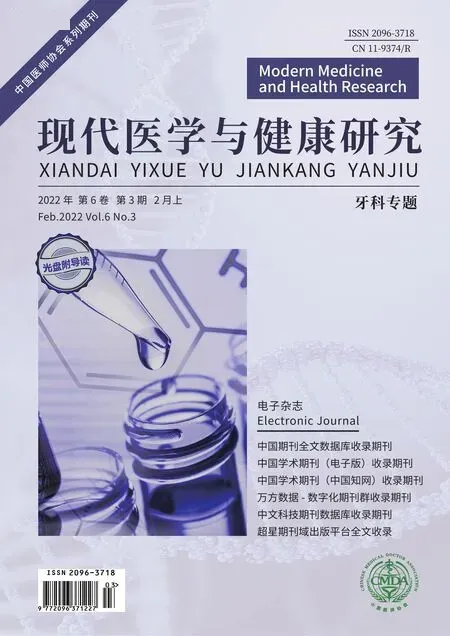從肺胃論治慢性蕁麻疹經驗采擷
袁帥帥,唐友斌,袁愛紅
(1.安徽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2.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針灸康復科,安徽 合肥 230038)
慢性蕁麻疹(chronic urticarial, CU)是指皮膚反復出現水腫性風團,時隱時現、大小不一、部位不固定、邊界清楚、劇烈瘙癢的過敏性皮膚病,且持續時間大于6周,部分CU患者還會伴有血管性水腫,每天發作或間歇發作,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現代醫學對CU的發病機制尚無定論,可能與自身免疫、慢性感染相關[1-2]。西醫治療CU常采用聯合用藥的治療方案,如抗組胺藥聯合免疫制劑或多種脫敏藥,臨床癥狀控制一般,且易產生藥物依賴性,長期服用,不良反應明顯[3]。祖國醫學認為,CU屬“癮疹”“風疹塊”“赤疹”“白疹”等范疇,癮疹發病主要是由于素體稟賦不耐于內,六淫侵襲于外;或飲食不節、腸胃濕熱;或素體虛弱氣血不足、衛外不固所致[4]。《素問》曰:“少陰有余,病皮痹隱疹。”CU的病因病機較為復雜,張素娟等[5]認為,本病屬本虛標實,正虛是其反復發作、遷延不愈的根源,治療應以補氣血、祛濕熱等為根本。
1 病因病機
CU俗稱“風疹塊”“鬼飯疙瘩”,《素問·四時刺逆從論》[6]曰:“少陰有余,病皮痹隱軫。”《神農本草經·充蔚子》[7]記載:“莖主癮疹癢,可作浴湯。”這是“癮疹”作為病名的最早記載。脾胃運化功能在氣的生成中占據重要地位,而本病多因表虛不固,感受風寒、風熱、濕熱之外邪,營衛不和,邪氣克于皮膚,而起風騷癮疹。脾胃也是后天之本,容易被外邪、情志、飲食、勞倦等所傷[8-9]。CU的發生與脾胃密切相關,應從脾胃論治,把握治療關鍵,分清標本,明確虛實;且CU病久可致脾胃損傷,脾虛濕停,濕熱內生,日久灼津煉痰[10-11]。袁愛紅教授在臨床診治中發現,CU患者多由肺胃郁熱所致,患者大多喜食辛辣刺激之品,致使胃腸積熱,而生痰熱,又復感風邪,營衛不和,致使玄府閉塞,氣機運行不暢,內不得疏泄,外不得透達,邪氣郁于皮毛腠理之間而發病。CU與患者體質也關系密切,患者素體陽熱,過食寒涼,致肺胃郁而化火,邪熱壅滯體內,不得宣泄,交爭于肌表,導致疾病的發生。
CU病程遷延,反復發作,多數患者伴有情緒不定、煩躁不安癥狀,易致肝氣郁結,日久郁而化火,肝火灼傷脈絡營陰,陰陽不和,夜寐難安[12]。袁師強調CU與心、腦關系密切,心主火,心火盛則郁熱更甚,熏蒸于肌膚而致疹色鮮紅;腦主神志,神志異常,上擾清竅,可致患者失眠。此外,飲食失調、體質因素也是影響癮疹發病的主要因素之一。現代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參與中樞神經系統的雙向調節,調控免疫系統,且不良飲食可改變腸道菌群菌株的分布,進而誘發本病[13-14]。研究指出,腸道菌群可相當于人體的一種重要“器官”,與人體營養代謝、消化吸收及免疫應答等關系密切,甚至對疾病的發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15-16]。現已知多種疾病均與腸道菌群紊亂相關,例如糖尿病,類風濕性關節炎,炎癥性腸病及自閉癥等,表明腸道微生物的紊亂不僅與腸道疾病相關,還可引起其他器官、系統的疾病發生。目前認為,腸道菌群在幫助機體營養代謝與阻止外源微生物感染方面起重要作用[17]。根據現代研究,袁師結合自身臨床經驗提出胃腸道功能紊亂會引起免疫功能失調,進而導致CU的反復發作,故調整胃腸道功能其意有二:一因素體脾胃虧虛,易受外感邪熱侵襲,加之飲食不節,邪熱郁于胃腸,從而致胃腸功能失調;二因素體胃熱,復感外寒,加之嗜食肥甘厚膩,痰熱互結于胃,致肺胃郁熱更甚,影響胃腸功能。因此治療時袁師首清肺胃之郁熱,調理肺胃之功能。
2 治療方案
2.1 臟腑與經絡學說 袁師認為,肺胃在經絡聯系上極為密切,《靈樞·經脈》曰:“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而胃之大絡,又“貫膈絡肺”。從氣血循行來看,手太陰肺經為十二經脈之始,足陽明胃經為十二經脈之長,陽明的盛衰直接影響肺經乃至十二經氣血的盛衰。從表里兩經看手太陰肺經和手陽明大腸經相表里,足陽明胃經和足太陰脾經相表里。《素問·痿論》曰:“肺主皮毛”,“皮毛”為一身之表,主要由汗腺、皮膚及毫毛等組成,主要對汗液分泌、水液代謝、呼吸和抵御外邪之功能起調節作用,是人體重要的免疫器官,協助人體抵抗外邪[18-19]。由此可見,肺胃關系之密切,經絡上的直接相通,為兩臟在生理、病理上的影響,以及氣血在脈象上的變化奠定了理論基礎。陽明經為多氣多血之經,且肺經與大腸經相表里,“肺主皮毛”,肺經經氣異常可導致皮膚病的發生,三者之間關系極為密切。
2.2 臨證取穴 治療上袁師依經重用陽明、太陰兩經穴位,取臂臑、肩髃、曲池、合谷、足三里、血海、陰陵泉、內庭、百蟲窩,其中曲池、內庭,可清泄肺胃之郁熱;血海、陰陵泉清熱、養血、息風,取“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義;足三里與內庭,清泄胃腸郁熱,合陰陵泉健脾、化濕、利水,可健運脾胃功能;臂臑、肩髃為治療癮疹之經驗效穴,在《西子名堂灸經》《針灸真髓》中均對此穴治療癮疹有所記載;百蟲窩為治療癮疹瘙癢之經外奇穴。取頭面部百會、神庭,以鎮靜安神;取腹部脾胃經與小腸經募穴,如中脘、天樞、章門、關元,旨在調理脾胃功能與胃腸道菌群,從而調節患者免疫功能。以上諸穴協調作用,施以針灸,起到清肺胃郁熱、通經絡、調氣血的功效,內合治臟腑,外透達腠理,故體表充實,皮疹自消[20-21]。袁師擅用耳穴,選取肺、胃、心、神門、風溪、內分泌,操作時采用0.18 mm×13 mm的毫針直刺,留針30 min。此外,針灸療法作為外治療法,除調理臟腑氣血之外,還可直刺皮部,對皮膚腠理有直接調節作用,治療本病有針對性強、不良反應少、療效確切、復發率低的特點。
2.3 組方遣藥 袁師根據其多年臨床經驗,博采眾長,自擬消疹方,方藥組成如下:炒黃芩、后下、茜草、知母、炒赤芍、蒼術、川防風、炒丹皮、生地黃、灸遠志各10 g,郁金12 g,生大黃、新疆紫草各6 g,凈山楂、薄荷、陳皮、炒枳殼各9 g。方義:黃芩、大黃、知母、薄荷,清肺胃上焦之熱毒;茜草、紫草、炒丹皮,活血涼血,祛瘀通經;當歸、川芎、養血活血,取“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義,蒼術、防風,燥濕固表;遠志、郁金、理氣舒肝,解郁安神;凈山楂、陳皮、炒枳殼,理氣化痰消積。諸藥合用,既清肺胃郁熱,亦奏涼血養血活血之效,輔之疏肝解郁安神,對于CU的治療可起到標本兼顧的臨床效果。
3 醫案舉隅
3.1 典型病例一 患者畢某,女,39歲,2020年5月2日初診。患者4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身起風團,劇烈瘙癢,皮損多可自行消退,時有反復,自服抗組胺藥物治療可改善癥狀。近期癥狀發作頻繁:雙臂少數紅斑、散在抓痕,伴瘙癢。納可,入睡困難,二便調。月經規律,量偏少。皮膚科查體:雙側前臂對稱少量風團、紅腫斑片,散在抓痕;皮膚劃痕癥(±);舌質暗紅,苔黃膩,脈滑數。西醫診斷:CU;中醫診斷:癮疹;辨證:肺胃郁熱證;治法:清瀉肺胃郁熱。處方:黃芩、大黃(后下)各6 g,茜草、紫草、知母、赤芍、蒼術、防風、牡丹皮、當歸、川芎、遠志各10 g,郁金、生地各12 g,薄荷、凈山楂、陳皮、炒枳殼各9 g,共14劑,1劑/d,水煎服,早晚2次分服。取穴:百會、神庭、合谷、曲池、足三里、內庭、血海、陰陵泉、百蟲窩,針刺手法均平補平瀉,留針30 min,15 min行針1次,4次/周,10次為1個療程。
2020年5月16日二診:皮疹基本無反復,偶有癢,無皮疹,時有乏力。納可,眠差,入睡困難,大便日一行,時不成形。加用耳穴,選內分泌、皮質下、風溪、心、肺、胃、肝。原方去茜草加白術、山萸肉各30 g,黨參、合歡皮各10 g,1劑/d,以水煎服,早晚分服。
2020年5月30日三診:皮疹消退,納可,入睡困難較前明顯改善,小便調。半年后電話隨訪,訴瘙癢、皮疹基本消失,偶有發作可自行緩解或消失。
按:患者為女性,病程4年,長期服用抗組胺藥物,皮疹與瘙癢控制不佳。平素因CU作息不規律,睡眠差,結合四診,證屬肺胃郁熱證。患者病程日久,雖有肺胃郁熱之表現,而久病必虛。袁師認為患者病程日久,在針刺治療的基礎之上,應采用耳穴直刺的方式,鞏固療效。一方面清瀉肺胃郁熱以穩其標,另一方面注重顧護患者之正氣以固其本,使治療效果更加確切。
3.2 典型病例二 患者張某,男,28歲,2021年1月6日就診。患者訴CU已2年,每于冬季復發,病程長,瘙癢明顯,影響夜間休息,平時口服左西替利嗪片,癥狀可緩解,但停藥后易復發。就診時,患者皮損呈淡紅色,界限不清,皮疹以四肢為重,納一般,眠差,二便正常。納寐差,小便黃,大便干,舌質暗紅,苔黃厚膩,脈滑數。西醫診斷:CU。中醫診斷:癮疹(肺胃郁熱證)。治則:清瀉肺胃郁熱。具體用藥:黃芩、大黃(后下)各6 g,茜草、紫草、知母、赤芍、蒼術、防風、牡丹皮、當歸、川芎、遠志各10 g,生地、郁金各12 g,薄荷、凈山楂、陳皮、炒枳殼各9 g,水煎服,共14劑,1劑/d,早晚分服。用藥期間囑患者飲食清淡,多飲水,勿熬夜。取穴:百會、神庭、合谷、曲池、足三里、內庭、血海、陰陵泉、百蟲窩,針刺手法均平補平瀉,留針30 min,15 min行針1次,3次/1周,10次為1個療程。
2021年1月20日二診,患者自訴癥狀減輕,出疹較前減少,但仍有瘙癢不適,夜間為重,影響睡眠。在原方基礎上去生地、陳皮、枳殼,加用白術30 g,黨參10 g,酸棗仁、夜交藤各12 g,再服14劑;繼續原方針刺。
2021年2月5日三診,患者自訴癥狀基本消失,夜間睡眠較前明顯改善。為鞏固治療,保證睡眠,故繼門診行針刺治療。若皮疹無反復,無需再診。
按:患者為男性,病程日久,且反復發作,結合四診,證屬肺胃郁熱證。患者久病,邪熱壅滯體內,肺胃之熱邪郁于肺胃,發于肌表,而發本病。袁師治療患者時,首清肺胃之郁熱,在病程后期,同時更顧護患者脾胃之正氣;患者病程日久,情緒波動大,也注重調整患者情緒,在臨床上進行有機結合,靈活運用針藥,達到治病求本之功效。
3.3 典型病例三 患者孫某,女,32歲,2021年2月10日初診。主訴:全身瘙癢、起風團半年余。初起因食辛辣食物后,全身皮膚突發紅色風團,癢劇,服用雷尼替丁后皮疹消退,瘙癢減輕,后嗜食辛辣油膩之品上述癥狀即復發,服上藥后療效欠佳。今患者全身大片皮疹,胸腹部較密集,瘙癢劇烈,伴腹脹,口酸,小便黃,大便1次/4 d,便干,夜寐欠佳,遂來求醫。患者體形偏瘦,舌紅苔厚膩,脈滑數。西醫診斷:CU。中醫診斷:癮疹(肺胃郁熱證)。治則:清泄肺胃郁熱。具體用藥:大黃(后下)、黃芩各6 g,茜草、紫草、知母、丹皮、川芎各12 g,生地黃、郁金、薄荷、凈山楂、陳皮、炒枳殼各15 g,水煎服,共14劑,1劑/d,早晚分服。用藥期間囑患者飲食清淡,多飲水,勿熬夜。取穴:百會、神庭、合谷、曲池、足三里、內庭、血海、陰陵泉、百蟲窩,針刺手法均平補平瀉,留針30 min, 15 min行針1次,3次/周,10次為1個療程。
2021年2月24日二診,患者訴皮疹明顯好轉,瘙癢減輕,晚夜間偶有發作性瘙癢,時有腹脹,口酸明顯減輕,大便1次/2 d。在原方基礎上,加用厚樸6 g,夜交藤、合歡各9 g,酸棗仁12 g,另加用耳穴,選內分泌、皮質下、風溪、心、肺、胃、肝。操作方法:0.18 mm×13 mm毫針直刺,留針30 min。
2021年3月10日三診,患者訴皮疹和瘙癢癥狀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夜寐尚可,二便尚調。漸停中藥,囑患者仍需門診繼續行針刺治療1療程。3個月后隨訪,皮疹和瘙癢偶有發生,均可自行緩解。
按:患者為女性,平素嗜食辛辣飲食、作息不規律,綜合四診,證屬肺胃郁熱。患者均為素體陽熱,平素嗜食辛辣,致肺胃郁而化火,邪熱壅滯體內,發于肌表,而發本病。袁師重用手足陽明經、手足太陰二經,巧用耳穴,輔之自擬消疹方,針藥有機結合,共奏清泄肺胃郁熱、止癢退疹之功效。
4 結語
中醫藥在治療CU 疾病中能隨證施治、臨證加減,用藥靈活,各類經典中有諸多針對不同證型癮疹的經典方劑,可以根據患者證型的不同,運用不同組方,能因人、因時、因地確立方藥,與西醫單純應用抗組胺類藥物相比,其針對性與機動性更強。袁師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臨床接診眾多CU 患者,結合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與飲食特點,從肺胃論治CU,并提出從腸道功能與免疫系統關系的角度診療此病,注重顧護脾胃功能以固其本,輔以清瀉肺胃郁熱以穩其標,針藥結合治療此病,應用于臨床中,療效頗佳。但臨床對CU 的機理研究較少,仍需中醫藥工作者的不斷努力,加強對傳統醫藥的研究,探討該病的發病機制與中醫藥治療機理,以發揮中醫藥的特色。
筆者就袁師治療CU 的經驗和思想進行學習和思考,并將跟師所見所感作一總結,由于筆者跟師時間甚短,醫道尚淺,在分析總結時難免以偏概全,還請各位師長同道不吝訂正。袁師在臨床實踐中,面對疑難雜癥時,辨證時不拘局限于一方一藥和定向思維,四診合參,把握氣血的盛衰,陰陽虛實的夾雜,包括患者體質,綜合辨證,同病異治,變通用藥,靈活用針,針藥結合,做到更具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