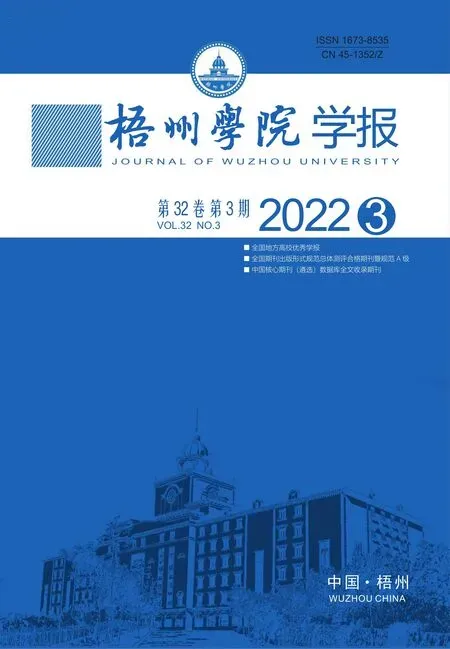綠色制造研究綜述及啟示
陳曉昀
梧州學院 機械與資源工程學院,廣西 梧州 543002)
作為傳統制造業轉型發展與綠色科技創新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和新業態,綠色制造已成為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和科技競爭的重要新興領域。制造業既是國家的經濟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中國制造2025》把綠色制造工程作為“中國制造2025”五大工程之一。綠色制造是“中國制造2025”的具體行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利器,是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工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是企業創新發展的推動力和創造績效的加速器。本文在闡明綠色制造的內涵、分析國內外綠色制造研究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綜述綠色制造及其能力提升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旨在為我國企業積極開展綠色制造創新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依據。
1 綠色制造的內涵
綠色制造也稱環境意識制造(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Manufacturing)、面向環境的制造(Manufacturing For Environment)等,是一個以生態環境與資源效益作為核心考量因素的現代制造模式[1]。促使產品從設計、生產、運輸到報廢處理的全過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最小,是綠色制造的目標[2-6],故綠色制造又被稱之為清潔制造。早在2000年,我國學者劉飛、曹華軍、何乃軍認為,綠色制造是一種綜合考慮自然環境和資源消耗,以達到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三者協調優化為目標的現代制造模式[7],與劉旭[4]、孫柏林[5]、宋天虎[3]、衣飛宇[6]提出的觀點大同小異。綠色制造涉及到環境、制造、資源等多學科交叉領域,其愿景是試圖促使整個產品全生命周期盡顯綠色,盡可能實現生態環境的負影響最小甚至趨于零、盡可能提高資源利用效能,使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盡可能共贏并可持續協調優化。
2 綠色制造研究綜述
2.1 國外研究綜述
2.1.1 綠色制造大勢所趨
綠色制造初始稱之環境意識制造。美國學者Hart研究發現:通過綠色制造技術可以減輕環境污染,使企業的規制遵守成本下降,并認為環境意識制造是同時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8];美國制造工程師學會(SME)1996年發布《Green Manufacturing》藍皮書,把綠色制造與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作為工業化快速發展背景下應對環境污染與資源短缺的機械制造創新模式[2]2,此后,隨著SME以綠色制造為主題的報告不斷對外發布及影響力不斷擴大,綠色制造在世界范圍內關注度迅速提升,英國、德國、加拿大、中國、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家紛紛制定并實施綠色制造戰略。毋庸置疑,工業轉型升級的發展,綠色制造是一個必然趨勢和大邏輯,在世界制造業領域中深入人心,并日益成為全球持續熱議的話題和深耕的土壤。
2.1.2 學會、協會引領研究
隨著綠色制造實踐績效的凸顯,各國相關學會協會相繼開展相關研究,并將綠色制造作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歐洲國際生產工學會對綠色制造產品生命周期與環境保護協調性的邏輯關系進行了探究[9];綠色制造在全球得到進一步重視與推廣應用,得益于國際標準化組織(ISO)1998年頒布的環境管理標準出爐[6]8。2010年英國可持續設計中心(The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sign,簡稱CFSD)除了對可持續性產品生命周期設計和環境設計等進行深入研究外,還開展了相關教育,同時發行了《The Joumal of Sustainable Product Design》(《可持續產品設計》)雜志[10],進一步擴大了其研究成果及綠色制造的影響力;英國拉夫堡大學成立創新制造與工程研究中心,對設計、工藝、材料、業務及管理的全流程開展廣泛研究[11];美國密歇根理工大學從2009年開始,在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專攻清潔生產技術,認為清潔生產技術實質上是在工業生產過程中,能夠使各種廢棄物有效降低,“三廢”排放量最小化[12];加拿大Windsor大學對制造行業的生態設計、綠色制造周期等進行了深入探索[13];劍橋大學可持續制造研究團隊在工業制造尤其是綠色工藝開發方面的研究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其研究領域涉及先進綠色工藝、聚合塑料和紡織品的回收利用、可持續生產的理論研究與應用、逆向供應鏈等[14];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成立可持續制造與生命周期工程研究組,與就業、經濟發展創新等部門對綠色制造相關問題進行產學研相結合研究[15];美國中西部研究所持續研究開發的Sima Pro、Gabi、Ecoinvent、Solid Works、Sustainability等綠色產品生命周期評價技術方法(LCA)與生態設計軟件及其基礎數據庫,以及ISO標準LCA研究框架,成為各國政府及其企業和消費者進行綠色制造研究分析與決策的參考標桿[16]。由此可見,學會、協會或研究院對綠色制造研究的主要內容體現在:一是強調綠色制造的產品生命周期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二是把綠色周期、生態設計、綠色材料、可持續生產、綠色數字化、綠色(清潔生產)技術與綠色工藝創新作為綠色制造的研發重點[17];三是把科學制定生態法規與綠色標準及綠色評價方法,作為實施綠色制造措施與技術推廣應用的先行條件。
2.1.3 專家學者聞風而動
早在1988年瑞典學者Thomas就提出了旨在降低企業產品環境影響的環境保護戰略EPR制度。Gutowski通過參加美國能源部對發達國家50多家企業調研項目研究分析,認為基于環境友好型的制造業發展是必然趨勢[18];Bras & Reap運用生物學方法,進行綠色設計研究,對企業綠色產品開發與生命周期綠色工程進行了設計與評價[19];Porter[20]、Misiolek & Eider[21]、Barla & Ambec[22]、Popp[23]、Sheppard[24]、Costantini & Mazzanti[25]、Yang[26]、Kemp[27]研究表明:環境規制與經濟績效呈正相關,環境規制不僅能夠激勵企業綠色制造的技術創新,而且還能有效促進企業提高經濟績效和競爭力;Thomas Graedel將生態環境與企業發展緊密相連,進行協同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28];Mariana,王偉昊經過多年來對綠色制造探索,認為在創新活動中,制造業乃至其他行業的中小企業創新能力提升,有賴于與大型企業加強聯系[29-30];Adrien Presley認為,充分運用現代計算機與自動化技術,加強智能化工藝創新理論研究及其成果運用,來有效提升工藝創新效率和制造能力[31]。可以看出,國外專家學者的研究聚焦于:一是將生態學、生物學、生命學和經濟學等學科原理融入綠色制造研究中,豐富了綠色制造研究內容和成果,形成了文理兼容、多學科整合的綠色制造研究方法;二是將研究視角向縱深發展,直接延伸到綠色制造的具體實施者企業中,將發展環境與企業技術創新、環境規制與企業績效、生態環境與企業發展、智能化工藝創新與企業競爭力、綠色制造與企業創新能力有機結合起來,促使企業提高綠色制造自覺行動意識和實踐績效。
2.2 國內研究綜述
2.2.1 研究機構不計其數
20世紀90年代,基于經濟快速增長與生態環境日趨失衡及自然資源日漸枯竭的背景,我國相關研究機構和學者開始關注綠色發展及綠色制造問題,在國家相關部委及其職能部門的支持下,對綠色制造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從中國綠色制造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中國綠色制造聯盟、綠色制造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等乘勢而生,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重慶大學、中國科學院、中機生產力促進中心、機械科學研究院、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創建綠色制造科技創新研究團隊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我國綠色制造研究蔚然成風。
2.2.2 學者研究雨后春筍
王能民等[32]、孫奎洲[33]、陶晉[34]、劉飛[35]、張光宇[36]、韓星[37]、鐘孟楠[38]、康靖晗[39]、李蒙蒙[40]、惠巖巖[41]等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了綠色制造理論,并進行了實踐探索。近年來,學者對于綠色制造研究進一步向縱深推進。王洪濤和陸銘論證了供需平衡、動能轉換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認為需以推動供需匹配和新舊動能轉換為導向,構建高質量的供需平衡體系、新能動體系與綠色制造體系,以實現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42];祖鵬陽通過SPSS23.0收集163份調查問卷研究顯示:綠色制造和環境規制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和經濟績效[43];陳昊和丁曉欽運用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綠色制造機理,認為:雖然在社會總價值層面上綠色制造具有明顯的價值創造效應,然而在行業和個體層面上綠色制造所創造的價值分配并不均勻,還可能發生價值轉移,在制定環境規制時要考慮多方利益博弈關系[44]。因此,曹華軍等提出了“企業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環境責任、生態責任和社會責任”[45],宋天虎[3]、孫柏林[5]、劉旭[4]和趙立華等[46]也提出了“綠色制造是一個綜合考慮環境影響、資源消費、社會和企業效益的現代制造模式,需綜合運用法律、金融、政策、標準等手段的支持、約束、引導甚至強制推動”等觀點;李新創[47]、郭立瑋等[48]分別從鋼鐵行業和中藥領域對行業綠色制造理論與技術進行了探討;王婷等對智能制造與綠色制造協調發展開展了研究,以產品生命周期為主線,提出大數據驅動的綠色智能制造服務體系和實現思路[49];晏恒等對照 《江西省綠色制造體系建設實施方案》,認為江西省綠色制造體系建設中要“強化管理體系建設、完善綠色制造標準體系、加大可再生能源推廣力度、完善體制機制以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50];榮燕燕從政策支持、服務升級、科技創新等方面提出了推動上海市構建高效、清潔、低碳、循環的綠色制造體系的相關建議[51];周志超認為,加強綠色制造統籌規劃、加快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提高企業綠色生產意識、提升綠色制造技術創新和應用,是廣西綠色制造發展之路[52];王斌來等認為“綠色制造推動高質量發展”[53];江小國和何建波從要素支撐、生產組織、產業提升與行業治理4個維度把握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推進路徑[54];李錦把“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應用數字技術的智能制造產業成為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作為“十四五”中國企業發展大趨勢之一[55]。與國外研究成果相比,綜合分析可知,我國學者對綠色制造研究內容具有中國特色,更趨于本土化和區域性。主要體現在:一是與時俱進地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綠色制造對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問題;二是專注環境規制對綠色制造、價值創造、綠色績效和綠色發展的邏輯關系;三是細化研究內容,把本地化、行業化、責任化、規劃化、服務化、標準化、模式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綠色制造,作為促進我國企業綠色制造的發展方向和行動標桿及推動我國企業綠色轉型發展的重要載體。
2.3 各國以及國際組織綠色制造戰略
德國政府制定《德國工業4.0》,《資源效率生產計劃》把資源效率列為工業4.0的關鍵領域,把促進經濟可持續性和競爭力作為未來工業目標[56];美國政府發布《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先進制造業的國家戰略計劃》、《制造業促進法案》、“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可持續制造促進計劃”等系列法案,推進綠色制造發展,《先進制造伙伴計劃》提出把“可持續制造”列為11項振興制造業的關鍵技術之一,并由能源部、商務部、國防部、基金委等聯合構建了《美國先進制造戰略框架》[57];英國政府發布《英國制造2050》、《高價值制造業戰略》,在《未來制造報告》中預計:全球人口從目前的70億增加到2050年的90億,隨之工業產品需求翻一番,繼而材料及資源需求量翻三番,從而制定了《2013—2050年可持續制造發展路線圖》,以應對未來人口、環境、資源等嚴峻挑戰[58];日本高度重視綠色制造發展,發布《綠色革命和社會變革》,2008年實施《建設低碳社會的行動計劃》,2012年在國家戰略發展大會上發布《綠色發展戰略總體規劃》,將新型裝備制造、機械加工等作為綠色制造發展重點,將節能環保汽車、大型蓄電池、海洋風力發電培育和發展列為落實綠色發展戰略的三大支柱性產業[59];韓國“新增長動力前景及發展戰略”和法國《新工業法國》提出“綠色供應鏈”、“低碳革命”、“增材制造”,進一步豐富綠色制造的內涵及其模式。在我國,國務院《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標志著綠色制造發展成型。爾后,科技部《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2011)、國務院《中國制造2025》(2015)等規劃或戰略文件,尤其《中國制造2025》,是中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10年的國家行動綱領[60-65],明確提出了“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到2025年綠色制造體系基本建立”[62],為中國制造業未來10年設計頂層規劃和路線圖。與此同時,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相繼發布實施了環境管理體系、《能源管理體系要求》等系列標準,以推動全球綠色制造發展。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各國以及國際組織研究制定的綠色制造戰略,一是基于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人口變化等綜合背景,綠色制造戰略已成為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政策略;二是各國政府推行綠色制造發展前,已經進行了科學的頂層規劃,設計了周密的發展路線圖,制定了詳細的發展規制與綠色標準。
3 研究分析及啟示
3.1 研究分析
3.1.1 研究領域高度集中
通過梳理與分析目前國內外綠色制造相關研究成果及各國綠色制造發展戰略,對綠色制造研究可歸納為三大領域:一是綠色制造發展的頂層設計,如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制定和發布的綠色制造發展規劃或戰略文件,以及綠色標準體系。這是綠色制造發展的先決條件;二是綠色制造核心概念、框架理論、方式模式、政策體系、能量模型、區域推進等研究。這是綠色制造發展的理論依據;三是對以綠色為底色的設計、材料、裝備、工藝、包裝、建筑、評價等綠色制造技術應用與創新研究。這是綠色制造發展的實踐指南。
3.1.2 豐碩研究成果與不足并存
通過對國內外綠色制造研究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各國學者或研究機構關于綠色制造研究及其成果,聚焦于綠色制造概念、綠色規制、綠色產品設計、環境意識制造、綠色工藝開發、產品生命期回收、綠色技術創新等方面[6],而關于綠色制造對企業綠色發展的影響效力與作用效能、企業綠色制造能力提升策略[5]、企業綠色制造實施效果及其能力提升路徑等方面研究,仍有很大空間,且現有研究中主要把綠色制造作為一項工程技術研究[6],而非聚集于綠色制造具體實施者(即企業)的綠色制造績效能力或競爭力等經濟手段研究。同時,直接對接企業及其綠色生產鏈、綠色供應鏈的接地氣能力研究關注度不夠,仍有較大研究空間。
3.2 借鑒啟示
3.2.1 綠色制造大勢所趨
綠色制造作為一種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已成為全球第4次工業革命和第4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新興領域,是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利器,也是企業轉型創新發展的引擎和企業創造綠色績效的載體。全面推行綠色制造,是破解工業化導致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失調問題的根本之策,是中國工業在經濟新常態下的必然選擇[66]。可以預計,數字化和智能化時代,作為經濟主體,企業通過人工智能實現綠色制造的同時,在智能制造與綠色制造協調發展中,不斷提升企業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績效及其高質量發展能力,將成為現代企業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有機結合的大邏輯。
3.2.2 綠色制造特征日益凸顯
目前,全球面臨著諸如生態失衡、環境惡化、資源枯竭、人口膨脹等困擾著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與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許多世界性難題,急需世界組織和各國政府既要高瞻遠矚進行頂層設計,又要腳踏實地進行實踐創新,來妥善解決。綠色制造的橫空出世,既是各國政府的新政施政要義,又是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這當然源于綠色制造特征。從綠色制造的內涵及其學術界的全球性研究熱度分析,低碳、清潔、環保、綠色、智能、創新、經濟、全球、可持續等等,這些方面凸顯了綠色制造的基本特征及其優勢。
3.2.3 企業綠色制造能力提升及其策略研究尤為必要
資源和環境是經濟社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兩大基礎性要件,其戰略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曹華軍等學者曾研究預判:按現在發展模式,到2020年中國人均生態足跡是人均生態承載力的6倍,將出現嚴重生態赤字[45]。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與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在北京聯合發布的《城鎮化與生態足跡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均生態足跡將在2029年達到峰值,為2.9全球公頃[67]。由此看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嚴峻的資源匱乏和環境治理的壓力。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的重大決策。與此同時,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在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兩型)社會建設背景下,企業綠色制造能力提升及其策略研究已成為解決制造業發展瓶頸的重要課題,既是當今世界時代潮流之急需,也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之要義,更是企業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之必需。
4 結語
4.1 闡述了綠色制造內涵及其發展趨勢
綠色制造涉及到制造、資源、環境、社會等多學科交叉領域。高質量發展需要綠色制造強有力支撐。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盡可能達成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共贏并可持續協調優化,是綠色制造愿景及其發展戰略。
4.2 梳理了國內外綠色制造研究成果
研究顯示:綠色制造作為一種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正成為全球第4次工業革命和第5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新興領域,以及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制高點和核心競爭力。發展綠色制造將促進我國新一輪技術創新與革命,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利器。
4.3 綠色制造大勢所趨已成為全球共識
我國經濟社會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尤為重要與緊迫。高度重視綠色制造戰略規劃。綠色制造頂層設計固然重要,落地生根更為可貴。綠色制造不僅僅是一項工程技術,而更是工業企業綠色制造實踐及其績效能力和競爭力提升的經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