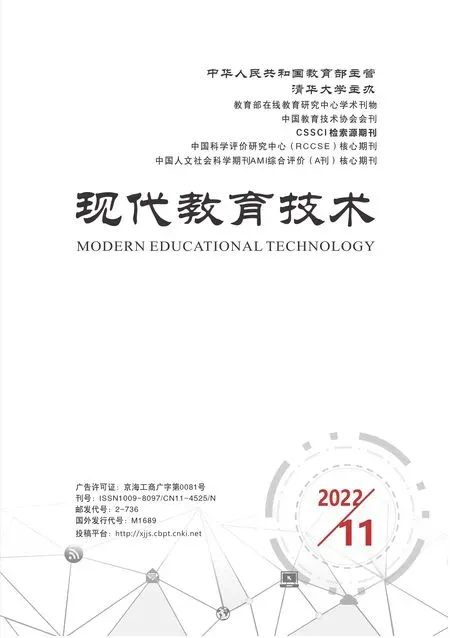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與行動框架*
舒 杭 顧小清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與行動框架*
舒 杭1顧小清2
(1.江南大學 “互聯網+教育”研究基地,江蘇無錫 214122;2.華東師范大學 教育信息技術學系,上海 200062)
數字化轉型是在信息化、數字化基礎上,通過充分挖掘并發揮數據的價值,以實現對教育系統的重塑,這為教育數字化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教育系統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和要求。文章從數字技術發展和教育創新發展兩個角度進行分析,發現當前的教育已然具備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然而,目前人們尚不清楚如何系統地去布局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為此,文章從“轉什么”“如何轉”“誰來轉”“轉去哪”四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并強調:在規劃轉型戰略時需考量目標與過程的系統變革,在設計轉型方案時應遵循政策導向與實踐導向的雙重范式,在落實轉型實踐時需重視“政-校-家-社”多元協同,在檢驗轉型成效時應聚焦教育新生態的“創變”。理清現實基礎并據此制定明確的行動框架,是我們尋找未來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路向的出發點,亦是推進我國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落地的行動指南,需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教育數字化轉型;現實基礎;行動框架;教育新生態
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再到數字社會,技術正在加速人類文明進化與社會變遷的進程[1]。其中,數字技術正在以不可逆轉的勢頭重塑整個社會的形態與結構[2],并促使整個社會都在經歷數字化轉型,因而教育的數字化轉型也成為了一種必然。以美國、歐盟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積極部署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3],如歐盟的《數字教育行動計劃(2021-2027)》、美國的《數字化轉型的領導力》等都強調教育數字化轉型對于社會進步與國力提升的重要性,希冀通過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數字化教育的深入推進,來應對全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挑戰與沖擊。受國際社會高度重視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我國也陸續確立了“數字中國”“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等目標與任務。然而,當談論教育數字化轉型時,我們卻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對于“教育為什么要進行數字化轉型?”“教育是否已具備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具體如何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等問題了解甚淺,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以明確未來教育改革的行動方向和著力點。
一 數字化轉型及其對教育的影響
1 何為數字化轉型?
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數字化轉型在教育這一特殊領域的表現形態,那么何為數字化轉型?對于此問題,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公認的權威答案。人們常將“信息化”“數字化”“數據化”“數字化轉型”等概念混為一談,這就造成了術語使用方面的混亂[4]。因此,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定義之前,有必要先對這幾個相關的概念進行深入辨析。
①信息化、數字化不等于數字化轉型。信息化是針對于單個系統或者系統局部的優化,由此帶來的一個明顯弊端是“數據孤島”的出現。而數字化從更為全局、全域的視角對系統和組織進行性能優化,尤其是在數據聚合方面,數字化使得“數據”成為一種全新的“隱形資產”。但是,信息化和數字化都不能被視作數字化轉型,其根源在于信息化與數字化指向技術的作用方式與手段,而數字化轉型更加強調行動的實踐指向。
②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是發揮數據價值。歷經多年的信息化建設、數字化發展,數據已成為數字化轉型的強大驅動力和基礎[5]。數據的使用可以刺激創新的出現,是提高生產力、改進決策的關鍵。數字化轉型指向整個系統的重塑,意味著相關業務需使用新的數字技術以實現突破創新,這不僅涉及資源的數字化,更關乎通過數字資產創造新的價值。在轉型過程中,數據要素將承擔“動力引擎”的重要角色[6]。因此,要想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長遠目標,必然要充分發揮數據的潛在價值。
③數字化轉型是組織的系統性“重塑”。早期,學者更愿意將數字化轉型解釋為“使用ICT技術從根本上創造和賦予商業、公共政府以及人們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新能力”[7],這樣的理解更多地傾向于對技術的價值審視。而Demirkan等[8]認為,數字化轉型應當是對業務活動、流程、能力和模式進行的深刻轉型。這種深刻轉型將帶來新的參與者、結構、實踐、價值觀和信念,也將改變組織、生態系統、行業或領域內的現有法則。
綜上,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新技術帶來的漸進式流程改進,更是充分利用新方法和數字技術從根本上對整個系統的內部要素及其關系、系統與外部環境關系的重塑,以形成新的生態系統。
2 數字化轉型對教育的影響
積極擁抱數字化轉型,既關乎教育的核心價值觀重塑,也關涉豐富和拓展教育的使命重建。數字化轉型有可能帶來極具創造性的新教學策略,并使教育能夠觸及更大量、更多元的人群。同時,數字化轉型為教育研究方法、流程的改進和創新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如基于大數據的價值挖掘、基于全樣本的大規模調查等都為審視教育的現實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證據來源。在此背景下,數字化轉型給教育領域帶來的回報無疑是符合預期的。但要在教育領域實現數字化轉型,就需要發揮多種驅動因素的協同作用,不僅包括育人目標調整、教學方式更新、教育資源生成等內部因素的牽引,也包括教育政策、技術期待、教育價值重新定位等外部因素的推動。這些復雜因素的交織融合,既為教育變革的發生提供了可能性,也為教育生態系統的重塑創造了機會。教育數字化轉型要求對傳統思維和核心實踐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實際上這也是對教育價值主張的重新構想。遺憾的是,目前我們還沒有獲得讓教育適應整個社會數字化轉型進程的有效實施策略。
二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
教育要實現數字化轉型,除了充分依賴數字技術的支持,還需要教育創新發展達到一定的水平——兩者構成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那么,當前的教育發展是否已具備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對此問題的回答,可從數字技術發展和教育創新發展兩個角度去分析。
1 數字技術發展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搭建了實踐平臺
數字化轉型的表現一方面是基于數字技術和技術的應用對組織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是新數字產品和服務的介入帶來了新變化。數字技術正從根本上改變組織的運作方式,而數字化學習的成功取決于是否有恰適的技術準備[9],可見數字化轉型必須依托于新一代數字技術[10]。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教育新基建,將為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強大物質技術基礎[11]。教育數字化轉型需以數字技術為基礎,而數字技術的發展狀態將決定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肇始與推進效率。如果不考慮技術的底層基礎建設,這種根本性的改變將難以實現,那么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就是:當前數字技術是否已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打好了基礎?我們的技術底座能否充分支持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
數字化轉型中的技術大致可分為三大類:ICT技術、智能技術、數據技術。其中,ICT技術為復雜系統的開發提供了必要條件。例如,廣域/局域網、5G通信、身份識別、定位系統等基礎型ICT技術,為教育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外部環境架構和技術“基石”。在此基礎上,眾多的新興技術得以集成、擴展,并為賦能教育教學創造了條件。人們普遍認為,數字技術尤其是智能技術可以極大地改變組織的形態與結構[12],并將深深根植于教育系統之中。例如,聊天機器人通過文本或語音識別提供在線交互服務,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算法被用于預測學生的成績等[13]。此外,數據技術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強大驅動力,始終支持著教育信息化的建設與發展,且各類系統中數據的累積呈“指數級”增長態勢。尤其是伴隨著多傳感器在教育場域中的嵌入,多模態數據與分析技術在破解教育“黑匣子”方面的價值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重視。
2 教育創新發展為教育數字化轉型帶來了新契機
①教育數字化環境的進一步拓展,促進了學習的高效發生。技術是教育創新的基礎,隨著互聯網、物聯網、5G等技術的不斷發展,教育的數字化環境已得到極大拓展。數字化學習空間已經實現了線上線下的無縫對接,場館、社區、家庭等新型的學習場域與學校場域高效聯動,將打破封閉的辦學體系、傳統的教學結構和固化的學校組織形態[14]。在這樣的空間里,人與人、人與機器之間的多層次高效互動變得便捷頻繁。尤其是當智能技術介入以后,學習者能以自然的方式與智能學伴交流,從而改變學習和創造知識的方式,擴展、增強學習者的思維和體驗[15]。
②優質數字資源的聚合迭代,推動了新型教學模式的常態化應用。在5G通信技術的支持下,技術為開展更多高階學習活動提供了多樣化數字資源的接入端口。2022年,“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正式上線。截至2022年7月,平臺已聚合了3.4萬條中小學資源、8000多門職業教育課程、近3萬門高等教育課程,這為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習提供了充分的資源和平臺保障。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下,依托這些優勢技術條件和優質資源實施的混合式、在線、協作式等新型教學模式,已然成為教育教學的新景觀。
③數字素養的全面提升,成為國際的共識目標。2021年,《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提出了“科普信息化提升重點工程”的行動方案,旨在將智慧科普與智慧教育深度融合,以提升人民群眾的數字素養,服務數字社會的建設[16];同年,《“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制定了“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的優先行動部署[17]。可見,提升數字素養與數字技能已經上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就國際層面來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歐盟等組織發布的報告也紛紛表達了對提高公民數字技能和數字化轉型能力的重視。
綜上可知,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道路上,無論是數字技術發展還是教育創新發展,都已經具備了推動教育走向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18]。
三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
數字化轉型要求我們深刻了解這種轉變發生的程度,并主動開展相關的變革行動。教育數字化轉型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19],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要想實現整個教育組織和教育系統生態的重塑目標,明確未來的行動方向是開展實踐的先決條件。然而,目前教育數字化轉型仍然是一個周旋于理念、價值、意義層面探討的話題,我們亟需一個能夠從整體、系統層面的行動框架來引領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具體實踐。行動框架是一系列以行動為導向的解釋模式,用于凝聚組織的成功經驗和指導組織的行動,不僅是個人態度和感知的集合,更是組織協商、共享意義的結果[20]。一個完善的行動框架往往包含明確的愿景、具體的執行過程、清晰組織成員關系、預期達成的目標四項要素,為此本研究從“轉什么”“如何轉”“誰來轉”“轉去哪”四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

圖2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變革元素
1 “轉什么”:目標與過程的系統變革
從本質上講,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教育的系統性、根本性變革。系統性變革模型被用來在更大的范圍內,解釋組織變革過程中各種變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關系。從組織變革的理論視角來看,教育數字化轉型亦可視為教育這一系統本身的根本性改變,尤其是教育系統的變革元素將發生徹底轉型,具體包括指向教育系統目標的戰略定位轉型、能力結構轉型和指向教育系統過程的教育機制轉型、教育組織轉型,如圖2所示。
①戰略轉型:強調從戰略層面的價值定位考慮。教育的數字化轉型首先要從戰略的高度進行整體設計,以引領轉型實踐過程的穩健推進[21]——這種設計不是舊有體系的延續或輕度改良,而是對傳統實踐范式和核心實踐進行實質性改變,從根本上說是對教育價值的重新構想。就國家而言,韓國在2019年發布的“邁向IT之外的AI世界領導者”戰略中,將人才培養和人類未來能力的提升作為其戰略實施計劃的重要內容;哥倫比亞政府認為“數字化轉型”正在徹底改變社會的結構,也將數字化轉型作為戰略核心;歐盟的“數字教育行動計劃(2021-2027)”戰略明確制定了“高性能數字教育生態系統發展”“迎合數字化轉型的數字技能和能力增強”專項行動。可以看出,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既關乎各國教育的未來發展,也會影響各國在整個國際教育格局中的梯隊與位階。因此,戰略定位轉型要重點關注國際教育的未來發展。
②能力轉型:強調以能力為本的人力資本輸出。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的發展,將改變大部分行業原有的體系結構,進而加劇教育的不平等。盡管對于技術取代人類的擔憂尚未廣泛流行,但不可否認的是,數字化轉型確實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巨大的沖擊[22],也對未來的勞動者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23]。技術在賦能、優化人類生產實踐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技術加劇了未來社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這就需要通過教育培養出更具創造力的技能型人才來應對相關的轉型挑戰[24]。因此,我們應更多地思考:如何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沖擊之下使自己處于“不可替代”的位置,讓自己具備更加契合社會發展、時代變化需求的核心競爭力?在教育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能力結構轉型需要提前規劃和布局,以能力為本的人力資本輸出關系著國家戰略的實現和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提升。
③機制轉型:強調數據驅動的教育治理格局。教育數字化轉型因受內外多重因素的作用,其實踐和發展必然涉及體制機制的改革。教育機制轉型是關涉教育數字化轉型整體設計與實踐推進的保障,也是推動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這是因為教育系統本身具有復雜性,其內部要素包羅萬象,對教育系統內部要素及其邏輯關系的治理需從整體上進行考慮;同時,作為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數字化轉型與社會數字化轉型之間的互動,需要我們從更為宏觀的視角對其進行整體性審視,如審視教育數字化轉型與技術變革、社會轉型、經濟發展等的關系。另外,數據是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驅動力,相較于經驗判斷,數據具有更為客觀的解釋力,因此在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對教育的治理也必然要實現從以往的經驗驅動快速過渡到數據驅動。
④組織轉型:強調系統視角的組織變革遠景。數字技術具有分散性、發展性的特點,因此由其引發的變革不僅存在于組織系統內部,還連同系統之外的一切實踐行動都發生改變。因此,數字化轉型終將引發和塑造系統性的組織變革與轉型。祝智庭等[25]指出,教育數字化轉型是一個綜合的、系統的、全方位的創新與變革過程。而Uvarov[26]認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教育活動內容、方法和組織形式轉變的過程。受數字技術的直接影響,教育系統內部的諸多要素及其關系將發生改變(如新的參與者、新的交互關系等),產生新的組織結構。同時,數字技術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也會間接影響教育的發展,形成技術與教育融合的不同模式,促使教育生態系統與社會其他子系統的互動結構發生變化,促進整個社會組織的協同進化。因此,教育數字化轉型必須始終圍繞系統層面的組織變革愿景來執行。
2 “如何轉”:政策導向與實踐導向的雙重范式
轉變組織以獲得應用先進數字技術所預期的效益,這早已不再是“能否”或“何時”的表層問題,而是對“如何實現”的深度追問。在教育變革的漫長歷程中,逐漸形成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雙重范式,包括以“政策導向”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和以“實踐導向”為特征的、自下而上的變革,如圖3所示。這兩種變革范式都是為了推動新技術的普及、應用,以加速教與學的流程改造,從而獲得更好的組織績效和更大的發展。

圖3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雙重范式

圖4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多元協同參與結構
①政策導向:注重激進式的顛覆性變革。所謂自上而下的政策導向,是指管理者根據組織需求和目標做出的決策。政策導向的變革邏輯更加注重通過文化轉型,來實現價值觀與范式的向下、向內滲透。文化轉型是數字化轉型的先決條件,體現的是一種“數字文化”調性,即強調對于數字化能力、數據驅動范式的高度關注。政策導向的變革是一種“激進式”(Radical Transformation)的顛覆性變革,由高層推動并大規模執行。例如,我國近年來發布的“互聯網+行動”“大數據行動”“教育信息化2.0行動”“人工智能創新行動”等,都從宏觀的視角確立了我國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在這些政策的指導下,教育數字化的發展與轉型穩步推進,而從這些政策中我們也能清楚地看到國家對“數字文化”的強調。無論是教育信息化還是“互聯網+”、無論是教育大數據還是教育人工智能,技術所應發揮的價值與作用都經由這些政策得以不斷向下滲透,最終落實并內化于一線的實踐活動之中。
②實踐導向:注重漸進式的進化性改良。與自上而下的政策導向不同,自下而上的實踐導向要從人的需求和投入開始,進而回升到組織層面。實踐導向的變革范式更加注重通過萃取最佳實踐,實現成功經驗與方案的向上、向外輻射。在很多情況下,最好的轉型方法往往不是革命性的,而是進化性改良,即教育管理和決策部門意識到了長遠發展的需求,在小型試點過程中探索新技術的真實、有效案例,并謹慎地擴大其應用規模。2016~2021年間,我國先后設置了13個大數據實驗室、18個智慧教育示范區、92個國家智能社會治理實驗基地、18個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1個教育數字化轉型試點區,試圖通過這些試點探索來積累契合整個國家教育發展和轉型的成功經驗。進化性改良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在實踐應用層面關注數字技術的真正用途,弄清楚技術如何創造價值、如何賦能教學以及如何變革教育。
然而,教育本身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系統內部各要素的協同作用、與外部社會之間的互動,決定了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因此,面對教育數字化轉型尚處于初級階段的現實,我們既需進行高屋建瓴的戰略前瞻設計,也要積累豐富多元的實踐應用經驗[27]。
3 “誰來轉”:“政—校—家—社”多元協同
(1)教育數字化轉型涉及多元主體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執行主體究竟是誰?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分析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哪些利益相關者,以及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和使命。教育數字化轉型體現了一種由多主體參與而引發的教育創新形態,其從根本上改變了參與者的結構與角色[28]。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辦好教育事業,家庭、學校、政府、社會都有責任”[29]。可見,教育數字化轉型需要政府、學校、家庭、社會四方主體的協同參與(其結構如圖4所示):①作為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制定的主體,政府在其中承擔著引領性角色。政府通過制定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與政策,引領教育變革的實踐。②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其主陣地必然在學校。因而,學校成為了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的關鍵性角色,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系列實踐需要在學校的場域內加以實施與檢驗。③教育的目的是促進人的發展,而家庭無疑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家庭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學校的數字化教育予以補充和拓展,擴大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的輻射面。④教育數字化轉型需依賴技術的支持,而技術源自社會發展與環境的塑造,社會在整個數字化教育的鏈條中擔當了重要的支持性角色。
(2)教育數字化轉型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推進并不能依賴某個單一主體,而是要依賴多元主體協同參與轉型的實踐。上述四類參與主體之間并非是一種割裂的關系,而是須以協同方式形成促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合力,共同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促進教育數字化轉型這一共同愿景的達成。教育數字化轉型指向的是全要素、全業務、全領域和全流程的數字化轉型[30],其多元主體的協同主要體現在數據協同、實踐協同、育人協同等方面:①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大量數據和信息在不同系統之間的流動變得更加快速,這為更大尺度上的數據共享和數據集成提供了可能,也為跨系統間實現多元主體的協同數據共享帶來了挑戰。②數據流通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使整個組織面臨如何更加高效協同的困境,這些困境既源于組織內部,也來自于跨組織部門和領域[31]。因此,要想全領域、全流程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多個領域之間的實踐協同是一條必經之路。跨領域、跨部門的實踐協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多元主體的價值,產生“1+1>2”的協同效果。③當前,在教育這一特殊的生態系統中,知識的生產、整合和再生都源自于多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同,多元主體的協同育人已成為重要的育人方式。通過高效的協同育人機制,能夠讓整個教育價值鏈上的參與者都真正進入新的協作模式,以確保整個數字化轉型戰略的成功[32]。
4 “轉去哪”:教育變革和教育創新打造新生態
在追問教育數字化轉型歸宿的過程中,美國定期發布的“國家教育技術規劃”(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一度成為引領美國教育改革的風向標,其歷年政策梳理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從早期教育數字化的迎接與準備階段,歷經實踐、個體能力提升、教育整體質量提升、重構教育系統階段,美國的教育數字化轉型正朝著生態重塑的階段邁進。教育數字化轉型作為信息化過程的數字躍遷形態[33],“生態重塑”也成為了各國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新目標與新訴求。只有將數字技術視作一種引領教育變革以破壞舊生態、誘發教育創新以重塑新生態的工具和手段,教育數字化轉型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祝智庭等[34]用“創變”這一上位概念概括了變革、創新兩個層面的含義,認為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歸宿在于實現教育系統的結構、功能、文化創變。這說明“創變”既包含系統破壞的變革過程,也包含生態重塑的創新結果。

表1 美國“國家教育技術規劃”歷年政策梳理
①教育變革引發舊生態破裂。教育變革的最終目的,在于重塑整個教育系統和教育組織體系,教育數字化聚焦于教育系統變化和轉型的不同方式可能會引發系統性變革[35],這種系統性變革將對當前的教育生態系統產生極大沖擊。數字技術的強勢闖入,不僅讓技術成為教育生態中的全新元素,而且拓展了系統諸多要素的內涵[36],如學校空間正打破物理邊界,快速向虛實融合的方向延展。此外,技術在引領教育變革中的價值還體現為對教育生態系統中各要素既有關系的“破壞”,使整個教育系統變得更為開放。例如,育人目標正逐漸打破固化標準,并從“知識傳承”向“能力發展”進化,且愈發關注世界發展趨勢和人力資本市場動向之間的關聯,師生關系、教與學的關系亦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②教育創新推動新生態重塑。如果說教育變革猶如一柄利刃破壞了教育生態系統,那么教育創新就好比是一劑強效的粘合劑,能將割裂的系統要素重新融合。這里的教育創新更多地指向教育的創新舉措,而非教育的常態化實踐。尤其是在當前,由智能技術誘發的教育創新舉措紛紛涌現。例如,“智能代理”使原本“人—人”單向的互動關系轉變為“人—技—機—師”的多元、多向格局,為推進“人機協同”教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再如,“虛擬現實”讓原本教與學的灌輸式模式變得具有活性與生命力,使個體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盡管這些教育的創新舉措尚未實現對傳統教育的徹底顛覆,但教育創新能否得以延續,關鍵就取決于我們對創新的教育機會所持有的態度[37]。
總的來說,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旨在厘清教育未來發展的行動路向與關注點,引導教育數字化實踐朝著組織層面的系統性變革目標前行,在實踐過程中注重政策導向與實踐導向的雙邏輯,關注轉型過程中“政—校—家—社”多元主體協同的價值,以重塑教育生態并形成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教育新格局與新形態。依托此行動框架,教育工作者需注意協調教育內部因素(如教育目標、教學方式等)與社會外部因素(如教育政策、技術發展等)之間的復雜關系,從系統性角度去構思具體實施方案,尋找教育內部因素與社會外部因素之間的合力,以最大程度地規避由多重復雜要素引發的潛在風險與挑戰,進而推動教育實現高質量內涵式發展。
四 結語
從信息化1.0到信息化2.0,無論是在數字技術發展方面還是在教育創新發展方面,當前的教育已然具備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基礎。整個國際社會的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競備賽已然打響,前行之路仍然存在或潛藏著未知的風險與挑戰。為了應對充滿挑戰和具有不確定性的未來,迅速響應并提前謀劃是推動我國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首要任務。只有明確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邏輯,才能從根本上規劃未來的發展路徑。為此,本研究從“轉什么”“如何轉”“誰來轉”“轉去哪”四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為我國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的推進和落地提供可循的行動建議,以教育的數字化轉型釋放教育的全部潛力,推動整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
當前,我國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尚處于起始階段,切實響應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我們需要進一步明確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與當前國內教育形勢的適切性,探討如何在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中形成多元主體的協同機制,如何在實踐中檢視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成效、規避數字技術引發的風險。作為研究人員,我們有責任去充分理解和解釋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目標與導向,并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其中、以有效的行動實踐推動教育生態系統的重塑。
[1]葉偉巍.技術的本質及教育啟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5):40-45.
[2]徐頑強.數字化轉型嵌入社會治理的場景重塑與價值邊界[J].求索,2022,(2):124-132.
[3][21][33][34][35]祝智庭,胡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探析與研究展望[J].中國電化教育,2022,(4):1-8、25.
[4]Kane G C, Palmer D, Phillips A N, et al. Strategy, not technology, driv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5,14:1-25.
[5]顧小清.教育信息化步入數字化轉型時代[J].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2022,(4):5-9.
[6]楊現民,吳貴芬,李新.教育數字化轉型中數據要素的價值發揮與管理[J].現代教育技術,2022,(8):5-13.
[7]Lankshear C, Knobel M. Digital literacies: Concep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151-176.
[8]Demirkan H, Spohrer J C, Welser J J. Digital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J]. It Professional, 2016,(6):14-18.
[9]Al-araibi A A M, Mahrin M N, Yusoff R C M. Technological aspect factors of E-learning readi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elphi technique[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19,(1):567-590.
[10]Kane G. The technology fallacy: People are the real key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9,(6):44-49.
[11]鄭旭東,周子荷.教育新基建三問:何為基?新在哪?如何建?[J].電化教育研究,2021,(11):42-47.
[12]Constantinides P, Henfridsson O, Parker G G. Introduction——platforms and infrastructures in the digital age[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8,(2):381-400.
[13]Iatrellis O, Savvas I Κ, Fitsilis P, et al. A two-phas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for predicting student outcomes[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1,(1):69-88.
[14]曹培杰.未來學校的變革路徑——“互聯網+教育”的定位與持續發展[J].教育研究,2016,(10):46-51.
[15]Inayatullah S. Gaming, ways of knowing, and futures[J].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2017,(2):101-106.
[16]國家發改委.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OL].
[17]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OL].
[18]楊宗凱.教育的全面數字化轉型已經必然趨勢[N].中國青年報,2022-4-11(5).
[19]祝智庭,鄭浩,許秋璇,等.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導向與生態化發展方略[J].現代教育技術,2022,(9):5-18.
[20]Benford R D, Snow D A.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611-639.
[22]Dengler K, Matthes B. The impa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labour market: Substitution potentials of occupations in Germany[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137:304-316.
[23]劉曉,劉銘心.數字化轉型與勞動者技能培訓:域外視野與現實鏡鑒[J].中國遠程教育,2022,(1):27-36、92-93.
[24]Sousa M J, Rocha á. Digital learning: Developing skill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s[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019,91:327-334.
[25]祝智庭,胡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邏輯與發展機遇[J].電化教育研究,2022,(1):5-15.
[26]Uvarov A Y. From computer literacy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J]. Informatics and Education, 2019,(4):5-11.
[27]Bond M, Marín V I, Dolch C,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and usage of digital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1):1-20.
[28]Hinings B, Gegenhuber T, Greenwood R. Digit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2018,(1):52-61.
[29]教育部.打好新時代基礎教育改革發展攻堅戰[OL].
[30]黃榮懷,楊俊峰.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涵與實施路徑[N].中國教育報,2022-4-6(4).
[31]Khan I S, Kauppila O, Fatima N, et al. Stakeholder interdependencies in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ject[J].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22,(1):1-17.
[32]T?dtling F, Trippl M.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beyond neo-liberal and traditional systemic view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9):1779-1795.
[36][37]顧小清.破壞性創新:技術如何改善教育生態[J].探索與爭鳴,2018,(8):34-36.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Action Framewor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HU Hang1GU Xiao-qing2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ims to realizing the remodeling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y fully mining and exerting the value of data, which has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the two angl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und out that the current education already had a realistic basi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at present,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to systematically deploy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action framewor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what to transform”, “how to transform”, “who to transform” and “where to transform”. Meanwhile, it was emphasized that the systematic change of goals and process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planning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the dual paradigm of policy orientation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designing the transformation plan, and the multiple coord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school-family-society” should be emphasized when implement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al ecology should be focused on when testing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Clarifying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accordingly formulating a clear action framework were the starting point to fi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lso the action guid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which called for our high atten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realistic basis; action framework; new educational ecology

G40-057
A
1009—8097(2022)11—0024—10
10.3969/j.issn.1009-8097.2022.11.003
本文為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多模態數據支持的概念轉變動態建模與診斷研究”(項目編號:21YJC880063)、江蘇省2021年度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重點項目“學習分析技術支持下的課堂高階思維能力發生機制與提升策略研究”(項目編號:C-b/2021/01/16)、江蘇省2021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指向概念轉變過程的多模態數據表征與診斷研究”(項目編號:2021SJA087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舒杭,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智能教育、教育信息化、學習科學,郵箱為287714486@qq.com。
2022年5月29日
編輯: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