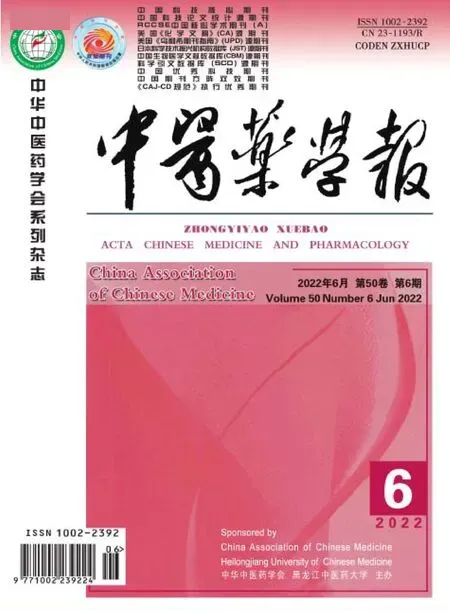從肝脾論治橋本甲狀腺炎的思路探析
王冰梅,張子默,李敬孝,岑嵐風,甘宇,聶雙蓮*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3.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橋本甲狀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是常見的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AIT)之一,病因多樣且復雜,發病率逐年上升,臨床上多以彌漫性甲狀腺腫大、甲狀腺內淋巴細胞浸潤與血清中甲狀腺特異性自身抗體甲狀腺過氧化物酶抗體(TPOAb)、甲狀腺球蛋白抗體(anti-thyroglobulin antibodies,TgAb)水平升高為主要特征,甲功可正常或不正常,可發展成橋本甲狀腺炎合并甲亢或橋本甲狀腺炎合并甲減。有關HT的流行病學研究調查表明,女性患病的風險遠遠高于男性,女性與男性的發病率之比約為5∶1~10∶1,并且甲狀腺自身抗體產生的陽性率在45~55歲為高峰年齡段,其患病率和發病率與地域特點呈現差異性,在碘充足地區生活的人群AITD發病率明顯高于在碘缺乏地區生活的人群[2-3]。
HT確切病因雖未闡明,但已知的發病機制涉及了遺傳易感基因與環境調節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目前主要與免疫及遺傳有關。近年來,臨床多應用含硒藥劑、左旋甲狀腺素鈉片和糖皮質激素治療HT,為疾病的首選藥物,雖取得了一定的療效,但仍然存在發生率高、停藥后病情反復的不理想結果[4]。
橋本甲狀腺炎,中醫學雖沒有明確定義,很多學者將其歸屬中醫“癭病”“癭瘤”“氣癭”等范疇,情志內傷、飲食及水土失宜、體質因素、女性和素體陰虛者易感,以情志內傷多見。其病機關鍵為情志內傷,肝失疏泄,肝郁氣滯,木旺乘土,脾土不盛其勢,日久則脾虛,脾虛痰濁自生,氣郁、痰濁壅滯于頸前,發為癭病,以頸前喉結兩旁結塊腫大為主要臨床特征。病位主要在肝脾,可與心有關。故本病應從肝脾兩臟調起,內安則邪自去,本文將著重從肝脾二臟角度探析治療HT的思路。
1 以“肝”論治HT的依據
時至今時,眾多醫家均認可在五臟中,肝與“癭病”關系最為緊密這一結論,正如嚴用和《濟生方》所述: “夫癭瘤者,多有喜怒不節,憂思過度,而成斯癥焉。大抵人之氣血,循環一身,常欲無滯留之患,調攝失宜,氣滯血瘀,為癭為瘤”,直接詮釋了癭病的發病與情志失調關系最為密切。肝屬木,主疏泄,其氣升發,喜條達,惡抑郁,情志不遂,多愁善感,憂思郁結,肝失條達致肝氣內郁,氣機不暢,傷及津液,運行受阻,導致臟腑功能的紊亂或失常,形成濕、痰、瘀等病理產物,最后百病叢生,氣血失和,氣滯瘀阻,虛實夾雜,氣血精津皆失正常,氣滯、痰凝、血瘀集聚而形成癭病。《靈樞·本神》言: “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抑郁憂愁情緒貫穿疾病終末,均與病位在肝臟有關。另外,就經脈循行通路而言,足厥陰肝經“循喉嚨之后”,肝經循行路線涵蓋了甲狀腺所處位置,故再次強調肝與甲狀腺關系密切。再者,隨著橋本疾病的病情發展,患者多有口苦、眼澀、目赤腫痛等癥狀,肝臟開竅于目,系目系,同樣反應出本病的病位在于肝臟。
臨床應用中,諸多教授都是從“以肝論治”角度為患者解除病痛,用藥也多為入肝經之藥。如在臨床用藥中出現頻次較高的柴胡,柴胡歸肝經,有疏散退熱、疏肝解郁、升舉陽氣的功效。橋本氏甲狀腺炎患者早期多為肝火熾盛證,主要表現為性情急躁易怒、怕熱多汗、焦慮、口苦、五心煩熱、寐差等高代謝癥狀。陳思蘭等[5]以柴胡為君藥自擬方劑治療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林蘭[6]應用柴胡疏肝散和四逆散加減方,采用開郁疏肝法在臨床實踐中治療HT,療效顯著;張毅等[7]運用“疏肝清火”法明顯改善患者憂慮、脾氣暴躁、頸前脹痛的癥狀,長期應用可降低TPOAb、TgAb的數值。
2 以“脾”論治HT的依據
HT患者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會出現一過性甲亢,而中后期多發生甲狀腺功能減退的癥狀,以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的低代謝癥候群癥狀為主,比如倦怠乏力、少氣懶言、肌肉疼痛、食欲不振、易汗出、記憶力減退、不寐、便溏等,究其原因責之于脾臟。因甲狀腺激素是一種氨基酸衍生物,生物學作用中影響廣泛,特別是對代謝的影響。在人體正常生理情況下,甲狀腺激素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促進蛋白質合成,尤其是對骨、骨骼肌、肝等蛋白質的合成起到明顯增加作用,當人體內甲狀腺激素分泌過盛時,反而造成骨骼肌的蛋白質大量分解,因而消瘦無力[8]。而脾作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當體內氣滯、痰凝、血瘀等多種病理產物阻礙氣血運行,使得脾失健運,津液代謝障礙,痰飲水濕積聚,日久脾氣虧虛,運納無力,故出現少氣懶言、食欲不振;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故泄瀉便溏;脾在體合肉,主四肢,肌肉的壯實可抵御外邪、保護內臟,當脾氣虛弱時,故肌肉酸痛;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脾腎先后天相互資生,腎中精氣的充盈依賴于脾氣運化化生的水谷精微的充養與培育,故脾氣虛弱致腎經虧虛時,則現記憶力減退[9]。《素問·玉機真臟論》有云:“脾脈者土也,孤臟以灌溉四傍也”“夫子言脾為孤臟,中央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10]。因此,脾氣虛弱,脾失健運,氣血乏源,致津液代謝障礙,機體內分泌循環失衡,也是HT發生的重要病機之一。高思華教授基于“肝脾腎同調理論主次把握”,提出以“固護脾胃”為中心,調腎固本為輔,多途徑、多角度防治本病,為甲功正常期HT在中醫臨床的診療提供了新的思路[11]。馬燕云等[12]用Meta分析法總結出應用益氣健脾類中藥聯合西藥的治療方案在降低TPOAb及TgAb滴度、改善甲狀腺腫大、提高臨床療效和中醫癥狀方面明顯優于單純西藥治療,且患者預后良好。唐漢鈞教授強調扶正健脾清癭法,佐以補腎護陰,選用生黃芪、黨參、白術、茯苓、靈芝、淫羊藿、柴胡、黃芩、麥冬及夏枯草等藥物組合成方,經多年的臨床應用總結,有效降低HT的抗體水平,患者病情明顯改善[13]。
3 “肝脾同調”論治HT的理論淵源及臨床應用
“肝脾同調”起源于我國古代唯物辯證法思想——陰陽五行學說的“抑木扶土法”,闡述了五行之間相生相克的規律,揭示了肝脾二臟相互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關系,對諸多疾病都具有指導意義。著名醫家趙獻可在《醫貫》[14]中提到:“世人皆曰木克土,而余獨升木以培土”,即通過升達肝木之氣達到培補中焦脾土的效果;《脾胃論·脾胃盛衰論》[15]有云:“大抵脾胃虛弱,陽氣不能生長,是夏春之令不行,五臟之氣不生”。肝屬木,應春而生,脾屬土,應長夏而運,肝之疏泄是脾之健運的前提條件,即應以疏散肝膽之火以化少陽之令,肝泄則脾安。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炎早期多以疏肝行氣、清熱解毒為主,后期當以溫補脾腎為主[16]。張蘭教授[17]主張在疾病早期從肝論治,多用清肝瀉火之法,佐以柔肝,選用龍膽瀉肝湯加減,疾病發展到中后期,重在溫腎益脾,以逍遙散為基礎加干姜、白術、黃芪等。丁治國教授[18]善用自擬方劑“清肝健脾消癭方”治療AIT,方中以柴胡、黃芩清肝瀉火,疏肝解郁,重量黃芪以補脾氣,資助脾胃運化,使水谷精微傳化有得,氣血津液運化有度,補而不滯,培土抑木,杜疾病發展之源。劉銅華教授[19]自擬方藥“甲炎康泰方”,方中用柴胡、郁金為君藥以調達肝氣,夏枯草、穿山龍為臣藥助君藥清肝化瘀通絡,另有黃芪、烏梅生津益氣,以制約肝郁犯脾,配伍得當,治療AIT療效顯著。吳謙在《名醫方論》[20]所言:“肝為木氣,全賴土以滋培,水以灌溉。若中土虛,則木不升而郁”,詮釋肝脾并非相互獨立而存在。黃麗娟教授[21]根據HT的進展趨勢,總結出“清肝瀉火-滋陰降火-活血化瘀-溫補脾腎”的臨床治療原則,臨床療效證明確實可以有效降低抗體表達水平,患者臨床癥狀明顯好轉。《金匱要略》有云:“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故HT雖常肝病為先,然易脾虛,故治肝之時勿忘補脾。若脾胃虛弱,生化不和,則應升發肝膽以行少陽之令,脾胃得肝之疏泄則運化自健,脾胃運化自如故能使機體“萬安”。因此,調暢肝之氣機的運行和促進脾的運化實為治療HT的重要手段。
4 小結
綜上所述,基于HT的病因病機及疾病發展過程中的證候表現角度,探索從“肝脾論治-肝脾同調”的理論角度論述其對治療HT的有效性。看似簡單的“肝脾論”,實則意義深遠,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各臟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任其一功能失調,都會導致機體內環境的紊亂。因HT的發生發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本病病變之初,多為肝旺,隨病變的發生發展,累及脾臟,故切不可拘泥于某一臟腑病變,應多角度、多領域探索,希望有更多的思路和角度解析AIT,為臨床工作做出科學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