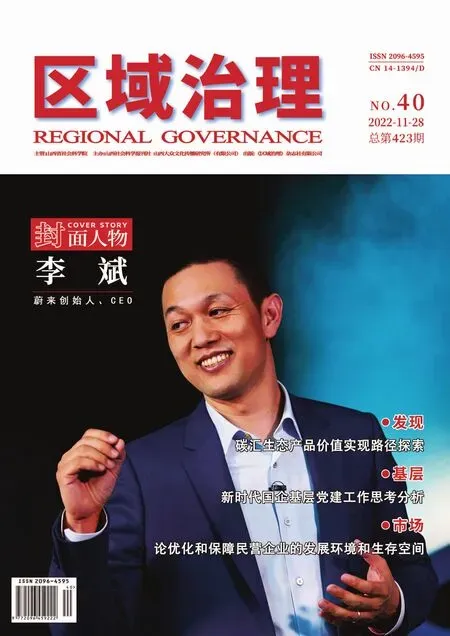專業交叉是否促進產學研合作?
——基于國家科技進步獎項目的實證研究
廣東粵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偉民
美國學者Woodworth在1926年最早提出“學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的概念。后來逐漸演化出“專業交叉”的概念,一般指兩個(含)以上學科專業協同參與的科研活動[1]。但學界至今對“專業交叉”“學科交叉”的準確定義沒有形成一致意見,這兩個概念經常混用。筆者認為,“學科交叉”更多地用于高校這一研究對象上;對于本文所關注的產、學、研三類主體,顯然用“專業交叉”更貼切。
學界研究產學研合作時,一般把“合作傾向”作為一個基本命題。經梳理文獻資料,研究者偏向從主體差異[2]、研發投入[3]、組織規模[4]、行業特征[5]、組織開放度[6]等多方面,對產學研合作傾向進行分析,并取得了不少成果。盡管如此,把專業交叉這一方興未艾的行為作為其中的影響因素,仍鮮有涉足。在選取研究主體上,國內外文獻資料一般把高校、科研機構、企業作為預設的研究主體。本文的創新之處,也在于把研究主體選為科研項目,聚焦國家科技進步獎項目這一典型樣本,并將之“打開”,探討高校、科研機構、企業等不同主體在其中的合作行為。本文將以2008至2019年國家科技進步獎項目信息構建樣本數據庫,從社會網絡的視角,深入研究專業交叉對產學研合作傾向的影響。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分類與處理
我國科學技術領域規格最高、最具權威性的五大獎項,均可以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官方網站(www.nosta.gov.cn)查詢。本文選取2008至2019年的獲獎項目,共有項目1918個及相應的獲獎單位3195家。根據本文研究目的,獲獎項目所包含的專業、完成單位等信息最重要,對此做二次編碼,形成數據庫。按如下步驟處理數據:
首先,逐一對獲獎項目名稱做出研判。旨在剔掉非本文所需的項目,共20個,包括創新團隊獎、科普創作獎等。經過初步篩選,獲獎項目1898個、獲獎機構3175家成為數據庫來源。
其次,逐一對獲獎項目簡介進行研讀。根據本文所需顆粒度,對照《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GB/T 13745-2009)列出參與該項目的所有專業。另有個別項目信息不完整的,需進一步檢索文獻來完善。
(二)專業交叉社會網絡分析
以上梳理結果顯示,2008至2019年的國家科技進步獎項目共有47個專業參與其中。本文進一步研究該47個專業的共現情況,利用共現分析軟件Co-occurence 6.7來構建共現矩陣,如表1所示。但限于篇幅,僅展示頻次前10的專業共現情況。從該表可見,某個專業出現的總次數就是對角線上的數字,其余數字是不同專業在同一個獲獎項目中兩兩共現的次數。

表1 專業共現矩陣(部分)
對以上分析所得的47×47共現矩陣,再用Co-occurence 6.7軟件生成共現圖譜。該47個專業的交叉情況在圖譜中直觀地顯現。如圖1所示。

圖1 專業交叉的共現圖譜
在社會網絡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中,交叉規模、交叉強度等維度,常常可以較好地刻畫交叉網絡的內在規律。
(1)專業交叉規模,即網絡中連接點的個數[7],測度專業交叉的廣泛程度與多樣程度。
(2)專業交叉強度,即網絡中實際連線數與所有可能連線數的比值[7],測度專業交叉的緊密程度與聚合程度。
根據社會網絡分析理論,計算整體網的網絡規模要先做二值化處理。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k(xi)表示數據集中距離xi最近的k個鄰居的集合。
理清以上概念后,將專業共現矩陣導入數據分析軟件Ucinet 6.0與Netdraw 2.084。整合軟件分析結果,2008至2019年國家科技進步獎項目數據,就形成了下表所呈現的時間序列結構,見表2。
二、產學研合作傾向分析
產學研合作傾向作為一個研究的基本命題,學界普遍采用二分法(合作與不合作)來測度[8-9]。本文取每年產學研合作獲獎項目數量與當年所有獲獎項目數量的比值。此外,根據評獎特點,獲獎單位若排在首位(牽頭單位),對獲獎所發揮的影響力與貢獻度,在所有獲獎單位中是最大的。牽頭單位的主動作為,在實現科研創新突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經統計整理,表3綜合呈現了獲獎數量、產學研合作傾向以及不同機構牽頭合作等情況。

表3 2008-2019年間產學研合作傾向情況
三、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根據本文研究主題,分別以專業交叉規模、專業交叉強度為自變量,以產學研合作傾向、不同機構牽頭產學研合作傾向為因變量。以上數值按時間序列導入SPSS 22.0做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1)專業交叉對產學研合作傾向有較顯著的影響。具體為:專業交叉強度對產學研合作傾向有正向促進作用(顯著性水平0.007);專業交叉規模對產學研合作傾向沒有顯著影響(顯著性水平0.593)。筆者認為,從知識共享的視角分析,知識異質性是一大動因。產學研機構協同創新的意愿,源自彼此為了整合知識資源以達到知識創造與技術創新。這一意愿最終轉化成知識合作、轉移、擴散的實際行動。“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同樣可以解釋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之間知識異質性的影響[2]。
(2)從不同機構牽頭產學研合作來看,專業交叉對企業牽頭產學研合作傾向有較顯著的影響,即專業交叉規模有抑制作用(顯著性水平0.037),而專業交叉強度沒有顯著影響(顯著性水平0.779);專業交叉對高校牽頭產學研合作傾向有較顯著的影響,即專業交叉強度有較顯著的影響(顯著性水平0.048),而專業交叉規模沒有顯著影響(顯著性水平0.103);專業交叉對科研機構牽頭產學研合作沒有顯著影響,專業交叉規模、專業交叉強度都沒有(顯著性水平0.680、0.396)。同時需指出,本文研究專業交叉對不同機構牽頭產學研合作傾向的影響所構建的模型,擬合優度有所下降,表明其他影響因素也應納入研究。但該結果也顯示,專業交叉對不同機構牽頭產學研合作傾向的影響效果,是大相徑庭的。
筆者對以上結論做出解釋:國家科技進步獎作為以成果為導向的綜合性科研項目,企業與高校在其中的表現是不一樣的。企業作為經營生產單位,以實用主義為導向,更聚焦本行業、本專業的創新問題。如果產學研合作所需的專業知識過于復雜多樣,反而造成知識轉移成本上升、組織協調難度加大等問題,最終合作意愿大大下降。企業作為專業知識的需求方,不牽頭開展多方合作,更可能是出于避險、降本等目的。相比之下,高校作為共性技術的供應方,在其擅長領域具有更強的跨學科、跨專業合作意愿。尤其隨著異質知識的內部聚合要求提高,高校有更強意愿去牽頭開展產學研合作。
四、啟示
產學研合作各主體、相關政策制定部門做決策時,本文實證研究獲得的結論,或可提供理論依據:
(1)廣泛搭建跨專業交流平臺,促進不同專業之間的交流合作。專業交叉的聚合程度與產學研合作傾向呈正相關的關系。建議政策制定部門推進科研體制改革、大力推行鼓勵政策;產學研機構積極共建多專業交流平臺,協同打造學科集群,共同為產業迭代升級提供多專業支撐。
(2)強化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核心作用。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體系仍存在很多薄弱環節。根據本文研究結果,企業埋頭本專業領域無可厚非,但也應避免過度的實用主義或短期行為,有意識地強化基礎科研能力。唯此才能扛起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核心擔當。同時,建議相關政策制定部門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為促進產學研合作推出更多精準化激勵政策,激發產學研合作主體的創新動力。
(3)以深化校企合作提升高校學科建設質量。高校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定位于打造知識策源地、人才集聚地。學科專業既是一種知識形態,也是一種社會組織體系。它本身就具備一定的組織制度和社會規范。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大背景下,高校應加強與企業的合作,著眼技術市場,突出需求導向,根據技術發展形勢適時增設新學科,尤其交叉學科;企業是知識和技術的需求者,應在產學研合作中主動輸出意見,共同促進產學研知識共享,以此形成良性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