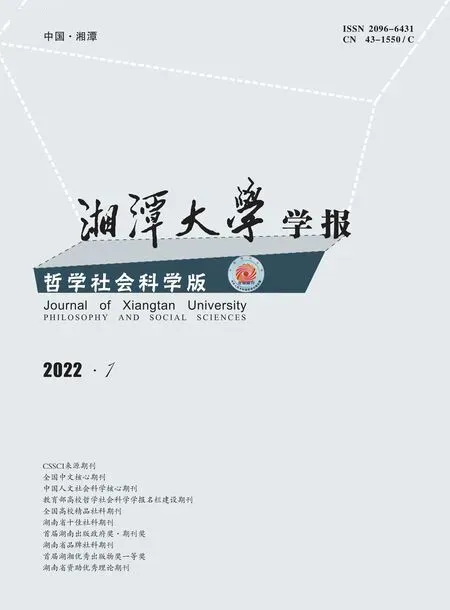村落文化的選擇與重構: 論泛傳統文化形象的再生*
許昕然,羅 立
(中南大學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083;湘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前言
基于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以及地方經濟發展的剛性需求,過去的古村落通過對當地傳統文化的保護與開發利用,重構其村落形象,登上了“中國傳統村落”的國家保護名錄,繼而被社會重新定位與認知。地方村落是如何開發利用當地的傳統文化并將其再造重構,使傳統文化獲得新生的,便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本文即是以具有這種背景的坳上古村為例,對當下鄉村中傳統文化的選擇與再生情況進行分析探討。那些“被選擇的”地方文化,還有那些與地方文化特色沒有關系的“被拿來的”地域文化,正以同樣的方式向廣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靠近,并由此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概念的泛化現象。在文化保護以及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地方文化建設中,可以說“泛傳統文化”的文化選擇與再生方式已經成為文化的一種新的生產機制。那些已經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地方傳統村落文化,通過國家對傳統村落開發建設的社會新契機,經過廣義的正統中國傳統文化視角的重新評估,再次登上了現代社會的大舞臺。
二、調研點的介紹
依靠連通中原與嶺南的湘粵古道而繁榮興盛的湘南(主要指湖南郴州和永州地區)古村落市集,隨著現代交通對古道的取代而逐漸沉寂。在新的社會發展時期,我們在保護傳統村落文化的同時,如何向外界展示宣傳這些歷史悠久的地方村落文化,并為其注入發展活力,同樣是村落文化保護的重要課題。
坳上村位于郴州市蘇仙區坳上鎮西南部,村域總面積約6.2平方公里。整個村莊呈“龍形”,臥于“兩水”(指東河和郴江河)腹地,形成“兩水夾金”的風水格局。村西面1公里處有一條著名的“湘粵古道”,是漢代至清代時期溝通中原與嶺南一帶的陸上交通要道。坳上村依托湘粵古道重要的交通位置和絡繹不絕的往來商人,逐步形成了歷史悠久、人文昌盛、交通地位重要的繁華墟市,并累積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品類繁多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直到清代光緒年間擴建了由郴入宜的另一通道,往來湘粵古道鳳形嶺段的人馬與貨物開始減少,坳上村才逐漸沉寂蕭條,村民則不得不在耕種與礦采中另謀生路。
在21世紀新的發展時期,國家對傳統村落保護與開發提出了新要求,營造新的人文與自然景象對于坳上村來說意義更加重大。坳上村于2017年全面退出了有色金屬礦采并進行環境整改,將村內的古建筑群申請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村委及村落居民對古建筑群、古民居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也在不斷加強。如今的坳上村,坐擁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先后入選各類省級與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步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代。
三、傳統村落文化展演與“地方”文化選擇
傳統村落中蘊藏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景觀,是中國農耕文明留下的寶貴遺產。胡彬彬認為:“當代村落文化研究,至少會出現兩個大的趨勢。第一是從宏觀的角度、有計劃有目的、分區域和民族,對村落文化進行整體性地考量;第二是從文化學的視角對中國村落文化進行研究。”[1]99-104據此,除了從宏觀角度對傳統村落文化進行分類整理研究,文化學視角下的地方文化的發展動向也是傳統村落文化關注和研究的重點。從坳上村的情況來看,雖然村落在對古建筑與湘粵古道的保護重塑、在趕年會活動中展演了傳統文化特色,然而當地的生活、生產文化并沒有在開發利用中得到完整體現,其中折射出來的地方文化選擇取舍現象值得探究。
(一)從“古村落”到“中國傳統村落”的文化形象背景
傳統村落文化不能片面地歸于物質或者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是“兼有著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在村落里這兩類遺產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屬一個文化與審美的基因,是一個獨特的整體”[2]9。坳上村連片建筑有200余棟,古建筑群歷史風貌保存完好,充分展現了清朝時期的湘南建筑風格,是研究明清鄉村建筑文化的標本,也是郴州迄今保存較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其中的58棟古民居與村域東南部一座古橋于2011年被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同年,坳上村被評為“湖南省第六批歷史文化名村”以及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被評為“湖南最美古村落”之一,2016年11月下旬入選第四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2017年入選湖南首批 “經典文化村鎮”。同年,郴州市蘇仙區文管所將隸屬坳上村的湘粵古道鳳形嶺段劃入保護重點區域,推薦申報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如其他許多傳統村落一樣,坳上村的保護與振興是圍繞著保護修葺后的村落觀光游覽為主展開的。從2016年起,當地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趕年會特色活動。由鎮政府主辦、村委會以及盛美文化傳播公司承辦的“逛古村趕年會”活動,迄今已舉辦了五屆。絡繹不絕的游客來到坳上趕年會現場體驗傳統年俗活動、購買心儀的年貨和農產品,并游覽坳上古村,了解坳上古村的歷史文化底蘊,感受湘南獨特的古村意境。
坳上村的開發時間較晚,除了一些步道鋪修和古建筑修復改善,暫時未因觀光開發而對當地傳統文化造成破壞影響。可是隨著知名度越來越高,坳上村的“中國傳統村落”形象逐漸取代了記憶中那個蕭條古道旁的寧靜質樸的地方古村落形象,這在為坳上村帶來資源機遇與社會關注的同時,也加重了當地的商業喧嘩。而“中國傳統村落”名錄設立的目的就是要對傳統村落文化進行保護與傳承,“其實質是傳承蘊含在其中的傳統哲學思想、生活智慧和優秀傳統文化,傳統村落文化傳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最終目標是延續傳統、實現民族與地方認同”[3]204。即使對坳上村進行開發的出發點是要保護和傳承逐漸消亡的傳統村落與瀕危的傳統文化,但是這種利用當地文化資產來進行開發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旅游的形式,“它依賴于目的地的文化遺產資產并將它們轉化成可供旅游者消費的產品”[4]211-219。故而“中國傳統村落”的文化形象標簽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當地文化保護與展示工作的風向,而來到此地的游客群體的觀光偏好與消費行為也將潛移默化地影響當地的文化再生產選擇。
(二)趕年會——國家、地方、民眾三方的互動載體
以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作為理論框架來研究社會問題與文化現象已經數見不鮮。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國家與地方民間的關系研究中,無論是對社會治理的研究,還是對新的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論述,國家、地方、民眾的立場都不在同一緯度。從對國家政權—鄉村社會模式的梳理[5]3-16,到國家通過“借用”民間儀式使國家力量、符號在社會中得以存在,并對社會實現間接塑造[6]42-50,或者通過研究儀式活動對國家在場和國家力量的借用以獲得對國家的歸屬與認同[7]61-67等都可以發現,國家與地方社會及民眾立場都處于一種不平等的關系層次。國家、地方、民眾呈現一種從高到低的從屬關系,且相互對立。但是從本文所闡述的坳上村趕年會這種被儀式化的地方節慶活動來看,三者并不完全處于相對的立場,而是呈現出一種新型的互動關系。
趕年會是自唐初沿襲下來的傳統歲時節日民俗。坳上村的趕年會活動從最初的一天延長為兩天,多安排于農歷十二月末的某個雙休日舉行,具體時間會提前公示。趕年會活動對于致力于地方扶貧的地方政府來說是一項重要工作。鎮政府、村委等除了會在傳統的電視媒體以及戶外媒體上投放趕年會的活動宣傳外,也會在微信、微博等互聯網媒介上發放趕年會活動的邀請函。
趕年會活動中不能被忽視的是國家的政策導向。從2018年起,活動現場設置了精準扶貧專區,至2020年已設置800多個攤位,所銷售的都是由當地經濟困難戶所養殖或種植的黑山羊、富硒米等農副產品,專區的現場銷售額也從106萬元增長至590多萬元(2019年)。依靠趕年會活動吸引的人流助力了當地的脫貧致富計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實現了觀光與扶貧的精準結合,有益于村落居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除了拉動地方經濟的政策驅動,國家文化發展的政策導向也在趕年會的活動中一目了然。趕年會的口號從“幸福年味”到“不一樣的鄉愁”,再到“最美古村”等,以及活動介紹中“趕不一樣的年會,逛別樣的古村”等宣傳語,無不凸顯著在趕年會的活動上一展當地古村落傳統風采的文化目的。被列入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龍舞、文化劇、套環等傳統文化項目,在一年一度的趕年會活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除此之外,當地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糖花制作、春聯書寫等活動也是趕年會的重要展示內容。
在趕年會這個活動載體中,國家振興鄉村的經濟政策以及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政策在坳上村得到了貫徹執行和有效渲染,坳上村的地方經濟也因為觀光活動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同時其傳統村落文化形象得以重構和展現,民間的傳統生活方式不但得以傳承,而且還進一步資源化,助力了當地社會的發展。雖然由政府主導的傳統文化開發利用可能會帶來文化舞臺化、商品化等諸多弊端,但在傳統村落文化得到繁榮發展的事實面前,民眾表現出了主觀能動性,其中折射出的國家、地方、民眾之間區別于單純從屬關系的新的有機互動,有利于我們繼續了解經歷“地方”選擇的傳統文化是如何被取舍和包裝的。
(三)傳統村落文化的選擇與淘汰
許多古村落的保護開發過程,都陷于歷史歲月流逝中古建筑的破敗以及社會的破壞式發展。早期傳統村落文化保護工作的初衷,主要是通過自身的實地調研經驗來建立相關的文化保護制度,捍衛民間傳統文化傳承人的利益,同時更有效地搜集與更全面地保存急劇消逝的傳統文化資料。而現在發展迅猛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卻遠遠超出了這樣的初衷。“它實際上變成了多種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共同參與、謀求自己利益的一項運動。”[8]14-20通過對坳上村的文化保護利用現狀以及趕年會活動上所展示的文化內容的分析,我們可以窺見坳上村是如何對傳統文化進行選擇與淘汰,繼而再向外界進行文化展示的:
地方傳統建筑是坳上村文化觀光的重要內容。村內現留存的58棟古民居依山就勢而建,這些建筑在被保護前很多已經破敗不堪,有些則被拿來做養豬場或雜物間,直到村落進行整體規劃保護后才被重新重視起來;坳上村旁的湘粵古道鳳形嶺段也因保存完整且歷史文化價值深厚而被政府反復提及和宣傳;套環是郴州鄉村地區家家戶戶過年會做的傳統食物,也是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形寓意傳統文化中的六六大順與闔家團圓。為了配合趕年會活動,在2018年的坳上村年會活動上,當地村民除了炸出標準的套環,還有為了表演而制作的遠超標準的巨型套環,并預備申請吉尼斯紀錄。這是對當地傳統套環進行革新創造的表演項目,也是當地對傳統村落文化的創新舉措之一。春聯更是容易引起聯想的傳統文化項目。在每年的趕年會活動上,蘇仙區老年書畫協會十多位書法家帶著精心準備的對子,揮毫潑墨,為往來游客和當地民眾書寫春聯,送上新春的祝福。
以上這些被選中的文化,固然能表現坳上村傳統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并不全是獨屬于坳上村的文化內容。首先,具有湘南地方特色的古民居建筑并非坳上村所獨有,蘇仙區的古村落中此種建筑風格的古民居比比皆是,而湘粵古道旁的集市也不止坳上村一個。古民居與古道只是被作為一種傳統村落的文化特征被用來包裝坳上村傳統村落的社會形象,套環亦是如此。再者,貼春聯作為中國的傳統習俗,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幾乎都是家戶標配。只是在坳上村的趕年會活動中,政府為了展現當地的詩歌文化底蘊與“才子之鄉”的美名,便將寫春聯也作為趕年會活動中必備的表演節目之一。
反之,一些可以揭示當地特色的傳統文化反而沒能得到很好的保護與開發,幾乎淪落到了被淘汰的邊緣:如拼布畫是當地頗具特色的藝術品,如今卻只有一位姓譚的老藝人能制作出精品。如若再無人繼續研習拼布畫手藝,拼布畫的傳承便將就此斷層,現存手藝都將成為坳上村的歷史。此外,還有村中遠近聞名的骨傷水師以及工藝卓絕的木雕手藝同樣面臨傳承斷層的問題。骨傷水師的老醫生為了傳承醫術已經打破了“傳男不傳女”的祖訓,卻仍然找不到合適的繼承人。木雕手藝因其工藝復雜,已經被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拋擲在村莊的歷史記憶里,只有若干被保存下來的成品向世人昭示著它的存在。
據此可見,坳上村作為中國傳統村落進行保護和開發的過程中,在趕年會活動上的傳統村落文化展演并沒有將當地的整體文化都納入其中,而是有選擇地重視那些容易引起大眾對“傳統村落”聯想(古民居、古道),或者是更容易引起對廣義上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共鳴的文化(春聯、詩歌),抑或是更具有觀賞性和娛樂性的文化項目(套環制作)。而那些切實反映當地民眾生活、生產習俗側面的文化(拼布畫、水師、木雕)并沒有在趕年會活動中得到全面而充分的體現,甚至有的在當地傳統村落文化保護的日常實踐中就早已被忽視淘汰。為了讓來到當地的觀光民眾的游覽符合他們對坳上村“傳統村落”形象的預期,地方政府會挑選那些更貼合廣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更具有藝術性、歷史性或者參與價值的文化來進行展示。上述經過當地政府的文化選擇后在趕年會上向外界展示的坳上傳統村落文化,其中既有地方曾經的民居與民俗,也有為了展演效果而被改造創新的文化創作。經過地方選擇與創作后的村落文化依舊被“傳統文化”的形象所包裝,因為地方主體要把不起眼的地方古村落打造成具有典型傳統文化特點的“中國傳統村落”,這便需要強化其村落文化中正統性和傳統性意義的文化側面。由于文化形象對傳統村落十分重要,這種形象包裝在其他傳統村落的開發利用中也隨處可見。
四、傳統文化再生與地方形象重構
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進一步推動中國傳統村落的保護與開發刻不容緩。坳上村希望成為郴州地區較具代表性的文化體驗型觀光景區,并依托周邊的社會資源,成為湘粵古道帶上的重要節點,打造成湘、粵地區觀光休閑度假的新空間。從2016年開始,在坳上村每年臘月的趕年會活動上,當地的傳統村落文化與相關特產被作為展演內容,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文化在活動上也被作為演出內容向外界進行展示,坳上村的“中國傳統村落”形象進一步被重構。
但是在坳上村的保護與開發過程中,其所展示的傳統村落文化形象并不是對當地生產、生活文化的全部反映。在文化項目展演中,也不能清楚地體現坳上村文化的獨特之處,卻能夠感受到“地方”這個主體對廣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懈追求。在文化選擇過程中所發生的傳統村落文化變遷與地方主體重構現象耐人尋味,同時也反映了我國當下的傳統村落文化被建構再生的現象可能是一個“泛傳統文化”的建構過程。
(一)村落開發中的傳統村落文化變遷
在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趕年會活動成為坳上村當地傳統文化存續的一個載體,在向外界展現坳上村落文化的同時,也展示了地方傳統文化的變遷過程。趕年會活動不是客觀表象上的普通趕集,而是承載著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意義與功能而被創造出來的活動載體,是重構從過去的坳上古村地方文化到現在的傳統村落文化的新客體裝置。
對文化變遷運動的研究,需要關注組織化的群體。“第一,我們需要研究那些作為文化承擔者的個體;第二,我們需要研究塑造文化的思想與實踐。”[9]364此外,還要對當地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合理的保護、開發與利用。在坳上村地方政府與民間有意識地整合各類傳統文化資源,并將之加入到村落扶貧開發與趕年會活動中之后,坳上村便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地游客。
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是推動觀光活動的原因之一。這中間值得注意的是,吸引人們前往坳上村的傳統村落文化,涵蓋的應是那些從過去到現在正在延續的文化習慣、知識以及生活經驗,抑或是能夠體現當地特色的、未經修改的藝術資產與文化遺產等。然而這些傳統村落文化之所以能夠得到鑒定、保護、傳承以及在活動上進行展演,是因為它們對坳上村具有的內在價值和意義,而不是由于它們作為村落開發或發展地方經濟的吸引物所具有的外在使用價值。
然而所有進入到趕年會活動之中的傳統村落文化,不僅服務于村落的外來者,也服務于包括地方政府、相關的文化傳承人以及其他的當地居民。這些不同的群體同為文化活動的承擔者,但是由于背景和出發點不同,他們對于文化的價值取向也不盡相同。然而在趕年會活動上,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使得個體發現了彼此之間存在交叉點。無論是試圖了解傳統文化的觀光者,還是希望文化得到延續的傳承人,又或是希望開發村落以及發展經濟的地方政府等,對傳統文化進行保護、利用與展示便是他們之間契合的新的利益點,同樣也是競爭點。這意味著在趕年會活動上所演出的傳統村落文化,已經經過選擇繼而被加工重構,實現了從地方傳統文化資源向旅游文化資源、消費文化資源等的變遷。在這樣的文化變遷中,“地方”主體功不可沒。
(二)“地方”主體重構對文化再生的意義
在過去,“地方”雖然可以是一股能和國家抗衡的力量,但從統治體制來說,地方政權只是中央政權的地域延伸。所以在一些對過往民間儀式等傳統文化的研究中,“地方”相當程度上被理解為國家權力的下放,顯示出中央權力對地方政權的絕對控制屬性。然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國家、地方、民間的互動呈現一種互惠互利的結構,而其中地方自身的獨立性不容忽視”[10]35。在坳上村的傳統文化保護與開發利用過程中,當地政府自發組建了保護小組,負責常規管理、保護文保單位、實施保護規劃,及時糾正古村落保護中存在的問題,宣傳保護傳統的現實意義;同時,為了擴大文化經濟的影響力而選擇通過趕年會的節慶活動作為文化活動載體向外界宣傳、展示傳統村落文化。雖然一切都離不開更高階權力部門的督導批示,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意義上的“地方”概念的擴展延伸。“地方”不再僅僅是指代某一低級別的行政權力機構,而是與地域空間所結合并具有一定界限,可由當地的權力機構發揮主觀能動作用的行政區域。據此,“地方”不再只是國家權力的空間延伸與下放,也因此具有了獨有的文化意識。
從本文對坳上村在傳統文化保護開發中的文化選擇事例探討可見,當下的“地方”主體及傳統文化保護工作已經發生了重大變遷,對廣義的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文化追求成為地方文化選擇的主流。同時,相關的主體互動也從“國家—地方”或者“國家—民間(民眾)”變為國家、地方、民眾三者之間的互動。現在的“地方”作為一個主體獨立于國家與民眾,既不能等同于國家權力的外延,也不能完全代表民眾的立場。在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前提下,傳統村落文化保護開發中的地方政府,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創造利用,試圖運用一種蘊含廣義上的傳統文化精神的文化模式來發展地方經濟與地方文化,并對當地的傳統文化進行一場地方性的選擇加工,引發了當地文化的發展變遷,完成了一場文化選擇與再生的創造生產實踐。
(三)“地方文化”“地域文化”向傳統文化的延伸
本文中的“地方文化”即為坳上的本地文化,“地域文化”則指湘南地區文化,區別于坳上村的本地文化。坳上村在進行村落開發和規劃保護中,究竟要向外界展示怎樣的文化內涵,我們可以做出以下概括:一是地方文化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延伸,即坳上村在展示當地特色傳統文化的同時,將這種“地方文化”向廣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延伸靠攏;二是地域文化的引進并向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延伸,也就是把原本不屬于坳上地區或者屬于更廣范圍的文化“拿過來”,把它們整合為“地域文化”,并向中國傳統文化這個概念進行延伸。這兩種傾向的最終目的,是向外界確切傳達坳上古村文化所內涵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性。比如前文提到的套環,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小吃,能從側面體現湘南地區村落居民生產、生活的風俗特色,但是對于趕年會活動上的巨型套環的革新制作來說,其不但反映了村落開發中對傳統文化的創造革新,那環環相扣的造型更多的是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生生不息與源遠流長,而不僅僅是標準小套環制作中家庭闔樂的含義了。再比如坳上古村落,是村莊布局形似龍形的“龍脊村落”,村民以李姓為主。在進行村落的開發規劃時,西面的湘粵古道鳳嶺路段被考古發現后,為了加大宣傳,村落已將宣傳語從“龍脊村落”變成了“龍脊上的村落,古道旁的李氏商集”,聲稱自己“雖不是古道旁集市卻勝似集市”,意圖便很明了。湘粵古道始建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4年),初為遠征南粵、消滅地方割據政權而修筑,在秦王朝統一中國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之后更是溝通中原與嶺南的經濟文化要道,直到20世紀30年代交通建設發展后式微。而附近新發現的鳳形嶺段,是古時候由郴入宜的重要通道,更是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閉關鎖國對外貿易政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有力物證。其沿途所保存的各種石亭與碑刻等古跡,更是具有相當高的歷史文化價值。所以坳上村想要依靠古道進一步發展,其所要依托的不僅是古道作為重要的歷史文化景觀的文旅資源屬性,更是希望向其所承載的深厚的中華民族統一和民族融合的歷史文化底蘊靠攏。
由上可知,這里的關鍵點不是對地方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區分,而是套環小吃中所蘊含的廣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之寓意,以及湘粵古道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換言之,地方或地域文化中所反映的地方性特色在坳上村的傳統村落文化開發保護中并未得到十分突出的體現,地方與民眾甚至還對套環做出了創新制作,或者將春聯等不屬于本地特色的文化項目同樣拿來展示。但是這些文化項目中所彰顯的歷史的、正統的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卻得到了當局的足夠重視。這種傳統村落文化的選擇中所傳達的文化精神就是一種傳統文化概念泛化的現象,是一種著力于突顯地方文化或地域文化中所具有的廣義上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文化選擇現象,也是將具有廣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性地位的其他文化引進和吸收進地方或地域文化的文化創新再生現象。
五、結語:“泛傳統文化”形象的成功再生
坳上村過去依托湘粵古道重要交通位置和絡繹不絕的往來商人逐步形成了有“地主之都”和“糧食買賣中心”稱號的古村落,現在又借助古道的文化號召力開發文化觀光與扶貧事業,同時成功入選了“中國傳統村落”“歷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國美麗鄉村”的名錄。過去與世無爭的古村落已經成為當下風頭正盛的中國傳統村落。在對村落中的傳統文化進行開發、保護、利用的文化選擇中,地方主導下的傳統村落文化的概念、內涵、外延等隨之也經歷了一個新的再詮釋的過程。在對傳統村落文化的重構與再生過程中,村落的形象與定義也在被建構與歷經重生。正因如此,沉寂許久的地方傳統村落文化經歷了正統的中國傳統文化視角的重新評估與抉擇,然后再次登上現代社會的大舞臺,并據此對傳統村落的形象進行再創造。在以地方政權為主體而實施的地方文化重構再生過程之中,具有獨立文化意義的“地方”已經出現。作為開發主體的地方政府,通過保護開發與創新利用當地的傳統文化發展文化經濟的手法,是區別于完全的文化商品化模式的一種文創融合的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屬性。這種發展模式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它是在具有獨立文化意識的地方主體的主導下,對當地的村落文化中更貼合廣義中國傳統文化意義的部分文化進行選擇與重構,而不是像工業化的文化商品模式一般創造無數個千篇一律的地方舞臺進行模式化的文化展演。在這樣的傳統村落文化的地方選擇與再生過程中,重點是地方對當地傳統文化的取舍偏好,“文化選擇”是其中的重要關鍵詞。從2016年開始舉辦的坳上古村趕年會活動中所展示的傳統文化項目,大都已收入或正在申請各級非遺保護名錄。趕年會作為當地向外界做文化展示的活動載體,在2020年的活動中,除了繼續表演以往所展示的地方文化或湘南地域文化之外,還增加了唐裝不倒翁等新的文化項目,并在其原來的表演基礎上改編和創造了新的文化形式。至此,地方文化、地域文化與外來文化(唐裝不倒翁等)在趕年會活動上聯合發展,并在地方舞臺上進行共同展演,一起為坳上村的傳統村落形象吶喊助威。由此可再次印證,在地方主體對傳統村落文化的選擇中,被選中的傳統文化是否能夠體現當地的文化特點并不顯得十分重要,其作為文化展示項目的娛樂觀賞價值,以及與廣義上中國傳統文化的貼合度高低才是被選擇或被淘汰的重點。在傳統村落文化的選擇與再生之中,村落文化的村落地域特色被弱化至可有可無的存在邊緣。
在對傳統村落的文化形象的再生建構中,并非是對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地方性傳統文化進行整體的復原和再利用,也并非僅僅是對地方特色文化進行再次挖掘和展示,而是通過對地方文化或地域文化中含有廣義上中國傳統文化淵源的文化因子進行選擇捕捉,并將之與泛化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以此使得地方村落文化獲得其國家的正統的存續意義和歷史地位。這種傳統村落文化的選擇與重構過程,就是一場“泛傳統文化”的成功再生過程,并且這種傳統文化再生的文化創新現象并非坳上村所獨有,而是中國傳統村落群像中一種普遍存在的傳統村落文化形象的創造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