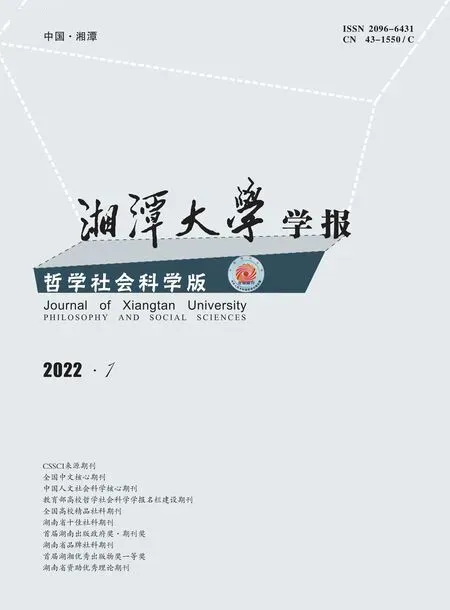論楊昌濟教育倫理思想的三個面相*
歐陽詢
(長沙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100)
現(xiàn)代著名教育家、倫理學家楊昌濟自弱冠之年就有志于教育,視教育為一種寂寞而神圣的事業(yè),其一生以“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1]92為己任。1913年,他在《教育與政治》一文中說明了自己篤志教育的初衷:“處此時勢,惟在少數(shù)之善良分子,協(xié)力與多數(shù)之腐敗分子奮斗,積誠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轉移其風氣,故政治而外,吾輩正大有事在。欲救國家之危亡,舍從事國民之教育,別無他法。”[2]43很顯然,楊昌濟是想借助教育活動來改造人心道德,進而喚醒民眾來挽救國家危亡。這表明,楊昌濟的教育思想與倫理思想并不是互為他者、相互隔絕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共生關系。遺憾的是,當代學界雖然對楊昌濟的教育思想與倫理思想進行了分別研究,并且都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忽視了對他的教育倫理思想進行綜合研究,這無疑是楊昌濟思想研究的一大不足。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師生關系三個維度,對楊昌濟的教育倫理思想作進一步探討。
一、教育目的觀:主張德智體全面發(fā)展,警惕泛道德主義傾向
關于什么是教育,楊昌濟作了這樣的界定:“教育者,乃心性已熟者,對于心性未熟者,有目的、有方案之意識的感化也。”[2]285根據(jù)這一定義可知,教育必須同時具有三個條件:第一,作為教育主體的心性成熟之人;第二,作為教育客體的心性未熟之人;第三,實施有目的、有方案的意識感化。在楊昌濟那里,“心性”亦即“意識”,是知、情、意三者的統(tǒng)一:“知”是指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科學知識與技能;“情”是指高尚的美感情趣,尤其是對大自然的美感;“意”則是指強大而純正的道德意志。
在楊昌濟看來,既然“心性”是知、情、意三者的統(tǒng)一,那么作為“意識的感化”的教育也就相應地具有如下三個目的:與“知”相對應的是,“教育不可不以與生存于社會之能力于個人,為第一之目的”[2]297;與“情”相對應的是,“教育不可不使兒童能理解環(huán)象,能知對之之趣味,此教育之第二目的也”[2]300;與“意”相對應的是,“教育又不可不養(yǎng)成可得貢獻于社會之生存發(fā)達之性格,此教育之第三目的也”[2]302。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第一目的”,并非指首要目的。實際上,楊昌濟是以養(yǎng)成人格作為教育的首要目的,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以能否養(yǎng)成人格作為教育有無效果的標準,亦即以能否養(yǎng)成人格作為教育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依據(jù)。例如,他在《論語類鈔》中說道:“處濁亂之世,但患自己無德,如其有德,自有同類者聞風興起,故有以匹夫而轉移一世之風會者,此教育之所以可能也。吾人茍無此信念,則不必復言教育。”[2]264結合其教育定義可知,楊昌濟的確把教育者與有德者、被教育者與后知后覺的同類者、教育與道德意識的感化等同起來了。另一方面,他有一種將道德理想視為人的本質的傾向,誠如其所言:“人者,理想之動物也。人生之目的在于實現(xiàn)其理想。”[2]247而研究理想的學問正是倫理學,“倫理學乃論吾人之道德的理想者,乃將來之情態(tài)之研究,當然者之研究也。倫理學雖亦研究過去與現(xiàn)實,然此非斯學本來之目的”[2]153。合而言之,只有在全社會著力開展倫理道德教育,才能使一種社會道德理想內化為人的本質屬性。
關于道德教育,楊昌濟所希望養(yǎng)成的人格是什么樣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教育不可不作成有公共心之個人主義之人”[2]308。這里所謂的“個人主義”,既指個人利益,也指個人的獨立人格。在20世紀初的中國,楊昌濟積極倡導個人利益,尤其是生命、財產利益,正如他所說:“生存競爭劇烈,人相集為一團體,于團體之下,守己之權利,圖己之利益。”[2]304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個人主義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比如,個人主義者有時不顧社會利益甚至損害社會利益,有時過于專橫而使周圍人都服從自己的意志。因此之故,楊昌濟特別強調道:“欲圖社會之維持發(fā)達,個人不可不為社會犧牲自己之利益,然其所確信之主義,則不可以之供犧牲。若個人枉自己之確信,則失其人格,無個人之價值。”[2]306-307此句中的“為社會犧牲自己之利益”,或者主動給予他人以同情和幫助,乃是“公共心”的外在表現(xiàn)。在楊昌濟眼里,最根本、最重要的“公共心”是愛國心,若國家利益與其他一切團體利益有沖突,則應當為了前者而犧牲后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楊昌濟明確指出,公共心與利己心是絕然對立的,故不可能同時養(yǎng)成公共心與利己心;但公共心與個人主義可以相結合,“故養(yǎng)有公共心同時有主張之人,乃可能之事”[2]308。
楊昌濟盡管主張教育以養(yǎng)成人格為首要目的,但他卻對教育教學中的泛道德主義傾向保持清醒的警惕。所謂泛道德主義,就是“一切皆以道德為主,道德方面的考慮支配一切”[3]138。20世紀初,德國海爾巴脫學派即認為,教育的唯一目的在于“養(yǎng)成受支配于道德之觀念之意志”[2]296,“道德之觀念”具體包括內心自由、完全、好意、正義、報酬等五種觀念。針對這一觀點,楊昌濟在《教育學講義》中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他說:“然造服從道德的觀念之意志,不可云已盡教育之目的。蓋雖道德上毫無可非難之人,若此人缺乏生活于社會必要之知識技能,則其運命果如何乎?如此之人,不賴他人之助,則不能一日生存于社會之中。”[2]297亦即是說,應根據(jù)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需要來決定教育的目的。在楊昌濟看來,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科學技術革命在促進工業(yè)發(fā)達、商業(yè)隆盛的同時,也促使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競爭日益激烈,這必須有強健的身體和健全的精神才能適應。因此,他進一步指出:“故養(yǎng)生存于社會之能力,為教育之一目的。因欲達此目的,而強健其身體,且授以生活上必要之智識技能,乃當然之事。”[2]299可見,楊昌濟主張的是以道德教育為中心的德智體全面發(fā)展。
二、教育方法觀:堅持經驗主義原則,提倡教授、訓練、養(yǎng)護相濟為用
教育方法是為了實現(xiàn)教育的目的和目標而采取的行為方式的總和,在教育活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楊昌濟在闡述教育學的定義時曾這樣說道:“教育學者,研究教育之現(xiàn)象之學也。詳言之,則研究教育之目的與達此目的之方法,乃教育學之所有事也。”[2]284可見,在楊昌濟眼里,教育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教育目的與教育方法,教育方法服務于教育目的。正是基于這一思路,他提出了三種教育方法:第一種是教授(教學),以傳授智識、培養(yǎng)社會生存能力為目的;第二種是訓練,以教育者直接給予感化于被教育者、養(yǎng)成善良品性為目的;第三種是養(yǎng)護,以鍛煉和保護身體為目的。[2]319就人的身心發(fā)展而言,養(yǎng)護關乎的是被教育者的身體方面,而教授和訓練關乎的是被教育者的精神方面,教授直接作用于被教育者的知的方面,訓練則直接作用于被教育者的意的方面。此處之所以強調“直接作用”一詞,是因為楊昌濟深刻地認識到:從理論層面對認識與意志作截然區(qū)分,只是為了說明的方便,乃是一種抽象的結果;而經驗表明,人的認識活動中同時包含著意志活動,人的意志活動中也同時包含著認識活動;所以,“吾人為教授之時,同時為訓練;為訓練之時,同時為教授”[2]319。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意思是說,興趣是激勵學習的最好老師。受此影響,楊昌濟在肯定教授的主要目的在于傳授學生將來立足社會的必要知識和能力時,又強調鍛煉學生的智力和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是教授的重要目的,誠如其所言:“教授先以授智識為目的,然此智識不可不為活動的,使生徒自教師得其已知者,更求得其所未知者。”[2]321這里所謂的智力主要包括記憶力、思考力、想象力等。以引起興趣的原因為標準,學習興趣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的興趣,即對知識本身的興趣和好奇;另一種是間接的興趣,即對知識本身不感興趣,而對知識所帶來的利益和好處感興趣,如名譽、獎賞、職業(yè)等。20世紀初,國內外一些學者大力倡導為讀書而讀書、為學問而學問的口號。在楊昌濟看來,這種做學問的精神固為一種美德,但“于自學問而得之賞與社會將來之位置毫不掛心,全脫名利之念,為學問而為學問,乃豪杰之事也”[2]322;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首先要確立一個現(xiàn)實的奮斗目標,然后為此而努力學習,否則就會對學問無熱心、無耐心,遂致學問不能進步。在現(xiàn)實的奮斗目標中,楊昌濟最看重的是“立他日為某職業(yè)之目的”,因為他認為職業(yè)不僅是利己的,同時也是利他的,每個人都努力從事自己的職業(yè),方能謀求國家和社會的興旺發(fā)達。
根據(jù)現(xiàn)代教育學的觀點,學科是教學的基礎,開設哪些學科是教學計劃的中心問題。學科也是教學科目的簡稱,意指“教學中按邏輯程序組織的一定知識和技能范圍的單位”[4]144。從這個角度看,楊昌濟在其《教育學講義》第二篇“教授論”中,正是圍繞學生將來立足社會的必要知識和能力,著重探討了普通學校所應設置的教學科目及其結構關系。他明確指出,普通學校應設置以下三類教學科目:第一類是基礎的教學科目,具體包括言語科、算術科和修身科,這類科目主要著眼于社會日常生活知識和技能,“人若無發(fā)表自己之思想與理解他人之思想之能力,則不能與人交際。為社會之生活,不知算術則日常之計算亦不能為之。不自修身之教授得知處事接物之道,則亦不能為社會之生活”[2]327。第二類是智識的教學科目,具體包括歷史科、地理科、理化科和博物科,這類科目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認識、掌握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其中,歷史科的本務是授以“本國及外國之歷史的事實,并歷史的事實之原因、結果,因使得社會之變遷與國家成立發(fā)達之概念”[2]337;理化科的本務則是授以“存在于自然物、人工物之理化的現(xiàn)象,并支配之之法則”[2]339。第三類是技能的教學科目,具體包括音樂科、圖畫科、手工科、體操科等,這類科目旨在培養(yǎng)學生的藝術技能和促進學生的身心發(fā)展。
前文已述,訓練是直接作用于被教育者的意志方面。這樣一來,要使被教育者養(yǎng)成善良的品性,在實施訓練時必須注意下面兩點:一是要使心意活動強大,亦即培養(yǎng)強大的意志力;二是要端正心意活動的方向,亦即保持純正的意志。倘若方向不正,意志強大也毫無價值,反而會危害他人和社會。為此,楊昌濟鄭重提出:應當遵守倫理學的法則來規(guī)定意志活動的方向,“在家則恪守家人之規(guī)則,入社會則勿背社會之習慣,對國家則不失國民之本務”[2]354;而培養(yǎng)強大意志力的方法,主要是通過日常反復練習養(yǎng)成意志活動的習慣,比如勤勉、勇敢、忍耐、克己、節(jié)制等德性,都是經過平日反復練習而養(yǎng)成的。同時,楊昌濟更進一步指出,欲由訓練養(yǎng)成道德心(良心),必須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用命令、禁止的手段,直接從外部施加影響。此可用之于發(fā)育程度尚低的幼童和兒童身上,使他們全然聽從教育者的意志。第二階段是用教諭、示例、賞罰等手段,使青少年逐步領悟和掌握道德規(guī)則。教諭即是對青少年“教以處如何之事,當適用此規(guī)則,又處如何之事,當適用彼規(guī)則,以處置其日常之行為”[2]358。第三階段是純恃反省的作用,“及心性漸次發(fā)達,乃自定一種之主義,以之為立身處世之道”[2]362。一個人一旦建立了正確的立身處世之道,其道德行為便是自己理想所要求的,而非他人所命令的,至此道德心才得以養(yǎng)成。很顯然,在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礎問題上,楊昌濟倡導的是經驗主義人性論,而明確反對天賦觀念論。
養(yǎng)護是楊昌濟極為重視的教育方法,“此所謂養(yǎng)護則體育之事也”[2]369。他明確提出,養(yǎng)護可以分為積極的養(yǎng)護與消極的養(yǎng)護兩類,前者是通過開設游戲、體操、手工等教學科目來實現(xiàn)鍛煉身體、增強體質的目的,后者則是通過注意衛(wèi)生、預防疾病來達到保護身體不受損害的目的,二者是一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從思想啟蒙的角度看,楊昌濟的養(yǎng)護理論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現(xiàn)代醫(yī)學衛(wèi)生、體育教育等學科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來批判和改革20世紀初中國的不良社會習俗和學校教育弊端。他在論述積極的養(yǎng)護時,先是著重介紹英國和日本獎勵各種體育運動及其產生的積極作用,然后接著說道:“中國文化深而腐敗甚,國民文弱,有東方病夫之目,從前與北方諸民族戰(zhàn)爭,屢次失敗;以當今日東西各國精煉之兵,宜其無能為役也。故獎勵運動,乃今日從事教育者所宜極力提倡者。”[2]371-372與此相似,他在論及消極的養(yǎng)護時,也是在比較了中西方學校教育的差異之后指出,我國學校普遍存在鐘點過多、功課繁重、食物不潔等弊端,從而使得學生身體發(fā)育受損、抗病能力減弱。客觀地說,這是從維護學生的生命健康權利出發(fā)賦予養(yǎng)護(體育)以倫理價值。
綜上觀之,楊昌濟對教授、訓練以及養(yǎng)護方法的闡釋,均立足于經驗主義的立場。他曾在英國阿伯丁大學留學三年,不僅系統(tǒng)地學習了英國經驗主義哲學,而且還深入到英國大中小學進行實地調研,撰寫和發(fā)表了《記英國教育之情形》《蘇格蘭小學規(guī)約》等文章。“經驗主義強調觀察的重要性,在觀察的基礎上思考、分析、發(fā)現(xiàn)規(guī)律。”[5]196從這個角度來看,楊昌濟的教育方法觀,主要是基于經驗主義原則。
三、師生關系觀:倡導平等交往關系,反對單向的對象化關系
在界定教育的概念時,楊昌濟的確將師生關系視為一種主客關系,即教師是教育的主體,學生是教育的客體。但與此同時,他卻明確指出:“第一,教育之主體,不可不為人;第二,教育之客體,又不可不為人。”[2]285也就是說,楊昌濟雖將學生視作教育的客體,但也強調應把學生當成活生生的“人”,而不能當成無生命的“物”來看待。這實質上蘊含著深刻的倫理意義。
從哲學角度來看,主體是相對于客體而言的,主體所面對的是客體,客體既包括自然物,也包括他人。自近代啟蒙運動以來,主體性被認為是一種現(xiàn)代觀念,也是人作為主體的核心品質,它強調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征服和占有,亦即主體把自身的意志、力量強加給客體。近現(xiàn)代教育中不尊重學生生命價值的種種現(xiàn)象,正是根源于這種主體性思想。“主體性教育立足于主客的關系認識人,實際上把人當作‘物’來認識,獲得的不是人的主體性,而是‘物化’的主體性。”[6]80因此之故,從20世紀初開始,許多哲學家和教育家不斷倡導主體間性,并辯證地提出真正的主體性是一種主體間性。比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曾言:“世界向來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7]146“此在本質上是共在。”[7]152這里所謂的“共在”或者說主體間性,意指人們在交往中相互理解、平等相待的特性。很顯然,基于主體間性所理解的教育才是“人”的教育,立足于主體間性教育所培養(yǎng)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楊昌濟認為教師是教育的主體,但他并不贊同教師以“我”為中心的占有性的個人主體性,而是主張把學生當作“人”、當作“一個生命體”來看待,并由此構建一種民主、平等、互動的師生關系。
在楊昌濟看來,只有構建一種民主、平等、互動的師生關系,才能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1914年9月26日,他在日記中介紹了美國學校新出現(xiàn)的一種教學模式,即:每個鐘頭,教師只講十幾分鐘,其余時間任學生自修;并把全班學生分成甲乙兩組,上午甲組聽講、乙組自修,下午則乙組聽講、甲組自修。在介紹完這一教學模式之后,他緊接著提出,學生不要太在意考試分數(shù),“課之可缺者缺之,可以遲到者則不妨遲刻,省出精力獨自研求,務求實益”[8]87-88。這里強調重視學生自主學習、獨自研求習慣的養(yǎng)成,無疑體現(xiàn)了楊昌濟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給學生創(chuàng)造自由發(fā)展空間的教育理念。需要注意的是,楊昌濟這一教育理念的形成,同時也受到了中國古代書院教學方法的啟發(fā)。他終生服膺的朱熹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時,就非常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并經常帶領學生到野外考察、隨機指導,說自己只是“作得個引路的人,作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朱子語類輯錄》)。迄至清末民初,書院仍然沿用著這一教學方法。1898年曾求學于岳麓書院的楊昌濟,就深切感受到了這一教學方法的益處。他在1914年6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英人之教法在于獎勵學生之自動,以養(yǎng)成讀書力為務,頗與吾國從前之教授法相似。……楊仲蘅在求實書院,為學生講御批通鑒,使學生點宋元學案,乃合用新舊教授法者。”[8]41在楊昌濟看來,英國人的新教學法與中國古代書院的舊教學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統(tǒng)屬于“以養(yǎng)成讀書力為務”的開發(fā)式教學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開發(fā)式教學法?楊昌濟認為,開發(fā)式教學法是相對于注入式教學法而言的,注入式教學法是指“惟教師活動,或講演、或說明,被教育者惟取被動的態(tài)度,以收納知識”[2]349;而開發(fā)式教學法則是指“教師自問答法,使被教育者活動,使被教育者發(fā)明關于某事項之知識”[2]349。由定義可知,注入式教學法所營造的師生關系,是一種師尊生卑、上施下效的對象化關系,教師將自己的目的、知識、能力等人的本質力量作用于學生,而學生只能被動接受、被動服從;開發(fā)式教學法所營造的師生關系,則是一種雙向互動、平等交流的交往關系,教師根據(jù)教材內容和學生認知規(guī)律提出恰當?shù)膯栴},讓學生通過自己的觀察、思考、實驗、探究等活動來掌握和發(fā)展知識。在楊昌濟那里,開發(fā)式教學法又具體分為問答式和課題式兩種,問答式教學法就是“教師發(fā)問,使兒童自發(fā)明真理而以語言表出之”[2]351,要求兒童(學生)不止于簡單回答“是”或“不是”;課題式教學法即是老師向學生布置課題研究任務,要求學生“自其已學得之知識,自考究而自解釋之”[2]351。對于這兩種開發(fā)式教學法,楊昌濟更重視課題式教學法,他認為教師設計課題應注意以下三點:一是要明確課題的意義和價值;二是課題的內容應適應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智力發(fā)展水平;三是課題的分量及其難易程度須適應學生的年齡特征、家庭情況和生活經驗。只有注意了這三點,課題式教學法才能達到激發(fā)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促進學生個性發(fā)展等良好效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楊昌濟本著知行合一的精神,自覺將開發(fā)式教學法應用于自己的教學中。1919年10月26日,他曾在日記中這樣反思道:“余思本學年倫理學之教法,要與上學年不同。不專教一本書,取各倫理學書中之精要者而選授之。每次講何書、何章、何節(jié),從幾版至幾版,皆標之于黑板上,俾學生就哲學門閱覽室領取是等書籍而閱覽之。……又擬教學生作倫理學札記:一、每讀一段即選擇一二精要之語;二、批評;三、志疑以備質問。”[8]197簡言之,楊昌濟計劃首先布置教學任務,然后讓學生閱覽相關書籍,并在札記中記下自己的讀書心得、批評和疑問,以備向老師和同學發(fā)問。據(jù)其學生后來回憶,楊昌濟用開發(fā)式教學法教授《倫理學》課程的效果非常好。如舒新城在1945年發(fā)表的《楊懷中先生》一文中回憶道:“他教我們的倫理學及倫理學史,為時不過一年,但他所給予我的影響很大。”[9]1275毋庸置疑,在實施開發(fā)式教學法的過程中,學生們也對楊昌濟產生了較大的思想影響,讓他不斷反思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在楊昌濟的日記中,既記載了許多學生的思想言行,也摘錄了許多學生的讀書心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陳生昌言學校修身之課,多言下手工夫;但學生多不解人生之目的,故聽之毫無感動,不能見之躬行,此語亦有理。……學生自不肯用心思索,雖善教者亦無如之何耳。”[8]175楊昌濟與學生平等交流、共同切磋的關系,以及他注重啟發(fā)學生主動思考的初衷,由此可見一斑。
四、楊昌濟教育倫理思想簡要評價
正如楊昌濟在《教育與政治》一文中說道,他自1913年留學回國后就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yè),意在借助教育活動來改造人心道德,進而喚醒民眾來挽救國家危亡。這種教育救國思路在20世紀初的中國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等人之所以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也是因為他們都抱有這樣一種想法:“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10]這清楚表明,楊昌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動,著重考慮了教育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考慮了社會政治賦予教育的任務和使命,故具有濃厚的倫理價值傾向。也正因如此,楊昌濟的教育倫理思想在當時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培養(yǎng)了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等一批有志愛國青年,并引導他們成立了新民學會這一著名的青年進步團體。新民學會成立時所確定的“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11]503的宗旨,與楊昌濟教育倫理思想的致思路向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楊昌濟是早期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2]6。
關于恩師楊昌濟,毛澤東1920年在《致黎錦熙信》中深情地說道:“我對于學問,尚無專究某一種的意思,想用輻射線的辦法,門門涉獵一下。……斯賓塞爾最恨國拘,我覺學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懷中先生(指黎錦熙和楊昌濟——筆者注),都是弘通廣大,最所佩服。”[12]431可見,在青年毛澤東眼中,楊昌濟有著兼容并蓄、超越門戶之爭的氣度與格局,這也從側面體現(xiàn)了楊昌濟學術思想的鮮明特征。客觀地說,楊昌濟的教育倫理思想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917年4月,毛澤東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體育之研究》一文,文章首先提出了“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12]57的教育主張,接著分析了體育的功效、運動的方法以及國人不愛運動的原因等;而且該文還明確指出,體育、德育、智育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分別是養(yǎng)護、教授、訓練。所有這些觀點和說法,甚至是基本概念和術語,都能看到楊昌濟教育思想影響的影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一直強調要讓廣大學生“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fā)展”[13]376。同樣,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已清楚地認識到,為了讓“學生方面很有自動的活潑的精神”[12]421,必須實現(xiàn)師生關系的革命性變革,即他本人所謂的“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12]576。事實上,青年毛澤東確實與楊昌濟建立了一種平等交往的新型師生關系,這一師生關系對青年毛澤東的成長進步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總而言之,楊昌濟教育倫理思想在教育目的觀上,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中心的德智體全面發(fā)展,同時又對教育教學中的泛道德主義傾向保持警惕。這不僅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思想而具有現(xiàn)代教育思想的意蘊,也超越了在20世紀初中國流行的海爾巴脫學派教育思想而具有綜合創(chuàng)新的特性。其次,在教育方法觀上,他認為教育目的決定教育內容和方法,并由此提出和闡釋教授、訓練、養(yǎng)護三種教育方法及其具體應用。從道德哲學的角度看,楊昌濟的教育方法觀是以經驗主義人性論為基礎的,其主要著眼于維護和保障最大多數(shù)學生的根本利益。最后,在師生關系觀上,他雖將師生關系視為一種主客關系,但也同時強調應把學生當作“人”、而不能當作“物”來看待,亦即尊重學生的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只有這樣才能構建民主、平等、互動的師生關系,才能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可以說,楊昌濟的師生關系觀,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的單一的主體性教育思維模式正在逐步轉向主體間性教育思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