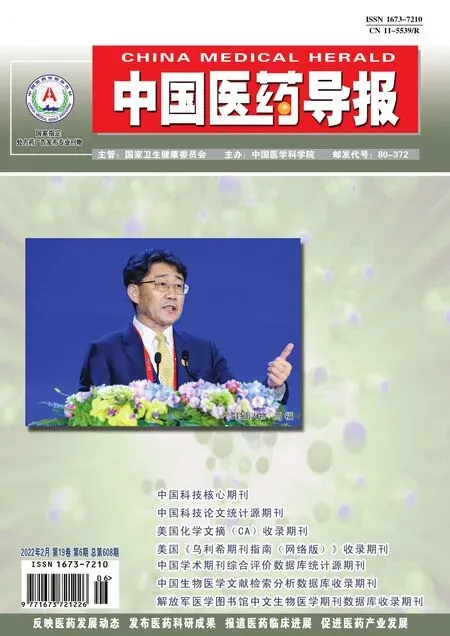從“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論惡性腹水的中醫治療
索菲婭 陳 晨 楊振寰 朱曉燃 姚樹坤
1.北京中醫藥大學中日友好醫院臨床醫學院,北京 100029;2.中日友好醫院消化科,北京 100029
惡性腹水是晚期惡性腫瘤患者的常見并發癥,多見于腹、盆腔惡性腫瘤病程后期,包括卵巢癌、結直腸癌、胃癌等,惡性腹水患者多為惡性腫瘤終末期,處于惡病質狀態,不能耐受癌癥治療,同時惡性腹水的形成又加重了患者的營養不良,因此預后較差[1-2]。有研究指出,惡性腹水患者1 年生存率<10%,平均生存期為12~20 周[3-4]。大量惡性腹水可見腹脹、乏力、喘憋、納差等表現。目前西醫治療手段主要為治療原發病、控制鈉鹽攝入、利尿、腹腔穿刺抽取腹水、腹腔局部藥物灌注等[5]。治療原發病一般需進行全身化療,但因營養狀況差,許多患者不能耐受治療。利尿、穿刺引流僅能緩解癥狀,并不能減少腹水的產生,并且多次穿刺引流容易導致低蛋白血癥及電解質紊亂。腹腔局部藥物灌注在近年發展較快,現已有腹腔熱灌注化療、靶向藥物或生物反應調節劑灌注等多種灌注治療方法,但總體療效有限,難以顯著延長惡性腹水患者的生存期[6]。中醫藥治療惡性腹水具有不良反應少、安全性高、患者接受度高等特點[7]。先前開展的許多中醫研究證實,中醫藥在治療惡性腹水時療效顯著,可明顯改善患者癥狀及卡諾夫斯凱評分,提高生活質量[8-10]。但目前對于治療惡性腹水的中醫理論研究較少。為從中醫理論闡述惡性腹水的治療,本文基于《金匱要略》中“大氣一轉,其氣乃散”理論進行探討。
1 “大氣一轉,其氣乃散”的理論內涵
“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出自《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原文所記“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并在其下附有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和枳術湯兩方。關于“大氣”的內涵,各名家經典主要將其理解為宗氣、胸中大氣、胸中陽氣。如《靈樞·五味論篇》講述“大氣積于胸中,名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隨呼吸出入”,與《靈樞·邪客》講述的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一致,因此《靈樞》中大氣應指宗氣。孫一奎認為宗氣又叫大氣。而喻嘉言在《醫門法律》中將大氣解為胸中大氣,胸中大氣能主持營衛之氣、宗氣、臟腑經絡之氣等,使諸氣周流不息,并且胸中大氣能包舉肺氣,使肺能發揮治節的作用。大氣一衰,則人身內諸氣失去統帥。因此,喻氏認為大氣能主持宗氣、臟腑經絡之氣,而與之不同。近代張錫純認為大氣即宗氣,大氣不僅能綱領諸氣,并綱領周身血脈,并創升陷湯治療大氣下陷之證。因此,“大氣一轉,其氣乃散”指在水氣病中,借助藥物之力,調動機體,促發宗氣,胸中大氣周流布散,來振奮衛氣,溫發內陽,促使表里三焦通暢,營衛之氣、臟腑經絡之氣、血脈有所主,則寒凝水液得以祛除[11]。
2 大氣的生理變化
結合經典及諸位醫家講述,大氣無論理解為宗氣或是胸中大氣,其生理功能都是統一的,即居于上焦,積于胸中,為全身諸氣及周身血脈之綱領。大氣的產生與維系和肺、脾、腎三臟息息相關。《靈樞·邪客》所言“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宗氣為脾胃運化之水谷與肺吸入自然界的清氣相合之產物。而腎中陽氣對于脾胃正常運轉、大氣的產生及功能行使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大氣能主持諸臟腑經絡之氣,而諸臟腑的功能對于宗氣功能的正常運轉同樣能產生影響[12]。脾胃為五臟氣機的樞紐,脾為之使,胃為之市,肺主治節,主一身之氣,肝主疏泄氣機,腎中陽氣為人身之根本,對于推動大氣的運轉同樣重要。
3 大氣的病理變化與惡性腹水的形成
惡性腹水屬于中醫“臌脹”范疇[13]。也可歸于《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石水”病,如《醫門法律》中講解仲景所謂石水,“凡有癥瘕積塊痞塊。即是脹病之根,日積月累,腹大如箕……不似水氣散于皮膚面目四肢”。惡性腫瘤患者多為久病,體內精血耗傷,正氣不足,漸成癌毒[14]。惡性腫瘤為有形癌毒,其形成與氣滯、痰、瘀、毒等皆有關,有形之癌毒能阻滯體內氣血之運轉[15]。大氣的病理狀態,包括痹阻、上逆、虛弱、下陷等[16]。腹、盆腔惡性腫瘤患者脾腎虧虛、大氣虛弱,甚則見大氣下陷;癌毒痹阻大氣之運行,大氣不能運轉,肺脾腎不能運化水液、水道不調,于癌毒壅阻之處水液停聚而成水邪,多原因共同導致腹水的形成。惡性腹水患者伴發呼吸困難、心悸、胸悶氣短等,是大氣不能“貫心脈,行呼吸”的表現[17]。惡心嘔吐、腹脹腹痛、便秘等亦與大氣不能主持脾胃、腸、臟腑及經絡之氣有關。腹水形成后則更阻滯大氣的運轉。惡性腫瘤患者本已有血瘀的病機,而大氣一衰則加重了血分的瘀滯,如《靈樞·刺節真邪論》所言“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血分瘀滯,則如《金匱要略》中所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更加重了腹水的形成。腹水既成,又如《血證論》中所言“水病則累血”,如此循環往復,隨正氣虧損,血瘀漸重,腹水不斷加重。人體水谷精微不能運轉,停留于腹中而成濁邪,氣血不得滋養,則正氣越虛,是本虛標實之證。此時治療切不可一味攻逐水邪,攻邪亦傷正,大氣受損,則易下陷。大氣下陷易導致心肺陽氣失去托舉,陽氣易脫,或導致下焦元氣欲脫,皆是中醫的危重癥[16]。
4 惡性腹水形成機制
惡性腹水形成機制包括:膈下淋巴管被腫瘤細胞阻塞,導致淋巴回流受阻,而潴留于腹腔;腫瘤細胞腹膜轉移,新生血管形成,與腹膜的通透性增加,大分子物質外滲;低蛋白血癥,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導致血漿外滲入腹腔中;門靜脈癌栓導致門靜脈高壓,促進腹水的形成[18]。以上多種原因的綜合作用導致了惡性腹水的形成。
5 轉“大氣”以治惡性腹水
《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一篇對于水氣病之治療已示其法門。水氣病先辨病位,再辨“氣分”“血分”。原文中轉“大氣”之法為治“氣分”,附有二方。一是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該方用于治療表證誤下、表邪內陷入胸中,能溫通胸陽,加入麻黃振奮宗氣,宣發肺氣,肺主治節,通調水道,更用附子、細辛入足少陰腎,可以鼓舞腎陽,使大氣得轉,陰邪則祛[19]。一方是枳術湯,枳術湯能健脾行滯,如《金匱玉函經二注》講述白術健脾強胃,枳實善消心下痞,逐水停,散滯氣,二者結合,通過健脾、運脾使大氣得轉。因此,轉”大氣“可從調肺、脾、腎著手。《金匱要略》原文對于血分并無明示用方,但氣、水、血三者病常相因,大氣可以綱領血脈,并且水氣病既成,必然會阻滯氣機運轉,因此,血分的證治同樣離不開轉大氣之法。惡性腹水繼發于惡性腫瘤,因此其治療需結合本虛標實、痰瘀郁毒內結的本質,用藥不可過于峻猛,以防驟傷正氣,危及生命。
5.1 補氣利水
補氣主要是通過補益肺脾,來補養大氣,使肺得治節,脾能運化,大氣得轉。該治法代表藥物為黃芪、白術、茯苓。生黃芪能補氣升陽,利水消腫;白術入脾胃,能補中除濕,李中梓《雷公炮制藥性解》講述白術能除濕利水道;茯苓是利水滲濕兼能健脾之要藥。《金匱要略》中以防己黃芪湯治風濕、風水,防己茯苓湯治皮水,皆取其能補氣利水之功[20]。黃芪既能補肺脾之氣,兼補胸中大氣,又能升提氣機,因而張錫純升陷湯中用大劑黃芪來升提下陷之胸中大氣。王貴等[21]研究發現外治法治療惡性腹水的用藥規律,所有外治方中黃芪的使用頻率達43.84%,僅次于桂枝。宋鳳麗等[17]對外治及內服的方劑進行分析,發現單味藥使用頻率最高的依次為茯苓、白術、黃芪、豬苓。用補氣之法需注意補而不能壅,若用過多壅補之藥,則恐不利于水邪滲利。
5.2 行氣利水
行氣主要是通過宣發肺氣、調理中氣、峻下逐水等法來梳理氣機,使肺得治節、脾胃能中轉氣機,從而使大氣得轉。宣肺利水之代表藥如麻黃,《金匱要略》中治里水以越婢加術湯、甘草麻黃湯,取麻黃發表并宣肺利水之效;調中兼能利水的代表藥物如大腹皮、檳榔、枳實,方劑如五皮飲,能行中氣而利水;峻下逐水代表藥物如牽牛子、甘遂、芫花、大戟等。如應用行氣利水藥時,應注意行氣則易耗氣傷氣,如李中梓對大腹皮的論述“然宣泄太過,氣虛者勿用”。峻下逐水藥,多能破氣,因此應用此類藥物時應注意攻補兼施、中病即止。為防止峻下逐水藥藥力過峻,或可將劑型改為外用藥,通過外用局部吸收起作用,而不影響全身。如王文等[13]研究發現,外敷消脹利水散(芫花、甘遂、牽牛子)組方中配合黃芪、白術等補氣藥,療效顯著,并且無不良反應。
5.3 清熱利水
惡性腫瘤患者氣血陰陽俱虛,其中有以肝腎陰虛表現突出者,其腹水形成可為水熱互結之證。然而其熱非大實之熱,乃陰虛之熱,此時治療則應以育真陰、清虛熱、利水邪為主,不可以大苦大寒之品清熱,或苦寒之品峻下逐水,以防止耗竭真陰,陰竭而陽脫。選方可用豬苓湯育陰清熱、利水滲濕。
5.4 溫陽利水
惡性腹水患者水邪泛濫,脾腎陽虛不能運化水液。癥見陽氣虛弱者,以扶陽為第一要務[22]。扶陽者,為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脾腎陽虛,應急溫腎陽,以防命門火衰;陰邪阻滯,應急破陰回陽,以防陰邪進一步耗傷陽氣。經典方劑如真武湯,真武湯能溫腎陽健脾運而瀉水邪,藥味少而功效專。溫脾腎之藥還可用仙茅、淫羊藿、肉桂、干姜等,溫運脾腎,則陽氣得以疏布周身,大氣得轉,水道通調,則水邪得利[23]。應用溫陽利水法時,應注意惡性腫瘤患者為正氣虧虛,陰陽俱虛損,若過用辛熱之品,如仙茅、真武湯中附子等藥,易耗傷陰液,有陰液耗竭之虞。因此,辛熱之品應用于急治標證,不宜長用。標證一治,則應改用辛溫之品,防止過用辛熱,也可配合龜板、阿膠等補養陰血。
5.5 活血利水
惡性腫瘤患者本已有血瘀之病機,血瘀與腹水相互促進,但因惡性腫瘤患者正氣已虛,氣血虛弱,因此,使用活血利水之法,應注意采用活血利水、藥性平和,而少破血逐瘀之品。活血利水藥如丹參、澤蘭、赤芍等,丹參在《神農本草經》中能治“腸鳴幽幽如走水”,能利腸中水氣;澤蘭在《神農本草經》中能治“大腹水腫”;芍藥在《神農本草經》中記載能“利小便”,《本草經集注》中能“去水氣”。方劑中,如當歸芍藥散,出自《金匱要略》婦人病篇,能和肝健脾利水,與西醫常規治療聯用治療惡性腹水療效顯著,并能減輕西醫治療的毒副反應[24]。張慶林等[25]提出平衡阻斷法治療惡性腹水,腹水治療應注重氣、水、血相關理論,并根據此法提出調燮陰陽、化瘀利水的治法,應用少腹逐瘀湯加減治療。但活血利水若采用逐瘀湯一類,則應小其制,使其能逐瘀又不傷正。破血逐瘀之方藥,如三棱、莪術或大劑逐瘀湯之類應慎用,以防止損傷氣血,戕害生機。
臨床診療中,所見患者往往并非證型單一。惡性腫瘤患者多病程較久,多個臟腑受累,病位復雜;并且本虛標實,病性復雜。因此,上述治法往往需要化裁合用。劉猛等[26]應用抗癌消水膏治療惡性胸腹水,組成方藥中生黃芪、桂枝、老鸛草、莪術等將補氣、溫陽、清熱、活血等治法結合。多種治法化裁合用,氣血同治,補而不壅,行而不散,溫而不燥,攻而不傷,通過補氣、行氣、溫陽、活血諸法使大氣的功能恢復,大氣周流,水氣得散。
6 結語
惡性腫瘤患者由于正氣虧虛、陽氣虛弱、氣機阻滯、血行瘀阻等諸多原因導致大氣不能周流,而易內停水氣,外可見惡性腹水的產生。在“大氣一轉,其氣乃散”的理論指導下,從大氣的生理、病理變化分析腹水的形成,通過補氣、行氣、清熱、溫陽、活血等法,使大氣得養,周流布散,從而發揮其綱領諸氣及周身血脈之功,則水氣得散。結合惡性腫瘤患者本虛標實的特征,采用攻補兼施的治法,藥遵王道,無虛虛,無實實,才能取得較好的療效。中醫藥對疾病的治療,需要落實到中醫理論中,才能指導遣方用藥。現代醫學對于惡性腹水的治療尚無良好療效,從中醫經典理論出發,認識惡性腹水的形成機制,并且指導治療,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