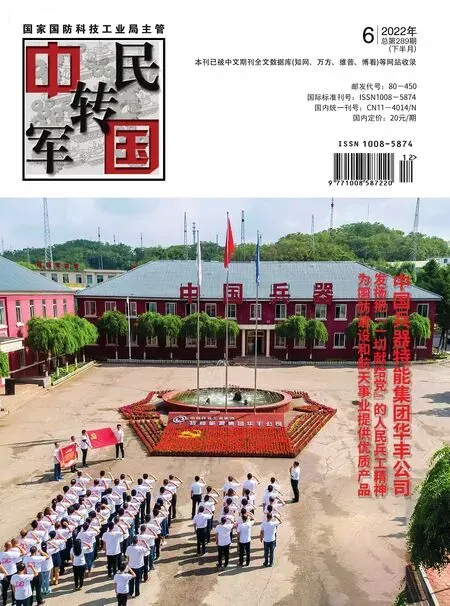堅定制度自信,走好中國民主之路
■ 劉志東
2021 年12 月5 日,我外交部發布的《美國民主報告》指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1]。應該說,民主有其多樣的實現形式,西方有西方的實現形式,中國有中國的實現形式,不能定于一尊,關鍵在于這樣的民主方式是不是符合各自歷史文化傳統,是不是由該國人民自主選擇,是不是能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可以說,中美民主的不同實踐方式和實踐效果,讓人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中國民主的實在性和美國民主的虛假性,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堅持和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斷走好中國民主之路。
一、中西民主的差別淺析
民主的形式不等同于民主本身,西方習慣用其所謂的政黨輪流執政、議會政治等形式作為民主的標志,混淆了民主的實質與民主的形式。用少部分人所謂的民主代替全民民主,其實質不過是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輪流坐莊,代表的始終是資產階級利益,而非全民利益,實現的只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民主而非全民民主。而中國的民主,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實現選舉民主,通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現協商民主,實現了最廣大人民的政治參與,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實質民主。
(一)西方民主是少部分人的形式上的虛假的民主
西方社會特別重視大選,候選人不惜花費巨資參與選舉。其背后都有強大的資本支持,一旦選舉成功,所謂的總統、首相將盡其所能為其背后的政黨及財團服務,開方便之門。其實質是西方選舉已淪為政黨及其背后財團的逐利工具,用選舉的投資換取執政之后的豐厚回報。要說民主,西方民眾也許只能在選舉之時能有一個投票上的政治參與,至于之后,民主則是政客們的民主,再與民眾無關。這種民主只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上的民主,而非人民大眾的民主、結果上的民主、實質上的民主。
(二)我國民主是人民大眾的結果上的實質的民主
中國的民主則大不相同。首先,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代表任何少部分人的利益集團。這個政黨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人民的代表。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現了最大程度上的社會整合,使絕大多數人能朝著一個共同的方向努力;擴大了民眾的政治參與,拓寬了人民利益表達的渠道,執政黨、參政黨和無黨派人士就一個問題充分醞釀協商,反復交流意見,最終達成符合中國社會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決策,這種機制保證了我們的民主是實質上的民主,而非形式上的民主。最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執政黨共產黨也有很強的民主監督作用,促使共產黨不斷地進行自我革命,不斷地改進執政方式,使這種執政方式更能為人民大眾服務[2]。所以說,中國的民主,是多數人的民主,全過程的民主和結果上的實質民主。
(三)中西民主的區別反映的是雙方歷史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
中西方民主方式的差別反映了中西方歷史文化傳統上的差別。首先,中西在政黨成立和政權取得的順序上不同。西方社會是先有政權,后有政黨。政黨的形成某種程度上講為的是權力上的制約平衡,防止產生權力的集聚,造成歷史的倒退。而中國是先有政黨,后有政權。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帶給了中國人民實實在在的利益,才決定了人民對共產黨執政地位的認可。其次,社會家庭觀念上的不同。中國人講求家國天下,很多政治理念是建立在對“家”這一概念的理解之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執政者與老百姓的關系有著類似于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家庭里,有相應的權力就要有相應的責任,講求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所以有什么事情,人民群眾都依靠政府,就像孩子有事就要找父母。西方則大不相同,他們家的概念相對較弱,子女一旦成年和父母的關系就弱化了,很多事情不再借助家的力量來解決,西方講求人的個人權利,追求自由與平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各個政黨要輪流坐莊,不可有絕對權威。最后,思維方式上的不同。西方看問題很多時候是零和游戲,你輸我贏,要靠競爭,優勝劣汰。在各項權力和義務上都要條理清楚,涇渭分明。對待民主、自由、公平上也是如此,講的是盡可能公平地分好蛋糕。中國不同,中國人講究合作包容,協作共贏。所以我們的民主是基于發展的,目的是實現更大的民主,而不是就現在的發展情況單純地要求絕對民主。
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礎、前提和最大優勢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在推動中國革命前進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實踐和制度方面實現了創造性運用、創新性發展,逐漸在多元主體互動中實現了對其他政治主體的全面超越,確立起在新型政黨制度中的領導地位,并最終通過人民政協制度的形式得到制度化肯定[3]。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始終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方向
中國的近現代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繼而向著共產主義社會不斷邁進,要求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無論施行怎樣的制度安排,都必須堅定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無產階級政黨要實現全面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前提和基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只有堅定這個前提和基礎,才能保證這項科學的民主制度為社會主義服務。
(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自身長期的穩定與發展
周恩來同志說過,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規定著這種新型政黨制度將長期共存。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保證這種制度長期存在的基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種制度就失去了其政治基礎,就不能展現出生機活力。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中國最大范圍上的社會統整,將中國人民凝聚在一起。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保證了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發展。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講,這種政黨制度的堅持與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各黨派間的協商決策能夠及時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
政黨是國家治理的設計者和推動者,政黨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團結合作和民主協商建立了新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創造了合作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制度[4]。在這種制度中,各黨派間充分的民主協商決定了社會治理決策的科學性,而中國共產黨堅強的政治領導以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執政地位保證了能夠將科學決策及時地轉化為社會治理行動。這種科學性和執行力是其他政黨制度難以比擬的,而其基礎也正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三、加強中西文化傳統研究,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話語體系
近年來,面對西方對我政治制度、社會問題的攻擊,我們給予了堅決的回擊。可以說我們的政治話語力量在不斷地增強,展現出新時代中國政治制度的自信。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更為自信,但我們對外宣傳話語力度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但面對千百年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我們有必要深化中西文化研究,特別是政治文化研究,進而用西方聽得懂的政治話語,展現我國政治制度特有的優越性。
(一)要增強文化自信,不斷堅定政治制度自信
制度與文化本身就是一體的。中國的政治制度適合中國最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文化基因的繼承。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實踐中發展,在發展中完善,越來越適合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展現出巨大的制度優越性。對此,在對外話語反擊與宣傳上,我們應當有也必須有充分的自信,不斷講好中國故事。
(二)要加強政治理論研究,完善中國政治理論體系
西方政治文明也有其悠久的歷史和政治文化傳統,在西方看來,其政治理論是相當成熟和完善的,故總希望用其理論范式來要求我們。對此,我們有必要不斷加強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研究,使我國政治理論體系不斷完善,進一步增強理論成熟度,只有解決了理論問題,政治上才能更加堅定。
(三)要研究中西文化,提升我國政治話語力度
我們對外溝通宣傳效果不夠的一個原因在于我們對西方文化傳統研究不夠,政治制度的背后是政治文化,只有深入理解對方的文化傳統,才能用合適的政治話語攻其薄弱,事半功倍。提升我政治話語力度必須對話語對象的文化傳統有充分的理解,否則只會空費口舌,無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