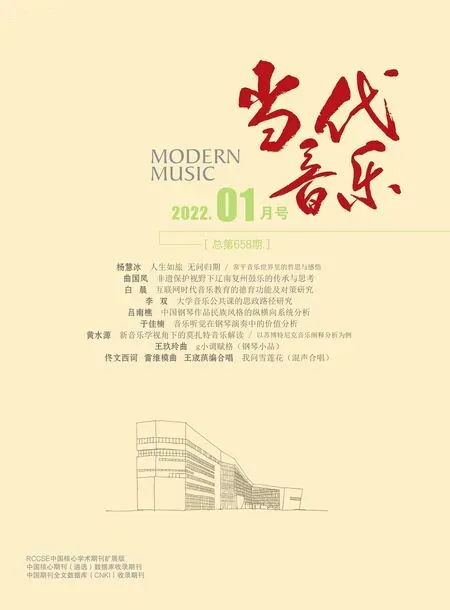新塘咕嚕苗族婚禮音樂文化“生境”探究
姚思梅 胡小東
一、咕嚕苗族婚禮儀式概況
咕嚕苗族歸屬于貴州省平塘縣大塘鎮新塘鄉管轄,新塘鄉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社區,在這片充滿生氣的土地上,除了苗族以外還居住著一部分布依族與漢族,因苗族居多而被廣泛稱為“咕嚕”。婚姻是人類最重要的人生儀禮之一,婚姻關系的成立通常以婚禮的方式來宣告。2021年初,新塘鄉咕嚕苗族陳天權先生、陳曉燕女士完婚,兩人雖系自由戀愛,但婚禮程序都按照本民族風俗逐一進行,將一場淳樸又極具儀式感的咕嚕苗族婚禮展現在親友面前。
與當地漢族和布依族不同的是,新人婚前無需進行“討八字”這一儀式。雙方家長按先男方后女方的順序到對方家中赴宴后,將擇日為新人完婚。雖不用進行“討八字”儀式,但咕嚕苗族十分重視天時地利人和,新娘的爺爺通過排八字的方式推算出吉日婚嫁后并通知男方,男方又再請人排八字推算,雙方達成共識后就擇定婚期舉行婚禮。婚禮分兩天進行。第一天是新娘家的“姑娘酒”,由新娘父母設宴款待鄰里親朋。次日凌晨四點,在一名懂禮節、擅唱歌的中年男子[1]的帶領下,新郎、“小伴郎小伴娘”和伙伴們出發并按著五點的吉時抵達新娘家。新娘家提前布好酒菜,幾名青年男子換上民族服裝,一人手執鑼、另外幾人各手持兩個牛角杯等候貴客的到來。新郎一行來到家門口,一青年男子敲鑼,另外幾人故作躲閃讓客人來“搶”手中牛角杯的酒喝,客人也表現出強烈的將酒“搶”過來暢飲的欲望,其間穿插著一聲聲富有律動性的歡呼。一番逗樂后,接親客拿到牛角杯痛快暢飲,而后按照女方家與男方家各一排的位置相對就坐并開始對歌,恩頌月神、致敬祖先、教化后人,一直開懷對唱到天亮發親。
早上七點,老人們一邊為新娘穿衣,一邊遞送祝福語。新娘身穿八條裙子(本族內有穿十二條的),既是表娘家心意,也表祝愿新娘衣食無憂。在裙子的內里放置了一面小鏡子(新郎衣服內也有一塊),意為反射所有看不見的不好的東西,將妖魔鬼怪都折射掉。與此同時,新娘家樓下對歌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新郎手持牛角杯(或碗)向新娘族中長輩敬酒,長輩們或是用手指刮過(一邊刮一邊說祝福語)碗后一飲而盡,或是刮了牛角杯送祝福語后,將其中一個牛角杯遞向新郎一同喝下。關于用手指刮酒杯,意為呼喚逝去了的祖先們來喝酒,保佑新人婚姻美滿。到出門吉時,新娘的弟弟拉著她圍著火盆轉三圈后踏出家門,象征得到了灶神的庇佑,日子越過越旺。與周邊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咕嚕苗族婚禮不興拜堂。新郎新娘等五位排序走的主要人員行至新郎家特意為他們準備的房間就坐,新娘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房間進門左側,左手拿著一只公雞、右手執一碗酒、口中說著禱告語,禱告結束后將酒碗中的酒喂予雞喝,而后殺雞供予祖先。意為向新郎的祖先傳達,從此這個家多了一個人,祈愿祖先保佑新人多子多福、和和美美。
二、《月亮古歌》——儀式的中流砥柱
(一)緣起
相傳,千百年前咕嚕苗族從很遠的地方遷徙到新塘這片大山中,是月光的一路庇佑才使得咕嚕苗族的祖先順利至此安營扎寨,故他們認為月亮是他們的保護神,時刻保佑著族人的興盛安康,因而世代都將月亮視為神圣的圖騰崇拜。基于此,咕嚕苗族為表對月亮的神圣崇拜,創造了《月亮古歌》與舞蹈《咕嚕跳月》,一表感恩,二表祈愿。其中,《咕嚕跳月》一般出現于大型的祭祀活動,每當月圓時,在寨老的帶領下,族人們相聚在一起舉行對月神的祭祀活動。男子們吹著蘆笙、女子們手執方巾,另有一人專司敲鼓,在一陣節奏聲中,族人們身著盛裝有規律地將手腳與腰身巧妙地結合扭動著。隨著時間的更替,跳月除用于祭祀外還衍生了不同的用途。在跳月過程中,族人們身上散發出清脆的鈴鐺聲,在過去是為了幫助族人們在逃避追殺的過程中聚集;而今,男女青年通過跳月的方式來傳達愛意,越是響亮的鈴鐺聲越能引起心儀對象的注意;隨著政府部門對民族文化的日益重視,現新塘鄉《咕嚕跳月》已被打造成當地用于接待外來游客的特有舞種。《月亮古歌》除應用于大型祭祀活動外,還被頻繁演唱于咕嚕苗族人民的婚禮中。
(二)《月亮古歌》本體分析
1.唱詞
咕嚕苗族祖先帶領族人一路跋山涉水至新塘,途中歷經艱險,故唱詞始終圍繞“遷徙”進行編唱。“從江西一路遷徙到貴州再到新塘,包括現在的祭祀,都是為了紀念祖先遷徙的不易。”[2]遷徙的過程是艱難且漫長的,故《月亮古歌》除歌唱遷徙的不易與紀念祖先外,還涵蓋著遷徙過程中的小細節。“大蚱蜢在前,小蚱蜢在后,我倆談戀愛,先不準老人他曉得”[3]。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青年男女們暗生情愫,在那個婚姻必須征得長輩同意的久遠年代,青年男女羞于將實情和盤托出,故借用“蚱蜢”在前后這一物象提醒對方保持警惕,也增添了一定的幽默趣味。
2.旋律、節奏
在演唱《月亮古歌》時,男女兩性所展現的是兩種不同的美感,但無論是男性演唱還是女性演唱,旋律中都應用了較多的附點音符,并以2/4拍為主要節奏型。大量地運用附點音符,使得旋律悠揚婉轉及將唱詞故事性延長的特點。男性演唱時多為一人獨唱,聲音較為低沉且有力,節奏較為穩定,時而伴有形如波浪線一般的發聲方式。轉換到女性演唱時,一般為二人及以上,音域跨度較男性高,聲音嘹亮且旋律性更加明顯。全曲圍繞do-re-mi-sol-la幾個音進行,當結束句落在“do”音,就像是歌者在交代聽眾,“我”方演唱暫時告一段落,輪到“你”方接唱。
(三)儀式的維系作用
《月亮古歌》于咕嚕苗族人民而言,是歷史的見證者與記錄者。隨著時代的變遷,把唱什么?怎么唱?什么時候唱都融匯到這首古歌的唱詞與旋律當中。在每一場大型活動與婚姻習俗中,《月亮古歌》的身影都是一種美好的象征,它是喚醒民族記憶、維系族人團結、增強民族情感的有利助攻。當咕嚕人民身穿裝飾著月亮圖案的民族盛裝,當新人即將跨入婚姻的殿堂,《月亮古歌》已經在咕嚕人民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種必唱的習慣。當古歌從歌者赤誠的心田流出,不僅是向月神祈愿,也是深表對月亮的恩澤與庇佑的感恩。
三、咕嚕苗族婚禮音樂的場域應用分析
(一)接親
咕嚕苗族祖先創作的《月亮古歌》能夠在這樣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中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得以沿襲,這與人們在人生儀禮中的應用緊密相關。《月亮古歌》在咕嚕苗族的婚禮中演唱,基本都是出現于新娘家,這首歌已成為咕嚕苗族婚禮“姑娘酒”的必唱曲目,如若苗族姑娘嫁了漢族男子,男方也必須要請一位會唱《月亮古歌》的人來接親。在本次調查的婚禮中,新娘家主要從事泡糟酒的自產自銷,在待客的場地周圍放滿了形制精美的酒壇,酒香四溢,同來接親的“小伴郎”都難敵這醇厚酒香的誘惑。咕嚕苗族向來講究“對酒應當歌”的習俗,《月亮古歌》篇幅較長、演唱者情緒平緩、聲音低沉且穩固,在唱完一段后的收尾處,旁邊本是聽眾的一行人會接著演唱一句“呀~”的拖腔進行襯托,從而起到一定的裝飾作用。《月亮古歌》被視為咕嚕苗族最為神圣的歌曲,在神圣的婚禮中演唱,傳達的不僅是對神的尊崇,同時也是代替新人向月神祈祐。又借用歌詞如“大螞蚱在前,小螞蚱在后,我倆談戀愛,不準老人他曉得”增添詼諧幽默的氛圍。
(二)攔門
在新郎家堂屋的大門前擺放著一張長桌,兩捧花、兩盤吃食以及一根用紅色布條纏繞的竹竿橫置于桌上,這與周邊漢族、布依族的攔門陳設是一樣的,對前往“打賀客”的親戚進行攔門對歌儀式。主人家歌手唱到:“舅爺抬腳來到處,心中歡喜三丈深”,舅爺不遠數十里來參加婚禮,心中已是欣喜萬分,再看舅爺家送來的琳瑯滿目的賀禮,內心深處甚是感激。舅爺家歌手回道:“我們來到姑家門,看到姑媽忙不贏”,既是夸贊姑媽勤勞能干,也表達了想要對方抬桿讓“我”進門的心情。攔門儀式對事不對人,舅媽們雖還未進門,但是她們一同前來的嗩吶手已被主人家安排至里屋坐下,被邀請一同來熱鬧的其他親朋也已入席就坐,嗩吶手不時地吹奏著喜慶的音樂,為忙碌的宴席增添了一道聽覺禮遇。主人家歌手根據不同賀客的身份進行不同的即興編唱,對本民族歌手就用苗語對唱,來者若是其他民族便用漢語交流,或自謙、或贊揚對方、或讓對方想寬心,現在禮儀都這樣興,攔門只為添樂趣。
(三)穿衣帽
咕嚕苗族與周邊漢族和布依族一樣,在大婚當日,新郎的舅舅肩負著為新郎新娘換衣帽的重任。在親手為新郎新娘穿上衣服后,兩位歌手便唱道:“自你今天穿上后,祝你子孫發滿家”,唱詞中充滿了對新人的祝福,穿衣完畢后新郎新娘向兩位舅媽分別送上一碗美酒致謝。再次送上喜歌祝福后,新郎新娘又各手執兩碗酒與兩位舅舅家的歌手一同歡飲。與文章前面所提及的不同,由于兩位舅舅家請來唱歌的“舅媽”長期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并沒有像族中其他長輩一樣用手指刮過盛酒的容器后才喝下,而是將祝福都融入到了歌聲中。新人也欣然接受這份祝福,在體現著較為明顯的族際間的文化差異的同時,也體現著新人對不同文化的尊重與認同。
四、咕嚕苗族婚禮音樂生成之思
(一)獨特的人文地理條件
新塘鄉四周群山環繞,咕嚕苗族的祖先在月亮的庇佑下一路遷徙至此依山傍水而居,月亮是咕嚕苗族最尊崇的神。圍繞月亮進行編唱的古歌,內含著苗族同胞對祖先遷徙不易的感慨,也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正是因為祖先的勤勞睿智,才有了后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新塘鄉地處平塘縣與惠水縣交界地,一同棲息在這片土地上的還有不少漢族與布依族。千百年來,咕嚕苗族與各民族和睦相處,始終保持著和平友好的友鄰關系,各文化在一來一往中形成了一種相互交流與借鑒的局勢。就婚禮音樂來講,咕嚕苗族很好地借鑒了漢族與布依族的山歌元素,如在新郎家進行攔門對歌時所采用的七言句式和曲調,都與漢族、布依族的山歌有極大淵源。新娘自娘家出門前,一個統一身著鮮紅色服飾的隊伍敲鑼打鼓而來,這是由新娘的姑爺請來祝賀的漢族歌舞隊。姑爺居住在臨近的通州鎮,那是一個漢族居多的小鎮,本是苗族的姑爺長期生活于漢文化氛圍相對濃郁的環境中,故受漢文化影響較深,這些都無疑是多民族雜居環境下文化交流成果的有力呈現。
(二)儀式烘托
儀式音樂是與所進行的儀式相呼應而非獨立存在的,在咕嚕苗族婚禮中演唱《月亮古歌》,很好地印證了做什么與唱什么相吻合。新人喜結連理,新郎一行人來接親時一定會唱《月亮古歌》,這是一首神圣的歌曲,唱給“神”聽也唱給在座的觀眾們聽,這比獨白式的向月神祈禱庇佑更加富有儀式感。在攔門儀式中,單純地置物攔人在咕嚕苗族看來是不禮貌的,他們認為:有喜事就要唱喜歌、有酒就要唱酒歌、攔了門就要唱攔門歌。在對歌過程中,采用漢語進行對唱,將攔門意圖、感謝客人送的禮物以及相互稱贊等都表述完畢后,一輪的攔門儀式結束,又對下一家來賀的客人把竹竿橫置起來后進行相同模式的對唱。舅爺家為新人穿衣帽,也講究強烈的儀式感,新人當穿新衣,將喜歌融匯到衣物當中為新人穿上,祈愿新人被神與祖先庇佑、福祿齊長。
(三)儀式執行者的橋梁作用
在咕嚕苗族婚禮音樂的“生境”探究中,除了音樂本體,還應將目光投向音樂的操持者。新娘家請來接客的老人,在族中頗有聲望,他具有豐富的儀式組織經驗,在無數場婚禮中演唱過《月亮古歌》。新郎家請來負責領頭工作的,是一位德才兼備、熟知咕嚕苗族婚姻禮節的中年男子。在新娘家,他是引頭的押禮先生,是懂禮節、擅唱古歌、可與新娘一方進行情感交流的溝通者;到新郎家,他又化身專職歌手,以即興編唱的方式迎接前來祝賀的賓客。新郎舅舅家請來幫唱、穿衣帽的兩位歌手,因不會本民族語言,加之長期通過微信、節慶、酒席等平臺接觸苗族以外的其他風格與形式的音樂,故而在婚禮的對歌中呈現出明顯區別于當地的音樂風格。不難發現,年齡較長的老人們由于與外界交流的機會甚少,在歌曲演唱中都會相對完整地沿襲著本民族的固有特色。而中年一代,在現代化的沖擊下,除了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覺沿承,還通過各種途徑的文化溝通交流與外族交好,構建起文化生成的有利環境。
結 語
新塘咕嚕苗族是一個對人生儀禮極為重視的民族,本次婚禮,新娘自述與母親婚禮沒有較大的差別,如果一定要有,那便是如今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彩禮嫁妝較以前豐富許多,該有的儀式程序都逐一進行著。通過對儀式的觀看,不難看出苗族婚禮與雜居民族婚禮的區別所在,這大概就是為什么人們會說“苗族被漢化得不算嚴重”的實例呈現吧。咕嚕苗族在對本民族文化強烈認同的基礎上對外文化又有著較大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在新娘家,男女雙方長輩用本民族語言唱著古歌從凌晨對至天明發親;在新郎家,不畏天氣嚴寒進行漢語山歌攔門,咕嚕苗族婚禮音樂在這樣一個維系本民族古老文化與兼容外來優秀文化的環境下得以延續和發展。
注釋:
[1]薛藝兵.儀式音樂的概念界定[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3(01):28—33.
[2]相當于布依族與漢族的押禮先生。
[3]新塘寨老陳明相先生口述。
[4]新娘的爺爺口述。
[5]曹本冶.思想~行為:儀式中音聲的研究[J].音樂藝術,2006(03):83—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