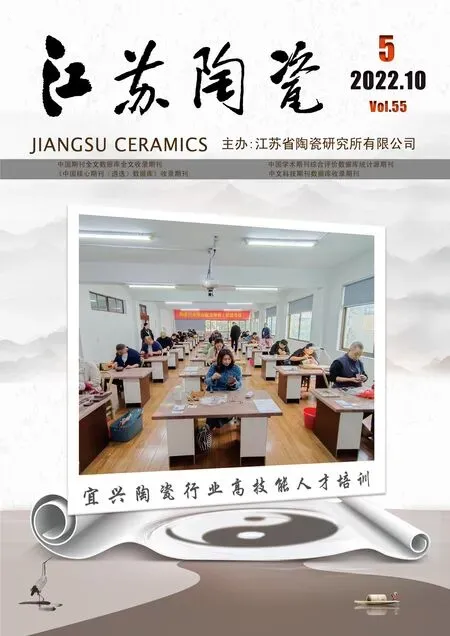淺析紫砂“田園清趣壺”的田園意蘊
王 瑋
(宜興 214221)
1 田園題材作品審美的三個層次
田園情懷是中華民族始于農耕社會,在漫長的歷史中自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心態,是中國特有的一種令世界羨慕的生活哲學觀。觀山則滿目生機,情漫于山;閱水則沉思風浪,情傾于水。田園情懷表現在對生活的藝術化、情趣化享受,“十笏芧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居陋室而懷田園山水,同時也看重超越自然物質的精神富足,表現為“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樂觀灑脫心境。文人畫客、工匠藝人往往把田園情結上升到審美情趣的高度融入自己的作品,于是各種田園情趣的藝術作品在歷史上層出不窮。
人們自古就把田園審美分為“應目、會心、暢神”三個層次。那么,我認為田園題材作品的審美也應該有相應的三個層次,這里的“應目”應該是指作品呈現的田園元素形象能給人帶來實實在在的感官愉悅,美的形態、美的色彩、美的布局,這是一種直接的視覺感受。在此基礎上,作品的田園形象要與內在主題相聯系,要有內涵支撐,塑造的田園意象要給觀者帶來感同身受代入感的“會心”體驗,使欣賞者與田園達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融。田園作品審美的最高境界就是作品能打動人的心靈,給觀者“暢神”的空間,使其游心物外、物我兩忘,求得宇宙與生命本原的融合與超越,“天人合一”。一件優秀的田園題材作品,一定能給觀者帶來這三個層次的審美享受。
2 紫砂“田園清趣壺”的田園意蘊
始于明朝的紫砂壺藝作為一種傳統文化技藝,發展至今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從一開始就秉承了當時社會追求藝術化生活背景下的“韻外之致”的基因,文人情懷始終貫穿其歷史進程的整個過程。藝人往往將個性化的創作主題融入到具體的器具審美之中。有許多以自然物像為題材的作品都被創作者融入了田園情結,紫砂“田園清趣壺”(見圖1)就是以“田園”為題材的一件作品。

圖1 田園清趣壺
造型與裝飾是作品形象的基礎,紫砂作品“田園清趣壺”首先以圓器為壺器基礎,壺體飽滿、開闊,拓展了主題表達的物理空間,上半部鋪覆荷葉,首先點出主題,后又分別以藕、荷葉及青蛙等田園元素雕塑來布局壺流、壺把及壺鈕,在賦予作品實用性的同時,更巧妙地架構了作品意象。圓雕青蛙更是刻畫細膩、逼真、惟妙惟肖,平添了幾分生機,是作品的視覺焦點。作品總體布局考究、嚴謹、用工匠心,在整體謀篇中又引入局部鋪砂的手法作細節點綴,既表達出大結構的素樸秀逸,又有局部的精致細耕,簡練中透出端重和秀雅。作品選用精制紫泥全手工制作,融功能之實用、技藝之素雅、意象之詩性于一體,精心營造了作品的形象美,給人感官以愉悅。
造型與裝飾同時也塑造了作品的審美意境,紫砂作品“田園清趣壺”呈現的是帶有秋韻的田園情趣,并給人廣闊的想象空間。秋天的田園是特別的,沒有春的多彩、夏的濃烈,看似只有落寞與無奈,但細品,它卻也有著不一樣的素麗與希冀。夾帶著清甜而憂郁的桂花香的風從遠處飄來,它就那樣霸道地浸漫了所有人的呼吸,荷塘里的風催黃了曾經那么濃郁的綠,殘荷綽綽搖曳,飄零的每一片荷葉都在風中述說著不一樣的故事,就同所有生命周期的輪回,都不得不在經歷著這樣新舊交替的宿命。蕭瑟秋風擾過,池中只留下一池的花莖殘葉與那波瀾不驚的水相依相伴、共渡余生,而秋實的蓮藕卻在蛙聲的祝福中于池泥中走向成熟,這就是作品展現給我們的一份田園清趣。
秋天的田園有失落、有收獲,正是有了滄桑才有過盡千帆的豁達,這種辯證的美不僅是作品外表所展現出來的,更是可以通過聯想而能感悟到的那秋默默傳遞著生命由輪回而獲得的永恒。借景寓情、觸景生情,帶給我們更多的是關于生命本原與自然的思考,這正是作品投射的田園意蘊。
3 結語
一件精美的紫砂壺作品,應該在給人帶來樸素淡泊、溫潤如玉的視覺美享受的同時,通過意境的架構傳達出背后的文化與情感,只有內外的完美融合才為一件好的器物。田園情懷是中華民族始于農耕社會自然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精神,把田園情結上升到審美的高度融入作品,能給觀者提供一種情趣化、藝術化的審美享受。在生活節奏高度緊張的當下,這無疑是一種我們不可或缺的回歸本真、釋放人性的體驗。
紫砂壺器是一種能寄托文化與情感的載體,創作的素材來源于自然,往往通過“觀物取象”、“以形寫神”的方式塑造意象、承載意趣。紫砂“田園清趣壺”通過提煉田園元素融入作品塑造意境,以儒為形,端莊大氣、溫潤靜篤;以道為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作品借景寓情,展示了廣闊的人文想象空間,折射出的是內心對閑靜和幽適的向往,表達了追求田園生活的愿望,能啟發人們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行思考,并引起內心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