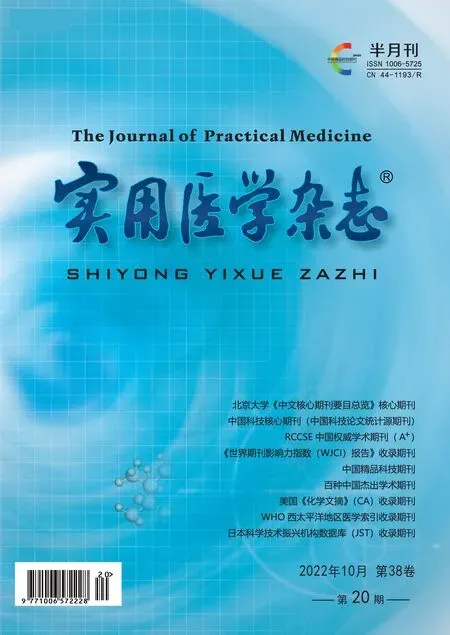吸入與靜脈全身麻醉對結直腸腫瘤患者圍術期T細胞分型的影響
李富裕 馮建國 王曉斌 白毅平
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瀘州 646000)
惡性腫瘤患者數量龐大,約2/3患者需要外科手術治療[1]。區域麻醉可改善惡性腫瘤患者總生存率[2],但大部分患者采用全身麻醉[3]。回顧性大樣本臨床研究存在爭議,有研究顯示靜脈全身麻醉患者術后死亡風險比吸入麻醉低,且有更高的遠期生存率[4-5];也有研究顯示兩種全身麻醉與惡性腫瘤術后總體、1年和5年生存率之間沒有關聯[3]。部分腫瘤患者還需多次手術[3],靜脈和吸入全身麻醉對遠期預后影響的差異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腫瘤的復發和轉移與機體T細胞功能缺陷密切相關,主要表現為T細胞耐受、無能或耗竭[6-7],主要是因為T細胞表面共抑制信號分子(programmedcell death protein 1,PD-1等)升高,共刺激信號分子(CD28等)不足。目前未見全麻藥物對T細胞分型及CD8+T細胞表面共抑制、共刺激信號分子變化的相關報道。因此,本研究采用流式細胞技術,探討靜脈及吸入麻醉藥對腫瘤患者圍術期T細胞分型及CD8+T細胞表面共刺激信號、共抑制信號表達的影響,為惡性腫瘤患者麻醉優化管理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該前瞻性、隨機、單盲研究經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KY2020170),中國臨床試驗中心注冊(ChiCTR2000039138),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納入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18~80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18 ~ 24 kg/m2,ASA(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分級(Ⅰ-Ⅲ)、全身麻醉>2 h,擇期腹腔鏡下行結直腸癌根治術患者64例。排除標準:(1)既往有藥物濫用史;(2)甲亢/減等免疫系統相關疾病;(3)急診手術;(4)圍術期輸血;(5)懷孕;(6)患者拒絕。中途退出標準:(1)術后1周內行二次手術;(2)患者要求退出。
1.2 分組處理麻醉誘導,靜脈給予咪達唑侖0.05mg/kg,舒芬太尼0.4μg/kg,異丙酚1.5~2.5mg/kg,順式阿曲庫銨0.2 mg/kg。氣管插管成功,連接麻醉機機械通氣。采用信封法,將患者隨機分為Sev組(n=32)和Pro組(n=32)。Sev組吸入0.7~1.3最低肺泡氣有效濃度(minimum alveolar concentration,MAC)七氟醚,Pro組靜脈泵入異丙酚100~200 μg/(kg·min);兩組均泵入瑞芬太尼0.1~0.2 μg/(kg·min)、順式阿曲庫銨1~3 μg/(kg·min)維持麻醉。麻醉藥物用量根據麻醉深度(Bispectral index,BIS)40~60增減。平均動脈壓低于術前基礎值30%,靜脈給予麻黃堿10 mg;心率低于50次/min,靜脈給予阿托品0.3 mg。術后病人靜脈自控鎮痛泵配置:舒芬太尼4 μg/kg+布托啡諾5 mg+格拉司瓊12 mg,生理鹽水稀釋到210 mL;背景輸注劑量3 mL/h,患者自控按壓劑量0.5 mL/15 min;術后患者靜息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4分,鎮痛泵藥物靜脈緩推5~10 mL至VAS≤3。所有患者由同一名主刀醫生實施手術及術后管理。
1.3 觀察指標記錄患者一般情況,包括年齡、性別、BMI、ASA分級、手術類型、腫瘤分期、術中麻醉用藥總量、手術時長、失血量,術后24、48、72 h VAS評分,術后并發癥及住院時間;麻醉誘導前(T1)、麻醉維持2 h(T2)、術后第3天(T3)以及術后第7天(T4),采集肘正中靜脈血采2 mL,肝素抗凝,室溫保存4 h以內,流式細胞術檢測CD4+T、CD8+T、CD28+CD8+T、PD-1+CD8+T、CD45RO+CD62L-CD8+T、CD45RO+CD62L+CD8+T含量。
1.4 統計學方法根據公式計算最小樣本量。α=0.05,Zα/2=Z0.025(雙側)=1.96,β=0.2,Zβ=Z0.2=0.842。基于前期 實驗結果 σ2=(2.872+2.432)/2=7.070 9,δ2=(30.23-32.76)2=6.400 9,計算得n1=n2=17.3;失訪率為10%,n1=n2=17.3/0.9=19.2。樣本含量最低為40例,每組20例。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24.0軟件。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比較。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情況本研究招募105例患者,排出41例。64例患者隨機分組,最終納入統計分析59例(Sev組30例,Pro組29例;圖1)。兩組患者一般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兩組患者T淋巴細胞亞群比較Sev組CD4+T、CD4+T/CD8+T在T2和T3時低于T1(圖2,F=10.010,P< 0.05;F=21.630,P< 0.05),PD-1+CD8+T、CD28+CD8+T 在 T2時低于 T1(圖3,F=4.383,P< 0.05;F=5.343,P< 0.05),CD45RO+CD62L-CD8+T在T3、T4時低于T1(F=10.700,P<0.05),CD45RO+CD62L+CD8+T在T2、T3時高于T1(圖4,F=2.674,P<0.05)。
Pro組 CD4+T在 T4時高于 T1(F=6.452,P<0.05),CD4+T/CD8+T在T2時低于T1(圖2,F=11.790,P<0.05),PD-1+CD8+T在T2時低于T1(F=38.000,P<0.05),CD28+CD8+T在T2、T3、T4時高于T1(圖3,F=2.063,P< 0.05),CD45RO+CD62L-CD8+T在T2時低于T1(F=0.686,P<0.05),CD45RO+CD62L+CD8+T在T3、T4時高于T1(圖4,F=16.540,P<0.05)。
Pro組 CD4+在 T2、T3和 T4時高于 Sev組(t=4.164,t=2.057,t=3.225;P< 0.05),CD4+T/CD8+T在 T2、T3時高于 Sev組(圖2,t=3.895,t=3.003;P< 0.05),PD-1+CD8+T在T2時低于Sev組(t=2.860,P<0.05),CD28+CD8+T在T2時高于Sev組(圖3,t=3.917,P< 0.05),CD45RO+CD62L-CD8+T在T3、T4時高于 Sev組(t=2.449,t=3.814;P< 0.05),CD45RO+CD62L+CD8+T在T3、T4時高于Sev組(圖4,t=2.231,t=3.356;P< 0.05)。
3 討論
全球每年新發結直腸癌兩百萬例,主要通過全麻腹腔鏡下手術切除治療[8-9]。既往有回顧性研究顯示了腫瘤患者使用靜脈全麻遠期生存高于吸入麻醉[4-5],本前瞻性研究探討吸入和靜脈全麻藥物對結直腸癌患者圍術期T細胞分型的影響,為惡性腫瘤患者麻醉優化管理提供依據。
CD4+T、CD8+T和CD4+T/CD8+T可評估患者免疫狀態[10-11]。CD4+T可通過輔助CD8+T細胞間接發揮抗腫瘤效應[10],CD8+T是直接殺傷腫瘤細胞的免疫效應細胞[11]。本研究中,麻醉2 h,兩組患者CD4+/CD8+T較麻醉前下降,吸入麻醉Sev組比靜脈麻醉Pro組降低更為明顯,Pro組術后第3天恢復至麻醉前水平,而Sev組是術后第7天;CD4+T也表現出相同趨勢,吸入麻醉患者麻醉2 h和術后第3天均明顯低于麻醉誘導前,而靜脈麻醉患者CD4+T并無明顯變化,而且在T2-4點都明顯高于吸入麻醉患者。CD4+T和CD4+T/CD8+T的變化,表明患者手術麻醉后存在免疫抑制,使用吸入麻醉患者免疫抑制更明顯。麻醉2 h,兩組患者CD8+T均明顯高于術前,可能與手術操作引起腫瘤細胞入血、刺激記憶T細胞增殖分化CD8+T相關[12],但該CD8+T可能存在明顯功能缺陷[13]。最近的吸入和靜脈麻醉對結直腸癌預后研究存在爭議,有研究顯示吸入比靜脈麻醉復發風險高[5,14],也有研究顯示兩種全身麻醉藥物與惡性腫瘤術后生存率沒有關聯[3],但局限于回顧性研究;而另一項兩種全身麻醉藥物對結直腸癌預后的前瞻性研究中,指出異丙酚通過囊泡microRNA途徑抑制腫瘤增殖轉移[15];也有研究顯示不同麻醉方法對腫瘤患者圍術期T淋巴細胞亞群存在明顯影響[16]。本臨床研究前瞻性探討了兩類麻醉藥物對結直腸癌患者圍術期一周T細胞影響,但對遠期預后有待于進一步隨訪。
CD8+T表面共刺激信號(CD28)能促進CD8+T細胞對入侵抗原作出免疫應答,共抑制信號(PD-1)則能防止過度免疫破壞正常結構。病理情況下,CD8+T細胞表面PD-1表達增加,CD28表達減少,導致CD8+T細胞不能對抗原刺激產生有效應答[6,17]。本研究中,在麻醉2 h,靜脈麻醉組CD8+T細胞表面CD28明顯高于吸入麻醉組,并且PD-1表達低于吸入麻醉組,說明靜脈麻醉可能對CD8+T細胞的抑制較吸入麻醉小。既往已有研究顯示CD8+T與結直腸癌患者疾病進展、早期復發預測和生存率相關[18-19],并且 CD28及PD-1的表達與CD8+T功能密切相關,還可能成為癌癥免疫治療的潛在靶點[20-21]。本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麻醉藥物影響結直腸癌患者圍手術期CD8+T,以及CD8+T表面共刺激信號(CD28)及共抑制信號(PD-1),并且發現使用異丙酚患者術后CD28不僅沒有像吸入麻醉藥組一樣降低,反而術后1周都高于手術前的基礎值,說明CD8+T功能是可能有增強。CD28升高的原因及臨床意義、CD8+T分泌功能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記憶T細胞可長時間存在于外周血液中,再次受抗原刺激時,記憶T細胞比初始T細胞能更快做出反應,參與免疫應答。循環中CD8+記憶T細胞可分為效應型(CD45RO+CD62L-)和中央型(CD45RO+CD62L+)[22]。效應型記憶 T細胞分泌大量的效應分子,包括IFN-γ和穿孔素;中央型記憶T細胞產生大量IL-2,增殖分化能力增強,并能分化為效應記憶型T細胞[23-24]。手術切除仍然是結直腸癌患者的最佳治療方式,但腫瘤細胞可能因手術,通過血管擴散轉移[24-26]。記憶T細胞圍術期對入血腫瘤細胞的快速應答,可能有利于減少腫瘤的復發[15]。本研究中,靜脈麻醉組在術后第3、7天,效應型和中央型記憶T細胞都明顯高于吸入麻醉組,甚至靜脈麻醉組中央型記憶T細胞還高于術前基礎值;說明腫瘤患者選用靜脈麻醉相對于吸入麻醉,可能有利于減少術后腫瘤復發。既往大樣本回顧性臨床研究[4-5]及最近一項前瞻性臨床研究[23]也提示了靜脈麻醉對癌癥患者預后更有益處,有研究也顯示記憶T淋巴細胞對腫瘤過繼免疫治療方案的改進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27]。本研究探討了靜脈麻醉對結直腸癌患者圍手術期記憶T淋巴細胞抑制比吸入麻醉輕,但納入患者遠期預后有待于進一步隨訪。
綜上所述,全身麻醉可能引起結直腸癌患者免疫抑制,但異丙酚靜脈麻醉抑制更輕;異丙酚靜脈麻醉對記憶T細胞抑制比七氟醚吸入麻醉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