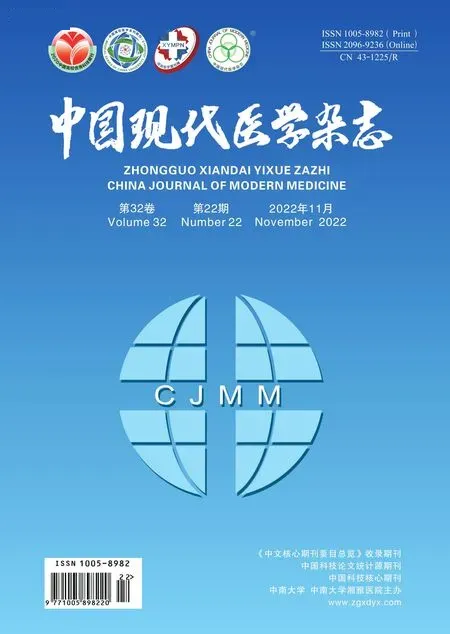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與孫氏手術治療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的療效比較*
潘虹,王智超,朱夢莉,韓瑞萍,蘇清,沈瀟
(武漢市第一醫院 急診醫學科,湖北 武漢 430022)
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主動脈內膜撕裂形成破口,血流沖入內膜和彈力層或彈力層與外膜之間,形成真、假腔,導致形成主動脈夾層[1]。急性期患者具有手術難度大、并發癥多以及死亡率高的特點,嚴重威脅患者身體健康[2]。臨床多采用孫氏手術進行治療,孫氏手術能夠創造性地在左頸總動脈與左鎖骨下動脈遠端之間橫斷,使吻合口上移,改變傳統象鼻手術在降主動脈遠端縫合,其療效受到國內外的肯定[3]。然而,該手術操作復雜,增加手術難度,延長手術時間,分支人工血管吻合時間較長,止血較困難,遠期栓塞仍然是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4-5]。近年來,隨著腔內技術和器材的改進,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治療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逐漸引起臨床研究者重視,該方法能夠進行弓部血管重建,擴大腔內修復的適應證,穩定血供以保證療效[6]。然而,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用于治療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效果與孫氏手術的差異尚不清楚。鑒于此,本研究選取武漢市第一醫院收治的82例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比較兩種手術方法的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 年3 月—2018 年3 月武漢市第一醫院收治的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82例。按照不同手術方法分為血管轉流術組和孫氏手術組,分別有39例和43例。納入標準:①符合2014 年歐洲心臟病學會發布的主動脈疾病診斷和治療指南診斷標準[7],并經CT 血管造影確診;②年齡26~62 歲;③首次發病;④無手術禁忌證。排除標準:①嚴重心臟疾病;②慢性腎功能損害;③對造影劑或麻醉過敏;④精神疾病;⑤惡性腫瘤。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孫氏手術組患者術前給予對癥支持治療,密切監測生命體征,術前采用靜脈吸入復合麻醉,采用胸部正中切開,游離主動脈弓及主要分支,于右心房和右腋動脈插管建立體外循環并降溫。阻斷升主動脈:根據主動脈瓣及夾層累及根部情形決定行根部替換或保留主動脈的竇部成形,病變重度累及冠狀動脈時,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病變重度累及主動脈瓣時,行瓣膜置換術,當鼻咽溫度降至22~25℃時,暫停體外循環,開放升主動脈,阻斷頭臂干、左鎖骨下動脈和左頸總動脈,行低流量選擇性腦灌注。探查夾層破口:遠端橫斷左鎖骨下動脈,降主動脈內置入覆膜支架,將支架象鼻血管近端與四分支人工血管遠端行端-端吻合。復溫:吻合頭臂血管左頸動脈,依次排氣,并行體外循環,止血、放置引流管,關胸結束手術,術后呼吸機支持,并給予血管活性藥物。
血管轉流術組患者術前準備和麻醉同孫氏手術組患者,對于錨定區在2 區的患者選取左頸部切口,游離出左頸總動脈,肝素化,部分阻斷左頸總動脈,切開左頸總動脈1 cm,滑線連續縫合,完成人工血管與左頸總動脈的端側吻合,排氣后完成人工血管與左鎖骨下動脈的端側吻合。錨定區在1 區的患者行右頸總動脈吻合,采用雙側頸部切口,人工血管與右頸總動脈行端側吻合,人工血管遠端與左鎖骨下動脈行端側吻合,完成頭臂血管轉流術,進行主動脈造影,再次確定破口位置和錨定區位置,并了解人工血管通暢情況,最后行常規縫合,術后操作同孫氏手術組。
1.3 觀察指標
①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②兩組患者術前和術后1 年左心室射血分數、升主動脈最大內徑和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③隨訪3年,觀察兩組患者腎衰竭、腦梗死、消化道出血、內漏、肺部感染等并發癥發生情況及生存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2.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比較用t檢驗或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以構成比或率(%)表示,比較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本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2.2 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比較
兩組患者體外循環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血管轉流術組手術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短于孫氏手術組,術中出血量少于孫氏手術組。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比較()
2.3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左心室射血分數、升主動脈最大內徑和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比較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左心室射血分數、升主動脈最大內徑和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血管轉流術組、孫氏手術組術前與術后1 年左心室射血分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297 和8.966,均P=0.000),術后較術前升高。血管轉流術組、孫氏手術組患者術前與術后1 年升主動脈最大內徑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3.775和16.280,均P=0.000),血管轉流術組、孫氏手術組患者術前與術后1 年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533 和5.317,均P=0.000),術后均較術前縮小。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左心室射血分數、升主動脈最大內徑和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比較()
2.4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
兩組患者并發癥總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82,P=0.043),血管轉流術組低于孫氏手術組。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例(%)
2.5 兩組患者生存情況比較
隨訪3 年,孫氏手術組有1例患者于術后31 個月因心力衰竭死亡,血管轉流術組患者無死亡,其他患者均正常生活。
3 討論
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是一種心外科危重疾病,高血壓是重要誘因,高壓力血流對主動脈管壁具有沖擊作用,當血管壁長期受到高壓沖擊變得脆弱時可能會發生撕裂[8-9]。此外,馬方綜合征、動脈瘤等主動脈自身結果存在缺陷的患者易發生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10]。該病具有發病突然、病情兇險、進展迅速的特點,臨床多采用手術進行治療,其中孫氏手術是近年來治療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金標準,然而,該手術方法吻合口較多,手術操作復雜[11-12]。因此,急需尋找更佳合適的手術治療方法,以提高臨床療效。
本研究結果顯示,血管轉流術組患者手術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短于孫氏手術組,術中出血量少于孫氏手術組,兩組患者術后1 年左心室射血分數均較術前升高,升主動脈最大內徑和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均較術前縮小,兩組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數、升主動脈最大內徑和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比較無差異,提示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用于治療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能夠降低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與孫氏手術療效相當。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容易實施,無需開胸,避免主動脈吻合口出血、低溫帶來的凝血障礙,降低腹腔臟器缺血等潛在風險[13]。此外,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能夠盡可能地游離至左鎖骨下動脈近端,在椎動脈下緣進行結扎,閉合左鎖骨下動脈,達到有效閉合左鎖骨下動脈的目的,有效避免血液反流入降主動脈[14]。本研究結果顯示,血管轉流術組患者并發癥總發生率低于孫氏手術組,隨訪3 年,孫氏手術組僅有1例患者于術后31 個月因心力衰竭死亡,血管轉流術組患者無死亡,說明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用于治療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能夠降低并發癥發生率,安全可靠。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通過縫扎左側頸動脈和封堵鎖骨下動脈,保證人工血管兩端的壓力差,減少發生腦梗死、血栓等并發癥[15]。然而,本研究病例選取有限,研究結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仍需擴大樣本進行多中心研究,進一步證實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用于治療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的效果。
綜上所述,主動脈頭臂血管轉流術治療急性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能夠減少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選擇性腦灌注時間,且并發癥發生率較低,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