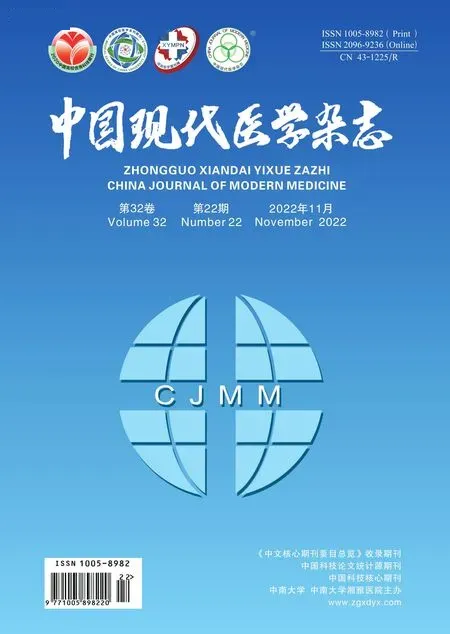導絲引導法經皮經肝穿刺膽道引流術治療急性梗阻性化膿性膽管炎的臨床療效*
劉紹華,張裕桂,肖振亮
(萍鄉市人民醫院 普外科,江西 萍鄉 337000)
急性梗阻性化膿性膽管炎(acute obstructive suppurative cholangitis,AOSC)是由于細菌感染或者膽管梗阻引起膽管內壓升高,使肝臟的膽血屏障受損,細菌進入血液循環引發的以肝臟損傷為主的全身性感染[1-2]。臨床上AOSC 患者表現為高熱寒戰、右上腹疼痛感強烈、黃疸等。其發病較快、病程短,如治療不及時可能引起多器官衰竭或膿毒癥[3-4]。AOSC 的傳統治療方法是手術開腹引流減壓,但風險較大,容易引起繼發感染,且手術的病死率較高[5]。隨著AOSC 治療手段的不斷發展,經皮經肝穿刺膽道引流術(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 and drainage,PTBD)逐漸得到推廣,PTBD 是在醫學影像設備的引導下,對膽管堵塞部位進行疏通并引流的手術,具有創口小、損傷低、引流減壓較有效的特點[6]。傳統的PTBD 手術是在X射線下注入造影劑來顯影,以引導外鞘管進入到膽管深處,但術后易加重膽管炎[7]。導絲引導法是利用導絲將外鞘管引導至膽管深處直接進行引流減壓的手術,目前鮮有研究其對患者術后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回顧性分析萍鄉市人民醫院接收的87例OSC 患者資料,觀察傳統PTBD 與導絲引導PTBD治療AOSC 患者的臨床療效,以期為臨床治療AOSC 提供數據支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8 年12 月—2021 年12 月萍鄉市人民醫院收治的87例AOSC 患者的臨床資料。按照置管方式分為傳統穿刺組與導絲引導組,分別有48例和39例。其中,傳統穿刺組男性27例,女性21例;年齡34~55 歲,平均(44.17±3.58)歲;導絲引導組男性21例,女性18例;年齡35~55 歲,平均(43.35±3.08)歲。納入標準:①符合《急性膽道系統感染的診斷和治療指南(2021 版)》[8]中的診斷標準,a.伴有急性腹痛、寒戰高熱、急性黃疸、嚴重腹膜刺激征,b.白細胞計數>2×1010/L,c.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IL)、非結合型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DBIL)水平上升,d.經過影像學檢查確認為肝內外膽管擴張;②口腔內鏡或鼻膽管手術失敗;③消化道狹窄不能進行口腔內鏡引流;④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年齡<18 歲;②曾服用影響本研究中檢測的細胞因子的藥物,如孟魯司特鈉等;③凝血功能障礙或血液系統疾病;④孕婦或哺乳期;⑤自身免疫系統疾病;⑥有慢性器質性病變。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其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兩組年齡、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傳統PTBD具體操作如下:10 F 套管穿刺針(外徑1.0 mm)刺入患者膽道,將針芯緩慢退出,保留外鞘管,確認有膽汁被引出;在膽道內注入造影劑顯影已確定梗阻位置,送入導絲,將外鞘管沿導絲送達膽管深處,緩慢退出導絲,通過外鞘管送入硬導絲,緩慢退出外鞘管,順導絲置入8 F 引流管,接引流袋并固定。術中有2例患者由于呼吸幅度過大,導致針芯退出后外鞘管離開膽道,給予補救后進行二次操作。
1.2.2 導絲引導法PTBD具體操作如下:10 F 套管穿刺針(外徑1.0 mm)刺入患者膽道,將針芯緩慢退出,保留外鞘管,確認有膽汁被引出;沿外鞘管送入導絲達膽管深處,再將外鞘管跟進至膽管深處,緩慢退出導絲,抽取部分膽汁進行減壓,在膽道內注射造影劑顯影,通過外鞘管送入硬導絲,緩慢退出外鞘管,順導絲置入8 F 引流管,接引流袋并固定。患者均置入成功。
兩組患者術后24 h 絕對臥床休息,禁水、禁食6 h,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注意保持引流管通暢,謹防彎折,如發現引流袋中出現紅色血液,及時通知醫生進行造影,確定出血位置再詳細確定治療方案,治療后再次造影以確定出血是否停止。
1.3 觀察指標
1.3.1 圍術期指標觀察兩組的引流手術時間、一次性置管成功率以及每日引流量。
1.3.2 肝功能及膽紅素變化檢測患者引流術前與引流術后1 周的空腹血清TBIL、DBIL 與谷丙轉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其中TBIL 與DBIL 采用重氮法檢測(檢測試劑盒購于深圳雷杜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ALT 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檢測試劑盒購于上海澤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3 細胞因子檢測檢測患者引流術前和引流術后3 d 血清與膽汁中白細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IL-4、IL-10、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以上細胞因子均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試劑盒購于上海蔚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4 并發癥統計兩組患者術后膽道出血、膽漏、急性重癥膽管炎、膿毒癥等并發癥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4.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比較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圍術期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引流手術時間、一次性置入成功、每日引流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AOSC患者圍術期情況比較
2.2 兩組患者引流術前后血清TBIL、DBIL 和ALT的差值比較
兩組患者引流術前后血清TBIL、DBIL 和ALT的差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引流前后TBIL、DBIL、ALT的差值比較()

表2 兩組患者引流前后TBIL、DBIL、ALT的差值比較()
2.3 兩組患者引流術前后血清及膽汁中IL-1、IL-4、IL-10和TNF-α的差值比較
兩組患者引流術前后血清及膽汁中IL-1、IL-4、IL-10 和TNF-α 的差值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導絲引導組細胞因子上升或下降程度大于傳統穿刺組。見表3、4。
表3 兩組患者引流前后血清IL-1、IL-4、IL-10與TNF-α的差值比較(pg/mL,)

表3 兩組患者引流前后血清IL-1、IL-4、IL-10與TNF-α的差值比較(pg/mL,)
2.4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
兩組患者膽道出血、膽漏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急性重癥膽管炎、膿毒癥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傳統穿刺組高于導絲引導組。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例(%)
表4 兩組患者引流前后膽汁IL-1、IL-4、IL-10與TNF-α的差值比較()

表4 兩組患者引流前后膽汁IL-1、IL-4、IL-10與TNF-α的差值比較()
3 討論
AOSC 是由膽管梗阻引起的全身性感染,大多數患者在抗菌治療的同時還要進行及時有效的膽管引流減壓[9]。由于AOSC 的發病較快,因此在患者發病早期進行合適與及時的治療十分重要,不僅可以避免患者的多器官衰竭,還可以降低該病的病死率[10-11]。傳統手術治療需要切開膽管進行引流減壓,創口較大,不僅術后恢復較慢,還容易引發繼發感染[12]。PTBD 是目前膽道梗阻中應用較廣泛的介入性治療技術之一,需要在醫學影像的引導下將外鞘管置入膽管深處,不同的外鞘管置入方式可能對患者預后及并發癥影響不同[13-14]。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AOCS 患者手術時間、一次性置入成功、每日引流量比較無差異,提示兩種置入方式的成熟性均較高,可以用于治療AOSC。肝臟中存在大量ALT,當肝功能受損時,ALT 會被釋放到血液中,因此可以作為肝功能的檢測指標之一[15]。TBIL 是指直接膽紅素和間接膽紅素的總和,主要由肝臟進行代謝,當膽紅素的代謝受阻則會引起黃疸[16]。DBIL 是未與葡萄糖醛酸結合的膽紅素,其水平升高會導致肝細胞性黃疸[17]。本研究結果顯示,引流術后1 周,兩組患者的TBIL、DBIL、ALY 水平均較引流術前降低,提示兩種置入方法均可較好地治療AOSC,恢復患者肝功能。AOSC 主要由于細菌、毒素導致的全身性感染,而內毒素可以刺激患者機體產生大量的細胞因子,這些細胞因子在介導全身炎癥反應的同時,也在膽汁蓄積中起到重要作用[18-19]。本研究中,引流手術3 d 后,導絲引導組患者血清與膽汁中IL-1 與IL-1 與TNF-α 水平高于傳統穿刺組,IL-4 與IL-10 高于傳統穿刺組,提示導絲引導法可以較好地降低術后患者體內炎癥反應。IL-4 與IL-10 是抗炎因子,IL-1 與TNF-α 屬于促炎因子,兩類細胞因子的平衡與機體炎癥狀態緊密相關,一旦兩者的平衡被破壞,除機體的炎癥加重外還有可能引發膿毒癥[20-21]。同時本研究結果還觀察到,兩組患者膽道出血、膽漏情況無差異。但傳統穿刺組患者發生急性重癥膽管炎與膿毒癥的情況多于導絲引導組。這一現象的發生可能由于傳統穿刺組在穿刺后立即在膽道中注入造影劑,使原本壓力較高的膽道壓力更高,增大了細菌與內毒素進入血液循環的概率,導致機體發生炎癥,破壞促炎因子與抗炎因子的平衡[22]。而導絲引導法在術中利用導絲引導外鞘管進入膽管深處,先吸出一部分膽汁降低膽管壓力后,再加入少量造影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術中由于膽管壓力持續升高引發的繼發感染,降低急性重癥膽管炎與膿毒癥的發生率。
綜上所述,傳統PTBD 與導絲引導法PTBD 的一次性置入率相當,且均可較好地改善肝功能與降低膽紅素水平,但導絲引導法PTBD 可以有效降低炎癥因子水平,降低術后急性重癥膽管炎與膿毒癥的發生率,在廣泛應用于治療AOSC 患者中具有一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