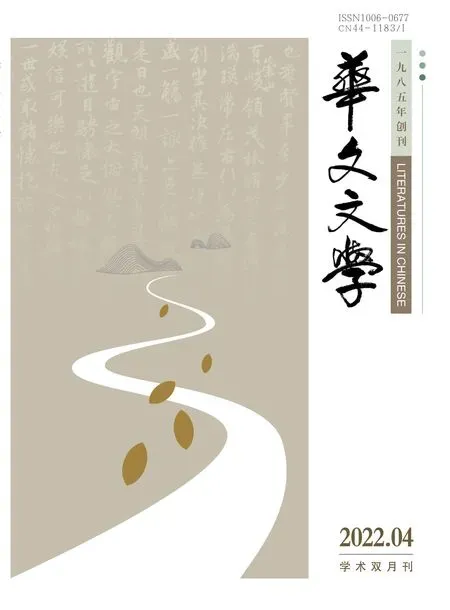伍慧明傳記小說的幽靈批評
汪順來
伍慧明(Fae Myenne Ng, 1956-)出生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的第一代華人移民家庭,是繼黃玉雪、湯亭亭、譚恩美等之后活躍于當代美國文壇的華裔女作家,也是位敢于直面華人移民歷史的傳記小說家。她的傳記小說《骨》(Bone, 1993)和《望巖》(Steer Toward the Rock,2008 或譯為《向我來》)基于自己的家庭經歷和華人移民群體的歷史記憶,將傳記的真實和小說的虛構糅合到一起,編織“一部由個人、家庭、民族的歷史和政治問題構建的民族寓言”①,重寫被美國官方歷史掩藏或抹殺的真實故事。兩部小說具有典型的自傳體敘事特征,都是以唐人街華裔“契紙家庭”的日常生活為題材,揭示移民法案給華裔家庭造成的精神創傷,從而批判美國移民政策的種族主義本質。在美國種族主義政治制度下,“契紙兒子”、“契紙父親”、“契紙家庭”、“坦白計劃”等已經成為早期華人移民心中難以言說的痛和不可告人的秘密,這些秘密如幽靈般地縈繞在他們心頭,揮之不去卻又無法忘懷,逐漸沉淀為他們集體無意識深處的創傷記憶。本文基于幽靈批評的思想和觀點,以伍慧明傳記小說《骨》和《望巖》中的幽靈人物為切入點,剖析他們“怪異”的心理空間,揭示美國主流文化霸權下華人移民的幽靈身份。
一、幽靈批評之“幽靈意象”和“幽靈性質”
幽靈批評并不成理論體系或流派,僅是一種具有幽靈性質的批評,具有神秘性和不確定性。何謂幽靈性質?就像海德格爾筆下“在刪除下書寫”那樣,是一種包含存在與不在、有形且無形、刪除與痕跡的矛盾體。德里達說:“一部名著如同一個鬼魂,時刻都在運動之中。”②根據德里達的觀點,文學文本具有幽靈性質,變化無常且捉摸不定。英國學者沃爾弗雷斯認為:“當代許多文學批評都是建立在顯性的或隱性的文學‘幽靈’之上,即形成于文學的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神秘糾結中。”③可見幽靈批評是以剖析文學文本中的幽靈意象為出發點,進而探索文本潛藏的隱秘因素。
(一)形形色色的幽靈意象
談到幽靈意象,我們自然會想到“鬼”、“靈魂”或“魂靈”、“精神”或“精靈”等令人恐懼的東西,它們是人死后脫離肉體遁入另一個世界的變形。荷馬史詩《奧德賽》、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中都有幽靈意象的出現,體現了文學處理和揭示秘密的怪異手法。這種手法的怪異或高明之處在于幽靈意象的選擇,恰當的幽靈意象能更好地揭示秘密和推動情節的發展。
《奧德賽》中,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在返鄉途中遭遇危險之時,首先得到預言師特瑞西阿斯的靈魂的指點:“你不用擔心你的船只沒有人引領……北風會撫送船只航行。”④接著又受到好友埃爾佩諾爾魂靈的懇求和母親安提克勒婭魂靈的指引,母親告訴他家中的變故和自己的死因:“須知我就是這樣亡故,命運降臨……是因為思念你和渴望,你的智慧和愛撫奪走了甜蜜的生命。”⑤荷馬選擇特瑞西阿斯的幽靈意象為奧德修斯回鄉指明方向,盡管路途兇險,但終會平安到家;又以其好友和母親的幽靈意象昭示奧德修斯的艱難處境,戰爭奪走了好友,命運帶走了母親,他得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孤獨前行。但丁在《神曲》中選擇詩人維吉爾和情人貝雅特麗齊的幽靈意象,表達自己對理性和愛情的信仰。前者指引幻游者但丁游歷地獄和煉獄,看盡了教會統治的罪惡;后者指引但丁步入天堂,看到了人文主義思想的曙光。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將幽靈意象搬上了舞臺,開辟了幽靈戲劇的先河。劇中亡父的靈魂出場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對王子哈姆雷特透露了一個謀殺的秘密,并賦予王子復仇和扭轉時局的使命。可以斷言,“沒有哈姆雷特父親的幽靈出現,哈姆雷特的性格和行動便均失去了依據和基礎。”⑥從此,歐洲文壇徘徊著形形色色的幽靈意象,尤其是18 世紀的哥特小說大肆描寫鬼魂、惡魔、幽靈等,揭示人性中的非理性一面,營造神秘恐怖的氣氛。到了20 世紀的現代和后現代文學,幽靈意象從后殖民歷史話語開始,蔓延到弗洛伊德主義的“怪異”心理和德里達的解構視域。
(二)歷史的幽靈性質
幽靈意象是隱約存在于文本內的幻象,在訴說的同時又保留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德里達說:“一切都從幽靈的幻象開始,確切地說從等待幻象的出現開始。這樣的等待在剎那間是急躁不安、焦慮重重,又是令人恍惚的……幽靈將會出現。”⑦幽靈是在焦慮的等待中忽現,這種等待是痛苦的煎熬,是對過去事件和歷史記憶的再回首。
對于這種感受,伍慧明的傳記小說《骨》將“契紙兒子”的復雜心情表現得尤其到位,再現了華人移民那段難以言說的歷史。“契紙兒子”利昂一直生活在焦慮中,他為自己沒能兌現將“契紙父親”的遺骨帶回中國而悔責不已:“利昂一直擔心那些遺骨,擔心會發生什么事情——比如失業、失去外賣店的競標、失去翁梁兩家合開的洗衣店。利昂甚至怨恨那些遺骨,但最終它們還是留在了這里。”⑧利昂的擔心源自內心痛苦的等待,等待“契紙父親”幽靈的出現,等待它報復自己的不守諾言;同時他怨恨自己的無能,不能讓“父親”魂歸故土。小說中的遺骨象征著華人移民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幽靈,它隱含“契紙父親”和“契紙兒子”間承下的諾言。這種諾言好比詛咒,對失信者的報復,對美國種族主義制度的控訴。因此,遺骨里藏著歷史,那段早期華人移民在美國遭受的屈辱歷史。
根據幽靈批評的觀點,文本中的歷史并非按時間順序線性發展,而是已逝的過去對現在的不斷侵擾。因此,歷史就是那幽靈,或者說是幽靈出沒的場所。沃爾弗雷斯說:“文本中的幽靈既不能令人感到保存了歷史,也不能讓人覺得擺脫了往昔。”⑨基于此觀點,小說敘述歷史時,離不開幽靈的參與,因為幽靈復活了過去,從而方便了生者與死者的對話,使得歷史被生動地呈現給讀者,同時敘述者對于幽靈充滿著疑慮和困惑,留下許多不確定性。
二、華人移民的幽靈意象
傳記小說屬于傳記文學,融忠于事實和歷史的傳記與基于虛構和想象的小說為一體,體現了傳記的文學性。王成軍認為,紀實傳真是自傳(傳記)文學作家追求的最高敘事倫理⑩。但是傳記小說顯然逾越了這一界限,更加注重人物個性的塑造,從而偏離了“真實”。為了展現早期華人移民的創傷歷程,伍慧明的傳記小說,確切地說是自傳體小說,以華裔家庭為單位,將自我敘述和敘述他者相結合,再現華人移民的悲愴歷史。在歷史敘述中,伍慧明跳出了傳記小說的傳統修辭模式,將傳記虛構成傳奇,書寫人物的幽靈意象,彰顯特殊語境下人性的扭曲。
(一)“父親”的幽靈意象
伍慧明出生于“契紙家庭”,其父曾花4000 美元購買“紙生子”的名額移民到美國。《骨》是伍慧明的處女作,一部典型的華裔自傳體小說,圍繞生活在舊金山的移民家庭梁家的生活經歷,突出表現了第一代華人移民與其后代間的恩怨,以及他們在同化和排斥之間的痛苦掙扎。小說的名稱與內容中“骨”的意象相呼應,暗示中國文化傳統對早期華人移民的影響,即使尸體腐爛了,但是遺骨尚存,會永遠銘記歷史。伍慧明借家庭傳記的外殼,充分展現了美國華裔作家的想象力,將歷史記憶的“碎片”粘合起來,形成融“家族故事、歷史事實與文學想象交結在一起,展現出一幅幅現實與夢幻相交疊的、充滿神秘主義氣息的圖景。”[11]美國華裔作家擅長鬼神、魂靈等意象的書寫,將傳記小說塑造成傳奇故事,如湯亭亭在《女勇士》《中國佬》,譚恩美在《接骨師之女》中編織了一個個虛無縹緲的鬼魂世界和異域色彩的中國。但是伍慧明并不囿于鬼故事的講述,而是以“遺骨”為證,重述那段被美國主流社會有意忽略的歷史。
伍慧明對美國華人移民史上“契紙兒子”或“紙生子”(paper son)現象非常關注,揭示“紙生子”概念的悖論性和荒謬性。“紙生子”是移民潮、“黃禍論”、舊金山大地震等共同作用的結果,是19世紀后期美國移民政策變化造成的歷史現象,它是“客體的‘紙’和家庭倫理身份的‘子’之間的結合,是虛假性和真實性的疊加。”[12]為了映襯“契紙兒子”的尷尬身份,作者挖出了被“紙”埋藏的“契紙父親”,盡管“父親”早已死去,但他的幽靈片刻不離“契紙兒子”,成為無法擺脫的痛苦記憶。《骨》中利昂是個“契紙兒子”,以5000 美元買下進入美國的“通行證”,并承諾將梁爺爺(梁海昆或阿福·梁)的遺骨帶回中國,從此梁阿福就成了利昂的“契紙父親”。由于美國《排華法案》的實施,梁爺爺的遺骨未能如愿地返回祖國,無法實現葉落歸根。因此,利昂一想到“遺骨”的存在,就有負罪感,擔心“父親”的幽靈會報復自己的不誠信,會給全家帶來壞運氣。利昂時常把自己的失業、生意的失敗和女兒安娜的自殺與“父親”的幽靈聯系到一起,把所有的不幸歸結為幽靈的報應。幽靈就像影子一樣,并不占據實際的空間,但是它早已填滿了生者的心理空間,成了無法言說的秘密。
(二)母親的幽靈意象
《望巖》是伍慧明創作的另一部自傳體小說,講述“契紙兒子”杰克的身份轉換歷程,“為沉默的第一代華裔男性賦予語言的力量。”[13]杰克與利昂一樣,游走在“倫理身份的錯位、缺失與找尋”[14]中,體現了美國早期華人移民的悲慘遭遇,夫妻不和、代際緊張、身份混亂使得他們成為主流社會的隱身人和失語者。為此,利昂選擇了說謊,杰克掙扎于“坦白”。面對《排華法案》的最后階段——“坦白計劃”,杰克陷入了進退兩難之中。要么供出他人,良心上受譴責,還可能招致報復;要么被他人供出,從而失去在美國的公民身份和居留權,可能被遣返回國。“坦白計劃”是美國政府在1956-1965年期間針對華人群體實施的種族歧視政策,是破壞華裔家庭、摧殘華人身心的惡毒計劃。其最終目的是剝離華人移民與祖國的聯系,以公民身份為誘餌,加快華人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和被美國文化同化的進程。杰克是伍慧明根據自己父親的經歷和文學想象而塑造出來的鮮活的“契紙兒子”形象,“展示了一個華人從此岸到彼岸的人生歷程。”[15]對一個“契紙兒子”來說,從痛苦的此岸到幸福的彼岸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旅程,跋涉者需要勇氣和力量。
小說名《望巖》(Steer Toward the Rock)很有詩意,形象地展現了華人移民杰克的“可望不可即”的人生目標。當杰克遭遇險境而迷失自我時,母親的幽靈意象顯現,指引他勇敢地戰勝恐懼:“你要相信這塊巖石,媽媽告訴他。要騰空你的心,把恐懼在巖石上摔碎。就像河神一樣,你要向自然低頭,要面對恐懼,相信恐懼,向那塊巖石駛去(向我來)。”[16]巖石就是生活的目標,是心中堅強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得到母親幽靈的指引,杰克終于放下心理包袱,勇敢地走出生活的陰影,找到了做人的尊嚴。
三、華人移民的“怪異”心理
伍慧明的傳記小說,非常注重人物心理刻畫,生動地再現了種族主義移民政策對華人個人和社區造成的精神創傷。趙白生認為:“傳記再現的對象不是純粹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17]傳記小說應忠于傳記的真實,但是小說的虛構往往突破了史實的條框限制,突顯其藝術性,也透露出傳記小說家的創作才能。為了彰顯美國種族主義法案對華人的傷害,伍慧明將現實與想象并置,展現高壓政策下華人移民扭曲的心理,塑造了一個個活著的“幽靈”。
(一)行為異常的利昂
《骨》的敘述者是大女兒萊拉,她對繼父利昂的描述非常仔細,勾勒出一個“紙生子”的怪異形象,一個簡直如幽靈般的怪物。“怪異”(Uncanny)與幽靈性質有相似之處,表現為異質個體,不同于正常人。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所指出的那樣,“怪異”是人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狀態,存在著“陌生和生疏感不斷侵擾人對周圍熟知和安全的心境,或者叫壓抑復現。”[18]這種體驗是潛在的無意識的感受,是某特定時空范圍內創傷如幽靈般的再現。
利昂的行為非常怪異,其怪癖之一是喜歡與廢物打交道,他制造出一堆稀奇古怪的東西,還收藏廢物,如一摞摞快餐盒、錫紙盒、裝滿番茄醬和糖袋的塑料袋、寫著紅色字母的白色罐頭盒,還有政府發放的蔬菜:切成片的甜菜、表面光滑的綠豆和南瓜[19]。利昂的怪癖行為與第一代華人移民在美國的遭遇密切相關,面對饑餓和種族歧視的雙重打擊,他們不得不忍受和壓抑內心的苦悶。在美國,一切可能成為證據,一切證據可能成為廢紙。因此利昂得出結論:“在這個國家,紙張比血液還貴。”[20]因為那些紙張和廢物證明了利昂在美國的時間,也證實了他對生活的忍耐。由于求職時曾被無數次拒絕,利昂養成了拼命干活的怪癖。他害怕失業,一直在尋找新的工作機會,來證明自己是一個有用的苦力。面對喪女的苦痛和生活的壓力,他選擇了不停地勞作,試圖以勞累忘卻創傷記憶。他不是在時間中度日,而是在汗水中奔命。他認為生命就是工作,而死亡卻是一場夢[21]。殘酷的社會現實扭曲了利昂的心理,將他變成了工作機器和人性麻木的另類。
(二)性格怪癖的杰克
心理分析學說中的怪異理論得到德里達、拉康、克里斯蒂娃等的發展,被廣泛用于后殖民文學、族裔文學、離散文學等,旨為闡釋內外交困的情境下人物所遭受的精神創傷。這種創傷“是對一個或多個重要事件的反應,時間上往往滯后,表現為重復、幻想、夢幻或事件促成的思想和行為等形式。”[22]精神創傷是一系列不平常的生活經歷對一個人心理的長期摧殘,結果造成思想混亂、性格怪異的他者形象。他者的人性由于受到侵擾和否定,成為似人非人的幽靈,因為“幽靈是人又非人,它既衍生于生前的人,卻又不是那個人,而是那個人的‘他者’;它活著卻又死了,是一個活著的死人。”[23]
《望巖》中杰克就是一個怪異的他者形象,或者說是一個活著的“幽靈”。小說以杰克·滿·司徒的坦白開始,講述了一個“紙生子”在美國經受的孤獨、恐怖的生活經歷。杰克是司徒一通花410 美元購買的“兒子”,取中文名“有信”,意為“言而有信”,作為對父子關系的一種承諾,然而實質上的金錢交易甚于父子情感。杰克為進入美國欠下了司徒一通4000 美元的債務,從此他成了司徒的債務奴隸。為了償還債務、贖回自由,杰克只有拼命地干活,卻怎么也還不完日積月累的利息。杰克看不到希望,孤獨的人生讓他覺得“自己像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只蝙蝠”[24],一直在盲目地突圍,最終還是四處碰壁、慘不忍睹的結局。更尷尬的是情感孤獨的困擾,他無權選擇感情,無法組織家庭。小說的一開始就將杰克拋入了情感的漩渦中:“我愛的女人不愛我,我娶的女人不是我的女人。張伊琳在法律上是我的妻子,但事實上她是司徒一通的女人。”[25]杰克與司徒訂立的契約內容非常荒誕,杰克與司徒的小妾張伊琳名義上的夫妻關系成為他合法入境的幌子,而他與喬伊斯·關之間只能止步于愛情,無法通過結婚組建家庭,以致于杰克與喬伊斯的情感日漸疏遠,都變成了孤獨的幽靈。
伍慧明不僅對像杰克一樣的“紙生子”的遭遇充滿了同情,而且非常關注華裔女性的不幸。小說中喬伊斯不敢結婚,女兒維達不愿生育,表明華裔女性遭受家庭創傷后的痛苦抉擇。作者以華裔女性的消極選擇控訴了美國移民政策對華人群體的精神傷害,尤其是對女性的迫害。杰克的怪異性格與“坦白計劃”營造的恐怖氛圍密切相關。“坦白計劃”是美國移民局對華人非法移民的一次身份大清洗,將華人移民拖入一個難以自拔的陷阱。華人間相互猜忌、彼此不信任扭曲了美好的人性,導致華人社區的全面恐慌。杰克成了另一個哈姆雷特,徘徊在“坦白還是不坦白”的困境中。因為渴望愛情和公民身份,杰克坦白過自己的歷史,卻并未得到移民局的原諒,也沒贏得想要的愛情,而被司徒的手下砍去一只手臂。從此,他活在自己幽閉的世界里。沉默寡言成了杰克的標記,女兒維達善解人意地說:“沉默的父親是安全的父親。”[26]在麥卡錫主義籠罩美國的時期,華人移民不得不將記憶封存,將思想禁閉,以免惹禍。種族主義移民法案正在將唐人街一步步變成可怕的“單身漢社會”和滅絕人倫的地獄,到處游蕩著孤獨的幽靈。
四、華人移民的幽靈身份
族裔文學離不開對身份問題的探討,身份和身份認同充斥于族裔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整個過程。華裔美國文學始于傳記文學,最早的華裔作品多是自傳或自傳體小說,如容閎的《西學東漸》(1910)、黃玉雪的《華女阿五》(1950)、湯亭亭的《女勇士》(1975)、譚恩美的《喜福會》(1989)、伍慧明的《骨》和《望巖》等。盡管華裔傳記文學的真實性引發爭議,但是它對身份塑造的藝術性是不容置疑的。趙白生認為,自傳作家往往從特定的身份出發再現自我,因此自傳是“作者身份的寓言。”[27]自傳體小說融合小說與自傳的特點,展現經過修辭處理的自我,旨在藝術般地表現身份的特殊性。華裔美國傳記文學“混合了美國官方的權威記憶(歷史)和華裔個人的歷史(自傳、回憶錄、日記等)”[28],近乎理想地呈現了美國華裔的動態自我,一個難以判定的幽靈身份。
(一)作為“他者”的幽靈身份
“他者”是與“自我、主體、同者”相對立的概念,可追溯到柏拉圖哲學關于同者與他者的定義,指一切從屬的、邊緣的、次要的低級事物。“他者”泛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和事物,也即是“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現,可看見還是不可看見,可感知還是不可感知,都是他者。”[29]盡管自我意識的構建離不開他者,但是二者的對立關系決定了他者的地位。杜波依斯從美國黑人身上找到了“他者”的屬性:“一種通過別人的目光看待自己,以周圍充滿輕蔑和同情的人群來衡量自己靈魂的感覺。每個黑人都具有二重性(twoness)——既是美國人,又是黑人;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種無法調和的斗爭;一個黑色軀體中的兩個敵對思想。”[30]在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眼中,黑人就是“他者”,一種靈魂被刺痛的感覺。黑人的雙重身份是其矛盾思想的根源,因為美國的種族主義政策決定了黑人無權決定自己的身份。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4)的名作《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1952)形象地再現了美國黑人的身份選擇。為了逃避種族迫害,主人公不得不隱藏到地下,成為白人眼中“看不見的人”,或者一個行跡不定的幽靈。
同為美國少數族裔,美國華裔的身份訴求與非裔美國黑人相同。自19 世紀中期開始,迫于饑荒和戰爭,大批華人移民美國做苦工。第一代華人移民參與了修建貫穿美國大陸的鐵路、開發加利福尼亞礦產、開墾夏威夷農場等,足跡遍布美國各地,事實證明他們是真正的美國建設者,應該享有公民身份。但是這些工程一結束,美國就開始揮舞種族主義的大棒,讓華人移民失業,遭受被驅趕、被迫害的厄運。作為第二代移民的“紙生子”是《排華法案》(1882)催生的產物,由于不是“土生子”,他們的身份很尷尬,既不是美國公民,又不是華人移民的真正后代。他們舉債購買的假身份隨時有被揭穿的風險,因此他們設法隱藏自己,成為美國社會里“看不見的他者”。
《骨》中的利昂一直生活在焦慮和謊言中。他擔憂自己會失業,擔憂“紙生子”的身份被曝光;他不得不說謊,自天使島入境開始,就以謊言來坐實自己的身份,后來他收集了一堆舊文件,包括求職時“我們不需要你”的拒絕信,用這些廢紙來證明自己在美國時間和為美國的付出。但是美國社會殘酷的現實總站在他的對立面,他不停地工作,不斷地失業,一直在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同時,婚姻遇挫、女兒自殺、生意破產讓他不堪重負,最后他簽約到一艘開往澳大利亞的貨輪上工作,以漂泊大海作為總結。
利昂的人生經歷是作者伍慧明對以父親為代表的第二代移民經歷的重寫,是對“紙生子”身份的重新定義。“紙生子”為美國奉獻了大半生,卻始終被質疑身份的合法性,是美國社會的“他者”。他們一直在尋求身份認同,卻找不到答案,陷入痛苦的身份悖論中:我是美國人嗎?可是我沒有入籍證明。我是中國人嗎?可是我不能回到中國。我兩者都不是或兩者都是。利昂有同樣的身份困惑,為了在美國生存,他只有通過自我否定和編造謊言來消極地回應美國社會,但是他始終“擺脫不了身份悖論的困境,成為飄在美國的幽靈。”[31]
(二)作為“面具”的幽靈身份
“面具”(mask)原指戲劇表演時的演員或狂歡節上的民眾遮面的偽裝物,后轉義為“欺騙、偽裝”。英國戲劇家王爾德說:“一個人講話時,他最不像自己;給他一副面具,他就告訴你真相。”[32]王爾德指出了人的兩面性,每個人都披著偽裝,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現不同的自我。愛爾蘭詩人、戲劇家葉芝認為:“面具是在行動和藝術領域實現自我超越的一種手段……是無盡的游戲。”[33]葉芝指明了面具的藝術性,它是行動和自我的能指。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則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格面具”(persona)理論,認為人格面具是人為了適應環境或獲取個人利益而具有的功能性情結,“它是人與社會之間關于人應該如何行事所達成的一種妥協……人格面具是一種偽裝。”[34]榮格的人格面具理論表明,人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受到人格面具的擠壓而被迫妥協,人格因此被扭曲。簡言之,“面具”不僅遮掩了身體,而且隱藏了自我,成為不利的社會環境下表達身份的偽裝。從舞臺道具、人物面具到人格面具,“面具”不僅體現了一種文化,而且成為“一種藝術符號,具有隱喻或象征功能。”[35]“面具”的符號性和藝術性是其在文學中的最好表現,它起到隱喻或象征變異身份的作用。
《望巖》中名字成了符號化的面具,隱喻人物身份的變異。主人公小時候因貧窮和饑餓被賣到司徒一通家,成為傳宗接代的養子“梁有信”。后來他購買了“契紙兒子”的身份,進入美國后改名為“杰克·滿·司徒”,用作自己謀生的工具。從此“杰克”成了他臉上摘不掉的“面具”,牢牢地控制著他,成為一個無法言說的秘密。這是所有華裔美國人“假身份”的秘密,是貼在身上的標簽和刻在臉上的烙印。種族歧視的高壓政策下,老一代華人移民生活在恐懼中,試圖借此掩蓋自己黃種人的面孔。正如杰克的女兒維達說,“老唐人街的恐懼:不跟生人說話,不回答問題,不要告訴別人爸爸的名字。”[36]爸爸的名字里包含了自己、他的父親和孩子的身份信息,一旦說破,將會殃及三代人在美國的生存權。小說的結尾處,杰克在入籍儀式上躊躇不決,女兒幫助他選擇了“杰克·滿·司徒”作為他公民身份的假名字。德里達認為:“選擇就是幽靈,即不確定性或幽靈性。”[37]“坦白計劃”制造了信任危機,將華人移民逼近心理崩潰的邊緣,在忠誠和背叛間艱難抉擇,造成了華人群體的精神創傷。杰克選擇代表面具的假名字作為自己的真身份,以宣示對美國的忠誠,并暗示對祖國的背叛和黃面孔的否定,但是“忠誠和背叛之間的幽靈性的倫理選擇加劇了杰克幽靈身份的矛盾性和悖論性。”[38]
盡管杰克最終成功入籍,但是面具與面孔、忠誠與背叛之間的矛盾選擇將伴隨其一生,“坦白計劃”的創傷記憶如幽靈般不時地顯現,再現其對幽靈身份的焦慮。
時至今日,美國種族主義制度仍未消除,保守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勢力不時地抬頭,對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實行限制和打壓政策,種族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隨著新中國的崛起,當代美國華裔感受到祖國的強大力量,但受美國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影響,少數華裔的“中國心”已經發生位移,出現了余茂春之流的民族敗類,再次印證了美國華裔的幽靈身份。
五、結語
《骨》和《望巖》堪稱講述唐人街華人移民生活經歷的姊妹篇,是伍慧明基于自己家庭的移民經歷,憑想象和記憶塑造鮮活的“紙生子”人物形象,并重新發現百年來關于美國華裔的歷史文本。“紙生子”是美國華人移民史上獨特的重要的一章,與《排華法案》、“坦白計劃”和麥卡錫主義密切關聯,反映了美國種族主義移民政策對華人的迫害,給華人群體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創傷記憶。
伍慧明的傳記小說打破了真實與虛構、歷史與現實的界限,重寫那段被美國官方話語忽略的華人移民史,編織了一部具有傳奇色彩的民族寓言。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此惡劣,華人移民整日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之中,如同游蕩在唐人街的幽靈。通過剖析幽靈人物的“怪異”心理和再現華人移民的幽靈身份,伍慧明揭示了美國種族主義政治的實質,即對人權的侵犯和人性的踐踏,從而撕下美國作為民主國家的面具,暴露其丑惡的真面目。
①陸薇:《直面華裔美國歷史的華裔女作家伍慧明》,載吳冰、王立禮主編:《華裔美國作家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7 頁。
②[法]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19 頁。
③⑨Wolfreys,Julian.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th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2002,p.259,p.265.
④⑤[希臘]荷馬:《奧德賽》,王煥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2-213 頁,第225 頁。
⑥曾艷兵:《關于“幽靈批評”的批評》,《文藝理論研究》2015 年第1 期。
⑦Derrida, Jaque.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a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Peggy Kamuf,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4,p.4.
⑧[19][20][21][美]伍慧明:《骨》,陸薇譯,譯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46 頁,第3 頁,第7 頁,第170 頁。
⑩王成軍:《“事實正義論”:自傳(傳記)文學的敘事倫理》,《外國文學研究》2005 年第3 期。
[11]詹喬:《美國華裔英語敘事文本中的中國形象》,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2 頁。
[12][13]王娜:《“紙生子”概念的旅行及其文學史意義》,《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
[14]蘇暉:《華裔美國文學中華人倫理身份與倫理選擇的嬗變——以〈望巖〉和〈莫娜在希望之鄉〉為例》,《外國文學研究》2016 年第6 期。
[15]王小濤:《“紙生子”現象的歷史現實與文學想象——以伍慧明〈望巖〉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6 年第3 期。
[16][24][25][26][36][美]伍慧明:《望巖》,陸薇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 年版,第118 頁,第11 頁,第3 頁,第240 頁,第238 頁。
[17][27]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44 頁,第99 頁。
[18]Buse,Peter and Stott,Andrew.Ghosts: Deconstruction, Psychoanalysis, History,NewYork:Macmillian Press,1999,p.55.
[22]Herman,Judith L. Trauma and Recovery,New York:Basic Books,1992,p.32.
[23]Bennett, Andrew and Royle,Nicholas.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 Harlow,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1999,p.241.
[28]Grice, Helena.Negotiating Identities——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94.
[29]張劍:《西方文論關鍵詞:他者》,《外國文學》2011 年第1 期。
[30]Du Bois,W.E.B.The Souls of Black Folk,New York:Bantam Books,2005,p.3.
[31]王娜:《悖論與解悖——小說〈骨〉中人物的生存境遇及策略》,《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1 期。
[32]Ellman,Richard. Oscar Wilde,New York:Vintage Books,1987,p.26.
[33]Brown,Terrence. The Life of W. B. 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Dublin:Gill&Macmillan Ltd.,2001,p.177.
[34][英]安東尼·史蒂文斯:《簡析榮格》,楊韶剛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7-158 頁。
[35]趙曉彬:《西方文學中面具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管窺》,《外國文學研究》2019 年第1 期。
[37]岳梁:《從幽靈到寬恕》,蘇州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43 頁。
[38]王紹平、閆桂姝:《面具與面孔——解讀〈望巖〉中杰克的‘幽靈’身份》,《語言教育》2017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