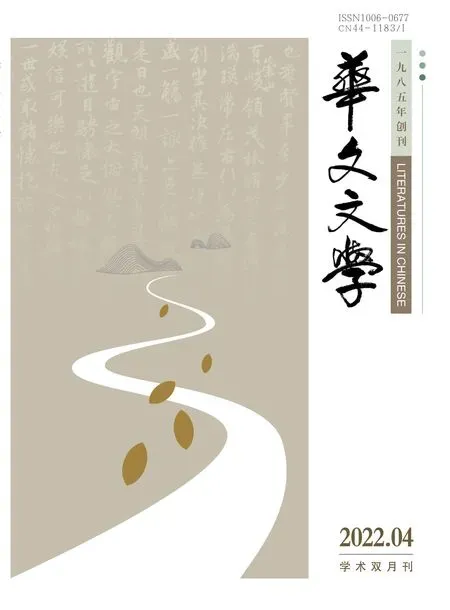“眷村一代”和“眷村二代”身份認同的矛盾與變遷
——以《臺北人》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為例
吳霜
一、歷史背景中的眷村場域與眷村文學
(一)眷村場域
若要提及眷村這一場域,首先要對眷村進行界定。所謂“眷”,其一釋為親屬,如眷屬、家眷;其二釋為關心、懷念,如眷顧、眷念。顧名思義,“眷村”便是國民黨撤退至臺灣后,安置隨軍家屬而建造的聚居群落。
在1949 年以前,臺灣還不存在“眷村”這個詞語。從1944 年到1956 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臺灣約120 萬人,其中軍籍便占6 至7 成,包括60 萬的軍隊,以及國民黨當局黨團官員、公務員以及軍人親屬等等。眷村遍布臺灣,而以臺北為最多。在臺北,“僅軍方正式興建的較大型軍眷區就有25 個,這些軍眷區坐落于以大陸地名命名的街道,眷村名‘空一’‘空海’‘自強’‘成功’‘蘭州’‘酒泉’等也帶有濃重的大陸政治、地域色彩”①。
有關眷村的建立緣由,據張錦錕將軍回憶,抗戰時期,為了解決軍眷問題,眷屬隨部隊四處調動期間,都有一個留守處負責聯絡和安排眷屬。這個留守處一直從大陸到了臺灣,眷屬隨著軍隊移動,留守處就近尋找學校、鄉公所、公家集會所等地方安置眷屬。可是暫時性的住所也不是長久之計,于是陸續興建眷村,留守處后來就變成了眷村管理單位。②不止如此,國民黨軍隊與眷屬由大陸遷至臺灣的過程中受盡艱苦,不僅逃亡船票與機票的一票難求,更有食物的緊缺、痢疾泛濫等等難題,也正是軍眷在戰亂期間顛沛流離,抵達臺灣后才更加急切地追求著穩定,因此希望能建立一個眷村一般的暫時休憩的家園。
臺灣第一處軍眷管理所于1950 年8 月1 日建立在如今的桃園市,該軍眷管理所管轄的地區包括桃園、臺中、新竹等地,收容了1100 多名遷臺軍眷。1951 年1 月又在大林建立了第二處軍眷管理所,管轄新港、溪口、員林等地區,收容了700余人。③不僅如此,國民黨當局還在1950 年10 月發布了“國軍在臺軍眷安置辦法”④,對臺灣的各處空余廠房進行征用,核發“急造眷舍專款”,并利用起日據時期日本人在臺建立的日式建筑來安置遷臺軍眷。1956 年起則開始軍眷籌建住宅運動,由“婦聯會”通過民間捐款的方式籌集了一大筆資金,推動了另一次大規模興建眷村的運動。
臺灣眷村的建造集中在1948-1970 年,即國民黨遷臺早期,之后便逐步減少。且眷村多圍繞在以臺北、臺中和高雄為代表的臺灣三大城市周圍。而大批興建的眷村背后,我們看到的卻是眷村建設的簡陋性。
初抵臺灣時,國民黨向軍人與眷屬宣傳的是眷村不過是臨時住處、暫時的避難地,軍人們也大都抱有“反攻大陸”的期望。當時遷臺的軍眷也普遍認為眷村不過是暫時的住所,因而對于眷村的建造一切從簡。眷村的建筑材料很多都是“竹椽土瓦蓋頂,竹筋糊泥為壁”⑤。不只是建造材料的簡易,當時的國民黨還對眷村房舍的建筑標準有所規定,將軍眷的家庭人口數量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分別占地面積為29.2 m2,22.9 m2以及16.6 m2,可以直觀地感受到當時眷村屋舍的狹小以及居住條件的艱苦。
正如前文所說,自軍眷遷臺,臺灣各地興建了諸多眷村。但是,當時建造眷村的倉促以及建筑材料的簡易,再加上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房屋的日漸老舊,使得這批極具地方與時代特色的眷村面臨著拆除與重建,也正是在拆除與重建的推動下,眷村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熱潮悄然興起。
(二)眷村文學
生長在眷村中的人們,因其本身來自大陸而非臺灣本地,在被稱為“眷村子弟”的同時,也有著“外省人”這樣一個稱呼。劉耀星對“外省人”一詞給出了定義,所謂外省人便是自1945 年開始由大陸遷往臺灣的群體及其后代的總稱。外省人群體來自大陸各地,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因為他們遷往臺灣前后所擁有的一些共享特質與共同記憶,使得外省人群體在與臺灣本省人接觸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一種與本省人所不同的“我族意識”,這便與“外省人”一名相契合。⑥正是在外省人群體的“我族意識”中,加之眷村的封閉性、眷村居民遷臺后的“落難”心態、以及遷臺早期國民黨所宣揚的“反攻大陸”口號的破滅,便隱含了“眷村一代”在文學中常見的懷鄉與迷茫的母題。而文學概念上的“眷村文學”,更多指的是以“眷村二代”為主要寫作者的有關眷村的文學。
所謂眷村文學,是與眷村相關的譬如記憶、歷史、文化的文學。⑦眷村文學在二十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后興起,以小說為主,也包括詩歌、散文、電影、話劇等文體。除卻大家耳熟能詳的朱天心、朱天文、蘇偉貞、張大春等“眷村二代”作家所寫的小說,還包括如話劇《寶島一村》、紀錄片《想我眷村的媽媽們》等文藝作品。
眷村文學的興起與眷村的拆除重建有一定的關系。興建眷村的繁榮期集中在二十世紀40 到60 年代,幾十年后,當初建造的眷村顯露出問題。因此,從1980 年5 月發布《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開始,臺灣逐步實施“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計劃,對老舊眷村進行原地改建或拆遷合并。從1980 年開始臺灣當局推動第一波眷村改建,到1996 年頒布新的眷村改建條例并開始的第二波眷村改建,以及近年來臺灣當局采取的讓眷村居民遷入高樓大廈等方式。生活在眷村中的人們感受到生活環境的變化,并遺憾于改建之后眷村文化的日益消損,從而想通過文字來書寫自己對于眷村的懷念與認同。“眷村二代”走出眷村之后,在文學中通過對于眷村的回望與重新審視,眷村文學得以誕生。眷村文學中包含著復雜的情感和認同問題,在文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也正是在“眷村二代”的推動下,眷村文學才得以在80 年代的臺灣文壇異軍突起,并在多年后依舊有著深遠的文學影響。
二、“眷村一代”的身份認同:懷舊與迷茫的矛盾——以《臺北人》為例
“眷村一代”主要包括隨國民黨于40 至50年代遷移至臺灣并居住入眷村的人們,因其不同于本省人在臺灣本土成長的身份而又可以稱為“外省人一代”。白先勇1937 年出生于廣西桂林,后于1952 年移居臺灣。白先勇雖算不上嚴格意義中隨國民黨遷至臺灣時早已步入中年的軍人眷屬,卻在文字里充滿了對“眷村一代”的關照,尤以《臺北人》一書為最。在《臺北人》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眷村一代”或是“外省人一代”們大多面臨著身份認同上的懷舊與迷茫的矛盾。
(一)大陸原鄉的懷舊
白先勇《臺北人》中的“懷舊”主題,在許多有關《臺北人》的文學研究中都有所提及。歐陽子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中便論述《臺北人》的主題有一部分是“今昔之比”,她認為,《臺北人》里的“過去”象征的是一切美好的東西,而“現在”則代表著丑惡的東西。⑧的確,在小說中,白先勇將筆墨伸向在大陸時有著風光的過去、到了臺灣之后則變得不那么如意的人。這種人不免陷入今昔之比中,暗嘆著過去的美好日子與現在的沒落。翻看《臺北人》的每一篇文章,從男人們的口中幾乎可以拼湊出一段輝煌的民國史,譬如《歲除》中賴鳴升胸膛上紀念“臺兒莊戰役”的傷疤,《梁父吟》中樸園的記憶里牽扯出“武昌起義”以及“北伐戰爭”,《冬夜》里余嵚磊和吳柱國回想起“五四運動”的崢嶸歲月,以及《國葬》里那位聲名赫赫的李浩然將軍……然而,這些有著光輝歷史的男人們,來到臺灣之后,有的成了伙夫頭,有的跛著腿困守在破舊逼仄的小屋里,有的年老辭世,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不只是男人們,《臺北人》中那些沒有參與歷史大事件的女人們同樣承載著屬于自己的輝煌歷史,并透露出懷舊之情。《永遠的尹雪艷》中不斷強調著尹雪艷的迷人與不老,儼然已將其神化為一個光輝過去的象征,因而圍繞著尹雪艷的人們無一不透露出懷舊之感。小說里提到,尹雪艷的老朋友到來時,一起聊聊昔日舊事、發發牢騷,仿佛尹雪艷已化身為上海百樂門時代的永恒象征。文章里充斥著許多屬于過去的物什,諸如百樂門、霞飛路、吳儂軟語、京滬小菜,就連尹雪艷對老友們的稱呼也是十幾年前便作廢的頭銜。與其說這是發生在臺北的故事,不如說這是屬于上海的繁華余韻。與尹雪艷相似的,便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上海百樂門出身的金兆麗,對于臺北的夜巴黎是有著諸多不屑的,她認為百樂門的廁所比夜巴黎的舞池寬敞,夜巴黎的童經理是沒見過世面的小赤佬。然而,金兆麗對于過去的回憶,不只是輝煌的百樂門舞女生涯,更有一份情意在其中。金兆麗表面上心狠手辣,對懷有身孕的舞女朱鳳雖咄咄逼人卻施以援手,甚而回想起年輕的自己曾與初踏舞場的月如的甜蜜戀愛,金兆麗的今昔之比,同樣流露出對于過去的懷念之情。
當然,除卻尹雪艷與金兆麗,《花橋榮記》中榮記米粉店的老板娘更是無時無刻不在流露著對故鄉桂林的熱愛與懷念。白先勇生于廣西桂林,也難怪在文中會透過老板娘的嘴述說著桂林的美。不只如此,老板娘總是懷念著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自家的米粉店,對于在臺北都是桂林小同鄉的盧先生也多有照顧。老板娘認定自己的桂林人身份,雖然生活在臺北,卻篤定自己是水靈的桂林人。這種“外省人一代”將自己的身份與臺灣本省人分裂,在白先勇筆下是屢見不鮮的。正如劉俊在文章中提出,白先勇的《臺北人》中那些“臺北人”并非文字意義上的臺北市民,而是生活在臺北但心系大陸原鄉的群體,因而與其稱他們為“臺北人”不如說是不得不遷往臺灣的“臺北客”。從某些方面來說,那些代表曾經的美好與光輝記憶,已經徹底控制與覆蓋了如今的現實生活,也正是這種遠離現實而趨向于過去的行為,“其實是一種躲避和自我保護”⑨。
懷舊始終是一種對于現實的逃避。一味地沉溺于對于過往的回憶之中,等到一朝夢醒,青春不再,承載著過往的物件也以自己的老去宣告著懷舊的虛幻性。譬如《游園驚夢》中居住在南部的錢夫人前往臺北竇公館赴宴,感嘆最多的便是物是人非。從她總認為臺灣粗糙與光澤扎眼的布料不如大陸的那么細致與柔熟,卻在將壓箱底的自大陸帶來的杭綢裁成旗袍后發現,原本綠如翡翠的顏色在燈下竟然有些發烏;到她赴宴后驚覺,臺北已不時興穿以往在南京時的長旗袍,個個夫人的旗袍都快短到膝蓋上去;再到以往錢夫人的“昆腔”可說是艷壓群芳,卻在這次宴會上推說嗓子不行而拒絕唱《驚夢》。當真如戲曲名字“驚夢”一般,大夢驚醒后的物是人非,在錢夫人身上可算是展現得淋漓盡致了。結尾處,錢夫人在與竇夫人分別時,竇夫人問道:“你這么久沒來,可發覺臺北變了些沒有?”,錢夫人輕輕說:“變得我都快不認識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⑩白先勇于懷舊之中包含的殘忍現實,便是對于“眷村一代”生活處境的反思。撕破表層懷舊的美好面皮,隱含于其中的,是“眷村一代”遷往臺灣后在現實中所經歷的諸多排擠、區別對待背后的對于自身身份認同的迷茫。
(二)陸臺身份的迷茫
當一味的懷舊被現實撕破,“眷村一代”就此陷入迷茫之中。《臺北人》里那些普通人們,在遭遇被迫離家、生離死別等一系列變故后,所感受到的更多是懷舊的無用性。于是,《一把青》中在新婚后不久便失去了做空軍的丈夫的朱青,從最開始的尋死覓活到漂泊至臺灣后的浪蕩不羈,面對愛人小顧的離世,全然不同于當年的心碎,而是如往常一樣做起了飯菜約好了麻將。其實像朱青一樣的人在戰爭時期并不少見,就以文中的空軍眷屬來說,轉嫁四次的周太太以及空軍眷屬們為了排解心事而鐘情于麻將牌這種娛樂項目,他們從最初的撕心裂肺到最后的云淡風輕,之中包含了太多的痛心經歷。朱青也正是在多年的顛沛流離中理解了當年“我”所說的話,明白了新婚之時懸掛在客廳中央的喜匾上寫著的“白頭偕老”不過是癡人說夢,于是看淡了回憶,更看重的是現在。
懷舊的被摧毀不只出現在《一把青》里,《思舊賦》中多年后回到李宅探望的順恩嫂看到殘破不堪的舊屋,又從羅伯娘的口中得知長官的衰老、夫人的去世、小姐的出走、少爺的瘋癲。白先勇以“思舊賦”為題,取向秀懷念嵇康呂安二位故友之意,卻在文章中更加突出了現實的蕭條與反差,名曰“思舊”,實則“摧舊”,在對過往的摧毀之下,“眷村一代”在臺北的生活中所包含的迷茫不定的漂泊感便展現得淋漓盡致了。
“眷村一代”隨國民黨軍隊遷至臺灣,被迫離開故土、與故鄉的親人們離散,其本身一定對遠在大陸的故鄉有著懷念之情。另一方面,他們作為國民黨的眷屬,對于大陸抱有仇恨之情。這種矛盾感使得“眷村一代”們將自己與臺灣人和大陸人劃分界限,而成為介于二者之間的孤獨的“外省人”群體。正是因為迷茫與不定,才會一味地懷舊,并通過建立“眷村”一類的新的居住場所,保護自己不同于本省人的特質并在群體中獲得認同,以此來獲得歸屬感。在《臺北人》中我們不難發現,遷居至臺灣的外省人們,所來往的幾乎都是有著相似經歷的外省人。正是因為“眷村一代”群體的特殊性和封閉性,其身份認同上也存在著因漂泊無助而具有的迷茫感。
那些生活在臺北卻堅稱自己屬于大陸某個地方的人們,在清明時節采用“遙祭”[11]的方式祭奠著遙遠的靈魂,平日里說著天南海北的方言,一日三餐仍舊保持著家鄉的味道。然而,1987 年蔣經國執政時開放了大陸探親,那些對大陸的故鄉日思夜想的“眷村一代”們來到大陸探親,卻發現故鄉早已變樣,昔日熟識的故友與親人早已衰老或是去世,面對“眷村一代”,故鄉的后代客氣而疏離地稱之為“臺胞”。與之相對的是,居于臺灣四十余年的他們,仍被稱作“外省人”。這無疑加重了“眷村一代”們生活上的漂泊感與身份認同上的迷茫感。
也正是在懷舊與迷茫的糾葛中,扎根于“眷村一代”心中的身份認同,恰如“外省人意識”一般,已逐漸偏離于大陸親族與臺灣本省人,而嘗試尋找一種位于兩者之間的新的身份認同。在這之后的“眷村二代”,更是繼承與發展了“眷村一代”的身份認同,在逃離眷村與眷戀眷村的矛盾之中,反思自己究竟歸屬于何處。
三、“眷村二代”的身份認同:逃離與眷戀的矛盾——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為例
從小生長于眷村而沒有原鄉記憶的“眷村二代”,不同于“眷村一代”在文學中對大陸的諸多回望,而是將筆觸伸向自己熟悉的眷村。朱天心生于1958 年,祖籍山東,是眾多“眷村二代”中的一份子,憑借《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里對于“眷村二代”生活的細膩描寫而被稱為“臺灣眷村文學第一人”。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之中,我們可以尋找到以朱天心為代表的“眷村二代”們對于眷村這一環境以及自身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
(一)逃離眷村
與有著原鄉記憶的“眷村一代”不同,自出生就扎根于這座島嶼的“眷村二代”們,將眷村看作自己生長的地方,卻又從小浸淫在父母對于原鄉的回憶中。《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里便對父輩的原鄉記憶多次提及,從清明節祭奠生死未卜的親人,到父母在兒女面前不厭其煩地回憶甚至夸耀著大陸生活與逃難經歷。這樣的場景并不少見,與《臺北人》中“眷村一代”的懷舊情結可以互證。而值得注意的是,“眷村二代”對于父母輩的回憶,所抱有的并非是一樣的懷舊,而更多的是一種迷茫、反思與逃離,之間存在著一層隔膜。
因而,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眷村二代”更接近于一種無根的漂泊者形態,他們無墳可上,也不理解本省人在祭奠親人時流露出的肅穆表情。并由此而生出一種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于是暗嘆著“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12]朱天心將這種“眷村二代”的漂泊形態比作《伊索寓言》中那只“徘徊于鳥類獸類之間,無可歸屬的蝙蝠”[13]。于朱天心而言,將“眷村二代”比作蝙蝠,取的是其不歸屬于鳥與獸這兩個族群的狀態,恰如眷村居民這一群體,在臺灣被視為“外省人”,回到大陸原鄉又被客氣而疏離地稱呼為“臺胞”。“眷村二代”親歷了“眷村一代”回鄉探視后的迷茫,開始思考沒有原鄉記憶的自己究竟屬于哪一方天地,于是嘗試著融于這方水土,從最開始的“她”對于另一半的要求“只要是眷村男孩就好”以及對本省農家同學的貧苦生活感到惆悵難言;到之后不再吹噓自己父母口中常提及的那個未曾見過的家鄉,且漸漸理解并接受了本省同學們為什么總是如此地篤定與怡然,甚而違背了自己少女時代的規定而嫁給了本省人。
生長于眷村中的二代們,為這特殊的外省人身份與眷村的規定所包裹,一方面內心扎根著一種無家可歸的漂泊感,且對“眷村一代”在晚年喟嘆的“反攻大陸”愿望的破滅銘刻于心。他們眼看著從大陸來到臺灣的媽媽們,從期盼著回到大陸到認清回不去的現實之后狠心將壓箱底的衣服拿來給孩子做成新衣。也正是在生活的種種失望之中,“眷村二代”對眷村制度產生了反思。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便有一處展現:每次選舉投票時,眷村的村口便會扯出橫幅寫著該村應支持的候選人的名字。[14]小說里展現的這一場景在當時的眷村極為常見,因為眷村居民基本都是國民黨軍人的眷屬,所以在選舉時自然要求站在國民黨一邊。正是如此,國民黨遷臺早期的選舉,眷村早已被統一劃歸為某位國民黨候選人的擁護群體,眷村的選舉票也因而被國民黨稱為“鐵票”。與一般的村落所包含的因生存所需與合作關系而建立起的集體不同,眷村的集體性和封閉性與軍人精神有很大的關系。
正是在這種種原因之下,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矛盾在“眷村二代”依舊存在。當“眷村二代”的女孩們嫁給了本省人,不免與自己的臺灣丈夫從政治到生活上都有著一番爭論。《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里有關省籍矛盾的描寫有好幾處:一是當報紙上大肆宣揚外省人二代的官宦子弟爭奪權力時,看報紙的丈夫便辱罵著她所屬的外省人身份,二是在嫁給本省男子后會為他們的怠惰而思考他們是否時受到日據時代大男子主義的遺風所影響,三是在選舉時雖然自己并未加入國民黨卻依舊要因為自己的眷村身份而代替國民黨與本省人丈夫進行爭辯。
然而,“眷村二代”的女孩們雖與自己的本省人丈夫因政治與生活而產生了沖突,又是否是真的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在說話呢?翻看《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我們不難找出諸多朱天心代表“眷村二代”想要逃離國民黨統制的發聲,譬如眷村后代的語言問題,因為外省人不會講閩南語而在求職上遭遇諸多碰壁。這既可以被歸為省籍矛盾,同樣也能夠看到“眷村二代”并沒有在臺灣得到當局的多少愛護卻依然要承受本省人的攻擊,因而加深了逃離之感,甚而稱自己與國民黨的關系更像是“一對早該離婚的怨偶”,于是“眷村二代”們叫囂著對它的恨,同時之中又糾纏著自己不得不為其維護的矛盾之感。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產生的多重心理糾葛與掙扎之中,“眷村二代”跳出“眷村一代”的懷舊與迷茫的心理,從而形成了一種“逃離”的想法。他們一面拒絕著自己的成長,一面又在成長之后想方設法地逃離眷村這塊承載著自己童年記憶與外省人身份的土地。因而小時候的他們眼看著“潘家二姊跟一個美國大兵黏著走路”[15]姐姐即將嫁給美軍男友的馬哥教男孩們跳著從未來姊夫那兒學來的新式舞步。少年時期的他們深信自己的漂泊狀態,并將自己與本省孩子們劃清界限,心中扎根著想要逃離的種子,男孩子多選擇出國讀書或者做一名水手,女孩子通過嫁了越戰來臺的美軍離開。于是,那些曾經一起成長,習慣了街巷里傳來天南海北口音,習慣了眷村的特殊安排與制度,習慣了聽自己的父母輩說不膩的回憶并由此確立身份認同的“眷村二代”們,終于在長大后風流云散,唯有在多年之后的報紙一隅或許可以找到他們的蹤跡,于是喟嘆一聲:“噢,原來你在這里……”
(二)眷戀眷村
眷村的孩子們在逃離眷村之后,對眷村又是怎樣的情感呢?《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之中,當她終于離開眷村而搬進新興社區,自己卻有著“河入大海”的落寞感之時,她在心里想到的是——曾經圍繞在身邊的那些眷村男孩們都到哪里去了?
正如題目“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所表達的情感一樣,“眷村二代”在逃離眷村后,對于眷村生活是包含著想念的。畢竟沒有原鄉記憶的他們,對于遠在大陸從未親歷只是反復出現在父輩口中的所謂家鄉有著幾分疏離和淡漠。而與之相對的是從小生長和居住的眷村,誠然它是逼仄、封鎖、雞毛蒜皮、雜亂不堪的產物,不同于父輩口中那個有著綠水青山、錦衣玉食的家鄉,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著的。正因如此,對于“眷村二代”們來說,眷村替代了父輩口中那個遙遠的故鄉而成為他們心中“家鄉”的符號。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之中,我們不難發現她對于曾經眷村生活的想念,從最開始想念他們的體溫汗臭、吃飽后打出的嗝兒,之后還如數家珍般地列舉出眷村的伙伴們因為父輩來自天南海北而有著不同的飲食習慣,回憶起那些朝夕相處甚至排排睡的伙伴們、自己親眼目睹出生與長大的毛毛、與她秘密戀愛的阿三、還有每次見面都會大打出手的大頭……那些在當時看來并不算什么的零零碎碎,在多年之后回憶起來竟然成為自己童年的佐證而變得甜蜜。
至于長大并離開眷村后,他們感嘆最多的,便是那句“眷村的兄弟們,你們到底都哪里去了?”“眷村二代”們會為乍然聽到的外省腔而頓生鄉愁,甚而想登尋人啟事來找回童年的眷村伙伴。他們所懷念的并非是與外省人并肩獲得的群體認同,而是找回幼年時期在眷村與伙伴們朝夕相處的感覺。小說的最后,配合著《今宵多珍重》歌詞里的“我倆臨別依依,要再見在夢中”,朱天心嘆道:“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到此處,“眷村二代”的逃離之感早已被沖散,只余下了濃濃的眷戀之情。
正是在“眷村二代”的眷戀情懷下,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后,“眷村文學”作為臺灣文學創作的一股潮流異軍突起,不只是如朱天心一般的眷村作家在書寫有關眷村的文學故事,更有許多眷村生活親歷者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憶并記錄著那段生活。如60 年代出生于臺南眷村的龔顯耀于《我在寶島長大》一書中津津樂道著眷村里的三家冰店、露天電影以及眷村菜。除卻親歷者的記述與文學書寫,眷村生活也成為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的對象,相關的調查研究也層出不窮。如張耀升的《眷村記憶》、張德南的《新竹市眷村走過從前:眷村的影像歲月》、何思瞇的《臺北縣眷村調查研究》等等。
眷村在幾十年的歲月荏苒中難免出現破敗的情況,因此面臨著拆除的命運。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眷村拆除的過程中,那些曾經選擇逃離的“眷村二代”,卻又在此時站出來,對這個承載了自己童年回憶而有著“家鄉”一般的地位的眷村表達懷念,呼吁對其加以保護、改造而不是一味地拆除。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眷村二代”對于眷村的眷戀之情。在如今的臺灣,由眷村改造而來的文創園區、博物館等數不勝數。譬如2002 年建立的新竹眷村博物館;臺北市在對“四四南村”進行改建的過程中保留一部分的眷村屋舍,并為了記錄眷村歷史而成立了信義公會館;以及桃園市舉辦的“桃園眷村文化節”等等。在眷村被提出拆除和改造之后,人們重新審視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地方,并開始思考其作為臺灣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在這個過程中,“眷村二代”作為從眷村走出來的正當盛年的群體,其對于重視眷村的呼吁更是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正是在“眷村二代”對于眷村的情感由逃離到眷戀的轉變中,“眷村”的“眷”字也從最初的“眷屬”之意向情感上的“眷戀”之意轉化。外省人的后代們在成長中不斷融入臺灣本省人時,也逐漸認清眷村在當時的歷史特殊時期所起到的家鄉一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眷村二代”眷戀的何止是眷村的兄弟們,眷戀的更是早已作為家鄉這個符號刻在心底的眷村。
透過“眷村二代”對眷村的逃離與眷戀的矛盾態度,我們看到其與“眷村一代”在身份認同上的變化的同時,也不難發現其深層的同一性。從“眷村一代”身上的“外省人意識”到“眷村二代”以離群索居的蝙蝠自比,眷村后代在身份認同上都呈現出了差異性與小眾性,即既懷念大陸又深愛自己所生活的臺灣這一片土地。因此,我們對于外省人后代的身份認同,不應該將其簡單地歸為傾向大陸或是臺灣,而是具有獨特性的,在二者之間尋找容身之地的一個群體。
四、結語
眷村作為國民黨軍隊及其眷屬敗退臺灣后特定時期的產物,雖在發展過程中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眷村的存在價值以及眷村后代的身份認同值得重視。透過白先勇的《臺北人》以及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我們可以看到,從“眷村一代”的對于大陸原鄉的懷舊到自己陸臺身份的迷茫,以及“眷村二代”對于眷村的逃離到眷戀,眷村兩代對于家鄉的認同出現了由大陸原鄉至臺灣眷村的轉變。不論是對何處的懷念,其都呈現出立足于大陸與臺灣兩者夾縫之間的特點,這也正是眷村后代在身份認同上所體現的獨特性。歷史潮流的激蕩造就了眷村的產生,而眷村這一環境本身又孕育了“眷村一代”的懷鄉文學與“眷村二代”的眷村文學。“眷村二代”究竟是否脫離了大陸的記憶呢?我認為并沒有,外省人的習慣早已根植其記憶與生命之中,當“眷村二代”在逃離與眷戀之中糾葛時,其本身已體現了父輩的原鄉敘述與眷村的生活記憶在其身上的交叉作用。因此,我們不能忽視眷村后代在文學表達中呈現出的矛盾與同一性,由此觸及的便是眷村群體身份認同上的獨特性與小眾性。
①黃萬華:《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花城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0 頁。
②林樹等:《新北市眷村田野調查報告書》,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 年版,第26-27 頁。
③④臺灣“國防部史譯局”:《國軍后勤史(第五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年版,第249-250 頁,第245-246 頁。
⑤丁瑋:《眷村與眷村文化》,《歷史文物》1996 年第8 期。
⑥劉耀星:《臺灣族群形成析論》,《赤峰學院學報》2007 年第3 期。
⑦劉俊:《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論蘇偉貞的眷村小說》,《暨南學報》2007 年第4 期。
⑧陳春生等:《20 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精華:小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385 頁。
⑨劉俊:《從“單純的懷舊”到“動能的懷舊”——論〈臺北人〉和〈紐約客〉中的懷舊、都市與身份建構》,《南方文壇》2017 年第3 期。
⑩白先勇:《臺北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92-193 頁。
[11]張國立:《原鄉》,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 年版,第193 頁。
[12][13][14][15]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九州出版社2018 年版,第24 頁,第38 頁,第20 頁,第2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