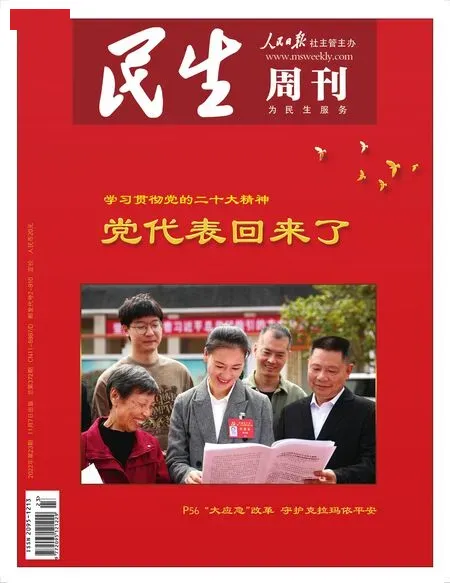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對策與建議
□ 中共忠縣縣委黨校 成惠明 張連花
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育新機開新局的“壓艙石”,構建新發展格局、夯實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基礎。
產業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更是鄉村振興的振興之本。面對壓力與挑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孕育而生,實踐探索出來的產業發展模式和路徑,將不斷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充分激活廣大農村生態資源,引導傳統農業企業逐步轉型為社會化農業企業,有效促進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繁榮,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進一步助推鄉村振興和城鄉統籌融合發展。
農村集體經濟存在的問題及內因
第一,少數干部群眾及社會投資主體思想認識上存在偏差。
少數基層干部缺乏農村經濟工作實踐,且思想觀念陳舊、說得多干得少、畏難情緒較大,導致其主動性和擔當意識不強;部分群眾固守以農為本觀念,小富即安、“等靠要”思想觀念嚴重,且受“紅眼病”攀比等狹隘思想影響,寧愿其承包土地荒蕪也不愿流轉租用,導致參與集體經濟的社會主體中途被迫放棄;少數社會主體投資人的社會責任缺位,受利益驅使,主觀上投機從村級集體產業項目中謀取其中的基礎設施工程項目利潤,客觀上因不懂經營管理和農業產業投入大、周期長、風險大等因素影響,導致工程建設盈利后放任不管或濫管產業發展而成為“爛攤子”項目。
第二,受區位等因素影響導致發展不平衡、資產結構不合理。
受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等因素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東部區域優于中、西部區域,重慶主城片區優于渝西片區、渝東北片區、渝東南片區,凡靠近區縣中心城市的鄉鎮優于偏遠的。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分為生產經營性、社會公益性兩類,經營性資產能實現自身“造血”不斷發展壯大,而公益性資產則要持續不斷地“輸血”;東部區域經營性資產占比遠高于中、西部區域,且東部區域經營性資產占比高于公益性資產,中、西部區域公益性資產占比高于經營性資產,重慶片區及區縣類似。因此,農村集體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集體收入中經營性、公益性資產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亟待在鄉村振興體制機制改革中逐步解決。
第三,部分鄉村生態資產閑置分散、資源整合利用不充分。
為應對全球經濟下行和疫情影響下的經濟振興問題,鄉村振興為生態資源充分利用與社會資本投資創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合作平臺。廣大鄉村擁有大量資源性資產,但大多處于閑置分散狀態,生態產業化發展亟待擴大農業農村有效投資,同時大量社會資本正迫切尋求產業生態化市場出路,兩者不謀而合共同聚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因此,通過不斷激活廣大農村生態資源要素價值,支持社會資本參與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發展,逐步實現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目標,同時不斷探索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等產業振興助推鄉村振興的實踐載體和有效途徑。
第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規章制度亟待進一步健全和完善。
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多為農戶土地,自實施家庭承包經營后集體土地分配至各戶經營承包,絕大多數沒有可供集體統一經營資產,導致僅部分統分融合經營模式可實現集體與農戶雙贏目標。同時,部分農村集體資產底數不清,基礎設施等公益性集體資產沒有經營性收入,且未配套對應維修管護資金和措施,導致后續投入較大;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盈利分配、獎懲激勵等機制不健全,導致集體經濟管理人員出工不出力,甚至出現少數合作社農戶中途變卦違約收回承包地等。因此,不斷健全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民主決策、風險防范、鄉村治理等制度以及土地要素、資金要素、市場要素等保障措施勢在必行。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對策及建議
第一,不斷健全人才隊伍培育機制,為集體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探索實施培養基層黨組織書記專業化“頭雁”、回引返鄉創業賢士“歸雁”、感召農業經濟專家“鴻雁”、商引群眾參與和社會投資“群雁”等“四雁”人才培育工程,鼓勵他們成才、創業、發展。分類專題培訓并動態建立健全重慶市農村經濟人才資源庫,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暢通人才交流渠道、激勵與約束并重等長效機制,促使他們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排頭兵和中堅力量。圍繞強化政治引領凝聚共同富裕思想共識,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政治、組織、資源、智力優勢,激發并增強民營經濟等社會各界創新發展、反哺社會的使命感、榮譽感,激發他們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提供資源和智力支持,推動農業經濟大發展、農村社會大繁榮。不斷健全誠信“紅黑名單”機制,將在渝國有、民營企業等社會投資主體納入誠信量化監管,凡社會責任缺位的,尤其是投機參與鄉村振興蓄意謀取工程項目利潤的等,納入誠信黑名單限期整改或吊銷其營業執照,同步將其曝光至企業及個體所在省市級市場監督管理局、銀行等行業監管部門;同時,為納入誠信紅名單的配套完善稅收、信貸等激勵政策,有效撬動并鼓勵社會資本共同助力鄉村振興。
第二,統籌縮小“三大差距”與城鄉融合發展,為集體經濟發展賦能。
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為解決區域、城鄉、收入等三大差距,建議中央財政擴大投資加大對地方產業扶持力度,不斷健全部省、東西部產業發展協同機制,積極推廣浙江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經驗做法,助力城鄉共同富裕;構建城鄉價值交換體系,進一步發揮以工哺農、重慶主城區帶郊區縣、以城帶鄉發展效能,按照一區(縣)多品原則,采取整合財政產業扶持資金、撬動社會資本投入等方式,逐步健全完善重慶市農村集體產業深度融合機制,聯動各區縣合力打造本土特色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產業鏈,進一步拉動市場消費促進重慶市經濟社會發展。健全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機制。為促進資源要素流動,不斷健全城鎮反哺農村供給和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制度,從政策、人才、資金等方面加大投入,推動資本、技術、數據等更多資源要素流入農業農村,促進城鄉基礎設施系統化整體推進、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持續推進,為其創造平等開放的良好發展環境;參照南岸區與石柱縣橫向生態補償等模式,不斷完善重慶市生態資源利用指導意見,切實盤活農村生態資源助力區域資源互補和經濟社會發展;參照重慶市宅基地復墾地票交易模式,逐步推進梁平區退地模式,試點推行“個人承包地—集體土地—土地入市”路徑,探索產權保全退出、康養保障、退地容錯等機制,進一步健全重慶市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入市等農用地指導意見,有效破除農村集體經濟封閉性,切實解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落地難題。健全收入分配改革機制。為優化市場分配機制,建議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為契機,深化拓展東西部經濟協作領域,借鑒廣東省預制菜等新業態發展模式,逐步健全重慶市訂單式聯結區縣農村集體經濟合作機制,配套完善重慶市預制菜智能裝備制造全產業鏈集群,探索借力渝新歐物流通道搭建西部(成渝陜)預制菜產業對外出口合作平臺,積極為重慶經濟社會發展賦能;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契機,探索征收重慶市農村集體經濟上市公司股息、債券所得利等,減收或免收加工型農村集體經濟稅收等資本利得稅,帶動低收入群體逐年穩步提高,提高城鄉發展平衡性和東西部經濟協作協調性;以農村集體經濟為切入點,逐步完善城鄉金融、電商物流等服務體系和對應配套激勵機制,不斷健全重慶市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公益性幫扶法律等,并探索健全重慶市農村集體經濟跨省市、區縣、鄉鎮等異地聯結和城鄉反哺互惠紅利分配機制,切實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助力農村共同富裕。
第三,健全完善“三農”工作規章制度,為集體經濟發展提供堅強保障。
健全社會資本準入促進機制。探索建立健全重慶市社會資本助力鄉村振興準入審核備案制度,重點監督并管控社會資本投資方受利益驅使私自改變集體流轉土地使用性質,甚至出現違規違建、污染生態環境等違法行為;優選區縣本土鄉賢或屬地民營企業資本落地,在不斷健全股份合作等機制的基礎上,配套完善社會資本下鄉對應的金融、土地等要素保障和稅收、信貸等激勵機制,同時探索建立資本方利益保護政策,切實暢通社會資本助力鄉村振興渠道。健全公益性投資及維護機制。建議中央財政擴大投資加大對農村公益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體系等建設投資力度,配套中央及省級國企、國有平臺公司投資反哺激勵指導意見;探索農村及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等公益性基礎設施資產因災或因非人為不可抗拒因素損壞的,由屬地區縣國有平臺公司籌集資金搶修恢復功能;其他因素的由屬地基層政府和村居負責,按照“誰受益誰維護”原則,運用村規民約議定受益群眾日常維護機制,村級基層黨組織牽頭商定從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收益中出資排危加固,不足部分由鄉鎮黨委和政府集體決策從政府固定資產收益或協調轄區村級集體地票收益等渠道解決;同步由各區縣結合實際細化反哺屬地國有平臺公司基礎設施入股招商引資企業、利用土地林地等生態資源融資、盤活閑置或優質國有固定資產市場營運“造血”等扶持政策。健全風險防范及治理等機制。堅持產業發展服從市場導向,規范完善村級集體經濟資金、資產、資源等“三資”臺賬并健全對應監管機制,試點全面推行財務票據聯審、賬務公開公示、績效收益評估等“三審”制度,并不斷健全村級集體經濟科學研判、民主決策、風險防范、收益分配等集體決策制度,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提供制度保障。堅持鄉村治理助力產業發展,不斷健全村民參政議政基層民主建設、鄉賢文化侵染、法治宣傳教育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村規民約等機制,促使鄉村文明落地生根、入腦入心,引導村民積極參與并支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同時前置限定土地流轉規模不宜過大、約定企業進場前向村(居)民委員會公賬上預繳一年的土地流轉費和復墾保證金作為質保金且納入屬地政府監管,并配套完善要素保障、引賢融資、資本下鄉利益保護、社會化農業企業財稅激勵等扶持政策,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提供政策保障。堅持黨建引領集體產業發展,不斷完善基層黨組織建設、“四雁”人才培育機制、“三變+”改革模式推廣、社會輿論宣傳引導、產業績效評估考核、黨建實績量化評比等考核制度,探索健全集體經濟組織管理人員薪酬績效掛鉤、集體收益分配權動態調整、產業盈利聯結群眾利益分紅等機制,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提供組織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