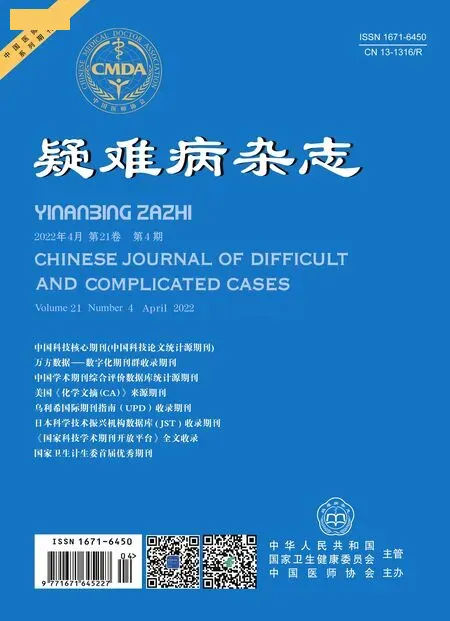神經元核內包涵體病的神經變性相關機制及臨床研究進展
陳阿楠綜述 錢海蓉審校
神經元核內包涵體病(neuronal intranuclear inclusion disease,NIID)是一種罕見的慢性進展性神經變性疾病,以腦、內臟器官細胞和皮膚組織內廣泛存在的嗜酸性核內包涵體為主要特征。2011年Sone發現皮膚組織中含有嗜酸性核內包涵體,使皮膚活檢成為除尸檢以外的NIID確診方法,2019年NOTCH2NLC基因5’非翻譯區(UTR)GGC重復擴增突變被確定為NIID的致病基因。近年,不斷有研究發現NIID與其他神經變性病之間的關聯,對其分子遺傳學、發病機制、臨床表現、影像學表現、病理表現及治療均有了新的認知。
1 分子遺傳學
NOTCH2NL基因位于人類染色1q21.1位點,在腦皮質發育過程中起重要作用。NOTCH2NL基因具有4個結構高度相似的功能基因,分別為NOTCH2NLA、NOTCH2NLB、NOTCH2NLC和NOTCH2NLR[1]。其中,NOTCH2NLC基因在大腦中的表達量最高,其在前額葉皮質的表達量會隨年齡的增長而顯著升高[2]。
NOTCH2NLC基因在5’UTR區含有三核苷酸重復序列GGC9、GGA2、GGC2, GGC重復序列擴增與NIID發病相關[2-5]。正常成年人 NOTCH2NLC 基因 5' 區域GGC重復擴增次數不超過40次,重復次數大于60 次具有致病性[6]。Tian等[2]研究中,健康對照者的GGC重復次數在5~38次,而家族型NIID患者的重復次數為66~517次。根據NIID的臨床表現進行分型后發現,各分型間重復次數不同。以肌無力為主要表型的患者重復次數為118~517次,帕金森型為66~102次,癡呆型為91~268次[5]。但尚未發現GGC重復次數和疾病嚴重程度之間有明顯聯系。
NOTCH2NLC基因的GGC重復擴增突變存在于多種神經變性病中,包括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白質腦病、特發性震顫、額顳葉癡呆、肌萎縮側索硬化癥等,在神經肌肉病如眼咽遠端型肌病(oculopharyngodistal myopathy,OPDM)3型中也有發現[2, 6-10]。Jiao等[11]對1 004例神經變性病相關癡呆患者進行研究,其中3例臨床診斷的阿爾茨海默病和 1例臨床診斷的額顳葉癡呆的患者存在 NOTCH2NLC基因的GGC重復擴增突變,表明該機制可能參與神經變性病等多種疾病的發病過程,但存在某種機制差異而導致引發不同疾病。現有研究提示,NOTCH2NLC基因5’UTR區的三核苷酸重復序列中斷類型可能與此有關。在NIID和帕金森病患者中,GGC重復擴增序列存在2種重復中斷形式:GGA中斷和AGC中斷。對比兩者的GGC重復序列發現,12%的NIID患者存在GGA中斷,而帕金森病患者無GGA中斷,但AGC中斷的頻率比NIID高3倍以上[9]。因此,有學者提出將NIID的疾病名稱變更為NOTCH2NLC相關重復擴增性疾病(NRRED),或NOTCH2NLC基因相關的重復障礙(NRED),包括NIID和其他的GGC重復擴增突變造成的神經變性病[12]。
值得注意的是,NIID中GGC重復擴增突變具有遺傳異質性。首先,亞洲人群中GGC重復擴增突變的檢出率高于歐洲人群。Chen等[13]通過對比11例NIID歐洲患者和20 536例志愿者的全基因測序結果發現,在歐洲人群中由NOTCH2NLC重復擴增導致的NIID十分罕見,表明歐洲人群的NIID發病可能是通過一個獨立的病理生理過程產生。其次,存在GGC重復擴增的無癥狀攜帶者。Deng等[14]對來自不同家族的2例散發型NIID患者及其直系親屬進行全基因測序,發現2例患者的父親攜帶大量NOTCH2NLC基因GGC重復擴增(分別為317次、709次)而無臨床和病理表現,推測NOTCH2NLC基因GGC重復次數大于300次可能產生無癥狀攜帶者。最后,存在無GGC重復擴增的患者,2020年Jedlickova等[15]通過尸檢確診1例NIID男性患兒,其NOTCH2NLC測序未發現該基因存在GGC重復擴增,提示NOTCH2NLC基因的GGC重復擴增突變可能并非NIID唯一遺傳原因。
綜上,NOTCH2NLC基因GGC重復擴增能否單獨作為NIID的確診依據,在NIID及一些神經系統變性病的發病過程中,該突變相關的分子機制之間有何差異?這些問題仍需進一步研究。
2 發病機制
三核苷酸重復障礙是一組異質性疾病,在一些神經退行性疾病中,蛋白質編碼序列中三核苷酸重復序列的擴增突變被認為是產生病理性核內包涵體的原因。NOTCH2NLC基因的GGC重復擴增突變表明,NIID和其他三核苷酸重復障礙相關疾病之間可能存在類似的機制。
2.1 毒性RNA功能性增益 GGC三核苷酸重復擴增可產生重復片段,該片段直接或間接與特定的RNA結合蛋白結合,降低表達從而導致生理功能障礙[14]。NIID和脆性X相關震顫/共濟失調綜合征(fragile X-associated tremor/ataxia syndrome,FXTAS)在臨床及病理學上具有相似的特征[16],二者有類似的GGC/CGG三核苷酸重復擴增,FXTAS的重復RNA序列會異常積累RNA團簇(RNA foci)[17]。在NIID中,NOTCH2NLC基因的GGC重復擴增RNA形成RNA團簇,隔離RNA結合蛋白,進而形成p62陽性核內包涵體導致發病[14]。被隔離的RNA結合蛋白包括Sam68、hnRNP A/B和MBNL1,而正常人或無癥狀攜帶者中未發現RNA結合蛋白。由此說明,毒性RNA功能性增益機制與NIID核內包涵體產生相關。
2.2 聚甘氨酸蛋白質毒性 NOTCH2NLC基因的起始密碼子為AUG密碼子,位于GGC三核苷酸重復擴增序列上游的非AUG啟動翻譯可能產生一些新的蛋白質,它們將誘導包涵體聚集并產生細胞毒性。正常狀態下,翻譯后uN2C蛋白與DNA結合蛋白Ku70、Ku80相互作用,激活DNA修復。非AUG啟動翻譯將導致含聚甘氨酸(polyG)或聚丙氨酸(polyA)的致病性蛋白表達。GGC三核苷酸重復擴增被嵌入到上游開放閱讀框架中,而后被翻譯成polyG蛋白,該蛋白會破壞其與Ku70和Ku80蛋白的相互作用,導致DNA修復受阻從而引發疾病[18]。Boivin等[19]在NIID患者皮膚和腦組織樣本中均發現聚合氨酸蛋白(uN2CpolyG)被轉錄產生,其積累在核內包涵體中導致細胞死亡,同時發現uN2CpolyG會導致小鼠模型的神經細胞丟失、運動障礙和早亡。Zhong等[20]在體內及體外實驗中發現NOTCH2NLC基因的GGC三核苷酸重復擴增被翻譯成多聚甘氨酸蛋白(N2NLCpolyG),導致核內包涵體異常聚集,破壞了核膜和核質RNA的運輸,證實該機制為NIID患者核內包涵體形成的主要機制。
基于此機制提出多聚甘氨酸病(PolyG diseases)的概念,提示以GGC/CGG重復序列擴增、PolyG相關蛋白異常積聚、包涵體形成和白質腦病為特征的相關譜系疾病的存在。進一步探索PolyG是否也存在于其他GGC/CGG重復序列擴增相關疾病,將拓展對NIID的認識。
2.3 重復序列異常的甲基化 重復序列的高甲基化水平可降低NOTCH2NLC基因的RNA轉錄水平,導致轉錄沉默和NOTCH2NLC蛋白缺乏[2]。CpG的胞嘧啶(C)甲基化是DNA中至關重要的表觀遺傳變化,基因沉默已被證明是由CpG島(CpG island)高甲基化誘導產生。雖然NIID患者的納米孔測序中并未發現NOTCH2NLC基因的重復GGC序列引發過度甲基化[2, 4-5],但近期在無癥狀攜帶者中發現了NOTCH2NLC基因的CpG島高甲基化[14]。
Deng等[14]在NIID的2組家系中發現NOTCH2NLC啟動子區域存在CpG島高度甲基化,并導致其宿主基因的mRNA水平下調。類似機制在其他基因遺傳病中已被證實。例如,脆性X智力障礙1基因(fragile mental retardation gene,FMR1)5’UTR的CGG重復擴增突變下調了其表達并導致FXTAS、DMPK基因的3’UTR的CTG重復擴增突變導致其下游基因的啟動子超甲基化而產生基因轉錄的下調[21]。當GGC重復次數超過300時,CpG島趨向于高甲基化和抑制表達從而產生無癥狀攜帶者,提示NOTCH2NLC基因啟動子區的異常甲基化可解釋NIID無癥狀攜帶者的產生。
3 臨床、影像學和病理表現
3.1 臨床表現 NIID根據主要臨床癥狀分為中樞神經系統型、周圍神經系統型、自主神經系統型。按起病年齡分為嬰兒型、青少年型和成人型,其中成人型NIID根據其遺傳特征可以分為家族型和散發型,而家族成人型NIID按臨床表現又分為肌無力型、帕金森型和癡呆型,各型的平均發病年齡分別在36歲、60歲和58歲[22],中老年起病者與神經變性病較難鑒別。
筆者以“NIID”“神經元核內包涵體病”“neuronal intranuclear inclusion disease”為關鍵字,檢索Pubmed數據庫、萬方數據庫、中國知網數據庫于1998年1月—2021年10月發表的相關文章,納入71篇文獻中經病理確診的NIID患者325例。總結NIID臨床表現及發生率如下。(1)中樞神經系統:癡呆(67.69%)、精神行為異常(32.00%)、震顫(28.00%)、腦炎(24.62%)、共濟失調(23.08%)、意識障礙(19.38%)、肢體僵硬/肌強直(17.23%)、嘔吐(16.00%)、構音障礙(6.77%)、癲癇發作(4.62%)、卒中樣發作(4.31%)、運動遲緩(4.00%)、吞咽困難(3.08%);(2)周圍神經:感覺障礙(26.15%)、肌力減退(36.92%);(3)自主神經:排尿障礙/尿失禁(44.31%)、瞳孔縮小(31.69%)、便秘(3.69%)、體位性眩暈(1.85%)、暈厥(1.54%)。其他癥狀如頭痛(9.54%)、偏頭痛(1.54%)、視力減退(8.00%)、腸梗阻(0.92%)也偶有出現,眼肌麻痹(0.31%)、不自主咀嚼(0.31%)、腹痛(0.31%)各有1例個案報道[23-25]。
NIID臨床表現具有高度異質性,各癥狀發生率雖有不同,但癥狀多成組出現且累及多個系統,識別NIID早期和突出癥狀可提高該病確診率。癡呆是NIID最為突出的癥狀,發生率為67.69%。既往報道中,94.7%的NIID患者以癡呆為初始癥狀,多呈慢性進展,但散發型NIID病例中,亦有快速認知功能下降或發作性腦炎后認知功能明顯惡化的報道[26]。且以癡呆為表現的患者中可能存在NIID。Yu等[27]通過檢索NIID的影像學特征對12萬份影像學報告進行回顧性分析,結合病理活檢確診了12例NIID患者,其中8例曾被診斷為認知障礙疾病。Fang 等[12]在189例多系統萎縮患者中確診5例NIID患者,這些患者發病年齡偏小、腦內白質異常病灶較多。
在Sone的研究中,21%的散發型NIID患者表現腦炎樣的發作性腦病,而家族型的發病率為5.3%[22,28]。筆者總結腦炎發作占比24.62%,合并意識障礙(19.38%)、癲癇發作(4.62%),也可有頭痛、嘔吐、腹痛等癥狀[23]。腦脊液檢查可出現蛋白增高(>450 mg/L)、細胞數增多(>5×106/L)等類腦炎表現[22]。發作性腦病在對癥治療后可于幾天內迅速恢復,但部分患者的恢復時間會隨著病情發展而逐漸延長[13]。另外,個別病例存在可逆性發作,數年間多次復發而癥狀可完全緩解[29]。
NIID的早期表現可為單純自主神經損害。排尿障礙/尿失禁是發生率最高(44.31%)、最顯著的NIID自主神經癥狀。尿失禁可在認知癥狀出現前6~8年發病,50%以上患者需留置導尿管,但同時期的認知功能損害并不明顯[2-3,22]。推測此癥狀的可能原因包括廣泛的周圍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節和內臟器官平滑肌細胞中的核內包涵體沉積[30]。瞳孔縮小是另一主要自主神經癥狀,發生率為31.69%,且易識別,因此對NIID具有診斷價值[31]。
以帕金森樣癥狀為主要表現的NIID患者,多合并出現震顫(28%)、肢體僵直(17.23%)、行動遲緩(4.0%)等。Chen等[32]通過對15個特發性震顫家系的基因檢測發現1個家系15例存在NOTCH2NLC基因的GGC重復擴增突變,其中1人確診NIID。因此,建議將震顫作為NIID或NRRED/NRED的早期鑒別癥狀。
偏頭痛和/或頭痛可作為NIID的首發癥狀,也出現在病程慢性進展過程中。Wang等[33]報道1例NIID病例具有長期偏頭痛病史,發病后呈偏癱型偏頭痛表現。
3.2 影像學表現 成人型NIID具有的影像學表現及發生率如下:皮髓質交界區彌散加權成像(DWI)高信號(68.0%)、白質腦病(44.0%)、腦室擴張(19.08%)、皮質MR增強(2.46%)、小腦萎縮(1.85%)、皮質病變(1.23%)、小腦(1.23%)及胼胝體壓部(1.67%)MR高信號。
頭顱MR出現皮髓質交界區DWI高信號是最為典型的影像學特征。DWI高信號多位于額頂顳葉皮髓質交界區,隨著病情進展向大腦后部延伸。因其選擇性累及弓形纖維而不累及深部白質區域,該特征被命名為皮質下“綢帶征”(subcortical lace sign)。在三項涵蓋家族型NIID的研究中,分別有37.5%、45.7%和81.8%的患者具有該特征,而散發型NIID的患者中個別病例無這種異常改變[2,4-5,22]。綢帶征的總體發生率為68.0%,對NIID診斷具有提示作用。既往認為,DWI的異常信號不會消失,但Kawarabayashi等[34]發現皮髓質交界DWI高信號會逐漸消退。因此,單純依靠“綢帶征”進行診斷并不準確,應該結合皮膚活檢及基因檢測來排除其他可能的情況。
腦白質病變,尤其是累及放射冠和半卵圓中心的彌漫性白質病灶,是另一主要影像學特征[31]。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FLAIR)序列和T2序列上可見雙側彌漫對稱白質高信號,范圍涉及整個白質,從腦室周圍深部持續延伸至皮質下區域,尤其是額葉[27]。個別以癡呆為主要表現的NIID患者頭顱MR可單純出現一定程度的白質病變,而無皮髓質交界區DWI高信號。NIID與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合并皮質下梗死和白質腦病(CADASIL)的患病率相似,提示NIID為不明原因的成年腦白質病變的常見遺傳疾病[10]。
胼胝體壓部病變MR表現為DWI異常高信號,早期呈明顯腫脹,晚期輕度萎縮[35]。部分患者甚至先于皮髓質交界區出現單獨累及胼胝體的病灶,提示胼胝體聯絡纖維和皮質下弓形纖維具有類似的易感性[23]。但胼胝體病變發生較少,主要與可逆性胼胝體壓部腦病、Marchiafava Bignami綜合征進行鑒別[36]。
除上述改變外,還可觀察到廣泛的腦萎縮、皮質MR增強及小腦異常信號。不同程度的腦萎縮可隨病程進展逐漸出現[37],包括顯著的腦室擴張和皮質萎縮。皮質MR增強發生率為2.46%。病灶多發于腦后部皮質,在DWI、ADC和T2圖像上同時顯示高信號,強化的同時可伴發皮質水腫,常出現在臨床急性發作期,并與發作性腦病相關。因而需與線粒體腦肌病伴高乳酸血癥相鑒別。Sugiyama等[38]在NIID患者的小腦旁區和小腦腳中部發現了異常高的FLAIR信號,包括小腦蚓部旁及小腦半球中部(蚓旁區)。因此認為小腦的特征病變可能為NIID診斷的早期特征性指標。
3.3 病理改變 核內包涵體可以出現在多種神經退行性疾病、神經遺傳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和肌病中,但不同疾病核內包涵體有不同的特征,在大小、形狀、嗜酸性/嗜堿性、纖絲的直徑和空間排列等方面各有不同。
NIID病理學以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及內臟器官內形成嗜酸性透明包涵體為特征。包涵體的本質是異常蛋白質的聚集,光鏡下可見核內圓形嗜酸性包涵體,電鏡下為無膜結構的致密絲狀材料組成,直徑為1.5~10.0 μm[22]。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核內包涵體易檢出p62和泛素呈陽性[39]。NIID核內包涵體廣泛分布在中樞神經系統(基底節、腦干、小腦和脊髓的神經元及膠質細胞)、周圍神經系統(交感神經節、背根神經節、肌間神經叢和雪旺細胞)及除骨骼肌和肝細胞外的體細胞(如皮膚細胞、腎上腺髓質、腎小管、心肌細胞和平滑肌細胞)中[31]。隨著 polyG蛋白毒性機制的研究深入,也有望使用相關蛋白特異性抗體來識別NIID核內包涵體。
自Sone等[40]發現NIID患者皮膚細胞內存在核內包涵體后,現已廣泛認可皮膚活檢作為NIID病理診斷方法。在對核內包涵體的病理診斷中,需要注意對陽性p62聚集物的鑒別。因為正常皮膚標本的免疫組織化學也可出現個別核內p62團塊樣物質,且p62沒有明確的定量標準。因此洪道俊等[36]建議觀察p62陽性包涵體的數量及其帶暈狀的形態,或結合p62的免疫熒光檢測進行診斷。另外,病理診斷中也需考慮包涵體出現的位置和數量。
4 治療及預后
目前,還沒有治愈或減緩NIID進展的方法,且缺乏對治療藥物的有效評估。在各類病例報道中,主要針對NIID病程中的不同臨床表現進行對癥治療。
治療帕金森型NIID可選用左旋多巴制劑、DR激動劑和抗膽堿能藥物。Vermilion等[41]報道了1例10年病程的青少年帕金森型NIID患者,左旋多巴對其運動癥狀在初期有效,但需注意產生多巴誘導的異動癥狀。聯用金剛烷胺、普拉克索、羅替戈汀等藥物雖可減少運動波動現象,但不能減緩帕金森型NIID運動癥狀的惡化。老年型NIID使用左旋多巴可改善多數患者的震顫癥狀,苯海索對部分患者有效,阿替洛爾則無明確效果[42]。
止痛藥通常可有效緩解NIID頭痛/偏頭痛發作[33]。類固醇激素被用于NIID發作性腦病的治療中,但尚無明確證據證明該藥可改善預后[13]。個別病例中靜脈予以甲潑尼龍沖擊治療,可改善急性起病患者的癡呆癥狀[26]。在呈腦炎樣表現的NIID治療中, 對癥予以甘露醇、甘油果糖等脫水藥物,可減輕腦水腫,改善癥狀。排尿障礙/尿失禁發病早且癥狀顯著,患者往往依賴留置導尿管或進行膀胱造瘺手術,對其日常生活影響較大。控制自主神經損傷、肌無力、異常行為、意識障礙、感覺障礙等癥狀的藥物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因此,普遍認為NIID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且預后較差。對NIID的研究熱點集中在基因調控方面,調節自噬的藥物化合物可能對預防這些蛋白質的毒性積聚具有治療意義[19]。
5 總 結
綜上所述,NIID的診斷關鍵在于認識該病復雜的臨床表現,基因檢查雖提高了該病的檢出率,但診斷仍需結合臨床表現、影像學檢查和皮膚病理活檢。鑒于NOTCH2NLC基因GGC重復擴增突變的重要性,應對毒性RNA功能性增益、多氨基酸蛋白質毒性、甲基化等發病機制進一步研究,拓展對NRRED/NRED、PolyG疾病的認識,以期為NIID治療提供新的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