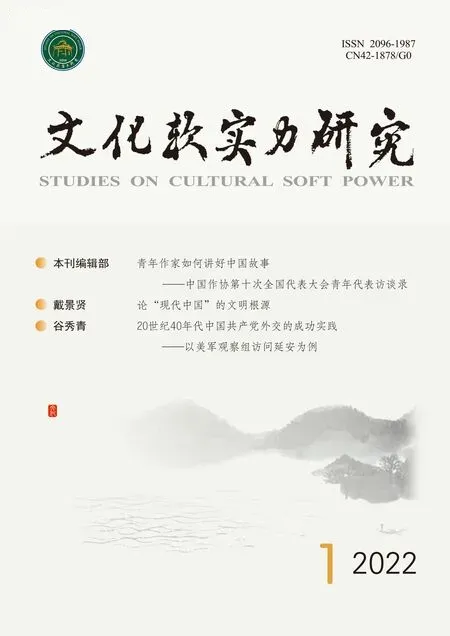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外交的成功實踐
——以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為例
谷秀青
(中南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10081)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轉折,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頻頻制造軍事摩擦與政治輿論上的封鎖,各種丑化、誣蔑中國共產黨之言論層出不窮。為樹立客觀公正的政黨形象,中國共產黨向美國政府發出派團訪問延安的邀請。美國為了與蘇聯爭奪遠東地區的利益,在極力扶持重慶國民政府的前提下,急需了解“中國國共兩黨關系的形勢”[1]984,“精確估計共產黨軍隊的實力”,“減少(中共)對俄國的依賴傾向”,[1]986故而于1944年7月派出了以包瑞德為組長的美軍觀察組奔赴延安[2]9-10。至1947年3月觀察組從延安撤出,美國先后派出一百余人。這是美國官方歷史上第一次與中國共產黨的正面接觸,構建起了美國官方對中國共產黨的最直接印象。本文以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美軍觀察組視野中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主要是八路軍)的形象,揭示中國共產黨公共外交的成功實踐經驗。(1)學界對于美軍觀察組的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原因、作用等。如于化民的《美國向延安派遣軍事觀察組的醞釀與決策》(《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5期)、[美]卡蘿爾·卡特著,陳發兵譯的《延安使命:1944—1947美軍觀察組延安963天》(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二是美軍觀察組人物的研究。如管永前的《美國“中國通”眼中的中國共產黨——謝偉思1944—1945年的延安報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年第2期)等。三是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建構。如彭波的《從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看中共抗戰形象的構建》(《毛澤東思想研究》,2018年第6期)、呂彤鄰的《美軍觀察組延安報告中的日本工農學校》(《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7期),這些代表性的成果整體上勾勒出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原因及其影響,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的基本概況等。然而作為第一批被派遣、地位頗為重要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在學界的研究視野中并不多見。目前關于包瑞德專門性的研究文章主要有兩篇:一是林治波回憶性的文章《包瑞德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的拍照“風波”》(《國防》,1999年第9期)。二是金先宏的《周恩來的美國老朋友包瑞德》(《世紀》,2001年第1期),該文介紹了包瑞德的生平與事跡,以及包瑞德擔任美軍觀察組組長時期的活動。但是學界關于包瑞德對中國共產黨形象認識的研究尚不多見,故而本文以美國國家檔案館新近披露的關于美軍觀察組的資料以及包瑞德的回憶錄等為主要資料來源,探討以包瑞德為中心的美軍觀察組視野中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形象,揭示中國共產黨外交的成功實踐經驗。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形象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直至抗戰結束,在長期動蕩的戰爭環境中,經歷了國內外政治勢力的重重封鎖,其形象在各方勢力的塑造下呈現出多元化特征,既有“革命者”的形象,也有被妖魔化的“赤匪”“文匪”形象,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甚至被誣蔑為“新式流寇”。以致1936年第一位受到中國共產黨許可奔赴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發出這樣的疑問:“他們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不是對于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社會先知,還只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斗的無知農民?”[3]2-5此后一大批中外記者奔赴延安,用他們的筆觸紛紛報道他們視野中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
此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認識,尚停留在模糊甚至偏頗的階段,為客觀重塑自身形象,中國共產黨邀請外國記者、政府觀察團奔赴延安考察。在此背景下,美軍觀察組于1944年7月22日進駐延安,直至1947年3月11日撤離,在延安與中國共產黨前后接觸963天,觀察組組長先后由包瑞德(1944年7月至1944年12月)、莫里斯·埃·德帕斯(1945年1月至1945年2月)、彼得金(1945年3月至7月)、伊萬·D·伊頓(1945年7月至1946年4月)、楊照輝(1946年4月至11月)、詹姆斯·巴勒特(1946年12月至1947年3月)擔任。這其中以第一任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記述最為詳細和全面,其記述和報告直接影響著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觀感。
包瑞德(David Dave Barrett)1892年出生于美國科羅拉多州色恩垂市,1915年畢業于科羅拉多大學后在中學任教,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美國陸軍,此后其人生軌跡與軍事以及中美關系密不可分。一戰結束后,包瑞德被派赴菲律賓,期間接受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培訓,學習四年中文。1924年,來華擔任美國駐華使館的助理武官。其后,又在天津、重慶等地的美國領事館工作,被拔擢為武官。1943年10月,至廣西桂林任職于美軍Z部隊司令部情報處。[4]至此,包瑞德來華工作已滿20年,其在使館、領事館、軍隊的工作經歷使得他對中國國情尤其是軍情應當說十分熟悉,故而作為蔣介石顧問的史迪威將軍推薦了這位“能得到共產黨方面的尊重,而且能說流利的中國話”的“中國通”擔任美軍觀察組組長。[2]28
初到延安,包瑞德等美軍觀察組成員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熱情接待。負責專門接待他們的是“兩位年輕的共產黨官員”黃華和陳家康,“他們是專門派來管理我們的住地,照顧我們的愿望的。他倆都是性格開朗的有禮貌的能干人。尤其是陳家康,更像一個北京學生而不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2]34此后包瑞德分別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彭德懷、陳毅、聶榮臻、林彪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通過與他們談話、參觀軍事演習、聽演講、看戲、跳舞等豐富多樣的活動,包瑞德筆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語言、外形、生活、信仰等方面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
語言方面,領導人講話大多帶有濃重的口音,其中“毛澤東的口語最不好懂。實際上,他的方言,即湖南省湘潭縣的地方語言,甚至許多中國人也難于聽懂。……周恩來的口語講得很好,他是在中國北方長大的。朱德和陳毅的四川方言講起來,對我來說總是那么刺耳和不愉快。葉劍英是一個客家人。……講話帶有明顯的廣州口音。林彪出生在湖北省,也在中國北方,我聽他講話沒有什么困難”。[2]40但就演講而言,包瑞德對毛澤東推崇備至。他寫道,毛澤東“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么就正是毛澤東”。因此,毛澤東是一個“極為好的演說家”。[2]60與毛澤東的演講風格相比,朱德的演講態度“謙和”,葉劍英的演講內容“有吸引力”,而彭德懷的演講顯得“枯燥無味”。[2]36
外形方面,領導人各有特點,且因各自出身、經歷等差異,呈現出不同面向的馬克思主義者形象。1944年7月26日包瑞德初見毛澤東時,“毛先生顯得相當健康,他用一種非常友好的態度來接待我們”。[2]1002跳舞時“毛澤東穿著白襯衫,黑褲子,沒穿制服。他和其他客人一樣,平等地站在隊伍里,準備接受領頭的姑娘的邀請”。[2]65葉劍英“是一位個子較高,英俊精干的人。他總是麻利地出來進去,似乎不像一般的久經戰爭磨煉的共產黨人”。[2]35聶榮臻“看上去既像一位普通戰士,又像一位彬彬有禮、舉止威嚴的人,具有經常參加社交活動者所具有的嚴謹作風”。[2]37而林彪“個子不高,但身板硬朗,有軍人素質,看來他的身體條件是最好的。他看上去有三十來歲,但一定是個老戰士了”。[2]38-39
包瑞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評價,獲得了觀察組其他成員的同感。如謝偉思寫道:領導們大多“青春年華”,“給人以極好的個人印象”。[6]184“由于年輕而精力充沛。作為一個集體,他們都是些活躍而稱職的人;沒有一個人看來是不堅強的、不結實的或懶散的。半饑餓的、貧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不見了;同樣也看不見吃得肥頭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頭的人。這些人從來也沒有享受過舒服的生活”,他們的“知識、興趣、閱歷是多方面的”。[6]197就毛澤東而言,他“彬彬有禮,待人誠懇,神情間也許有一種靦腆含蓄。……他談話機智俏皮,愛用中國古典譬喻,條理分明而又令人吃驚”。[7]
包瑞德等人作為美方代表、美國國家利益的維護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評價,盡管有褒揚,但也時有偏頗甚至歪曲,顯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歷史虛無主義思想。當包瑞德聽取了陳毅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后,其認為“陳將軍不但公開抨擊國民黨,而且在幾杯‘白干’下肚以后,還在一定意義上一般地排外,有時也特別指出美國的不是之處”。故而其寫道:“陳毅給我的印象不太好,至少在我看來,他的外表是不討人喜歡的。他長著一雙從不改變神情的小眼睛——即使是嘴角掛著微笑的時候,眼睛的神情也不改變。”與此同時,包瑞德認為聶榮臻在介紹晉察冀工作時,“對國民黨過多地使用了宣傳性的生硬的語言”。[2]37
生活方面,領導人發揚了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為歡迎美軍觀察組,中國共產黨特意為觀察組成員們修建了高標準的窯洞、餐廳、舞廳等,然在包瑞德的眼中,“室內擺設象斯巴達人一樣簡樸:一張粗糙的桌子,一兩把簡易木椅,每人一張臺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馬上),一個搪瓷洗臉盆架和一個毛巾架,沒有地毯。……晚上是用蠟燭來照明的。房間內外根本沒有什么水管。廁所被安排與住房距離比較適當的地方,這無疑是專門為慣于挑三揀四的外賓們建造的。”[2]33通過對國共領導人的生活比較,包瑞德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生活“是節儉的,依我們的標準看則非常清苦”。[2]118“那里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言辭和行動上都如此。”“衣著和生活都很簡樸,除農民外,幾乎每個人都穿同樣普通的、用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在衣著、生活或接待方面,我們看不見炫耀虛飾的現象。”[6]187故而包瑞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還是由衷地“豎大拇指頭”,贊賞“你們共產黨是這個”。[8]166
信仰方面,領導人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的核心人物,周恩來是最早向美國發出邀請訪問延安的人,也是包瑞德到延安后最先見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其在給美國使館的報告中寫道:“在溫文爾雅的外表之下,周實際上比人們通常認為很堅定的共產黨人還更為堅定。”[2]17-18謝偉思也寫道:“他們都是些具有無容置疑的堅強信念的人。”“在相識中產生的一種有點未曾料到、然后卻是強烈的印象是他們的現實主義和實踐精神。”[6]198美軍觀察組對于領導人信仰的評價在外國記者和傳教士的評價中皆有共識。埃德加·斯諾曾寫道,周恩來“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毛澤東更是強調:“共產黨永遠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標。”[3]45被迫參加長征的瑞士籍傳教士薄復禮在描寫蕭克將軍時也寫道,“憑他的文化教養就可知道,將軍的家境是不錯的,生活是安逸和舒適的,可是他為什么要拋棄這一切而去為被壓迫的農民、為80%的窮人勇敢奮斗呢?……后來我知道,將軍在青少年時代,讀了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并接受了他們的思想觀念,他確認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以他為之奮斗,堅定不移。”[9]
包瑞德等美軍觀察組成員觀感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語言上方言突出,外形上各有特點,生活上艱苦樸素,信仰上是無比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如謝偉思所言,“人們得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總的印象是,他們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一的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于崇高的原則,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堅毅的領導素質。”[8]202
二、八路軍形象(2)美軍觀察組訪問的區域主要集中在以延安為中心的地區,故而本文所指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主要是八路軍。
美軍觀察組考察延安除了構建起直觀的中國共產黨形象,主要目的在于重估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包瑞德坦言,其主要承擔對中國共產黨“有關軍事方面的報導”,例如“估計共軍的力量”、八路軍的“戰術、裝備、訓練、紀律和士氣”等。[2]43初到延安,中國共產黨“軍事和行政官員都明顯地在其權力范圍內盡一切努力與觀察組合作并幫助它”,給包瑞德留下了“一種我以前在中國從未遇見過的極大的主動精神和有條不紊的計劃能力”的深刻印象,故而包瑞德對于考察目的的達成充滿了期待。[5]1002此后通過聆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系列演講、參觀軍隊演習、開展中美情報合作以及觀察組成員開展講座等活動,包瑞德對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抗戰精神與作用、軍民關系、思想教育進行了多方面的書寫。
吃苦耐勞、艱苦卓絕的抗戰精神構成了包瑞德筆下最重要的八路軍形象。包瑞德曾寫道,“在吃苦耐勞方面,共產黨軍隊的優勢超過美軍是很顯然的”。[2]46“他們是優秀的游擊戰士”,雖然百團大戰之后,中共軍隊在“武器裝備方面遭受了十分嚴重的損失”,“但是我相信,經過一些訓練,再裝備以適當的美國武器裝備,他們也完全能夠參加正規的對日作戰。”如1944年7月1日至7日,八路軍在京漢鐵路附近從邯鄲到磁縣一帶,發起三次對日軍的攻擊;7月7日晚,“人民軍”(八路軍)在邢東攻擊日軍,殲滅日軍40人,奪回了被日軍占據長達三年之久的桐花嶺,解放了35個村莊。同一天,在河南輝縣的戰斗中,八路軍攻克了日軍10個軍事據點,殲滅20名日軍,抓獲了80多名偽軍,繳獲了11挺機關槍、80多把手槍和來復槍。[5]2701944年8月20日至30日,八路軍在山東沿海一帶擊斃并俘獲日軍共計1900人,繳獲16挺機槍,207支步槍。8月25日,在山東樂陵殲滅200名日軍,俘獲620名偽軍,繳獲420支步槍,13挺機槍。[5]302-303
這些看似零星、遍地開花式的對日軍的游擊戰爭,卻在抗戰后期狙擊日軍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據美軍觀察組的文件披露,1943年至1944年八路軍共狙擊了64%的在華日軍和95%的偽軍。1945年4月日軍在華人數共計58萬人,其中八路軍狙擊了32萬日軍和80萬偽軍,占據在華日軍人數的56%。[5]436-437
八路軍在抗擊日軍的過程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壯大。以晉察冀邊區為例,1937年至1941年八路軍人數從6500人增加到了160000人,百團大戰后部隊人數減到93000人,1944年增加到108000人。截止到1945年,該地區共有225000名民兵,230000名自衛軍,75000名游擊隊員。[5]426-427就中國共產黨軍隊的總兵力而言,截止到1945年6月7日,正規軍有91萬人,民兵有220萬人。[5]436-437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所轄區域有所拓展。1945年4月30日至5月底,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華中地區共從日軍手中奪回17個城鎮,至此中國共產黨軍隊共計奪回66個城鎮。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域總人數達到9500萬,幾乎占到當時中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所轄軍隊與區域的觀察與數據統計,既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中國共產黨抗戰的決心與成效,也為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形象的樹立提供了數據支撐。
民主團結的軍民關系也給美軍觀察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瑞德曾言,“在延安,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都沒有一個衛兵。在毛澤東簡陋的住處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崗,這對于一個偶然的過路人來說,也是不顯眼的。”而重慶國民政府隨處可見“警察和衛兵”;“毛主席在公開場合出現時,他經常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輛封閉式救護車。”“在重慶,當委員長從街上穿過時”,總是被衛兵和便衣人員組成的“封鎖線包圍著”。[2]109延安民主寬松的政治氛圍在謝偉思的報告中也有書寫,“這里到處都強調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魚水關系。這一點在他們的文化工作上也表現出來。”[6]183
正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始終堅持“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使得民眾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最為重要的力量依靠。包瑞德提到,與美國“使用偵查員和巡邏兵”獲取情報不同,八路軍“很少強調偵察、巡邏、搜索和其它收集情報”的方法,因為“當地居民總是找到好機會獲得關于敵軍的重要情報,并且很愿意把情報報告給共產黨軍隊”,可以說“共產黨正在得到全國人民支持”。[2]46且人民群眾提供的情報信息相對迅速準確,如包瑞德所說,東京報紙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2]42
重視思想學習與改造也是八路軍的重要特色。對于軍隊的思想學習,包瑞德自始至終是反對的,正如其在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不喜歡政治委員”,“我從來未能克服自己對軍隊中政治工作者的反感”。因此,當他聽聞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對士兵們進行教育,以堅定他們的忠誠”,曾把“一個廢倉庫上撕下來”的宣傳材料“貼在前面一名士兵的背上以供跟近人之閱讀”的事件時,覺得不可思議。[2]115同時作為一名武官,參觀培養中國共產黨軍事和政治干部的學校——抗日軍政大學是包瑞德延安活動的重要議程。去延安之前,包瑞德想象中的抗日軍政大學“應該是一個軍事訓練中心”,參觀之后發現,“學校里不進行任何關于軍事訓練的教育”,“不講授任何軍事課程,實際上是一個休養和思想改造中心”。學校課程的這種安排在包瑞德看來是“這所學校的根本性錯誤”。但是其也坦言,“思想教育畢竟是(共產黨)一個最需考慮的重要問題”。[2]51
中國共產黨對日軍戰俘也開展思想改造,成功地使戰俘志愿對日軍開展反戰宣傳。抗戰時期延安地區成立了日本工農學校,專門招收被俘獲的日軍。中國共產黨通過優待戰俘等政策以及身體力行的實踐行動,成功地使數百名戰俘思想發生轉變。思想轉變后的日軍戰俘通過散發傳單的形式宣傳反戰思想。如1945年1月,華中地區的日本戰俘印刷了日文版的“解放周報”,張貼在日軍經常出沒的地方。2月10日,12名日軍士兵爬到華中地區一個山坡上看到了一份日軍戰俘張貼的“解放周報”,紛紛湊上前去觀看,后被日軍指揮官驅趕,但因思鄉心切,一名士兵仍情不自禁地把宣傳報偷偷撕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3月9日寧波光明戲院日軍觀看專場電影時,戰俘趁機散發反戰傳單。[5]4283月底,日軍戰俘又在山西省一日本據點附近的集市散發反戰傳單。[6]418后來,日軍戰俘加入日本人民解放聯盟,使得反戰宣傳更具有組織性和戰斗性。[5]428
對于八路軍的訓練方式,包瑞德頗有微詞。在觀看了八路軍120師359旅的軍事演習后,包瑞德寫道,這支軍隊雖然“顯得很年輕,并且裝備良好。除了膠底布鞋以外,他們還穿著較好的制服”,但在訓練方式上與“美軍顧問訓練以前的國民政府軍的訓練方式相類似”,“太拘泥于形式了,沒有什么價值”。[2]45而且八路軍物質條件差,即便美國觀察組成員科林上尉給八路軍進行“爆破演示”,這“對于共產黨軍隊來說,也不會有多大價值,因為他們并不像我們的軍隊那樣,擁有足夠的非常昂貴的爆破材料”。[2]53
盡管如此,在戰爭環境極端惡劣、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時代背景下,“他們(中共)正在盡一切可以預料的努力與日軍戰斗”[2]108,這與重慶政府“把很大力量用于同共產黨之間時常發生的摩擦,而不是把全部力量都用于對日作戰”[2]27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在包瑞德看來,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抗日決心最堅決,“應當給予共產黨少量的步槍、機槍、迫擊炮、反坦克炮和一些輕炮,裝備上這些武器之后,完全可以期望他們提高游擊戰爭的效力。如果他們充分利用這些武器裝備對日軍作戰,我建議再進一步向他們提供更多的武器裝備。”包瑞德相信,這種建議“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傾向于贊同”。[2]120
三、中國共產黨成功外交經驗
由上文可知,盡管以包瑞德為代表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認識,仍然存在一定偏頗之處,如對于八路軍的思想政治工作、訓練方式等,但整體上“抗日、民主、團結”的正面形象給其留下深刻印象。這一結果實與中國共產黨開展的積極外交密不可分。
一是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任務,確立外交方針,做好外交工作部署。
實現中華民族解放,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歷史任務,邀請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不僅是建構中國共產黨客觀形象的迫切要求,更是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贏得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民族解放的重要步驟。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區黨委下發《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后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后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為普通行動,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10]同時,在與美軍觀察組接觸中,我們要積極主動,站穩民族立場,堅持“國際統一戰線”政策。在接待美軍人員的方針上,一是“要講原則,堅持我們的立場,決不無原則的讓步”。同時對于美軍觀察組人員提出的問題,“凡屬在我們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開誠布公地交換”。二是生活上,“我們要熱情周到,給他們予優待和照顧,使他們適應延安的環境”。[8]166中國共產黨周到的安排獲得了包瑞德的肯定,其寫道,“在延安,共產黨人十分關心我們的伙食安排”,“在吃飯時,常有一個或幾個共產黨領導人來看望我們,他們通常也接受邀請,和我們一起就餐”。[2]70
二是利用媒體平臺,掌握輿論的話語權。
1944年8月15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歡迎美軍觀察組戰友們》一文,可以視作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形象最為重要的詮釋。在該文中,毛澤東指出,國民黨在抗戰期間“一不許共產黨發表戰報,二不許邊區對外銷行,三不許中外記者參觀,四不許邊區內外人民自由來往”。“國民黨的丑詆、惡罵、造謠、誣蔑,向世界橫飛亂噴,決不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真相稍許透露于世”,正是由于“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影響了世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感。[11]毛澤東用中國共產黨抗戰的事實講好了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影響了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的印象。
三是通過談話、演講等形式,積極塑造中國共產黨形象。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期間,中國共產黨開誠布公、竭盡所能提供美軍所需之情報,安排領導人與美軍觀察組成員頻繁地交流與溝通,塑造出了客觀積極的中國共產黨形象。如包瑞德寫道,其在延安聽取了毛澤東、葉劍英、彭德懷、林彪、陳毅、聶榮臻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于革命根據地的開創、抗日情況、國共關系等演講,使得包瑞德較為全面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形象。謝偉思在其初到延安時,一星期內有兩三次與毛澤東談話的機會,據其統計,僅僅前四個月其與毛澤東的談話就進行了50余次。[7]
中國共產黨開展的積極外交活動,贏得了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的刮目相看。周恩來后來曾說:“美國人為什么這么尊重我們呢?一是我們與美國是盟友,幫助美國人做出許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團結抗日,不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氣。美國人佩服我們哪!”[8]163因此,在塑造中國共產黨形象的途徑上,我們在積極宣傳自己的政策方針時,還需完善自身建設,依據事實,講好中國共產黨乃至中國故事。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者認識的構造往往還摻雜有他者本身價值觀念、自身利益的考量。因而隨著冷戰格局的形成,以包瑞德為代表的美國政府對于共產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又抱有敵視態度。如包瑞德在其后來出版的著作中寫道:“紅色中國成為了我們所生存之世界中最危險的敵人”,“共產黨人就是共產黨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可能輕易和平共處”。[2]1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