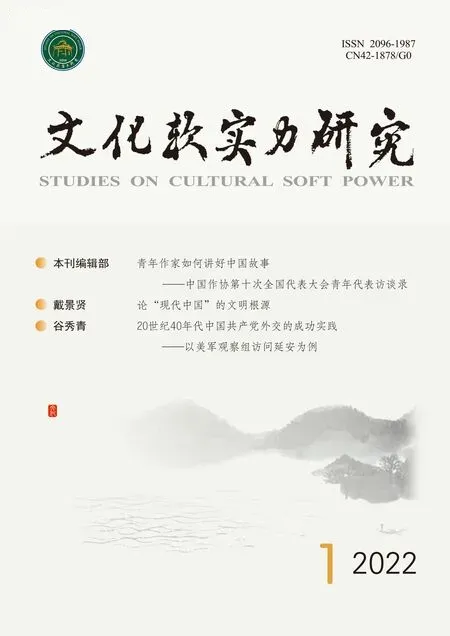試論語言雅俗與國民語言文化素養的提升
石紹浪 魏 暉
(北京語言大學 語言科學院,北京 100083)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的要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20〕30號)提出“開展國民語言教育,提升國民語言文化素養,提高國民語言能力。”語言文明是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國民語言文化素養是國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語言領域的應用情況出發,總結當下語言生活存在的突出問題,嘗試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并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提出若干建議。
一、當下語言生活在雅俗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網絡語言低俗化現象嚴重
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數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為70.4%(1)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網絡已成為當代人重要的生活方式,網絡生活催生了網絡語言。由于在文字、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的鮮明特點,網絡語言已經成為網絡空間的“共同語”。網絡語言更新傳播速度之快、影響范圍之廣,堪稱“語言史上的一場革命”。
網絡也正在成長為一種新的語言文化資源載體。網絡語言文化作品大致有音頻、視頻、文字、圖像四大類。這里,我們以網絡小說為例來討論網絡語言問題。
我國網絡小說發端于上世紀末,經過20多年的“野蠻生長”,網絡小說業已成為獨特的文化奇觀。至2016年,40多家文學網站的作品總量達到1454.8萬部。至2017年12月,僅閱文集團一家的網絡作家就有690多萬人,收錄作品超過1010萬部。[1]一些優秀的網絡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為更多人所熟知,如《步步驚心》《瑯琊榜》等。有一些仙俠類和愛情類的網絡小說很受國外年輕人追捧,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全球傳播。至2019年底,我國以翻譯出海、直接出海、改編出海等方式向海外輸出網絡文學作品1萬余部,覆蓋40多個國家和地區。(2)根據《2020網絡文學出海發展白皮書》。“隨著其海外傳播規模逐漸擴大,開始進入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反哺階段’,有望與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等全球流行文藝一樣,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能夠代表本國特色的文化輸出力量。”[2]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講話指出:“文藝要通俗,但絕不能庸俗、低俗、媚俗。”網絡小說走的是低端路線,“零門檻”帶來了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這是值得肯定的。網絡小說屬于“快餐式”文化,缺點同樣突出。網絡小說網站對簽約作家的更新進度大多有嚴格的要求,不給作者預留推敲打磨的時間,故粗制濫造的比例極高。多數小說靠離奇的故事、夸張的情節和媚俗的語言來吸引讀者。作品的審美價值普遍“低開低走”,幾無“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根骨和底氣[1]。
對于中文,網絡是一把雙刃劍。首先,網絡語言追求新奇、幽默、夸張的效果,特別重視修辭與創新,不斷促生新詞,極大推動了共同語詞匯系統的豐富和發展。其次,語言暴力、語言霸凌、語言歧視等問題難以禁絕,語言低俗化、粗俗化現象嚴重[3-7],并間接影響到國家通用語的。像“尼瑪、屌絲、撕逼”等生活禁忌詞,經過網絡再進入口語,成為一代年輕人的口頭禪,甚至被傳統紙媒頻繁使用。第三,網絡社區自創新詞或賦予舊詞新的語義,形成交流鴻溝。如“不明覺厲”“安利”“種草”等,知道其網絡意義的人占比很小。
針對網絡語言的這些問題,2015年開始,人民網連續發布《網絡低俗語言調查報告》,呼吁廣大網民自覺凈化網絡語言環境。2020年8月,教育部等六部委聯合發文批評網絡游戲社區以辱罵代替問好的“祖安文化”。國務院辦公廳頒發的《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強語言文明教育,強化對互聯網等各類新媒體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和管理,堅決遏阻庸俗暴戾網絡語言傳播,建設健康文明的網絡語言環境。”
網絡語言低俗化現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英語、法語、阿拉伯語、俄羅斯語、西班牙語等也都面臨類似的“威脅”[8-10]。如何規范網絡世界的語言,目前尚無成功經驗可循。西班牙于2012年推出了第一本網絡語言使用規范手冊——《寫在網絡:新媒體與社交網書寫指南》,就即時通信、電子郵件、撰寫博客、網絡交友、對話語表達與網絡設計等提出建議性意見。
(二)城鄉標語鄙俗化趨勢突出
我國標語文化起源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起初主要用途是革命動員、宣傳鼓動。建國后,內容則偏向政策方針的宣傳。因其發布主體一般是政府職能部門或部隊,具有權威性,故多使用正式規范的書面語體。1990年代以后,標語制作主體范圍明顯擴大,企業、學校、單位、個人出于各種目的,也加入標語制作隊伍。標語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成為一種非常有時代特色的城鄉語言景觀。同時,標語的行政色彩漸淡,廣告色彩漸濃,口語化傾向明顯。出現了很多幽默調侃、用詞夸張的標語,像“今天你踩我頭上,明天我長你墳上”(公園草地)、“事故就是‘兩改一歸’,老婆改嫁,孩子改姓,財產歸別人”(建筑工地)等。
在抗擊新冠肺炎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標語。從規范和“得體”的角度回頭審視這些標語,宣傳思想工作類的標語大多比較規范;非常口語化的提示性標語,大多延續了調侃風格,有的確實比較輕松詼諧,但也有不少修辭不當、言不得體,甚至滑稽、鄙俗。比如,“今天走親和訪友,明天家中剩條狗”“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
2020年1月,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給湖北高校捐贈物資,外包裝上除了兩國國旗、“加油中國”外,還有一句古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其創意來自中國赴日留學生)。這個化用古詩的標語很快上了網絡熱搜,好評如潮。之后,又出現了一批類似標語,如“豈曰無衣,與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等。
文言文時代,經常要借用古雅詞語,以實現“莊敬”的表達效果[11]。在今天的中文體系中,古詩詞和古語詞也具有“莊敬”修辭功能,“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走紅實際上是中文“莊敬”語體規則在起作用。再回顧2008年汶川抗震,除“汶川加油”和“四川加油”外,似乎沒有其他印象更深刻的口號標語。“加油”是個新生詞,它不能勝任抗震救災對語體的要求。
(三)大學生母語書面語表達雅正不足
母語通常指一個人最初學會的語言,本文指中文。關于母語能力的內涵,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12][13],李宇明[14]根據語言的社會功能,將公民語言能力(主要指母語)概括為“三語層三語體”,即:“文化語言層、主要交際語言層、發展語言層”和“口語體、一般書面語體、典雅語體。”
根據載體不同,我們可將母語分為口語和書面語。前者以語音為載體,后者以文字為載體。因我國大多數地區存在方言,故口語能力包括方言能力和普通話能力(民族地區則為民族語和普通話)。趙元任根據語體(也稱“語體色彩”),將書面語分為“俚俗級”和“典雅級”,兩者之間還可再分出一般口語、正式口語、一般書面語[15]。
上世紀90年代開始,高校學生母語寫作水平下降的“警報”不斷在媒體上出現[16-22]。母語寫作水平低集中表現在日常作業和畢業論文上,錯別字、語法錯誤、格式錯誤、邏輯混亂等錯誤類型五花八門[23]。賀陽等[24]對清華、人大、北外和中戲四所高校在校本科生母語能力進行抽樣測試,結果顯示“學生漢語語文基礎薄弱”,在319位大學生中,測試成績在70分以下的占68%,60分以下的占30%。“書面表達能力不足”,74份中國人民大學“大學語文”課程“自薦信”作業中,49份存在行文格式問題,占比66.2%;64份存在表達語氣與自薦信要求不符的問題,占比86.5%;語法方面的問題更為突出,每一份樣本都存在搭配不當或虛詞誤用等問題。另在一些國際中文比賽中,當代大學生也沒有表現出特別明顯的優勢。如國際大學群英辯論會(前身是國際大專辯論賽)從1993年至2011年,共舉辦了十屆,其最重要的“全程最佳辯手”獎,四屆由中國臺灣選手獲得,一屆由中國澳門選手獲得。
1998年,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國家技能振興戰略》中把職業核心能力分為“與人交流、數字應用、信息處理、與人合作、解決問題、自我學習、創新革新、外語應用”等8項。中國就業促進會原副會長陳宇指出,“母語能力(與人交流能力)決定了其他各項能力的表現。”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人,職業成功的決定要素是母語水平,而不是外語水平[25]。潘文國認為,“母語能力是外語學習的天花板”。
關于母語書面語合格的標準,李宇明[26]概括為“雅正”,劉楚群[27]提出“中和誠雅”的觀點。遺憾的是,目前高校學生母語書面語整體水平“正”尚不足,“雅”更難求。
(四)小結
以上語言生活現象反映,當下語言應用總體上俗化過度、雅正不足。
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化也有賴于語言進行傳播。許嘉璐[28]把文化分為表層(物質文化)、中層(制度文化)、底層(哲學文化)互相關聯的三個層次。在傳統文化觀念中,每一層的文化形式還存在雅俗的分別,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則更為明顯。雅與俗的特點和社會功能不同。雅文化加工細致、欣賞者少,具有規約性;俗文化加工簡單、與原生態接近、容易取悅受眾,具有趨同性[29];雅與俗互補存在、互動循環,共同推動文化的前進。有兩點需要補充強調。
首先,俗語有俗語的用處,如果用對了語境,它能解決用雅言、大道理解決不了的問題。《呂氏春秋》里有一則小故事。孔子率弟子出游,拉車的馬跑了,吃了當地人的莊稼。農夫把那匹馬扣留下來。子貢前去交涉,沒有成功。換馬夫去,三言兩語便說服農夫放了馬。那位農夫說,“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向之人?”意思說,說話就要這樣清楚,怎能像剛才那個人那樣(不清不楚的)?孔子說,“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本文“俗化過度”是指俗語沒有用對語境或缺少雅俗觀念。
其次,雅言是國民的潛在追求和愿望。宋畫中有一幅“二我圖”,畫面主體是一榻一屏,榻上坐著一位方巾文士,榻下有童子、酒盞、茶具、果盤、鮮花、硯臺、書籍。屏風上繪汀洲蘆雁圖,并懸掛該文士畫像一幅。寓意是完整的人生既有物質的需要,也有精神的追求,互為表里。與之類似,國民語言需求也存在不同層面,既有日常通俗層面的,也有精致優雅層面的。本文“雅正不足”是指以俗為雅或缺失“雅正”的表達能力。
二、俗化過度、雅正不足的原因探析
(一)雅言、俗語溯源
先秦時期,漢語以“夏”言為正為雅,“夏”的周邊方言是俗語。推測,夏言與通語音比較接近,或許本身就是通語。文言文起初記錄對象便是先秦口語(雅言)[30],后代詔書、律令等公文都是使用文言語體[26]。
南北朝時期,傳統雅言已經明確分化為“金陵”“洛下”兩大流派(顏之推《顏氏家訓·言辭篇》)。這種分化一直持續至明清時期的“南、北官話”。明清兩代長時間以南官話為正音,清中期開始,情況才開始轉變。北官話在通用語層面逐漸強勢,并取代南官話,成為正統官話。
隋唐時期的正音體現在《切韻》音系中,經過《禮部韻略》(1037年)、《集韻》(1039年),至《壬子新刊禮部韻略》(1252年)和《平水新刊韻略》(1229年),漢語雅言正音被簡化定型為106韻的《平水韻》。它是傳統詩歌創作的語音依據,也是舊時科舉考試的語音規范。唐宋以后,它一直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不過,它只規定了音類,缺少具體音值。而漢語方言受移民和民族融合的影響,一直在變化,方言間差異在不斷加大,各地方言與書面語正音的脫節越來越嚴重。于是,不同時期、不同方言背景的韻書所描述的官話音不得不在方言和傳統正音之間來回搖擺,有的取方言音多點,如《古今韻匯舉要》《李氏音鑒》等,有的更靠近傳統正音,如《洪武正韻》《韻略易通》等。
古人用雅言正音(官話音)讀書是個傳統,“四遠皆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后為正。”(3)語出自明陶宗儀《說郛三種》卷五《談選》。不過,傳統正音因為缺少明確口語標準,一直無法真正落實,致使“讀書音”實際上更接近方言(文讀音),跟今“地方普通話”類似。新中國普通話的確立和推廣,才徹底解決了這個千年難題。
古代能使用文言閱讀和寫作的只有少數讀書人,但文言文是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載體,經史子集,農工百科,甚至音樂繪畫,概無例外,以至于其本身都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跨方言的溝通能力,超時空的存儲功能;它也是現代漢語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深入理解、準確解釋現代漢語的基礎和鑰匙[30]。王寧[30]、劉丹青[12]、陸儉明[13]都認為國民母語能力應包括文言文閱讀理解能力。
文言文是個歷史綜合體。不同時期的文言文在詞匯、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即使是受過訓練的讀書人,研讀前代文言文也存在一定難度。“漢初距周平王東遷幾百年,一般人已經很難讀懂先秦的文獻,需要專家進行注釋了……(唐代)當時的人對漢朝人給先秦典籍作的注釋已經感到生疏,又要請專家進行二度注釋。”[30]同一時期的文言文,因創作目的不同,語體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越是嚴肅莊重的文體,古代成分占比越高[31][32]。
古人日常交流使用的語言是方言、俗語。大量口頭文學和民間藝術是以口語的形式代代相傳(部分兼以文字形式流傳),如民間歌謠、民歌、變文、鼓子詞、諸宮調、散曲、寶卷、彈詞、鼓詞、子弟書、地方戲等,鄭振鐸[33]名之為“俗文學”。這些民間文學活躍在廣大鄉村和城市瓦肆,是普通民眾主要的精神食糧。唐代傳奇、話本,宋元戲曲,明清小說都是“俗文學”這個土壤上結出的碩果。這些作品使用的白話,與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白話一脈相承。
從雅俗角度看,漢語書面語由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也是雅俗兩種文化競爭的結果。
(二)歷史原因
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是民族自救、國家現代化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是一場革命,所以主張和措施都比較激烈。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黎錦熙等都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漢語拼音化。他們對文言文的態度更是全盤否定,只有魯迅等極少數人例外[34]。
白話文運動對文言文采取“突然死亡”法,在很短的時間,以口語和西式語法相結合的方式建立了白話文體系,表面成功的背后也給白話文留下了一些歷史難題。其一,白話文雖然以成語等方式繼承了一些文言文詞匯,但主體來源于口語,導致其先天性典雅不足。其二,文言詞匯與中國人文價值觀之間形成的穩定結構,事物名稱與意象之間形成的中國式審美意趣,白話文繼承的很有限,致使白話文對某些語境下的表達難以令人滿意。比如,傳統文化強調尊人卑己,提及對方及對方有關的東西要使用尊稱、敬稱,自己及自己有關的東西使用謙稱,名詞有系統固定的表達,如“令尊、家父”“令郎、犬子”等。與人相處強調把自己置于低位,動詞有固定用法,如“垂愛、仰慕”“俯允、遵命”。在藝術創作中,喜曲不喜直,一些名物有多種表達方式,之間有微妙的差異,如“九月”也稱“菊月、霜序”等。還有各種委婉用語,如“如廁”可用“更衣、凈手”[35]。而這些禮儀要求和價值觀念作為民族文化的核心基因,一直延續至今,并未改變。其三,白話文語法與文言文相互抵牾,難以真正調和,形成了中文書面語的“代溝”。其四,白話文“寫話”主張影響深遠,多數人拘泥于口語,不敢逾矩,擔心被批為“復辟”“復古”。
我們應該看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參與者都受過系統文言文訓練。民國和新中國初期,出現了一大批文筆優秀的作家,像魯迅、汪曾祺、楊憲益等等,他們都有極好的文言文基礎。大約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文學創作語言出現一股粗鄙化潮流,泛濫至今[36],文筆優雅的作品難得一見。客觀上,可能與文言文基礎的缺失有一定關系。
文言文退出書面語也影響了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傳統詩歌面臨徹底失傳的風險;書法失去創作新內容的能力(只能抄寫古詩、名句);國畫創作失去用詩歌點睛的能力;戲曲舞臺演出反復“炒冷飯”。
新文化運動為了推行白話文,對文言文的態度和做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可厚非。百年之后,我們反思這場運動,其偏激與草率也是顯而易見的。白話文本有口語、西式語法和文言文三個來源。“漢語莊雅語體的表達方式都來自于文言。”[35]因此,在今天白話文作為書面語體的地位非常穩固的前提之下,應考慮給文言文提供一個可延續生存的空間,畢竟現代漢語典雅語體的重建離不開文言的加持。
(三)時代原因
二戰以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長期由美國主導。在這樣形勢下,幾乎所有大的語種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文化及英語的滲透,中文也不例外。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網絡在全球的普及,網絡語言粗俗化、網絡暴力也是世界各國共同普遍面臨的問題。
中文本身是個多元、異質、包容的體系,曾經大量吸收佛教詞語、從日語借詞、從其他民族語言引入詞語(4)根據《佛學大詞典》統計,漢語中與佛教有關的詞語多達35000余條。基于《漢語外來詞詞典》統計,漢語借詞總數為7971,分別來自83個國家和民族的語言,其中,從日語借詞總數是850個。[37]。全球很多語言也都是如此,像韓語、日語也都有大量的漢語詞匯和英語詞匯。也就是說,語言系統多元是常律,“純粹”“純潔”是反常規的。所以,看待當下語言生活中雅俗問題的視角要客觀、歷史、多維。
(四)“教”方面的原因
目前中學教育階段的語體知識過于簡單,發揮不了指導作用。現代漢語書面語并非口語的實錄,之間有相當大的距離。兩者不僅功能不同,詞匯系統和語法系統也不同(5)馮勝利將書面語法的特點總結為“嵌偶詞、合偶詞、書面語句型、文言虛詞”三項,并且做了窮盡式歸納。另外,很多詞匯本身就帶有語體屬性,如“父親、爸爸”。。如果將兩者混同,特別是將口語的詞匯和句式當作書面語來用,必然會降低文章的典雅程度。
早期,西方人學習中文時,重點是書面語。明清時期,西方教會分別在北京和南京設有語言學校,傳教士(6)根據哈利《百年前的中國》,十九世紀20年代,中國境內至少有10000名西方傳教士。根據將要赴任的地區,選擇學習南官話或北官話[38],而教士們學習的書面語是文言(不是白話)。利瑪竇、金尼閣[39]說,“中國人把絕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書面語上,而忽視口語。”“在風格和結構上,他們的書面語言與日常談話中所用的語言差別很大……”
重視書面語、輕視口語的傳統對西方的漢學研究和中文教學的影響很大,持續時間很長。如芝加哥大學,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一年級二年級的主課還分別是《孝經》《論語》和《孟子》《史記》。這種教學方式下,培養了一批能閱讀古籍,而不太會日常交流的“啞巴”漢學家。趙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學教授中文時改變了這個傳統(1922年),將口語教學引入美國中文教學,編寫了《國語入門》和《中國話的讀物》,教學生“可說的”(sayable)漢語。趙先生同時也非常重視書面語,他為哈佛大學中文部定下的教學宗旨是“說地道漢語,寫典雅文章”。這個宗旨一直被哈佛沿用至今,低年級課程以口語為重點,高年級以書面語為重點。
海外華人中文教學、國外中文教學和我國臺灣、香港及澳門地區的中文教學所使用的教材、教學重點各不相同。與之相應,我國臺灣、香港及澳門地區傳統公文以及海外華人和海外漢學家現在還經常會使用文言詞語和文言句式,內地反而不太常見,這在典雅性上便形成了一定落差。這個問題需要重視,否則可能會影響我們在國際中文教育領域的主導地位。
在文言文為書面語時期,“雅正”是書面語規范的重要標準和目標,強調“文章爾雅,訓辭深厚”(7)語出自《史記·儒林列傳》。。進入白話文為書面語時代,特別新中國建立之后,語言規范強調“正”更多,較少顧及“雅”[26],這與建國初期國內教育水平低、文盲率高等客觀因素有關。經過九年義務教育的推廣普及,文盲問題現已基本解決,城鄉居民的語言文化水平發生了質的飛躍。李宇明[26]指出,進入新的時期,語言規范應當“正”“雅”并重,重建典雅語體,完善書面語的語體結構和表現力。
“雅”“正”并重就意味著要重視語體區別。外國人學習漢語時,經常會被語體問題困擾。“在漢語國際教育領域,學習者可以熟練運用漢語的口語,但在書面語表達方面,因為缺乏莊雅語體表達方面的訓練,在莊雅語體的表達方面總是不知所措,即便向老師請教如何能夠得體地使用比較典雅的表達方式,許多老師也不知所以。”[35]盛炎[40]、常敬宇[41]、丁金國[42]、李泉[43]等都呼吁將語體教學引入來華留學生中文教育。目前,關于漢語語體的研究已經比較系統,在美國部分高校的中文教學中也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把語體概念引入國際中文教育的條件已經比較成熟。國內語文教學也應該借鑒相關研究成果,適時豐富語體知識體系,培養學生的語體意識和語言雅俗觀。
(五)“學”方面的原因
學習層面的原因,研究頗多,我們將其概括如下。
首先,對母語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與文言文時代相比,當代學生在對母語書面語的重視程度、學習時間、學習深度及系統性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中學階段受高考影響,學生更重視數理化的學習,因為數理化得分差距大,語文分差小,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學階段,為了畢業和就業,學生要用大量的時間學習專業課和英語。出于這些“實際”需要,學生對母語的重視程度普遍偏低。而相關研究表明,語言能力與工作機會和勞動收入呈正相關;語言對于智力開發、文化修養、情商培護等都有重要作用;書面語的使用能力更是影響人的知識建構、信息獲得與加工思維的能力與品質[14]。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人們在使用語言的同時,即在用語言塑造自己的個人形象,母語水平及其雅俗屬性不該等閑視之。
其次,學習主動性不夠。日常口語可以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自然獲得,但優雅書面語必須經過主動學習和長期積累才可能習得。大部分大學生學習母語的主動性不夠,投入時間精力亦有限,書面語“雅正難求”是必然結果。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寫作實踐是個很好的正面例證。自1986年開始,中山大學中文系一二年級本科生都要完成“百篇作文”“八篇書評”(8)中山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系列課程是“百篇作文”“八篇書評”“百篇朗誦”。起初“百篇”是150篇,1989年后改為100篇(中山大學中文系,2015)。的寫作訓練,經過三十多年不懈堅持,中大中文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已經形成了品牌優勢。
三、提升國民語言文化素養的幾點思考
中華民族的崛起必將伴隨中華文化的復興。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武夷山參觀朱熹園時指出,“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承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提升國民語言文化素養,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時代要求。以下是我們對此的幾點思考。
(一)提高國民思想道德修養
“志高則言潔,志大則辭宏,志遠則旨永。”(清代,葉燮)思想和價值觀(底層文化)引導并制約著表層和中層文化的變化[28]。如果缺少思想道德基礎,所謂“雅好”“雅行”只能徒有其表,附庸風雅。以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為基礎,逐步提高國民的思想修養和道德水平是創造新時代民族文化、提高全民語言素養的前提條件。
(二)凝聚社會共識,樹立新時代語言雅俗觀
我國傳統社會是個多元自足、“表層、中層、底層”三個層次相互適配的文化形態。晚清以降,西方列強入侵,國人因軍事、經濟、科技上的落后,引發文化上的自我懷疑和價值觀上的自我否定。以西為雅、以洋為雅,盛極一時,而本民族的一切幾乎都被貶為落后或土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改革開放成功證明,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蘊藏在中國文化自身。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極大提升了國民的自信心,以洋為雅已成為歷史陳跡。民族文化各個層面正在重新建構。一方面,大量吸收了外來文化,為我所用。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中既重視內在修養又強調社會責任的君子文化重新成為民族文化的基石。為適應文化發展,我們必須樹立新的語言雅俗觀。
首先,要有雅俗共存觀念,不提倡孤立于世的“雅”,也不提倡低級趣味的“俗”。其次,判斷雅俗的標準是內容,不是形式,其核心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否相符。第三,雅與俗不是對與錯的關系,也不是高與低的關系,而是兩種都要具備的語言能力,重在得體,重在有利于溝通交流。該俗時則俗,該雅時能雅。
(三)建立母語能力立體化結構
為實現國民語言文化素養的真正提升,我們必須深化對母語的認識,建立母語能力立體化結構,做到四個“區分”,即:(1)區分雅與俗。不能扁平化地看待母語能力,雅俗不分;(2)區分口語與書面語。書面語雖以口語為基礎,但不能簡單將兩者劃等號;(3)區分語體。動手寫文章之前,要先根據需要進行語體規劃,選詞造句要圍繞這個規劃進行;(4)區分語言應用與語言本體。書面語大致有雅俗兩個層面表達方式,但形不成一一對應關系。對于不能對應的部分,要區分是語言本體的問題,還是語言應用的問題(比如第二人尊稱“您”,第三人稱沒有相應尊稱,只能用“她”,這是語言本體的問題;面稱對方女兒,尊稱可以是“令愛”,如果仍選用“女兒”或“閨女”,這是語言應用問題)。語言本體上的問題可以采用通用語體,最好是從文言中借鑒,文言文的雅俗體系非常完備。語言應用上的問題則要通過多讀書、多積累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