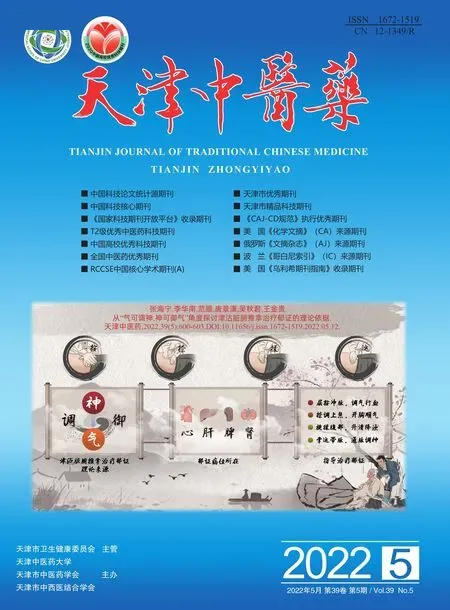馬融教授“審因辨治”抽動障礙驗案舉隅
石海娜,馬融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381)
抽動障礙(TD)是起病于兒童或青少年的一種神經精神障礙性疾病。以不自主、反復、突發、快速的,重復、無節律性的一個或多個部位運動抽動和(或)發聲抽動為主要特征[1]。以運動性抽動和發聲性抽動為主要臨床表現[2]。TD病因及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目前研究顯示抽動障礙的發生與生物學因素(遺傳因素、免疫因素、神經生化因素、微量元素失衡、圍生期異常等),精神心理因素(家庭氛圍、教育方式),其他因素(藥物因素、頸椎損傷、食物攝入不合理)等相關[3]。中醫古籍中無此病名的記載,根據其臨床癥狀,中醫屬“肝風”“慢驚風”“抽搐”“瘛疭”“筋惕肉瞤”等范疇。馬融教授從事中醫兒科臨床、科研、教學工作30余年,對兒童腦系、精神類疾病有著獨到見解,臨床經驗豐富,擅于分析患兒發病誘發因素,對癥針對治療。現將馬融教授“審因辨治”小兒抽動障礙驗案1則分享如下。
1 典型病案
患兒男性,15歲2個月,2020年7月14日初診。主訴:間斷點頭、伸胳膊伴喉中異聲3年,加重1年。患兒3年前因情緒抑郁出現面部肌肉抽動,就診于天津某醫院,查腦電圖(2018年12月5日)示:正常腦電圖,考慮“抽動障礙”,予相關營養神經類藥物治療(具體不詳),癥狀未見緩解,后就診于天津另一醫院,考慮“抽動障礙”,予阿立哌唑25 mg每日1次,期間調整用量至100 mg每日1次,服用一年余癥狀未見好轉,遂自行停藥。為求進一步系統治療,就診于馬教授門診。患兒當前抽動癥狀以搖頭、點頭、伸胳膊伴喉中異聲為主,發作頻繁,動作連貫,尤以興奮時明顯。患兒為第一胎,獨子,足月生,剖宮產,出生時健康狀況良好。既往過敏性濕疹病史。無家族史。患兒現上初中三年級,文化成績差,音樂能力強。脾氣急躁,易焦慮,膽量小,注意力不集中,小動作多,頻繁汗出,納可,寐欠安,二便調。于本院查耶魯綜合抽動嚴重程度量表(YGTSS)示:運動20分,發聲21分,缺損率20分,總分61分,提示重度抽動障礙。兒童總體評定量表(CGAS)示:70分,提示一般功能表現良好,某一方面有些困難。Conners(多動指數):1.0(提示陽性)。查體:全身可見濕疹樣皮疹,凸出皮面,顏色鮮紅,瘙癢伴鱗屑,集中于頸部、軀干及四肢,夜間尤甚。舌淡紅,苔白膩,脈沉細。診斷:1)抽動障礙。2)濕疹。先后予滌痰湯、龍膽瀉肝湯等豁痰開竅、清肝瀉火之方。抽動癥狀未見好轉且濕疹頑固難愈。
馬教授考慮患兒因濕疹瘙癢難耐致抽動癥狀綿延難愈,伴汗出之癥明顯,綜合“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及標本兼治”原則,以治療標急之濕疹為先,兼治抽動之本。綜合辨證:營衛虛弱證,治以益氣溫經,調和營衛。于2020年9月29日始服黃芪桂枝五物湯加減。處方:黃芪30 g,桂枝15 g,白芍15 g,大棗3枚,蟬蛻6 g,白鮮皮10 g,地膚子10 g,當歸10 g,葛根 30 g,地骨皮 10 g,浮小麥 30 g,甘草 6 g,干姜6 g,全蝎3 g。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連服14劑。
2020年10月13日2診:藥后較前改善,抽動仍以搖頭伴喉中異聲為主,注意力稍差,小動作多,脾氣較前稍好轉,膽量小;濕疹時好時壞,常反復,集中于前胸及脖頸部,干燥、瘙癢較前好轉。納寐可,二便調。舌淡紅,苔白,脈平。守方調藥,處方:黃芪 30 g,桂枝 15 g,白芍 15 g,大棗 3 枚,蟬蛻 6 g,白鮮皮 10 g,地膚子 10 g,當歸 10 g,葛根 30 g,地骨皮10 g,浮小麥 30 g,甘草 6 g,干姜 6 g,荊芥 10 g,防風6 g,蜂房6 g,龍骨15 g,牡蠣15 g。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連服14劑。
2020年10月27日3診:藥后癥狀好轉,抽動偶有搖頭伴喉中異聲,偶有踮腳行為,頻次、幅度均較前好轉,注意力尚可,小動作多,脾氣較前稍好轉,膽量小;濕疹范圍較前減少,癢感減輕,主要集中在背部及雙臂,納寐可,二便調。舌淡紅,苔白厚,脈平。守方調藥,處方:黃芪30 g,桂枝15 g,白芍15 g,大棗 3枚,蟬蛻 6 g,白鮮皮 10 g,地膚子 10 g,當歸 10 g,葛根 30 g,地骨皮 10 g,浮小麥 30 g,甘草6 g,干姜 3 g,荊芥 10 g,防風 6 g,蜂房 6 g,木蝴蝶10 g,苦參 10 g,佛手 6 g,玫瑰花 6 g。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連服14劑。
2020年11月10日隨訪:患兒藥后好轉,抽動偶有點頭伴喉中吭吭聲,無其他抽動表現,脾氣好轉;濕疹較前明顯好轉,癢感減輕,范圍明顯減小。
2 討論
《醫門法律》記載:“故凡治病者,在必求于本,或本于陰,或本于陽,知病所由生而直取之,乃為善治。若不知求本,則茫如望洋,無可問津矣。”而“本”即為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記載:“然六淫,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流入,內合于臟腑,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郁發,外形于肢體,為內所因;其如飲食饑飽,叫呼傷氣,盡神度量,疲極筋力,陰陽違逆,乃至虎野狼毒蟲,金瘡折,疰忤附著,畏壓溺等,有背常理,為不內外因。”將疾病的發生細致分為內因、外因及不內外因3類。本例患兒即為內因所致。該患兒平素情緒急躁易惱怒,情志失調,肝失調達疏泄,致氣機不暢,氣郁而化火生熱,熱極生風,肝風內動。而風為陽邪,易襲陽位而出現點頭、搖頭之頭面部抽動癥狀;木火刑金,循經上逆,痹阻咽喉,發為喉中怪聲。而濕疹之癥能加重抽動障礙患兒感覺異常之癥狀,該患兒以抽動障礙之主癥前來診治,伴濕疹之癥,若濕疹之標急之癥不去,則抽動之本癥不能緩解。《醫宗金鑒·血風瘡》指出:“此證由肝、脾二經濕熱,外受風邪,襲于皮膚,郁于肺經,致遍身生瘡,形如粟米,瘙癢無度,抓破時津脂水浸淫成片,令人煩躁、口渴、瘙癢,日輕夜甚。”表明濕疹的發生與肝、脾等臟器密切相關。《素問·調經論》記載:“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該患兒濕疹綿延不愈轉為慢性,久病耗氣耗血,氣血不足,營衛不和,血虛風燥而致肌膚瘙癢難耐。因肌膚之瘙癢明顯而加劇筋肉之不自覺收縮抖動,致使抽動癥狀不能好轉。
黃芪桂枝五物湯由黃芪、桂枝、芍藥、大棗、生姜5味藥組成,始見于《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記載:“血痹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痹狀,黃芪桂枝五物湯主之。”為治療血痹之代表方,由桂枝湯去甘草,倍生姜,加黃芪而成。故馬融教授始終守黃芪桂枝五物湯方微調加減治療,患兒取得良好效果。該患兒初診中抽動癥狀以搖頭伴喉中異聲為主,發作頻繁,動作連貫,時見上半身抖動。頻繁汗出,濕疹嚴重,根據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及標本兼治原則,故予益氣溫經,調和營衛之黃芪桂枝五物湯加減。方中重用黃芪,補氣升陽,固表止汗,生津養血,固表實衛為君藥;桂枝發汗解肌,溫通經脈,助黃芪溫陽實衛;芍藥養血和血,斂陰益營,與桂枝相伍調和營衛,共為臣藥。生姜易干姜取其溫中降逆之效更強,助桂枝以溫經散邪。大棗補中益氣,養血安神;姜棗相合調和脾胃,共為佐使。《婦人大全良方》記載:“醫風先醫血,血行風自滅”,除主方外加當歸,即為補血調經,養血柔肝之意;加蟬蛻、白鮮皮、地膚子,共奏清熱燥濕,祛風止癢之效;葛根、地骨皮生津涼血,通經活絡,針對治療患兒頭頸部之抽動癥狀;浮小麥、甘草合大棗為甘麥大棗湯之方,以疏肝解郁,清熱除煩,養血安神;加全蝎以息風鎮痙。
2診患兒抽動癥狀好轉,濕疹時好時壞,常反復,集中于前胸及脖頸部,干燥、瘙癢較前好轉。舌淡紅,苔白,脈平。守方調藥:減全蝎;加重針對治療濕疹之藥物,從解表之徑出發加荊芥、防風、以解表散風止癢;加蜂房,性善走竄,以祛風止癢;加龍骨、牡蠣以平肝潛陽,重鎮安神,調節情志。
3診時患兒抽動癥狀偶爾出現,濕疹癥狀較前明顯見好,癢感減輕,范圍減小。舌淡紅,苔白厚,脈平。因患兒舌苔白厚考慮患兒里證明顯故偏溫之干姜6 g減為3 g,減龍骨、牡蠣;加苦參,與白鮮皮、地膚子、當歸、蜂房、荊芥、防風共奏清熱燥濕、散風止癢之效。加木蝴蝶、佛手、玫瑰花以疏肝理氣,調暢情志。患兒抽動癥狀故而明顯減輕。
該患兒于本院查Conners多動指數雖為陽性,但患兒注意力不集中,小動作多的病程尚未達6個月,且CGAS提示該患兒一般功能表現良好,僅某一方面有困難,無明顯社會功能損害。考慮有濕疹之病史的作用因素,且濕疹好轉后患兒注意力較前明顯改善,故暫不予診斷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
此外,在觀察眾多抽動障礙患兒中發現,因心情狀態及情緒的波動起伏等誘因出現抽動癥狀出現反復或加重者非常多見[4]。《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素問·舉痛論》云:“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均體現了情志變化對人體五臟及氣機的影響。本例病案患兒平素性急易怒,脾氣急躁,性格敏感多思,怒則傷肝,憂則傷脾,氣機失調,肝脾同病致使抽動癥狀及濕疹病癥時常反復難以痊愈。《東醫保鑒》云:“欲治其病,先治其心。”指出了調整情志心態對疾病轉歸的重要影響。故馬融教授在主方基礎上加入甘麥大棗湯等調和情志氣機,疏肝解郁理脾的方藥共同調理,服藥后該患兒之病癥出現轉輕之勢,這無不體現了馬融教授“審因辨治”思想在診療疾病中的運用[5]。同時,馬融教授在診治抽動障礙患兒的同時,同樣重視患兒家長在患兒康復道路中的重要作用,要讓患兒家長正確地看待抽動障礙,如對患兒頻繁出現的抽動癥狀不應進行過度提醒,可進行轉移患兒注意力的方法進行干擾等。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當患兒出現情緒波動的情況時,患兒家長應理性的對患兒進行心理疏導,調整患兒情緒狀態,以達到治療效果。
綜上所述,該患兒起初運用針對治療抽動障礙之方并未奏效,而后重視標癥之濕疹方而顯效。故“審因辨治”疾病,發現疾病反復或加重的誘發因素,分清癥狀之主次,結合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本兼治的治療原則,是極為重要的。此病例的分享,以期為臨床提供更多的診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