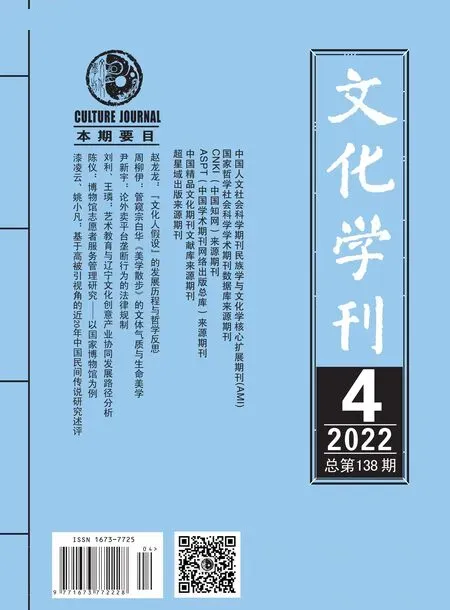動詞“吃”的音義關系及其配價研究
李林燕
“吃”表示人類生存最基本的行為活動,出現次數頻繁,“吃了嗎?”一度是人們日常對話中最常用的語句,由此,“吃”所構成的同一形式的結構模式往往蘊含多種意義,存在歧義紛爭。如“吃的”這一“的”字短語結構。然而,“吃”是否自產生之初便具備飲食義,需要對其音義關系進行進一步梳理。如何分析“吃了他三個蘋果”這一特殊結構形式的句式結構及判定動詞“吃”的配價歸屬也存在爭議,值得進一步探究。
一、“吃”的飲食義溯源
吃,最初不具有飲食義,按“六書”言,“吃”屬形聲字,從口氣聲,“氣”不僅表聲音,其形又像彎曲的云氣,表示口吃者聲音不能自然直出。《說文解字·口部》:“吃,言蹇難也,從口氣聲。”即其本義指口吃、說話結巴。在飲食義動詞“吃”還未產生時,古代漢語中表飲食義的動詞多為“食”和“飲”,“食”多與固體食物的食用搭配,“飲”則常與流體食物或液體的食用搭配。漢至魏晉時期,動詞“喫”出現,開始競爭“食”的飲食義,在此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完成了對動詞“食”的飲食義的歷時替換。
宋代徐鉉校訂的《說文解字》收錄了“喫”字,注:“喫,食也。從口,契聲。苦擊切。”魏晉之后,動詞“喫”不僅具有“食”的意義,還兼有“飲”(現代漢語“喝”)的含義,《洪武正韻》:“喫,飲也”。唐宋時期,《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朱子語類》等文獻中,“喫酒、喫茶、喫水”等詞語多有出現。現代,寧波方言等方言中仍存在“喫(吃)茶”“喫(吃)水”等說法,這也為“喫”古代兼具“吃”“喝”兩種意義提供了佐證。在動詞“喫”對“食”飲食義的歷時替換過程中[1],由于語音的發展變化及方言的影響,“吃”被借來表飲食義,同“喫”出現混用現象,隨著語言發展,“吃”成為表飲食義的主導詞。
從語音特征看,“喫”與“吃”的聲母、韻母均不相同。依據《唐韻》,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標注“喫”的讀音為“苦擊切”。而“吃”在《唐韻》《集韻》《韻會》《廣韻》均注為“居乙切”,又《集韻》“欺訖切,音乞。吃吃,笑貌。”總的來說,“喫”字屬于溪母錫韻入聲,“吃”字屬于見母迄韻入聲。漢語史上,有些音同或音近的字會發生替換現象。“吃”與“喫”的混用說明,在漢語發展過程中,“吃”與“喫”的語音經歷了逐漸趨同的發展過程或說兩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某些讀音,因此,“吃”被假借承擔了“喫”的飲食義,同時,“喫”所具備的“飲”的意義又逐漸被動詞“喝”分擔,使得“喫”字以飲食義的身份出現在書面語中的次數大為減少,呈消亡趨勢。
就語音層面看,“喫”屬溪母,“吃”屬見母,而“吃”在《集韻》中又有“欺訖切”一音,此音聲母與“喫”聲母相同,同屬溪母,雖義有異,但為“吃”與“喫”的混用提供了可能。此外,漢藏對音、日譯漢音及現代南方方言均存在溪母字讀為見母字的用例[2],這側面印證見母“吃”與溪母“喫”混用是可能的。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中的擬音[3],入聲錫韻的“喫”收“—k”尾,入聲迄韻的“吃”收“—t”尾,據上古音看,兩者相混的可能性極小,然而,由于語流音變的存在,并且隨著入聲韻尾逐漸消失,“吃”與“喫”皆變為陰聲韻,兩者混用不是沒有可能,由此,動詞“吃”才能取代“喫”成為飲食義的主導詞。而后動詞“吃”以飲食義為基點,引申發展出了其他義項,為“我吃了他一個蘋果”特殊句式的出現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動詞“吃”的配價分析
語法包括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個方面,僅從一方面去探析配價是不完整的,陸儉明(1995)指出:“確定配價應該以意義分析為基礎,同時得到形式上的可操作性”。相較而言,從語義、句法兩個層面探究動詞“吃”的配價歸屬更顯合理。
(一)簡單句“吃”的配價
動詞所支配的“行動元”的數量決定著其價數[4]。古代漢語中的飲食義動詞(如食、飯、飲、抿等)及現代漢語中的飲食義動詞(如吃、喝、吞、咬、含等)主要支配施事和受事兩個配價必有的語義成分,在簡單句中構成基本句式:施事+動詞+受事,其中施事充當主語,受事充當賓語。常見的例子如:1.他吃飯。2.我喝水。3.狗咬肉。4.她含糖。
盡管這里主要探討的是動詞“吃”在飲食義項上的配價歸屬,但除了飲食義義項,“吃”所具有的其他引申義項一般也只能帶施事和受事兩個語義成分。如:1.紙不吃墨。2.又吃掉了敵軍的一個營。3.快看,那兒有一艘吃水很深的船。這里,例1“吃”有吸、吸收之義,可將“道林紙”看為施事,“墨”看為受事;例2“吃”有殲滅或摧毀之義,施事未出現,受事是“敵軍的一個營”;例3“吃”有浸入水中之義,指船身入水的深度,“船”是施事,“水”是受事。因此,一般情況下,動詞“吃”主要支配兩個行動元,從配價角度而言,屬二價動詞。
(二)特殊句式“吃”的配價
唐元發、孫卉姿[5]對陸儉明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中運用語義指向分析法指出“吃了他三個蘋果”分析為雙賓句[6]是可取的說法進行了反駁,其文章認為“吃”是個二價動詞,“他”可以實指,也可以虛指,整個結構組合體應看成單賓結構。
目前,學界已認可“他”存在虛化的說法[7],因此,這里從“他”作虛指成分和實指成分兩個方面探究“吃”的配價。唐元發、孫卉姿指出,當“他”是虛指成分時,“他”大致相當于一個句中語氣助詞,不充當句法成分,因此,與“三個蘋果”沒有領屬性語義關系,在句法結構上,只有“三個蘋果”作“吃”的賓語。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他”在某些時候沒有實在的詞匯意義,僅起湊足音節等作用。如:
我當時餓極了,一口氣吃了他三個蘋果。
我當時餓極了,一口氣吃了三個蘋果呢!
這兩個句子在語氣上存在著些許差異,但是在語義表達上沒有差別,均在陳述“由于我餓極了而吃了三個蘋果”的事實。因此,當“他”是虛指成分時,“吃”在“我吃了他三個蘋果”這種句式中確實只支配了施事和受事兩個成分,屬于二價動詞。
然而,當“他”是實指成分時,“吃”是否仍是二價動詞,便值得深入探究。唐元發、孫卉姿文章認為,當“他”作實指成分時,“他”和“三個蘋果”有語義領屬關系,在結構上是偏正關系,“他三個蘋果”整體作“吃”的賓語。同時通過該例句與“給了他三個蘋果”進行“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轉換進行論證,認為兩句之間存有明顯差別,即動詞“吃”的配價不同于三價動詞“給”。如:
我給了他三個蘋果——我把三個蘋果給了他——他三個蘋果被我給了
我吃了他三個蘋果——我把三個蘋果吃了他——他三個蘋果被我吃了
進而從是否可將“他”和“三個蘋果”拆開轉為把字句、合攏變為被字句論證兩者是否存在領屬關系。這就否定了動詞“吃”在此例句中所具有的三價性質。這一說法看似有道理,但并不具備周遍性。同是動詞“給”,出現在其他例句中,便不能完全符合以上條件。比如:
1.我給了他一個巴掌(我給了他一巴掌)——我把一個巴掌給了他——他一個巴掌被我給了
2.我給了他一腳——我把一腳給了他——他一腳被我給了
這里的例1和例2既不可將“名①”和“名②”(1)“名①”指“他”,“名②”指“一巴掌、一腳”合在一起轉換成“被”字句,也不能拆開轉換為“把”字句,可見,單憑能否將“他”和后面的詞組拆開換成“把”字句,合攏變換為“被”字句是不能精確判斷兩者在語義上是否確有領屬關系的。
從語義、句法的配價角度來說,動詞“給①(了他三個蘋果)”與“給②(了他一巴掌)”都支配了施事、受事、與事三個成分。盡管“一個巴掌(一巴掌)、一腳”存在量化趨勢,但僅從配價而言,“我給了他一巴掌”和“我給了他三個蘋果”兩個例句之間并無太大不同。因此,當“他”做實指成分(后面默認“他”是實指成分)時,這里的“吃”不能被簡單當作二價動詞。
(三)“吃”是否具有三價性質?
許多學者分析論證了“吃”等二價動詞構成雙賓句的可行性,那么能夠構成雙賓句的“吃”是否就此具有了三價性質呢?本文認為,“我吃了他一個蘋果”這類句子可以算作一種特殊的雙賓句,從配價角度而言,這種特殊句式中的“吃”具有三價性質,只是這種三價性質并不穩定。
陸儉明(2002)解釋了將“吃了他三個蘋果”分析為雙賓結構的可行性[8]。他認為,從語義角度看,“他”和“三個蘋果”存在領屬關系,但從句法角度來說,兩者并沒有同“他的三個蘋果”這樣直接的句法關系,因此“他三個蘋果”可以不看作偏正結構,“吃了他三個蘋果”可分析為雙賓結構。此后,他又借用“語法動態性”理論對“修了王家三扇門”這個例子進行解釋說明,指出這里的“名③”(2)“名③”指“王家、他”,“名④”指“三個蘋果、三扇門”既是“名④”的領有者,同時又以動詞的與事論元身份出現,因而具有雙重語義身份。換言之,在這類雙賓結構中,“王家”“他”都是動詞的與事,故其在句法層面可判定為雙賓結構。
由于“詞語的語義配價是句法配價的基礎,并要求句法配價盡量同它相適應”[9],因此,在研究動詞的語法配價時,多數學者會同時考慮語義和句法兩方面,但不可能所有動詞的語義配價成分都恰好與句法配價成分完全一致,為便于描寫,往往只能忽略相對不明顯的一方面。如,陸先生在對“修了王家三扇門”例句進行解釋時,承認“王家”是具有雙重語義身份的成分,同時承認其在句法結構中的與事身份,進而將其判定為雙賓結構。本文贊同陸先生的觀點,這是綜合考慮語義和句法兩個層面配價最后選擇的結果。可同理分析“吃了他三個蘋果”的結構。
就“我吃了他三個蘋果”這個句子來說,不能僅因為“他”和“三個蘋果”存在語義領屬關系就將其分析為單賓句。如“我送了他三個蘋果”這類句子,“我”和“三個蘋果”之間也暗含領屬關系,但這并未影響動詞“送”的配價數,其仍屬于三價動詞。兩個句子句法無差別,區別在于具有語義領屬關系的兩者遠近距離不同。
總而言之,“他”和“三個蘋果”之間確有領屬關系,但如同“我送了他三個蘋果”中“我”和“三個蘋果”存在暗含領屬關系一樣,這在句法上沒有直接表現。因此,綜合考慮語義、句法和句式配價[10]要求,“他”應當被看作與事成分。即,在“我吃了他三個蘋果”句式中,“他”符合語義學上與事的定義,即施事所發動事件的非主動參與者,最常見的是因施事的行為而受益或受損者[11]。“他”沒有主動參與“我”的施事行為,但確是因為“我”吃東西的行為損失了“三個蘋果”。因此,可以將“吃了他三個蘋果”這類句式看作擁有雙賓語的句子,這就承認了動詞“吃”的三價性質。
三、結語
承認動詞“吃”在“我吃了他三個蘋果”這類句子中的三價性質,不是指必須將其劃入三價動詞類別。單就“我吃了他三個蘋果”例句可見,動詞“吃”是在進入“我吃了他三個蘋果”這一句式后產生了增價行為,具有了三價性質,但其本身未表現出這一性質。即句式的配價要求大于動詞本身的配價要求,故動詞在某種句式中,它的某些語法屬性會發生某些變化,產生增價現象。因此,某些動詞需要綜合語義、句法及其在句式中配價現象以明確其在特定例句中的配價數。
盡管某些二價動詞可構成雙賓句,在這些句式中具有三價性質,但這時的三價是不穩定的,只有在特定句式中才會表現出來。而這些動詞本身所具有的二價性質又是極其穩固,可脫離特定句式而存在,例如,在提到動詞“吃”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吃”的施事者和受事者,一般很少會考慮到與事成分。這是人們處于靜態環境的思考。這與陶紅印的看法相似,“動詞的論元結構并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句法語義現象,而是隨實際語言運用而不斷變化的[12]”。
這可適當參考現代漢語中詞類的劃分情況。現代漢語中,詞與其所歸屬的詞類之間,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一對一的關系,存在名詞、形容詞在特定句式做謂語成分以及量詞充當主語成分等情況,但最終還是要依據詞的主要性質將詞劃分進一個詞類。同樣,在劃分動詞“吃”的配價歸屬時也應著重考慮它的主要價數性質,即動詞靜態的配價而非句式的動態配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