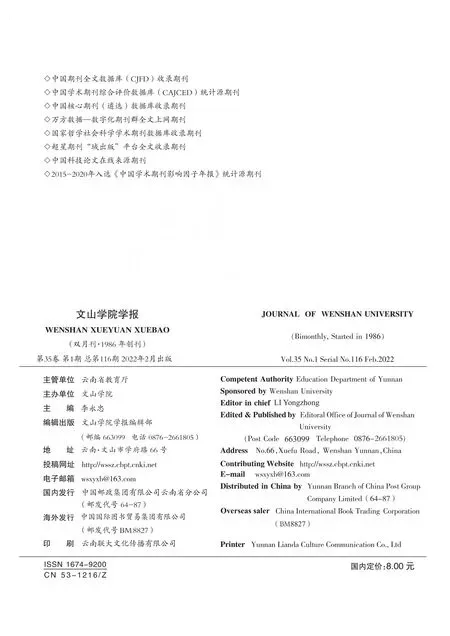西雙版納傣族拴線儀式的文化表達
崔 宇
(云南民族大學 社會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4)
魂線,即白線,是傣族傳統宗教活動中的一種信用物。魂線在傣族社會被視為福線、吉祥線,每逢小孩滿月要用白線拴線祝福,訂婚、舉行婚禮、升小和尚、叫魂等也要拴線祝福。[1]而將魂線纏繞在人手腕之上的行為便被稱之為拴線,是西雙版納傣族社會中極為常見的一種風俗文化。拴線文化源于傣族傳統崇拜,是“萬物有靈觀念的神秘性和直觀性,歪曲地反映了原始社會人類生活與自然之間的矛盾。”[2]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將宗教歸為一種社會行為,“宗教的表現是表達集體實在的集體表現,并認為儀式是在集合群體之中產生的行為方式,它們必定會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3]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一書中認為“儀式可被看作是某些情感的有規則的象征性體現,當儀式對調節、維持和代代相傳的那些社會構成所依賴的社會情感起作用之時,儀式的特有社會功能也就呈現出來了。”[4]而拴線儀式同樣在傣族傳統社會中具有群體情感表達,以及群體所依賴的一種精神力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穩定群體情感的社會功能。范熱內普則在《過渡禮儀》中提出將儀式行為具體分為隔離、轉換、重整三個階段論述,認為“伴隨著每一次地點、狀況、社會地位以及年齡的改變而舉行的儀式”,[5]而特納則在《儀式的過程:結構與反結構》中將此理論進一步發展,形成分離、閾限、聚合三個階段,他認為“分離、閾限和交融無處不在,而處于閾限階段的人則像站在門檻上那樣,處于一種不進不出的狀態,但唯有經此階段閾限者的處境或位置才能被重新標記。”[6]而拴線儀式則是使得被拴線者相信只有經此過程,自身才能從病痛中得以“解脫”或獲得祝福的狀態,才能在心理上被自我或集體所重新標記。艾罕炳在《西雙版納傣族拴線系魂文化》中論述到,“傣族萬物有靈的觀念使其認為一切的病因都是因為靈魂受到傷害所致,若想使病情痊愈則必須先給病人系魂拴線,做好安魂之事。這種拴線系魂可以起到未雨綢繆的作用,如若失去靈魂之后,亦可找回并系好以達到穩住其魂之效。”[7]2-3由于傣族拴線儀式在當地社會應用面廣泛,因此本文將以西雙版納勐龍鎮部分村寨作為主要田野調查點,并著重論述傣族的拴線文化所承載的“治療”及婚慶中的祝福等文化功能。
一、“治療之線”
西雙版納位于我國云南省最南端,地處熱帶北部邊緣,屬熱帶季風氣候,具有氣候炎熱、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物產豐富等特點,但西雙版納也因潮濕、悶熱的氣候成為病菌滋生的“溫床”,尤其在古時,在對外交流不便、醫療手段有限的情況之下更是如此。雖然傣族有著聞名于世的民族醫學,但“對于傳統的、民族的、民間的醫藥,還不可能具備純粹的科學手段,更何況傣族醫藥是脫胎于古代鬼神世界的傳統醫術。”[7]44因此傣醫便難以避免有巫術文化的色彩。對于疾病的治愈方式通常可分為醫藥及心理兩類,積極樂觀的心態配合藥物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而傣醫已然意識到精神作用對于患病者的重要性,因此他們便將此類精神稱之為靈魂,“傣醫會把生病或沒有精神的人認為是由于靈魂丟失所導致,這就是所謂的‘人在魂不在’,而有些人在喝酒后,在酒精的作用之下精神倍增,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精神開始恍惚,這種情況又被認為是‘魂在人不在’,兩者都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人,必須要進行治療、招魂、用線把魂‘拴牢’等行為,否則引起不良的后果。”①由于古時人們對某些正常現象的認知局限,以及受靈魂觀念的影響,因此無論由上述或其它何種因由所引起人的行為規范或精神狀態出現異常狀況,則會被當地人視為是“形神分離”所致的結果,因此須采取“招魂”“拴線”等措施。之后,隨著南傳佛教的傳入,傳統崇拜、巫術文化便隨即與之交織融合,并使之得以進一步的拓展及完善,意義也更加豐富與深遠。
(一)巫醫時代的拴線儀式
在佛教未進入西雙版納傣族地區之前,巫術文化在當地起著至關重要的地位。當地巫術文化的掌握者為巫師,他們被視為可“溝通天地”,具有操控自然的“非凡能力”,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不僅是傣族巫術文化的主要掌握者及傳播者,而且能夠察言觀色、透析心理,因此“當時民間的民眾在有事之前都愿意去找巫師進行占卜,特別是在病痛比較嚴重時,大家總會第一時間求助于巫術的幫助。屆時,巫師不僅會將生病的緣由歸因于患病者靈魂受到鬼魂的傷害或被‘勾去’,導致家人患病不愈,而且還會告訴救助之人解決的方式,那就是進行拴線系魂儀式。”①以治療為主要目的的“拴線”行為通常有兩個因素構成,首先是患者家屬對于疾病的有限認知,加之“救人心切”的心態,他們希望巫師能通過操控超自然的能力使病患者所患之疾能得以好轉;其次是“拴線”的治療方式在當地傣族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拴線”儀式便是當時傣族人民治療病痛的主要途徑之一,即使是今天,以治療為目的的“拴線”儀式在人們藥石無果的情況之下,也不失為一種撫慰患者及其家屬心理的一種選擇。
此外,傣族巫師的治療方式除采取心理撫慰式的“拴線”儀式作為純粹精神治療方式之外,會輔以藥石作為醫治病痛的手段,兩種方式同時作用于患者的心理及生理之上,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對求醫者起到積極的效果,“直至現代,有一些醫療機構不健全或文化素質較落后的地區,有的草醫仍借用巫術作為幌子,以用藥為真,在虛實之間既治好了病,又強化了自身的神秘性。”[9]可見,傣族巫醫在用“拴線”儀式為患者進行心理治療的同時,亦會以藥石為患者進行身體治療,可謂是一種“神藥兩解”治療方式。隨著佛教的傳入,當地巫醫的部分功能也逐漸被佛寺僧侶所取代。
(二)佛寺中的拴線儀式
當某種文化作為異文化傳播至某地之時并非一帆風順,通常會經歷碰撞、調適及融合的過程,以此適應在當地文化環境而求以生存與發展,佛教在進入西雙版納之時亦是如此。但由于佛教自身的教義與當時社會上層的意識相符,于是便得以至上而下的推廣,很快便成為絕大多數傣族信仰的宗教。佛教文化對民間文化的差異性亦采取包容甚至融合的態度,“拴線”文化便是佛教納入自身的體系當中并加以發展與完善的范例之一。西雙版納拴線文化的起源與佛教并無關系,而是“源于傣族萬物有靈的觀念以及巫術文化的治病方式,到后來南傳佛教進入以后便與之相互交融,得到進一步的延伸和拓展,所蘊含之意義也更加深遠,并最終形成集治病、慰藉、消災、安魂、調節、釋放、解脫及化解心理障礙于一體的綜合功能,被大眾廣泛接受。”[10]佛寺亦成為當地民眾求取平安、安撫心靈、調節情緒、釋放壓力的重要場所。
佛寺中的拴線儀式通常是由寺中僧侶,尤其是主持僧(當地稱之為大佛爺)擔當儀式主持人,而拴線所涉及的范圍也較為廣泛,如祛病消災、保佑平安、“解除晦氣”等心理安慰功能。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需求范圍也更加廣泛。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曾多次目睹當地民眾因各種因由而至佛寺請大佛爺為其進行拴線。如勐龍鎮景乃村一名村民攜帶其孫輩請村寨佛寺的大佛爺為其孫進行拴線,而大佛爺便會在其孫輩面前先念誦一段平安經,之后便將一根白色棉線拴到小孩手腕之處,至此一個簡單的拴線儀式便完成。據事后筆者向當事人了解得知其情,“我孫子這幾天晚上都在啼哭,搞得一家人晚上都睡不好覺,所以就到他帶佛寺請大佛爺給他念經、拴線,好讓他晚上不再哭鬧……”,無論小孩是因拴線后停止夜間啼哭抑或是受藥物作用的結果,經此儀式后,其家人的心態在此中得以調節,使之能夠以一種相對平和的心態應對此事,進而能夠細心了解小孩啼哭的真實原因。此外,村民在購置新車或車輛在發生禍事之后亦會到佛寺請求大佛爺為其車輛進行拴線儀式,而村寨佛寺僧侶對此也持包容和接納的態度,承擔著佛寺對村寨應盡的義務。“不論有什么人來佛寺請求拴線,我們基本會答應,一來體現普度眾生的教義,二來佛寺日常的開銷用度均是村民所供養,所以村民有什么要求,佛寺會盡量給予幫助,甚至有的時候有的人想發財,或者是做生意不順利,都會來佛寺請佛爺拴線。”②佛寺中的拴線儀式所承載的社會功能,所涉及的范圍之廣,由此可見一斑。其實佛寺中的拴線儀式更多的是呈現出精神層面的“治療”,使得信仰群體在接受“治療”之后能以一種相對平和的心態回歸日常生活,正如特納所呈現出儀式過程中所具有分離、閾限、交融的儀式功能。
總體而言,西雙版納的拴線文化始于傳統崇拜文化社會,發展于巫術文化社會,最后在南傳佛教社會定型。佛教與巫術文化時期的拴線儀式均有承載“治療疾病”的社會文化功能,但不同之處在于巫術文化時期的巫醫會用“神藥兩解”的方式共同作用于被拴線者,以達到其“治療”的目的,而佛寺中的拴線儀式則在其完善的宗教體系的基礎之上,為被拴線者提供純粹精神上的撫慰、心理上的調節及心理平衡,但無論何種方式,均在一定程度上使當地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保持良好心態與人為善、和諧相處。
二、“祝福之線”
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的演變,西雙版納傣族的拴線儀式也由原初以治療為目的的文化內涵發生延伸,被廣泛地應用于生活當中。傣族人民在建新房時需要請佛寺僧侶為其拴線,外出遠門及歸來之時需要拴線,在婚慶禮儀中的拴線儀式亦具有其豐富的文化表達,“此類儀式通常佛寺并不參與,是由村寨中的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召曼④作為儀式的主持人”,④并通過為結婚雙方拴線的形式完成對村寨集體男女雙方婚姻的祝福,是民間立定婚姻“契約”的一種形式。
婚姻是人生當中最為重要的人生禮儀之一,當事雙方除以隆重的婚慶形式加以慶賀之外,得到家中長輩或村中長者的祝福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西雙版納傣族的婚慶禮儀便是如此。傣族婚禮儀式中的“拴線”行為不僅承載著村中長者為對新婚雙方的美好祝愿,也是新婚雙方共同建立家庭的傳統文化標志,是傣族婚禮上不可或缺的傳統。因此,婚禮在當地傣族村寨除全寨人參與之外,得到村寨長者的祝福亦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傣族在結婚之時,必須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長者為新婚方雙主持拴線祝福(此類拴線行為僧侶通常不會介入),傣族認為只有經過村中長者拴線之后婚姻關系在民間才被視為婚姻關系的建立,才可得到民間的認可。如果雙方只是拿到結婚證,只能證明婚姻關系得到國家的認可,而如果沒有經過拴線便視為沒有得到村中長者的祝福,那么這段婚姻在村寨中是得不到大家的認可,除非雙方離開村寨。”⑤此外,在長者為新婚雙方念誦完祝詞之后,雙方還需進行一道必要的儀式程序,即在眾人的見證之下雙方需各自進行“滴水儀式”,以此表示雙方白頭偕老,永不反悔的愿意與決心。
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地傣族村寨的婚禮中,如若婚姻雙方的其中一方為其他民族或非佛教信徒,那么須將遵循一條“民間法則”,即入鄉隨俗。雙方仍需得到主辦婚禮的村寨長者的拴線祝福,得到村寨群體的認可,否則將會視為對當地村寨神靈的冒犯,是一種觸犯當地禁忌的行為。“在信仰南傳佛教的傣族村寨中,不管你是什么人,或者信仰何種宗教,雙方均須以跟跪姿接受老人的拴線祝福,如若不然,這便是一種犯忌的行為,傣族有一句話是‘無論你進入哪個寨子,你必須尊重那個寨子的神靈’,如果你不尊重人家寨子的神靈,那還不被人家趕出去嗎?”⑤因此,如若不遵行當地的拴線習俗,新婚雙方不僅得不到村寨民眾的祝福,而且其婚姻關系在民間也得不到認可。因為“你可以不信佛教,但你必須尊重我們的神靈,因為‘掌管’婚姻的是村寨神靈,不是佛教,你不能用你的習俗來衡量人家的風俗,所以宗教與鬼神是兩碼事,這個就是屬于鬼神的范疇。”①因此,入鄉隨俗的民間約定在文化差異的群體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使得多元文化依此民間約定而達到相互尊重的目的。
傣族婚禮儀式中的拴線祝福儀式,村寨長者對婚姻雙方的拴線祝福可謂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長者對新婚雙方進行的拴線行為,并非只是將一根細線簡單地纏繞于被祝福者的手腕之上,而更多的是承載其先祖之靈對后世子孫的庇佑與祝福,以及對其民族傳統文化尊重與傳承等深刻的文化內涵。
三、結語
傣族的拴線文化是借以拴線儀式這一具象的行為方式,將人們心中所盼之愿望借以拴線行為以期獲得。傣族人民相信,身體承載著靈魂,而靈魂主宰著身體,兩者即分離又統一,因此便借拴線的形式將身體與靈魂牢牢“拴住”,不受疾病的困擾。拴線儀式對身患疾病者在精神層面可謂是一種心理撫慰,使之能夠將身體痊愈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力量而積極應對現實生活。而儀式治療對患者所帶來的希望并不僅限于患者對儀式本身的期盼,而更多是信仰群體所賦予的集體力量,而這種力量將會激發、維持或重塑社會群體中的某種心理意識,此類群體性的意識又給予個體心理上的鼓勵與“判定”,此“判定”將給予個體極大的心理慰藉與自我認同。拴線祝福儀式中所獲得的集體認同與祝福亦是出于此類群體性“判定”的延伸與演變。
綜上所述,西雙版納傣族的拴線儀式不僅承載著傣族人民相互慰藉、勉勵、安撫,以及在心理上解除 “祈求者”的思想障礙等功能,同時也寄托了當地民眾美好愿望與祝頌,是西雙版納傣族人民獨特的文化表達方式。
注釋:
① 巖XX,66歲,傣族,西雙版納州傣學會主要負責人之一,對傣族原始崇拜、儀式、禁忌、歷史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
② 勐龍鎮景乃、景龍、景棟以及景洪市村曼閣村波章及數名村寨老人以及西雙版納州傣族協會負責人獲取的訪談資料。
③ 召曼為管理村寨寨心、寨神、祭祀等原始崇拜事物的管理者。
④ 洪景曼閣寨佛寺、勐龍鎮景乃、景棟佛寺大佛爺以及村寨召曼和長者。
⑤ 刀XX,傣族,70歲,西雙納州傣學會主要負責人之一,長期從事西雙版納傣族傳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