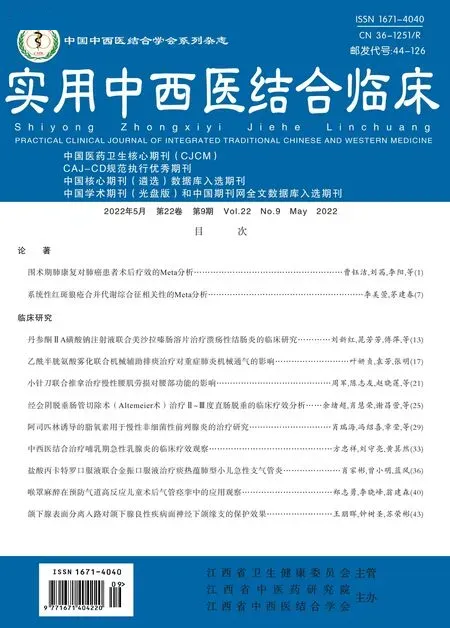肝郁脾虛型潰瘍性結腸炎中醫治法及機制研究進展*
王佳慧 郝民琦 朱向東 王燕#
(1甘肅中醫藥大學2020級研究生 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 蘭州730000;3寧夏醫科大學 銀川 750004)
潰瘍性結腸炎(UC)是一種結腸黏膜的特發性慢性炎癥性疾病,從直腸開始,通常以連續的方式延伸至部分或整個結腸[1],主要表現為腹痛、腹瀉、黏液膿血便等[2]。隨著對UC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學者發現UC作為一種全身系統性疾病,可引起一系列嚴重的關節、肝膽管、眼部疾病等并發癥。長期疾病導致機體免疫力低下、機體微循環障礙進而又影響到潰瘍的愈合,使得病情反復發作,成為世界范圍內的疑難雜癥[3]。中醫將本病歸于“久痢、腸澼”等范疇,肝郁脾虛型是UC主要的證型之一[4]。中醫藥治療肝郁脾虛型UC具有副作用少、療效顯著、復發少等優點,且可通過多種生物機制發揮治療作用。現將近十年中醫治療肝郁脾虛型UC的方法及其分子機制概述如下:
1 肝郁脾虛型UC中醫治法研究
1.1 內治法
1.1.1 經典方藥通過研究近年國內學者治療肝郁脾虛型UC的文獻發現,在以中醫經典方為主與以單純西藥治療為主的對照實驗中,中藥臨床效果堪稱顯著。如徐佳萍等[5]通過對比美沙拉嗪顆粒劑治療,西藥基礎上加用柴芍六君湯治療UC療效發現,中藥組可有效調節患者免疫功能,減輕炎癥反應。吳萍建[6]通過對比柴芍六君湯、美沙拉嗪腸溶片治療UC效果發現,中醫組在臨床癥狀改善及腸鏡黏膜愈合度方面效果更加顯著。蒙竹韻[7]通過對患者6個月隨訪發現,相比于口服柳氮磺吡啶治療,柴芍六君顆粒加味治療的效果更顯著,復發率低且無明顯毒副作用。陳薇等[8]對比四君子湯合痛瀉要方加減與柳氮磺胺吡啶片治療UC的療效發現,中藥組對于癥狀的改善更為明顯。
1.1.2 自擬中藥方近年來,為應對UC復雜的癥狀,眾多醫家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結合臨床經驗組成諸多自擬方劑。郭志偉等[9]研究發現腸炎1號方能夠顯著提高UC治療效果。陳旭[10]臨床研究發現針對輕、中度肝郁脾虛型UC,疏肝健脾顆粒比柳氮磺吡啶腸溶片的療效更加顯著。崔麗麗[11]發現,名老中醫張東岳教授經驗方腸舒安治療效果優于常規西藥美沙拉嗪腸溶片。王忱[12]臨床研究發現,名老中醫謝晶日教授經驗方解郁止瀉方對緩解期慢性肝郁脾虛型UC患者臨床癥狀有明顯的緩解作用。凌巧云[13]發現采用熊之焰教授自擬解郁消潰方聯合美沙拉嗪腸溶片口服,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中一氧化氮(NO)濃度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水平,調節腸道免疫平衡,抑制炎癥反應發生。張寧[14]研究發現辛學知教授自擬解郁消潰方對于肝郁脾虛型UC的主癥及伴隨癥狀的緩解較西藥艾迪莎更為明顯,且經濟實惠,無明顯毒副作用。
1.2 中醫外治法
1.2.1 中藥保留灌腸中醫外治法從肝脾論治UC安全有效,常用的療法有中藥灌腸法、針灸療法等。中藥灌腸法多數屬于內服和外用一方兩用,節約藥材。但由于所剩藥渣再次煎煮后藥效有所降低,亦有研究多選用新方行保留灌腸。如吳平恭等[15]觀察中藥內服聯合保留灌腸對照口服美沙拉嗪腸溶片治療活動期肝郁脾虛型UC的臨床療效,發現中藥內服聯合保留灌腸效果更優。曹春歌[16]觀察發現口服中藥制劑配合灌腸方治療活動期肝郁脾虛型潰瘍性結腸炎療效顯著。蔣忠等[17]發現,肝胃百合湯加減聯合結腸寧保留灌腸治療療效優于口服柳氮磺胺吡啶腸溶片聯合甲硝唑保留灌腸治療。有研究觀察中藥灌腸方與西藥灌腸藥物療效的差異,對比更加直觀。如張春陽[18]通過觀察白芍甘草煎劑灌腸與美沙拉嗪灌腸液灌腸治療UC的療效,發現針對輕、中度遠端肝郁脾虛型UC中藥灌腸治療效果更顯著。
1.2.2 針灸針灸治療為中醫特色自然綠色療法,具有簡、便、廉、驗的特點,各醫家也越來越重視UC的針灸療法。牛錦錦等[19]將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后,均給予美沙拉嗪片口服,治療組同時給予俞募配穴法針刺治療,取穴脾俞(章門)、胃俞(中脘)、肝俞(期門)。結果發現俞募配穴法可降低血清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組胺(Histamine,HIS)的水平,明顯改善患者臨床療效,更好地抑制復發率。王倩等[20]探析王樂亭“老實針”防治肝郁脾虛型UC的方法,“老實針”基于“肝病實脾”理論,組方為中脘、足三里、上脘、下脘、氣海、天樞、內關,臨床收效良好。宋永紅等[21]的研究中,對照組予柴胡疏肝散合痛瀉要方加減,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針刺療法(中脘、足三里、上巨虛、天樞、關元、太沖、三陰交)治療,結果顯示治療組在臨床癥狀改善、中醫證候表現和總體療效方面均顯著優于對照組。
2 肝郁脾虛型UC中醫治療機制研究
2.1 免疫調節痛瀉要方為治療肝旺脾虛所致腹瀉的經典方,療效顯著,但作用機制尚不完全明確。研究表明痛瀉要方可抑制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細胞介素-9(Interleukin-9,IL-9)等致炎因子的表達[22];調控肝臟SCD1與腸道5-HT的平衡,下調TNF-α等促炎因子[23];降低UC大鼠血清中TNF-α水平、結腸組織中Caspase-3、CHOP的表達[24];上調白細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和白細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下調白細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和干擾素-γ(IFN-γ)[25];下調IFN-γ并上調白細胞介素-13(Interleukin-13,IL-13)的水平,促進機體Th1/Th2之間的免疫平衡[26]。痛瀉二草方同樣是臨床治療肝郁脾虛型UC的有效驗方,研究顯示痛瀉二草方可下調Mapk8、Fas基因的表達水平[27]。另有研究表明柴芍六君湯合半夏瀉心湯治療可調控UC患者血清NO、乙酰膽堿酯酶(AchE)、胃泌素(GAS)、5-HT含量[28]。
趙恩春等[29]發現怡情止瀉湯能降低UC患者體內IL-6、IL-8、TNF-α水平。王曉妍等[30]的實驗表明四君痛瀉方可降低患者血清神經壞死因子(NGF)、TNF-α水平,同時提高IL-10表達。易文等[31]研究發現,左金丸合四逆散可通過抑制一氧化氮合成酶(iNOS)、NO等炎癥介質,TNF-α、IL-1β和IL-6等促炎因子的分泌,提高IL-4和IL-10等抗炎因子的分泌,進而恢復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之間的平衡。
2.2 平衡機體氧化/抗氧化能力研究顯示,在UC的急慢性期,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PAR-γ)蛋白和mRNA表達都呈下調趨勢,表明肝郁脾虛型UC的發生發展可能與PPAR-γ的表達受抑相關,PPAR-γmRNA和蛋白表達可能與結腸的損傷呈負相關[32]。郭軍雄等[33]通過對痛瀉要方加風藥組(升麻、柴胡)、痛瀉要方組、痛瀉要方去風藥組(防風)的檢測對比發現,配伍風藥可通過提高血清抗炎因子IL-2水平,降低致炎因子TNF-α水平,起到保護UC大鼠結腸黏膜的作用。
2.3 調節腸道菌群俞媛等[34]研究發現痛瀉要方可調節腸道菌群紊亂,腸道內有益菌(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數量升高,有害菌(大腸埃希菌)的數量降低,從而發揮臨床治療效果。另有研究表明痛瀉要方調控腸道菌群紊亂的療效主要由其中的有效成分如石防風素、麝香草酚、漢黃芩素等發揮[35]。趙恩春等[29]研究發現,經怡情止瀉湯治療后患者雙歧桿菌及乳酸桿菌數量升高,而糞腸球菌、大腸桿菌數量顯著降低。
2.4 調節自噬水平張旭飛等[36]通過研究發現,痛瀉要方補脾柔肝的機制可能是通過調控外周5-HT作用于肝臟S-HT-(2A)R的表達,維持肝臟脂代謝穩態以及改變肝細胞自噬水平,從而改善結腸組織病理變化,影響緩解期肝郁脾虛型UC。
3 小結
從古至今,UC的病因病機一直是醫家關注的重點。對UC的記載最早可見于《黃帝內經》,《素問·舉痛論篇》載:“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劉完素在《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同樣提到:“春宜緩形,形緩動則肝木乃榮,……獨火木旺,而脾土損矣,輕則饗泄身熱脈洪,谷不能化,重則下痢膿血稠黏”。中醫近年來在肝郁脾虛型UC的治療上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有著比較詳實的治療及用藥方法。綜上可知,目前治療UC常用的方法有中藥內服法、中醫外治法、中西醫聯合療法等。在中藥內服法中,經典方劑研究多選用柴芍六君湯與痛瀉要方加減及變方,效果較好;目前大量的自擬方臨床療效確切;中西醫聯合療法臨床上有效率確會顯著提高,但成本也會增加。
中醫治療UC的療效顯著,但仍存在些許不足:(1)一些經典組方如逍遙丸類方同樣值得探索;(2)自擬方缺乏嚴格的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研究;(3)中醫外治法研究樣本量小,應加大樣本量并細化研究指標;(4)目前亟需一種或多種成本低、效率高的綜合治療方法。我們要篩選和開發治療肝郁脾虛型UC的有效中藥復方,進一步研制成系列專藥,以更好地發揮中醫藥治療本病的優勢。要在治療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依然任重而道遠,中醫藥干預治療該病仍具有很大潛力和廣闊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