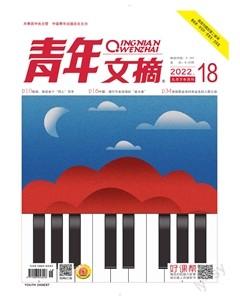我叫鄧穎超,不叫什么周夫人
小飚

提到她,人們會首先想到“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然而讓眾人感動的浪漫,或許不足她生命的百分之一。這位女士并不喜歡某某夫人的身份,也從來不是一個愛情至上的人。
70 年前,她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態度鮮明地擁護女人離婚的自由。她用盡畢生精力,為女性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奔走呼號。她是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婦女工作者。她是鄧穎超。
一
鄧穎超自小跟母親四處奔波,顛沛流離。母親全力供女兒讀書,實在沒錢,就在家自己教她看書識字。因為母親的開明,鄧穎超很小就成為學生組織的一員。雖然家境貧苦,她依然樂觀、熱情、自強、獨立。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于五四運動。當時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界已經很有名氣。
后來鄧穎超在文章中回憶,學生大會上,周恩來坐在主席臺上,戴鴨舌帽穿西服,長得非常好看。但“感覺是淡淡的”,并沒有別的想法。當時的鄧穎超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讀書。
20 余名進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鄧穎超是其中最年輕的成員。他們用抓鬮的辦法決定各自對外的代號,鄧穎超為1 號,后化名“逸豪”。
“逸豪”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帶領天津進步女青年走向街巷,宣傳反帝愛國思想。
與她對周恩來“淡淡的感覺”不同,周恩來對她印象很深。她的一手好文章、出色的演講能力,都讓他贊嘆。
周恩來曾經指導社員演愛國話劇。有趣的是,因長相清秀,周恩來經常反串女角。而鄧穎超英姿颯爽、大方利落,經常扮演話劇里的男主角。
1920 年1 月,天津學聯調查員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政府不但不懲辦日本浪人,反而指使軍警攻擊學生。周恩來等人率領各校五六千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愿。這次活動遭到軍警血腥鎮壓,重傷50 余人,周恩來等人當場被捕。
得到這個消息,鄧穎超當即帶領一批學生,在警察廳示威聲援,自愿要求替換獄中學生,并積極聯絡社會各界開展營救活動。在鄧穎超的呼吁下,全國各界都開始聲援學生。7 月,法庭被迫宣布,無罪釋放周恩來等人。
經歷了局勢動蕩、烽火四起的考驗后,兩個人更親近了些。一年后,周恩來赴法留學,臨行前鄧穎超送了他一件毛衣。
二
剛剛萌生的感情就被千山萬水阻隔,似乎只能中斷了。當時的鄧穎超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婦女運動上。
彼時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是如今無法想象的。作家丁玲就曾說過:“現在女生剪發是太平凡了,在當時女孩子不梳辮子,卻會遭受嘲諷或責罵。”
鄧穎超所做的,就是為女性的權利抗爭,同時用教育喚醒女同胞。1923 年年初,鄧穎超等人創辦女星社,拯救被壓迫的女性。就在這時,她的好友張嗣靖因為包辦婚姻被丈夫和婆家虐待慘死,去世時還懷有身孕。
密友的去世讓鄧穎超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在張嗣靖的追悼會上,鄧穎超聲淚俱下地念誦悼文:“你一生的遭遇和慘死都是現在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
她明白,好友的遭遇只是中國千萬女性悲慘命運的折射。而大多數女性不幸的根源就是,她們不能和男性一樣平等地接受教育。此后,鄧穎超創辦了專門面向平民婦女的補習學校——“女星第一婦女補習學校”和“女星星期義務補習學校”,以推進女子教育。
這些學校教授失學女子普通知識及基本技能,讓她們能自謀生活,而且不收學費。這為婦女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解放創造了條件。
畢業典禮上,鄧穎超說:“希望你們以后承擔起社會的責任,能時時關注女性解放問題的同時,幫助她們脫離苦海。”
遠在法國的周恩來,得知鄧穎超在國內組織“女權運動同盟”后,特地從法國寄來油印刊物《少年》《赤光》,為她帶來更先進的女性思想,這讓鄧穎超感到耳目一新。
這期間,兩個人的信件往來有上百封,還有很多明信片,但里面沒有甜言蜜語,更多的是他們對當時中國時事的心得。只有一封信,似乎有點不尋常。
周恩來在信中寫道:“希望我們將來,也像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德國的革命者)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鄧穎超看到“ 上斷頭臺”時蒙了。后來是朋友一語道破:這是周恩來想要與你同生共死,這是一封表白信啊!
三
讓他們走到一起的,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志同道合的價值觀。
20 世紀40 年代,重慶《大公報》刊登端木露西的署名文章《蔚藍中的一點黯淡》,主張婦女回到家庭去做主婦、做母親,在“小我的家庭中”尋找幸福。
沈從文、陳銓等人發表多篇贊同婦女回家的文章,為妻為母,能“賢”能“良”。汪偽政權控制下的婦女刊物的主基調也是宣傳“賢妻良母”“婦德”“齊家”等論調。
當時主張婦女解放的男士很少,主要的反對聲音來自鄧穎超等女性,她們認為,“治家和育兒并不永遠是婦女的天職”,讓婦女回家從根本上違反了“男女平等應從經濟入手”的原則。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也加入了這場反對“婦女回家”的論戰。
周恩來的《論“賢妻良母”與母職》,首次發表于1942 年9月25 日的《新華日報》上。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要雙標。丈夫和妻子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員,“賢良”的標準應該是對夫妻雙方共同的要求。這些思想,即使放在現在也不過時。
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參與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對于婚姻自由的原則,大家基本無爭論。但對“一方堅持離婚可以離婚”這條,大部分人都不支持。
不光男性干部不同意,女性干部也不同意。她們顧慮的是,進城以后,一些男性干部以“離婚自由”為借口,把農村的原配拋棄,這將給那些隨意拋棄妻子、另結新歡的“當代陳世美”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擁護“一方要求離婚可以離婚”這一條的,只有鄧穎超和極少數人。
最后,黨中央同意了鄧穎超的建議,采用了“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準予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準予離婚”的條款。這是鄧穎超拼盡全力,給當時水深火熱的女性指出的一條生路。
鄧穎超一生為婦女權益奔走,其間遭遇的苦楚外人難以想象。
她和周總理, 一生無子。在革命斗爭最殘酷的時候,她喝藥打掉了第一個孩子,因為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有了孩子就有了軟肋。生第二個孩子時,丈夫不在身邊,她難產,苦熬三天三夜后,孩子還是不幸夭折。
喪子之痛、虛弱的身體,丈夫在戰斗中又杳無音訊……產后病痛和奔波動蕩,使她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但是她終生堅持參與婦女解放運動,帶領婦女工作者打破社會落后的框架。她沒有孩子,可每一個中國兒童,她都視如己出。
今時今日,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女性,都受益于這位偉大先輩的付出。她始終堅信: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尺度,兒童幸福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摘自“視覺志”微信公眾號,知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