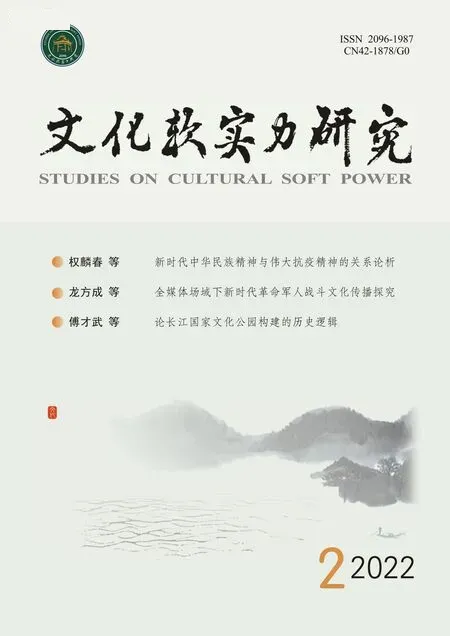傳統中國的“誕日”與時間記憶
馬芷妍 楊 華
(武漢大學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漢 430072)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歲時之間的節點劃分是順天時而定的,因此節日的構建也一般是基于節氣、農時等時令變化而來的,春節、中秋、冬至等傳統節日都是個中典例。但對進入了工業時代的現代社會而言,節日的構建形式大有不同。基于經濟消費或政治意識而產生的新節日比比皆是,譬如五一勞動節這樣發源于近代人民意識覺醒的新興節日,以及近年由于信息網絡大發展而興起的雙十一購物節等。但在眾多的傳統歲時節日之外,古代中國還有一項不基于歲時變化或宗教傳說而構建出的特殊的傳統節日——誕日,即慶賀皇帝生辰的節日。這一具有近似現代社會人文氣息的特殊節日雖產生于唐代,但也在一千多年的悠久歷史發展中衍生出了多樣的慶祝活動與豐富的歷史內涵,與冬至、中秋這樣基于節氣、農時等時令變化而構建的傳統節日一道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成為了帝制時代的歷史記憶。
誕日在史籍記載中也有誕節、誕圣節等別稱,首創于唐玄宗時期,爾后成為了歷代王朝的慣例,一直延續到了清末。“誕日”的名稱是為了方便總結這類為皇帝慶賀生辰的節日而作的統稱,在實際的慶祝活動中并不直接使用。而不同朝代、不同皇帝的誕日都有其特定的名稱,多取一些有美好政治寓意的詞匯,譬如唐玄宗的誕日最初名為千秋節,寓意李唐的統治千秋萬代,后又更名為天長節,取天長地久之美意。另一方面,誕日的內涵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在創設之初的唐代還僅僅只是慶賀皇帝生辰的節日,到了明清時期慶賀范圍擴大化,將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生辰也囊括了進來。誕日逐漸演變成古人為皇室與想象中的國家概念而慶賀的特殊傳統節日。不過,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員慶賀其生辰需要在“誕日”名稱前加上限定詞,稱“皇太后誕日”或“太皇太后誕日”。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誕日”仍主要是針對皇帝生辰而言的稱呼。
在古人對誕日的研究僅限于概括性記載,如明代徐應秋在《玉芝堂談薈》中詳細列出了唐至宋諸位皇帝的誕日時間及名稱,但僅限于記錄,并沒有什么衍生論述。[1]當時的誕日在古人眼中與元旦、冬至等傳統節日一樣屬于確定年歲變遷的重要參照,在古人的時間記憶中也并不具有別樣內涵。直到誕日隨著帝制時代的結束而消失,這一不基于歲時、有賴于人文意識而構建出的特殊節日才體現出了它有別于元旦、冬至的歷史意義。今人有關誕日的研究多是斷代性的,僅將視角局限于某一朝代或某一皇帝的誕日上,考察其形成與發展。例如張勃在《唐代節日研究》一書的第二章“新興節日研究”中詳細考察了唐玄宗千秋節的構建歷程與興衰變遷,并將其與中和節做對比,以期說明內涵的公共性才是構建型節日得以存續的必要條件。[2]再如李曉媛的《清代萬壽盛典研究》,以康熙、乾隆與慈禧的三次萬壽盛典為研究對象總結萬壽節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功能。[3]另一類有關誕日的研究則并不將重點放在節日本身而是其文化、政治衍生上,如王蘭蘭的《唐日皇帝誕節比較研究》,焦距于唐玄宗千秋節與日本仿設的天皇天長節之間的風俗異同,用以探討唐代文化對日本的深遠影響。[4]又如劉林魁的《唐五代皇帝的三教講論——基于皇權與佛教關系的考察》,從誕節賀壽的佛事活動出發,論述了三教講論這一節慶政治儀式中皇權與佛教之間的互利互動對唐代及以后王朝政教關系的融合與發展所產生的積極意義。[5]此外,還有并不焦距于誕日而是專論節日輔政意義的研究,如王靜的《歲時與秩序——唐代的時間政治》,該文以唐代歲時節日為例,探討歲時與王朝秩序之間的關系,認為自然的節慶是極具象征意義的時間,為統治者提供了確認與強調自己的權力與天下秩序的契機,[6]頗有見地。此文發于《唐研究》第二十一卷《唐代長安及其節慶研究專號》,同樣收錄于該專輯的還有楊為剛的《節日·空間·記憶——關于千秋節幾個問題的再探討》,通過對千秋節的活動細節、意象與文學塑造進行探討,重新描繪了其節日形象與傳統的形成和發展過程,[7]視角新穎。
由前人研究可見,誕節作為一個由唐至清不斷發展的節日還需要得到貫通性的考察一輯針對其本身內涵與歷史意義的進一步研究。
一、古代帝王的誕日慶賀
誕日起于唐玄宗開元十七年,據《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料的記載,開元十七年的八月五日,唐玄宗在花萼樓與百官一同舉辦慶生宴,宴上左丞相源乾曜與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奏請玄宗將自己的生辰(即每年的八月五日)設定為千秋節,“天下諸州咸令樂,休暇三日”[8]。史書的記載十分簡短,但實際上除了籠統而言的設宴作樂之外,誕日之時的宮廷與民間還有著很多別樣的儀式與慶祝活動。
(一)宮廷的慶祝活動
千秋節之時,宮廷內會舉辦盛宴慶祝。與平日宴席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千秋節的宴樂不僅更為盛大,而且增加了兩項特殊的重要儀式:一是群臣百官向皇帝上萬歲壽酒,二是王公戚里向皇帝進獻金鏡綬帶。
正如今人會在壽宴上為壽星進酒一樣,千秋節宴上的群臣按禮也需向皇帝上酒進壽,但以古人對禮儀的重視與嚴格規定,整個上壽酒的儀式顯然不似今人宴飲一樣隨意,而是有著一整套的復雜流程。上壽酒之前,群臣百官需在御座之南等候,待到皇帝入座后行拜禮,由皇帝身旁的侍官跪奏進言道:“千秋令節,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群臣此時需與侍中一同再拜。爾后主事官吏在專用的壽罇中酌酒并進于皇帝,皇帝受酒后還需稱:“得卿等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并舉酒向眾人示意。群臣上下再行拜禮并三呼萬歲,然后才能就座,宴樂正式開始。[9]
千秋節宴上,前來朝賀的王公大臣當然不會是空手而來就宴的,因此宴席的另一大重要活動即是王公大臣們向皇帝進獻金鏡綬帶,依禮尚往來的慣例,皇帝也會回賞群臣金鏡、珠囊、絲帛等物。所謂“金鏡綬帶”是指綴有長絲帶的銅鏡,由于其在唐玄宗時期大量鑄造并用以進獻賀壽,因此后世慣稱為千秋鏡。正如時任宰相張說所作的《奉和圣制賜王公千秋鏡應制》一詩所描述:“寶鏡頒神節,凝規寫圣情。千秋題作字,長壽帶為名。月向天邊下,花從日里生。不承懸象意,誰辨照心明。”[10]鏡子在古人的文學中常有心明眼亮、明察秋毫的暗喻,而綬帶之“綬”與“壽”同音,因此金鏡綬帶也象征著臣下對皇帝賢明有德、福壽綿長的美好祝愿,而皇帝回贈的金鏡則是對臣下知事明理、清廉正直的美好期待。
除宴席外,千秋節時宮廷內還有不少雜戲、歌舞表演,《文獻通考》曾記載一種名為“傾杯舞”的馬戲舞,唐玄宗十分喜愛,每逢千秋節宴都要于勤政樓下令樂工奏樂,演此馬舞以為助興。[11]時任丞相的張說留有《舞馬詞》描繪當時的宴舞場景,詞中寫道:“彩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圣君出震應箓,神馬浮河獻圖。足踏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躕。”[12]從中不難窺出當時千秋節的熱鬧與盛大。值此歡慶之日,皇帝也常有施恩天下之舉,或是為囚徒減刑、免其死罪,或是為百姓減稅、安置流民,唐玄宗甚至曾在開元二十四年的千秋節時親自與京兆父老同宴共樂,這也可看作是千秋節惠民之處的一個側面。
(二)民間的慶祝活動
宮廷的慶祝活動不論如何盛大,都只關乎王公將相與達官顯貴,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當時社會在千秋節之時的全貌,民間有關千秋節的慶祝活動同樣十分豐富,且體現出有別于朝堂的民俗色彩。
千秋節之時的民間同樣會設宴作樂為皇帝祝壽,一般士庶自然沒有向皇帝上壽酒或進獻金鏡的機會,但他們會互贈承露囊以示對節日的慶賀。承露囊是一種絲質的囊袋形禮品,按《困學紀聞注》的記載,承露囊也稱為盛露囊,是以五彩絲帶結成的、用以盛裝葉上露珠的囊袋。當時民間流傳著“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的傳說,又一說稱有人在八月入華山采藥時見到有童子用絲囊盛接露水,詢問童子后得知這露水是“赤松先生取以明目”的。(1)據《困學紀聞注》所言,“赤松子”說引自《荊楚風土記》,“華山采藥”說則引自《華山記》,兩書成書年代未知,但翁元圻注中稱這兩說在南朝梁時成書的《荊楚歲時記》與《續齊諧記》中也有提及,可見這些傳說故事在當時流傳之廣泛。[13]在這些當時廣為流傳的傳說故事的影響下,古人形成了在八月制作承露囊的習俗,認為將草木上的露水收集起來擦拭雙眼,可以明眼凈心。或許正是因為承露囊具有這樣的美好寓意,因此千秋節時,不僅是民間士庶會互相贈送承露囊來表達祝愿與問候,甚至在王公進獻給皇帝的禮物中有時也會包括承露絲囊。
除壽酒宴樂與贈禮外,民間對千秋節的慶賀與宮廷相比,其最大差異在于囊括了秋社日的相關活動。開元十七年百官上表請設千秋節之時,眾臣就已經提出村社在節日期間不僅可以設宴作樂,還應舉行“賽白帝、報田神”的慶祝活動,次年又正式決定“移社作千秋節”[14],也就是將本該秋社日進行的節日活動挪到千秋節一同舉行。秋社日是古人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這一天百姓多半會暫停農事、飲酒作樂,還會舉行祭神的相關活動,其用意一是向神靈傳達今年的農事生產情況,二是祈求神靈保佑來年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而白帝、田神就是當時民間最常見的祭祀對象。歷代秋社日的具體日期多有變動,但一般都定在八月,恰好與玄宗的生辰相隔不遠,因此將秋社日與千秋節合并,以此讓民間百姓能夠更好地參與到千秋節的熱鬧慶祝活動中來,也讓玄宗的生辰增添了與民同樂、與民同享的色彩,使千秋節不至于僅作為王公貴族的盛事而存在。
雖說民間對千秋節的慶賀方式看似與其余歲時節日相差無幾,也不與宮廷慶祝活動存在直接互動,但這并不代表對千秋節慶祝與其余傳統節日無異。由于千秋節所蘊含的政治內涵與創新意義,民眾“慶祝千秋節”這一行為本身就代表了對王朝所宣揚的皇權強化的認可及其所構建的新的生活秩序的接受。古人對生產生活的安排有賴于王朝所頒行的歷法與節慶,換言之其生活節奏是被統治者有意識地掌控著的。民間的時間秩序從屬于王朝的政治秩序而存在,前者被后者所規訓和維護。
(三)唐以后誕日的演變
千秋節自唐玄宗之首創,曾有過一段極盛的歲月,但天寶十四年爆發的安史之亂使得與開元盛世相生相隨的千秋節就此走向衰落。安史之后,千秋節的宴慶規模大不如前,到了唐德宗時期取消了三日休假,直至唐憲宗時期正式廢除了該節日。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發展,當唐玄宗過世、不再具有皇帝的特殊身份后,再慶賀他的生辰就是不合時宜的了。但千秋節的廢除只是意味著人們不再慶賀唐玄宗的生辰,并不意味著誕日也一并消失了。實際上,自玄宗創造性地將自己的生辰設立為節日之后,歷代皇帝于自身誕辰設節慶賀便成為了一項保留傳統,待到他們去世后,下一任皇帝就會廢除舊節,用自己的生辰代替而設立新的誕日。(2)皇帝去世后取消其誕日的慣例,是在唐憲宗時期正式形成的,詳見下文。
正如唐玄宗將自己的誕日命名為千秋節、后又更名為天長節一樣,歷代皇帝的誕日都有不同的名稱,如唐肅宗的天成地平節、唐武宗的慶陽節、宋太祖的長春節、宋太宗的乾明節等等。但到了元代,歷任皇帝的誕日被統一命名為天壽節,不再另起新名,明清時則更名為萬壽節,一直延續到清末帝制時代結束。不過稱呼雖不一,但誕日的慶祝方式是大同小異的,一般而言都包括全國休假、設宴作樂、群臣進酒賀壽、進獻賀禮、皇帝賞賜、大赦天下等幾項基本內容。若是處于中原多政權并立的分裂時期,還會有他國遣使朝賀,例如契丹、高麗都有遣使朝賀宋太宗誕日的記載,西夏也曾多次遣使朝賀金朝皇帝的誕日。此外由于佛教的影響,自唐文宗時期開始正式規定誕日禁止屠宰,宮廷宴席上只供應蔬菜、干肉和肉醬,但允許飲酒奏樂。群臣百官除進壽酒與賀禮之外,還增添了入寺為皇帝行香、作祝壽詩等慶祝活動。
蒙元起于朔漠,習俗與中原存在很多差異。元世祖忽必烈繼位后命劉秉忠、許衡制定朝儀,規定皇帝即位、天壽節、冊立皇后皇太子、外國來朝、君臣朝賀等國家重大場合都沿用唐宋以來的朝會之儀,只在大宴宗親或賜宴大臣的時候使用蒙古的本俗之禮。[15]依《元史》中對天壽節的些許描述來看,元代皇帝誕日的主要內容也確實與前代相差無幾。明清時期的誕日也一樣,只不過將名稱從天壽節改為了萬壽節,并增添了皇帝宴前向太皇太后、皇太后行禮的儀式。萬壽節當天的京城百姓也是張燈結彩、奏樂祝壽,還會在寺觀建壇為皇帝祈福,足以見得誕日在民間影響并不弱于其余傳統節日。由于古代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核心政治地位,中華文化也對周邊政權產生了極大影響。日本從奈良時代開始也效仿唐代設立天長節以慶賀天皇誕辰,在二戰后更名天皇誕生日,隨日本皇室制度一直延續至今。而對中國而言,清末帝制終結、皇帝不復存在后,誕日也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去,成為了帝制時代的歷史記憶。
二、誕日與傳統中國的時間記憶與秩序
節日其實是一種用于劃分與界定時間的節點,人們在特定的時間以特殊的儀式塑造出有別于常日的社會氛圍,以此寄托特定的情感表達,并確立時間流動的概念,這也是節日的誕生之所以與天文歷法息息相關的原因所在。群體文化記憶的構建正有賴于這些特殊時間下才會產生的特殊儀式與社會氛圍。誕日作為中國古代綿延近千年的一大重要傳統節日,自然也深刻地影響了古人的生活與他們對時間的記憶,其對皇帝個人地位的強調與國家認同感的塑造使其擁有了不同于元旦、冬至等歲時節日的政治價值。其次,王朝所頒行的歷法與節慶對治下之民的時間做出了官方規劃,這實際上是對整個社會基本生活節奏的掌控與安排,也是統治者確立政治秩序與合法性的權力體現。民眾依靠何種歷法、慶祝何種節日、以何種時間節奏來安排一年的生產生活,無一不是受到其所處的統治秩序的影響的。對于國土廣袤、民族多樣、地區差異極大的古代中國而言,國家意志就貫徹于統一的歷法與節日的實行之中,如同統一的文字、統一的科舉、統一的儒家意識形態一樣,民眾時間節奏上的一致也是國家統一性的體現。統治者依靠節日影響民眾的生活節奏與社會觀念,統一的政治秩序也隨著國家權力意志的影響而擴散,節日的規律性與延續性又反過來使其逐漸融入了民眾的時間記憶里。
正如前文所言,誕日作為一個非典型的、因時令變化而產生的傳統節日,它的構建基于弘揚教化、維護國家認同感的政治文化目的,并在推行過程中將統一的生活節奏與政治秩序傳播至王朝影響力所及的所有地區,因而具有了雙重的歷史意義,這可從誕日的構建過程及其在后世的興廢中體現。
(一)誕日的構建
史書中有關千秋節之設立過程的記載十分簡短,難以從中讀出背后的考量,但《全唐文》中輯錄了張說等人所進的《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可供今人一窺當時人創設誕日的用意與緣由。表中稱千秋節之設“上明元天,光啟大圣,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16],因此在張說等人看來,千秋節是為宣國之教化、正國之風俗、傳國之美譽而設立的。而玄宗在回復中也表示千秋節之設是“感先圣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朝野同歡,是為美事” 。[17]
從這兩封與千秋節設立直接相關的文本中能看出,在當時朝堂君臣的考量里誕日之設立和推廣與政治教化、塑造國家認同感是緊密相關的。在古代社會,皇帝是承天所生治理天下之人,其本身即是最突出的國家象征,因此以皇帝生辰作為朝野同歡的節日,在為皇帝慶賀之時暗含了為國家歡慶的意味。無論是千秋鏡、長壽帶還是承露囊,這些用以祈禱皇帝福壽綿長的意象物件,實際上在另一種層面上反映出了百姓對國泰民安的期盼。這即是誕日在歷史價值與意義上不同于歲時節日的重要側面,相比于冬至、中秋這樣有感于節氣、天文等自然變換而產生的特殊時間節點,誕日是人為創造并有意識地賦予其文化意義的,其間蘊含著人民對想象中的國家概念的認同與祝愿。因此,古人對誕日的記憶也總是與特定的皇帝與王朝緊密相連,這樣的政治文化屬性使得不同年代的人們對誕日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觸與記憶。
(二)唐人的誕日
唐人創造了誕日這一特殊節日形式并將其發揚光大,誕日也深切地融入了唐人的生活中,這不僅僅體現于每年固定的休假、宴飲、祭祀等儀式性活動對人們時間規劃的影響上,還體現在誕日的興廢與唐朝國力盛衰的緊密相連上。王朝的時間秩序是其政治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穩定狀態是相輔相成的,這一點可從安史前后文學作品的對比中窺得。
天寶十四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是唐朝興衰的分界點。安史之前,文人們沉浸在開元盛世的繁華中,其詩文無不在歌頌盛世之美。如梁锽的《天長節》:“日月生天久,年年慶一回。平時祥不去,壽遠節長來。連吹千家笛,同朝百郡杯。愿持金殿鏡,處處照遺才。”[18]王維的《奉和圣制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金天凈兮麗三光……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獻珍。”[19]這些詩作所描繪的都是千秋節鼎盛之時宮廷的繁華景象,盛唐時期國家的強大國力與開放自信的氣度在字里行間顯露無疑。唐玄宗本人也曾無不得意地作詩云:“蘭殿千秋節,稱名萬壽觴。風傳率土慶,日表繼天祥……獻遺作新俗,朝儀入舊章。月銜花綬鏡,露綴彩絲囊。處處祠田祖,年年宴杖鄉。深思一德事,小獲萬人康。”[20]當時的盛況可見一斑。
安史之亂打破了大唐盛世的迷夢,兩京動亂、山河破碎的現實引發了無數文人墨客的悲嘆,與千秋節相關的一切事物都能使他們回憶起昔日盛景,并借節日之名表達對盛世不再的悲思。如杜牧的《過勤政樓》:“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鋪。”[21]勤政樓正是昔年千秋節唐玄宗大宴群臣的場所,但當杜牧在多年后途經此地的時候,昔日繁華盛景早已煙消云散,唯有雜草青苔在宮門門環上旺盛生長,感傷之情油然而生。另有杜甫的《千秋節有感二首》:“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君臣得,金吾萬國回。衢尊不重飲,白首獨余哀。”[22]作為現實主義風格的代表性詩人,杜甫的詩作中總是常懷憂國憂民之心。《千秋節有感二首》作于八月二日,杜甫在親歷了安史之亂后,在又一年的千秋節前夕產生了對國家衰落的無限哀思,其間詩句無不傳遞著對昔日盛景的緬懷。
這些詩作借千秋節之名感懷回不去的大唐盛世,足以顯現出誕日與其余因時而起的傳統節日不同,其顯明的政治教化內涵和易于聯想的家國寓意使得時人將千秋節與國家興衰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安史前有關千秋節的詩歌多是玄宗、張說等宮廷宴席親歷者所作,可以視作官方對節日盛景的溢美之詞。而安史后有關千秋節的文學作品則證明了千秋節作為開元盛世的意象代表已經融入了一代人的歷史記憶中。詩句中所描述的千秋繁盛之象也許并非詩人們親眼所見,但這不影響后人依托于樓宇、金鏡等文學意象來追思、緬懷他們心中的昔日盛世,此刻對歷史的想象替代了歷史的真實,這即是集體時間記憶的影響所在。其次,共同的節日生活結合其附帶的特殊儀式與社會氛圍,在一定時間內塑造了民眾之間共通的生活秩序。歲時秩序的正常運行是王朝統治穩固的體現,也是天子本身具有的調理四時、維護世間秩序的基本義務所在。節日慶賀儀式的如常象征著天下秩序的穩定。千秋節作為唐王朝所構建的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安史前后的興衰變遷也映射出了唐王朝本身的盛極而衰。
(三)誕日在唐以后的影響
相比于元日、冬至、中秋這些在歷法上相對固定的歲時節日,誕日的人為性質決定了它所代表的特殊時間節點會隨著人事更替而不斷變換。唐代在最初創設誕日的時候還并沒有皇帝去世就取消其誕日的習慣,因此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及順宗的誕日都在他們去世之后仍作為國家的固定節日保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唐憲宗時期李元素上奏,稱先帝在天已久而慶誕猶存,不合禮意,因此取消了玄宗至順宗五位皇帝的誕日慶祝。[23]此后歷代王朝便形成了在皇帝去世后取消其誕日并立新皇帝誕日為節的慣例。
古人并沒有今日法定節假日的概念,當時的節日大多是流傳已久、約定俗成的。以古代中國國土廣袤、歷史悠久的社會現實而言,不同年代、民族與地域間流傳的節日與節俗也存在很大差異。若以是否存在官方性質的休假、宴飲與朝賀作為衡量節日是否正式的標準,則唐及以后歷代得到官方重視的固定節日一般是元日(即正月初一)、冬至與誕日。其余的傳統歲時節日如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官方與民間雖也有豐富的慶祝儀式與習俗,但仍不如這三個節日意義重大。在古人的觀念里,元日是“歲之始”,即新的一年正式開始的日子,而冬至是“陽之復”,即陰氣盛極而衰、陽氣衰極復盛的時刻,因此這兩個時間節點在歲時變換中最為重要。而誕日則是歷代皇帝的生辰,在帝制時代承載了不同于歲時節日的政治文化意義,塑造了人民對于想象中的國家概念的認同。因而雖不存在固定的日期,誕日也因其特殊的文化內涵與標志性的慶祝儀式,同元日與冬至這兩大重要節日一起融入了古代的社會生活中。
除此之外,節日的教化意味蘊含在其特殊的儀式與習俗里。與慶賀有關的法令,無論是倡議還是禁令實際上都是中央王朝政治控制力的具體表現,是對時人社會風俗的積極影響與主動塑造,這一點在誕日這樣基于政治因素而產生的節日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無論是民間與宮廷對誕日的慶祝儀式、還是有關誕日的構建過程,都能看出其間對皇帝個人地位與權力、對天下等級秩序的強調。百官進酒上表是君臣秩序的體現,地方朝覲與番邦朝賀則是天下秩序的強化,皇權借助誕日強調的不僅是國內政治秩序的統一,還維系了國外政治秩序的穩定。對時間的劃分與界定、對禮俗的規定與塑造使得誕日同時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秩序與文化記憶,因而具有了雙重的歷史意義。
三、誕日的廢止與近代時間記憶的變遷
時間是一個抽象的無形態概念,人們必須借助參照物來確定其流動狀態,歷法即是這樣基于自然變換而產生的。節日作為以年為單位的時間線上的特殊節點同樣具有劃分并界定時間的功能,譬如古人將農歷正月初一稱為元日,視作舊的一年結束與新的一年開始的標志。這一社會習俗從古代延續到了現代,至今正月初一的春節仍然是中國人用以確定年歲變換的最重要的時間標尺。人們為了感受時間的流動與劃分一年內的不同時段,創造了這些被稱作節日的特殊節點,而節日在歷史長河中的興衰更替也反過來為不同年代的人們塑造出了不同的時間記憶與生活節奏。
(一)誕日的廢止與歷法的更替
中國在近代的轉型過程中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到國家的意識形態與基本制度、小到個人的衣食住行與思想觀念,變革發生在文明的每一個角落。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的不僅僅是帝制時代,還有伴隨著帝制時代而生的一切舊式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模式,歷法與節日自然不會例外。
歷法與紀年是一個社會有關時間制度的最根本的體現,也是一個政權塑造政治生活秩序最直觀的手段。中國傳統歷法是一種與農時、節氣緊密相關的陰陽合歷,俗稱農歷,在紀年方面則一直以皇帝年號為準。但隨著帝制時代的結束,皇帝紀年被廢棄,農歷也受到了來自西方文明的沖擊。為了與世界接軌、更為了徹底拋棄舊時代的秩序建立新社會,民國政府決定自1912年1月1日開始使用西方格里高利歷,也就是今日俗稱的陽歷、公歷,但在紀年方面仍采用民國紀年。新中國建立后沿用了公歷并徹底拋棄了舊式的紀年方式,采用了與世界各國一致的公元紀年。
雖說一同在近代遭到外來文明的沖擊,但農歷與有賴于帝制而存在的皇帝紀年不同,基于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生活與習俗的深刻影響,它在辛亥革命后也并未徹底被公歷取代,而是將影響力保持至今,以至于在官方的傳媒與文宣表達中仍具有與公歷并列的地位,在民間的生活里更是從未遠離。這應當歸因于農歷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度融合,使得它不僅是指導古代中國農業社會基本生產生活的指南,更在古人的時間界定與劃分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影響,直到今天國人仍然習慣于用節氣來確認與感受季節變換。正如前文所言,歷法是人們用以計算與明確時間流動的制度,而節日是以年為單位的時間線上具有界定與劃分時段意義的特殊節點,兩者都與社會的時間記憶與生活秩序直接相關。農歷對現代中國社會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其所附帶的傳統時間秩序與文化記憶無法被輕易替代,基于農歷而產生的眾多傳統歲時節日就是其間的重要部分。
與春節、中秋這些至今仍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傳統節日不一樣,同樣歷史悠久的誕日是依附于帝制而存在的,在皇帝這一特殊階層消亡后,誕日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這類具有特定人文價值的節日不能脫離其特定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而存在,反而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自然消失。作為一個不基于歲時變化或宗教傳說而構建出的特殊的傳統節日,誕日所承載的弘揚教化、維護皇權及國家認同感的政治文化意義是建立在帝制時代的社會基礎上的,最終當然也會隨帝制一同變為歷史,其標志性的慶祝儀式與習俗最終也只能成為舊時代的記憶。
(二)古今時間記憶的變遷
對時間變遷的感知是文化記憶之所以形成的重要來源。正如揚·阿斯曼在其代表作《文化記憶》中所論述的:“回憶的內容之所以在時間上具有延續性,一方面是因為回憶總圍繞那些原始或重大的事件展開,另一方面是因為回憶具有周期節奏性。比如節假日日歷所反映的是一種在集體中被經歷的時間。”抽象的記憶需要寄托于具體的形式、概念或象征而存在。儀式與節日作為文化記憶的首要組織形式,定期重復的、具有特殊意義的群體儀式,保證了“文化意義上的認同的再生產”,并在時間維度上區分了常日和節日。[24]節日對時間的影響也在無形中賦予了其將生活節奏化的能力,社會的時間秩序因此產生。與此同時,文化記憶的產生和消亡也被社會環境的興衰變化所牽動。
節日在特定的時間節點以特殊的儀式習俗塑造出有別于常日的社會氛圍,從而對以年為單位的時間進行了界定與劃分,并由此成為人們時間記憶與生活秩序構建中的重要因素。可以說,節日的興衰變遷影響并牽動著人們對時間的感觸與表達,對古今的重要節日、尤其是受社會變革影響最大的人文節日進行對比更能清晰地反映出這一點。現代中國的法定節假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自古延續的傳統歲時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與中秋;另一類是近代興起的新節日,如國慶節與勞動節,元旦則是依據公歷而產生的有別于春節的歲首節日。古今節日的主要差異即體現在后者這些基于人文、政治因素所構建的節日上。具有特定人文價值的節日只能建立在特定的社會基礎上,這類節日的存在是對當時文化環境的直觀反映,其興衰也是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鮮明寫照。同樣是基于政治文化意識而構建的節日,誕日承載著古人對皇帝與想象中的國家概念的祝愿,國慶節與勞動節卻寄托了近代人民覺醒后的自主意識,三者在作為紀念日最重要的紀念價值來源上存在著時代進步所帶來的價值觀代差。
節日作為劃分年歲的特殊節點,其差異決定了古今歷史記憶與時間秩序上的不同。古代的許多節日都在時歲變遷中失去了曾經的影響力,例如中和節、春秋社日、佛誕節等與農業社會和宗教氛圍聯系緊密的節日都因失去了其特有的文化環境而在社會變革后逐漸落寞,誕日這樣因帝制而生的節日也是如此。它們曾經影響了古人的時間秩序,主導了當時人的生活節奏,并以祭祀、朝賀等內涵豐富的慶祝儀式融入進了舊時代的歷史記憶。但伴隨著近代的變革,農業中國的一切都在社會發展中被迅速替代,公歷替代了農歷、公元紀年替代了皇帝紀年、民主共和替代了君主專制。誕日是過去帝制時代時間記憶的代表,它在帝制時代結束后也被國慶、五一這些飽含新時代人文價值的節日所取代。如今人們不再互贈千秋鏡與承露囊、不再為皇帝的生辰而設宴慶賀,取而代之的是在國慶節觀看閱兵儀式、懸掛五星紅旗以表達對國家的熱愛與祝愿。皇帝通過誕日與紀年影響社會時間秩序與文化記憶的時代已經過去,新興的節日正以新時代的慶祝儀式重新規劃著人們的生活節奏,時代變遷的縮影就體現在這些日常生活里。
四、結語
誕日是中國古代一項不基于歲時變化或宗教傳說而構建出的特殊的傳統節日,它承載了古人對皇室與想象中國家概念的祝愿與認同。古人在這個特殊的節日中為皇帝的生辰而慶賀,并由此衍生出了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使得誕日同元日、冬至等眾多傳統歲時節日一起規劃了當時的生活節奏,塑造了王朝的政治秩序,在古人的時間記憶中留下了深刻影響。
但是,誕日這樣基于特定人文價值而構建出的節日不同于元日、冬至等歲時節日,它只能依附于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文化環境而存在,正如歷法所構建的時間秩序有賴于政治秩序的穩定而持續。近代中國的巨大變革動搖了誕日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讓誕日與其標志性的慶祝儀式一起隨著帝制時代而結束,時間記憶也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而經歷了新一輪的消亡與產生。歷法與節日的變遷更迭了新時代的生活節奏,重塑了新中國的時間秩序。相比于今日仍在影響著人們生活規劃的春節、清明、中秋等傳統節日,誕日則已經被國慶、五一等具有新時代人文價值的新節日所取代,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現代文明不再依賴皇帝與皇帝的生辰來確認年歲的流轉和維系統一的社會政治秩序。新興的節日將以新時代的慶祝儀式與文化內涵來重新規劃人們的時間與生活,這也是歷史的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