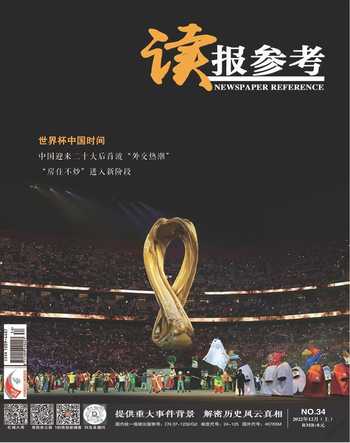王巍:探尋中華文明的“童年”
夏鼐先生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1978年,正是夏鼐先生的演講開啟了中華文明起源課題。2002年,時任社科院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的王巍與北京大學趙輝教授接過接力棒,領銜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聯合20多個學科探尋中華文明
在王巍看來,中國考古界對文明起源研究真正的發端是在1983年。那一年,夏鼐先生發表了6次演講,這一系列演講作為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著作在國內發表,開啟了這一宏大而意義深遠的課題。隨后,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和“古文化古城古國”。1996年,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啟,跨學科合作使得考古成果開始突飛猛進。同年,王巍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帶隊到偃師商城發掘商代早期都城內的宮城,發掘結論是偃師商城的興建應該是夏商分界的界標。這一結論被吸納進“夏商周斷代工程”成果中。偃師商城發掘是王巍第一次領隊,整天琢磨城址的布局,為他今后對考古學的總體框架思維進行了一次深度培養,也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考古熱情——中華文明是否有一個漫長的“童年”?
2000年,王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對于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形成了自己的設想。在設想中,王巍提出設置多學科聯合研究課題,不僅有考古學、歷史文獻學、古文字學等人文學科參加,還要聯合環境科學、體質人類學、遺傳學、物理學的科學測年、化學成分分析、地質學、天文學等。他呼吁讓社科研究加入探源工程中,全方位展開考古探源研究。王巍對記者說:“這篇文章大約形成了我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總體框架思路。”
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兩年后,在預研究階段結束時,形成了以都邑性遺址和區域中心性遺址為重點的布局。
到2017年,王巍從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任上卸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基本完成了第四階段。可以說,王巍的考古生涯一直聚焦于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用他的話來說:“一個文明,不可能生下來就是成年階段,它一定有著孕育時期、童年期、青壯年時期和老年時期,弄明白中華文明的‘童年期’,對了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今天的我們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 探源工程一開始,王巍等牽頭人就面臨著定義文明標準的問題,西方學術界通過研究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提出文明出現三大要素——冶金、文字和城市。但如果教條地引用這三大要素,就會給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造成誤導與阻礙。“文明‘三要素’不應該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比如說,瑪雅文明,它就沒有冶金術,印加文明并沒有使用文字。我們就要找出既符合學術普遍價值,又符合中國歷史存在的要素。” 由此,探源工程提出了中國文明定義三要素——物質資料生產不斷發展、精神生活不斷豐富、社會分工和分化加劇。在新的定義下,中華文明探源的廣度被打開了,“根據此定義,可以將中華文明探源上推至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通過研究這個時間跨度,能夠全面解釋我們是怎么來的”。
? 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布,證實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三赴埃及爭取考古走出去
在探源工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王巍和研究團隊還清醒地意識到今后漫長的探索路程。他感嘆:“探源這幾年,我覺得有一個遺憾,文明比較方面我們還有弱點。通過探源工程,我們大致可以在目標上試圖概括中華文明發展的道路和特點,但很難精準定位自身特色。我們以為是自己的文明特質,卻很可能是共性的東西,比如等級制、王權,其實世界其他文明都有類似的制度。古埃及文明、瑪雅文明都是。所以,我開始意識到,如果你對其他文明不了解,耍概括自身文明也是很難做到非常準確的。”
在尋覓自身“童年”的同時,王巍非常重視擴展視野。他積極探討中華文明與周邊地區文明化進程的互動,進而通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總結早期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
王巍說,探源工程團隊一直想對埃及有直接的了解,但遇到了不少困難,“先是埃博拉病毒暴發,然后又是埃及國內形勢發生變化。我們一直去不成”。就在王巍一籌莫展的時候,2016年1月,他遇到了好機會,帶一支研究阿拉伯語文學的小團隊前往開羅大學交流。他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促成中國、埃及兩大文明古國在考古挖掘方面的合作。
2016年之前,從未有一支中國考古隊參與古埃及文明的遺址挖掘工作。“我到了埃及,就想方設法見到了埃及國家博物館館長,但館長說已經有206支外國的考古隊在埃及發掘。”王巍表達了中國考古隊的愿望,并詳細講述了中國考古的實力與發展。館長被王巍的熱情打動,表示贊同。
? 這一年8月、11月,王巍又兩次前往埃及商討合作。埃及文物部部長問他:“中國考古隊來可以,但你們有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才嗎?”王巍回憶說:“當時,對方提出這個問題,很可能料到我們沒有相關人才,這個合作就免談了。可對方萬萬沒想到的是,我們中國有20多個研究埃及史的學者,其中不乏懂得埃及象形文字的人才。”
后來,中國考古團隊終于如愿來到埃及新王國時期首都盧克索著名的卡爾納克神廟和戰神神廟進行考古挖掘。中國考古隊采用的考古技術手段和考古方法不僅不落后,甚至比肩西方考古隊,引起了國際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
2015年,經過王巍的努力,還促成了中國和中美洲國家合作發掘瑪雅文明首都科潘遺址項目。通過這些年對世界各地考古的比較研究,王巍和研究團隊取得了不少重大發現。“比如,我們發現小麥大約在5000年前傳入中華大地。通過對黃牛、綿羊的DNA研究表明,這些動物物種來自西亞;而中國的粟、黍也往西亞傳播。”其中,冶金術的傳入極具代表性,王巍解釋說:“冶金術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從西亞傳入中國時,大多是體積較小的武器和工具,而由于中華民族的祖先在冶金術傳入之前已掌握了燒制陶器的高溫技術,所以,在學習吸收了冶金術技術后,將冶煉青銅器工藝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制作出大型青銅器,并用作表現等級的重要禮器。在眾多從外傳入的技術中,中華文明將青銅文明發揮到了極致,很好地證明了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為我所用、創造發展’的特性。”
2017年,王巍從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任上卸任,但他并未停下忙碌的腳步,身為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長,仍在考古一線奔波操勞。
退休后這兩年,王巍又多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新身份——唱作人。他將對中國考古的一生熱愛寫入歌曲中,由他作詞、作曲并演唱的《我是中國考古人》和《百年心語》,飽含了他對中國考古的感情與期待:“我是一個父親,不能常照顧家庭。我是一個丈夫,不能與妻朝夕與共。我是一個兒子,不能常把父母陪伴。舍小家為大家,要為中國考古貢獻終生。”這些歌詞在王巍的心中極具畫面感,每次唱起,他都會想起自己和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家,“雖然苦,但值得”。
(摘自《環球人物》劉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