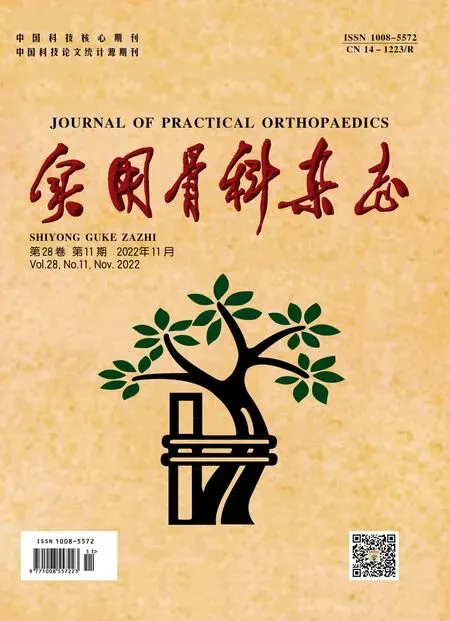膝關節鏡術后慢性期疼痛預測模型的構建與驗證
馮重陽,姬振偉,吳鵬,王志學,張智翔,方懷明,丁勇
(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骨科,陜西 西安 710038)
膝關節鏡用于治療多種膝關節損傷,包括輔助性診斷、半月板損傷、前交叉韌帶斷裂等,是骨科醫生常用的手術方式之一[1]。和傳統的膝關節開放手術相比,關節鏡能夠最大限度減輕軟組織損傷、縮短住院時間[2],減少術后并發癥,被認為是一種安全性高的微創手術。因此在過去30年間,手術量大幅增加[3],但“微創”并不意味著“無創”。Hoofwijk等[4]的研究發現,大約有30.8%的患者在膝關節鏡治療后出現慢性疼痛。術后慢性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CPSP)是一個嚴重的醫療保健問題,可導致康復延遲、功能障礙殘疾、疼痛相關的抑郁或焦慮加劇,致使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和經濟負擔增加。因此,識別CPSP高危患者,并開展針對鎮痛策略非常重要。
目前,CPSP的病因學和病理生理學機制尚不清楚,盡管在各個外科領域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確定了CPSP的發病率和部分危險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學資料、遺傳多態性、社會心理狀態、手術類型、術后急性期疼痛[5],但仍然存在爭議,且目前對膝關節鏡術后CPSP的發生、發展還知之甚少,同時也缺乏針對關節鏡術后CPSP的高效預測模型。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不同膝關節鏡治療方式術后CPSP的獨立危險因素,建立適用于臨床的列線圖預測模型,幫助骨科醫生早期識別高危人群,制定個性化干預措施。
1 資料與方法
1.1 選取資料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收集了2019年9月至2021年2月在唐都醫院骨科收治擇期行膝關節鏡手術的患者。患者接受腰麻或全身麻醉,手術方式包括關節鏡清理性手術(游離體取出術、滑膜清理術、交叉韌帶囊腫清理術)、半月板修復或縫合術、交叉韌帶重建術、髁間棘撕脫骨折復位內固定術。所有患者手術均為單側,術后常規給予抗生素2 d預防關節感染,術后12 h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鈉預防下肢血栓形成,針對不同手術方式提供個體化的康復指導,4~5 d出院。本項研究所有手術均由科室同一組醫生完成,術者經驗豐富,操作精確,最大程度減少了手術帶來的損傷。研究經唐都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向患者介紹研究目的及方法,均表示同意后進行此次研究。
1.2 資料收集 對于符合標準的患者入院后由主管護士指導進行疼痛認知及疼痛數字評分(numeric rating scale,NRS)宣教,正確理解,并向醫護人員匯報自己的疼痛評分,收集術后72 h和術后3個月的NRS。從醫院電子病歷系統中記錄患者的性別、年齡、手術側別、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受傷方式、病程、吸煙史、糖尿病史、關節軟骨損傷Outerbridge分級[6]、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中關節腔灌洗量。
1.3 入選標準 NRS范圍0~10分,其中0分代表無痛,10分代表最嚴重的疼痛。CPSP的診斷依據國際疼痛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11th re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1)指南[7]:(1)手術后出現的疼痛;(2)疼痛持續超過3個月[8-9];(3)排除慢性感染或惡性腫瘤作為疼痛來源。CPSP的分界值設定為NRS≥4分[4,10],指的是中、重度疼痛。術后3個月主管醫生對患者進行電話或門診隨訪,記錄手術區域的NRS,觀察是否發生CPSP。
1.4 一般資料 236例患者參與完成了本項研究,其中男127例,女109例;年齡16~77歲,平均(42.71±14.12)歲。根據患者術后3個月的NRS分為疼痛組29例,無痛組207例。疼痛組男13例,女16例;平均年齡(62.03±09.52)歲。無痛組男114例,女93例;平均年齡(40.00±12.46)歲。

2 結 果
2.1 一般情況 術后3個月時患者均未發生化膿性關節炎、下肢血栓、傷口愈合不良等并發癥。
2.2 CPSP單因素分析結果 兩組患者在年齡、BMI、糖尿病史、術后72 h NRS、關節軟骨損傷Outerbridge分級等方面,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CPSP多因素分析結果 將單因素分析提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危險因素行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5,容忍度>0.2,說明各因素之間無明顯的共線性問題,而后行多變量Logistic回歸,結果顯示高齡、BMI≥24 kg/m2、術后72 h NRS≥4分、Outerbridge分級Ⅲ~Ⅳ級是膝關節鏡術后CPSP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

表1 術后CPSP危險因素單因素分析

表2 術后CPSP的Logistic回歸分析
2.4 CPSP預測模型的構建 利用R語言實現預測模型的可視化,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將年齡、BMI、術后72 h NRS、Outerbridge分級4個獨立危險因素導入模型中,個性化預測膝關節鏡術后CPSP發生概率。根據每個危險因素對應分數相加得出總分,總分做垂直線所對應的風險軸的點即為膝關節鏡術后CPSP的預測概率(見圖1)。例如1例57歲女性患者,行右膝關節鏡檢查,半月板修整成型術。分別找到每個獨立危險因素所對應的分值,57歲為64.68分;BMI為26.67 kg/m2為17分;Outerbridge分級為Ⅱ級為0分;術后72 h NRS為6分為14分。所有變量總分值=64.68+17+14=96.68分,術后CPSP的發生概率約為55%。因此該患者是膝關節鏡術后CPSP發生的高危人群,應當提前給予相應的對癥處理措施(見圖2)。
2.5 CPSP預測模型的驗證 本研究得到該預測模型的C-index為0.969,具有良好準確度。采用Bootstrap法進行內部驗證,收集的患者信息重復抽樣1 000次,得到C-index為0.968,說明該預測模型具有較好的區分度。此外,校準曲線顯示術后慢性期疼痛的預測發生率與實際發生率基本一致,有很好的擬合關系(見圖3)。通過繪制預測模型的ROC曲線,得到模型的AUC=0.969[95%CI(0.950,0.992)],以約登指數最大值所對應的分數為最佳截斷點79.41分[11],這表明本模型的預測價值較高,可以為臨床預測提供一定的參考(見圖4)。

圖2 膝關節鏡術后CPSP發生概率示意

圖3 術后慢性期疼痛預測模型的校正曲線 圖4 術后慢性期疼痛預測模型的ROC曲線
3 討 論
膝關節鏡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創傷小、術后恢復快、并發癥低的微創手術[12]。隨著治療性關節鏡手術量的增加,尤其是涉及韌帶重建等復雜手術的開展,術后持續疼痛已成為患者對術后療效質疑的主要原因[13]。CPSP使患者承受巨大痛苦,最終可能導致焦慮、抑郁和其他心理問題[14]。因此,我們需要重視術后慢性期疼痛。之前的學者也分析了多種因素對膝關節鏡術后CPSP形成的影響,但都無統一定論,也無預測模型,不能將影響因素以直觀的方式量化表現出來。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膝關節鏡術后慢性期疼痛的獨立危險因素,首次建立可以用于預測CPSP的模型,為促進臨床實踐中CPSP高危人群的篩選制定個性化的鎮痛策略。
本研究通過對236例膝關節鏡患者隨訪,術后急性期疼痛92例(38.99%),術后3個月CPSP 29例(12.39%)。Hoofwijk等[4]的研究得出膝關節鏡術后急性疼痛的發生率為37.5%,術后1年慢性疼痛的發生率為30.8%。本研究與Hoofwijk研究的術后急性期疼痛發生率相似,但慢性期疼痛的發生率較低,可能與我們只統計了術后靜息態NRS有關。
本研究預測膝關節鏡術后CPSP的獨立危險因素包括高齡、BMI、關節軟骨損傷、術后急性期疼痛。(1)高齡是術后慢性期疼痛的危險因素。Palazzo等[15]研究發現50歲以上患者術后慢性疼痛患病率更高,這可能與高齡患者的膝關節疾病主要以退行性半月板撕裂或骨關節炎有關。1997—2014年間,多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顯示,關節鏡治療退行性半月板撕裂和骨關節炎是無效的[16]。Moseley等的研究以及Sihvonen等的一項多中心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關節鏡下清理或灌洗治療膝關節骨關節炎的效果和假手術療效沒有差異[17-18]。另一方面由于高齡患者局部血液循環較年輕人差,術后組織修復能力弱,并且理解和認知能力下降,對術后疼痛較恐懼,容易產生焦慮、抑郁的心理,導致術后慢性疼痛發生[19]。(2)BMI≥24 kg/m2是術后慢性期疼痛的危險因素。肥胖在全球已非常流行,2016年美國的肥胖患病率就高達39.8%[20]。研究表明,肥胖是膝關節鏡術后功能損害的危險因素[21]。Enrico等[22]的研究表明肥胖是膝關節鏡術后6個月繼續使用阿片類藥物的預測因素。(3)Outerbridge分級Ⅲ~Ⅳ級是術后慢性期疼痛的危險因素。研究觀察到伴隨Outerbridge分級增加,患者CPSP患病率有明顯的增加趨勢[4]。Westermann等[23]的研究發現關節損傷越嚴重,術后阿片類藥物使用會增加。關節軟骨磨損造成下肢力線改變,行關節腔清理和半月板修整只能減輕臨床癥狀,無法徹底根治,導致術后CPSP發生,因此要充分認識疾病的發展過程[24]。(4)術后72 h NRS≥4分是術后慢性期疼痛的危險因素。Perkins等[10]的研究證明術后急性期高度疼痛會增加患慢性疼痛的風險。Horn等[25]研究也證明了術后急性NRS是CPSP的重要風險因素和預測因素。CPSP的潛在發病機制可能是由于手術壓力導致的炎癥細胞因子的不平衡,使中樞神經系統敏感化。術后急性疼痛通過使外周神經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敏感而與CPSP密切相關[26]。據報道,對術后急性疼痛的有效管理可以防止中樞神經系統的敏感化,從而降低CPSP的風險[27]。綜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的膝關節鏡術后CPSP預測因素可信度強,提示加強關節鏡圍術期疼痛管理尤其是術后急性期疼痛控制是未來降低術后CPSP的一項重要突破口。
列線圖模型作為可視化的風險預測工具,是將多因素回歸分析得到的危險因素進行加權整合,而后直觀的顯示臨床指標對個體預測值的影響[28],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隊列研究。現階段國內尚缺乏具有針對性、個體化的膝關節術后CPSP預測模型。本研究將分析出來的獨立危險因素進行模型構建,開發了一個簡單、直觀的列線圖,用于量化術后CPSP發生風險。采用內部驗證、校準曲線、ROC曲線多角度證明了模型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該模型所需的臨床參數獲取方便,可對患者進行初步預測;對于有較高風險患者及時采取相應的治療措施,這不僅可以降低經濟成本,還對改善患者生活質量,治療意義重大。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單中心的回顧性研究,納入的樣本量有限,手術種類相對較為簡單,治療性關節鏡手術如多發韌帶損傷修復重建的比例低,潛在的危險因素也被限制只能在病例記錄中獲取。而術前患者疼痛程度及心理健康程度等可能對術后CPSP產生影響的因素并未予以分析。下一步我們將設計更詳細和完整的大樣本前瞻性隊列研究,以進一步提高和確認構建預測列線圖的準確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識別了高齡、BMI≥24 kg/m2、術后急性期疼痛、Outerbridge Ⅲ~Ⅳ級是膝關節鏡術后3個月發生CPSP的獨立危險因素,構建的術后CPSP列線圖模型在驗證過程中表現出較好的預測能力。模型中的危險因素定義明確、易于采集、概率計算操作簡便,有望在今后為預防和個性化治療膝關節鏡術后CPSP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