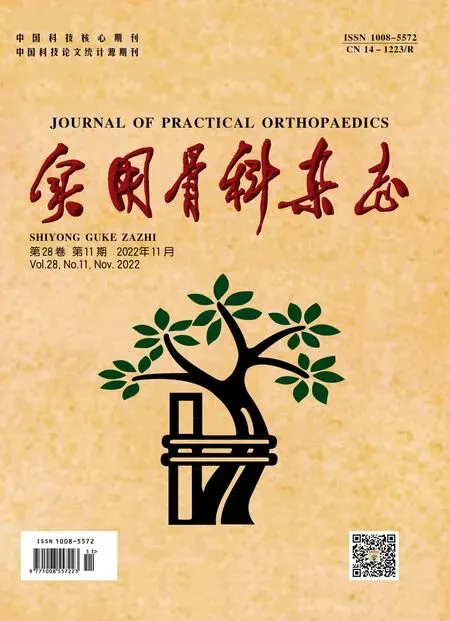脆性骨折患者骨轉換標記物的變化及相關性分析
譚同軍,錢衛慶,劉暢暢,高潤子,姚年偉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南京中醫院骨傷科,江蘇 南京 210000)
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一種常見的全身代謝性骨骼疾病,主要表現為骨量減少、骨小梁的微觀結構退化、骨強度逐漸降低,進而導致發生骨折的危險性升高,是中老年人尤其是絕經后女性常見的疾病之一。根據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療指南[1],目前臨床上骨質疏松癥的診斷主要為使用雙能X線吸收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EXA)進行骨密度測定,骨密度T值<-2.5 SD即診斷為骨質疏松癥。筆者臨床工作中發現有患者骨密度檢查結果為骨量減少或骨量正常,但是發生了脆性骨折,進而診斷為骨質疏松癥。此類患者的骨密度、骨轉換標記物等是否存在一定的特殊規律,目前研究較少。筆者收集了發生脆性骨折且DEXA骨密度檢測為骨量減少患者的骨密度、骨轉換標記物等指標,并和同樣骨密度范圍內、未發生骨折患者的骨轉換標記物進行比較,探討骨轉換標記物對脆性骨折的發生、發展及治療的指導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在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南京中醫院門診和住院治療的確診為脆性骨折(包括脊柱椎體骨折、橈骨遠端骨折及髖部骨折)且骨密度檢查為骨量減少(-2.5 SD≤T值≤-1 SD)的中老年女性患者為觀察組。為保持比較對象的一致性,設立骨密度檢查為骨量減少,但未發生脆性骨折的中老年女性患者為對照組。共計116例中老年女性患者納入本次研究。根據是否發生脆性骨折,對入選的患者進行分組,其中45例發生脆性骨折患者為觀察組,71例未發生脆性骨折患者為對照組。兩組患者年齡、體重、身高、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骨密度T值等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年齡在60~95歲之間且骨密度檢查為骨量減少(-2.5 SD≤T值≤-1.0 SD)的女性患者。排除標準:(1)曾經發生過脆性骨折或骨密度檢測達到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已使用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者;(2)患者有影響骨代謝的疾病,如甲狀旁腺功能異常、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庫欣綜合征、慢性肝病、慢性腎病及肝腎功能異常等;(3)存在自身免疫系統疾病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柱炎及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疾病;(4)患有惡性腫瘤、嚴重營養不良、長期臥床不能下地活動的患者。
1.3 研究方法 所有入組患者均行DEXA骨密度檢測,測量腰椎和股骨頸的骨密度T值;對于測量部位既往有骨折史(非脆性骨折)者,選擇對側未受損肢體作為測量部位。參照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基于DEXA骨密度測定T值在-1.0 SD~-2.5 SD之間為骨量減少。骨轉換標志物測定:所有患者于就診第2天晨時空腹采靜脈血,檢測相關指標。骨轉換標志物選用血清骨鈣素(osteocalcin,OC)、Ⅰ型原膠原氨基端前肽(N-terminal peptide of type Ⅰ collagen,P1NP)及β-Ⅰ型膠原交聯羧基末端肽(C-terminal peptide of type Ⅰ collagen,CTX)、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及Ca2+濃度。試劑盒設定的正常范圍如下:OC為6~24.6 μg/L;ALP為42~140 U/L;P1NP為21.3~112.8 μg/L;β-CTX為131~900 ng/L;Ca2+為2.1~2.6 mmol/L。對比分析兩組患者的年齡、身高、體重、BMI、骨密度、骨轉換標記物(OC、P1NP、β-CTX及ALP)及血清Ca2+濃度。

2 結 果
兩組患者在年齡、體重、身高和骨密度T值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觀察組平均BMI較對照組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兩組患者OC、ALP、β-CTX和Ca2+濃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觀察組OC、ALP、β-CTX和Ca2+濃度高于對照組(P<0.05),而觀察組P1NP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各項骨轉換標記物比較
將脆性骨折的發生作為因變量,年齡、身高、體重、OC、ALP、P1NP、β-CTX、BMI、Ca2+濃度及骨密度作為自變量,其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脆性骨折的發生與體重、OC、ALP、β-CTX、BMI和Ca2+濃度均呈顯著的負相關(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脆性骨折發生的相關因素分析
3 討 論
隨著社會老齡人口的不斷增長,骨質疏松癥作為一種年齡相關疾病其發病率逐年增高,脆性骨折是骨質疏松癥最嚴重的并發癥。脆性骨折一般是指受到輕微外傷或日常生活即發生的骨折[1]。骨質疏松癥的診斷一般是根據DEXA骨密度檢測結果確定,但是DEXA骨密度檢測結果僅反映骨的靜止狀況,不能全面反映患者的骨強度。在描述骨骼質量時,需考慮骨轉換情況、骨小梁結構等骨質量因素。
臨床工作中常會遇到患者骨量減少但發生了脆性骨折的情況,此類患者根據指南[1]應該診斷為骨質疏松癥,但對其是否需要抗骨質疏松治療目前存在一定的爭議[2-3]。鄭博等[2]研究認為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中“發生了脆性骨折臨床上即可診斷骨質疏松癥”這一條可能擴大骨質疏松癥人數,浪費更多的醫療資源,由此認為對僅發生脆性骨折的患者診斷為骨質疏松癥者需慎重,警惕過度治療可能。但是姚寶紅[4]通過對1 315例60歲以上的骨質疏松性骨折患者研究發現,患者骨質疏松癥總體診斷率為13.0%,首次骨質疏松性骨折人群中,骨質疏松癥診斷率僅為10.2%,認為當前骨質疏松癥的診斷和治療率均偏低。同時國外的一項研究也認為對于髖部、橈骨遠端及椎體發生脆性骨折后抗骨質疏松治療相對較少,應當加強[3]。對骨量減少的老年患者抗骨質疏松治療能改善其腰椎和股骨頸的骨密度,降低發生脆性骨折的風險[5]。
如何判斷骨量減少患者是否需要抗骨質疏松治療是臨床醫生面臨的問題。血清骨轉換標志物可用于評估個體在一段時間內發生骨質疏松的可能性。骨轉換標記物骨重塑過程中產生的生物因子,存在于尿液或血清中,并指示骨轉換的速度。骨轉換標記物可分為骨形成的標志物,如總ALP、骨特異性ALP、P1NP、OC和β-CTX。骨吸收的標志物如羥脯氨酸、吡啶啉、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5b、脫氧吡啶啉。P1NP反映成骨細胞合成骨膠原的能力;β-CTX反映破骨細胞的骨吸收活性,一般推薦P1NP為骨形成的生化標志物,β-CTX為骨吸收的標準生化指標[6]。骨轉換標志物有助于預測絕經前女性在絕經之后發生脆性骨折的概率[7],根據骨轉換標記物結果合理抗骨質疏松治療可以降低絕經后女性發生脆性骨折風險[8-10]。一項病例對照研究[11]招募了210例符合條件的絕經后婦女,并比較了她們的DEXA骨密度掃描結果及檢測各組ALP、β-CTX、P1CP,顯示骨質疏松癥患者ALP、β-CTX顯著升高,P1CP顯著降低,提示骨質疏松癥患者的骨形成及骨吸收均處于高水平狀態。
本研究對發生脆性骨折但骨密度檢測為骨量減少患者的骨轉換標記物發現,發生脆性骨折的患者骨轉換標記物和未發生骨折患者存在一定差異。本研究選擇了OC、ALP、β-CTX和P1NP作為骨轉換標記物,發現發生脆性骨折且骨密度提示骨量減少的患者,其OC、ALP和β-CTX均顯著升高,雖然P1NP的指標較對照組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結合觀察組OC及血清Ca2+濃度的顯著升高,筆者認為觀察組患者骨量減少且骨轉換處于高轉換狀態,這樣患者易于發生脆性骨折,需要抗骨質疏松治療。同時通過脆性骨折的發生和骨代謝指標的相關性分析發現,脆性骨折的發生與體重、OC、ALP、β-CTX、BMI和Ca2+濃度均呈顯著的負相關,對于體重和BMI高,OC、ALP成骨指標和β-CTX破骨指標升高的患者,發生脆性骨折的風險升高。
骨質疏松癥的早期診斷非常重要,抗骨質疏松治療的首要目標是預防骨折,減緩骨質疏松進展和降低其后導致的脆性骨折的風險。骨質疏松癥的發病機制源于骨轉換的不穩定狀態,骨質量減少而導致骨強度下降。因此,必須認識到骨密度檢測作為綜合評價骨強度的唯一手段是不夠的。骨密度的變化可能很小,其作為治療反應的單一監測工具并不是特別靈敏,需更多的指標來評估骨質疏松的程度。有研究認為應用血清25羥基維生素D及血清總膽固醇水平預測老年女性髖部骨質疏松骨折具有可行性[12]。結合本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對于骨量減少的中老年女性,需檢測骨轉換標記物,若骨轉換標記物結果提示患者處于高轉化狀態,患者發生脆性骨折的風險很高,需要進一步抗骨質疏松治療。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對于骨轉換標記物的選擇方面,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選擇了ALP而未選擇更為精確的骨特異性ALP作為參考指標,通過排除患者肝腎功能異常的方法降低其誤差。同時,本研究比較了患者就診時的相關指標,暫未涉及后期的隨訪結果,后期需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