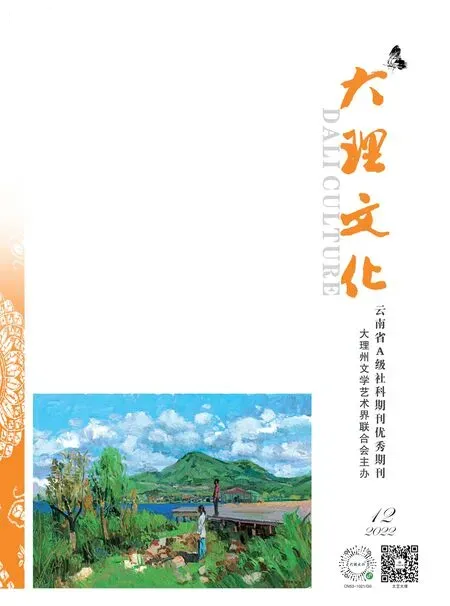書事
●疏雨
雨天紙墨明潤,尤其使人心安。若手中有一本心儀的紙質書,紙頁綿密,指尖觸處便有了一種自然的、隱匿的情愫在悄然洇漫。
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大理師范讀書,當時對閱覽室的眷戀,因為書,也因為人。
學校的閱覽室設在電教館內,從我們住的女生院到電教館可以穿過常青園,抄近道。閱覽室每天晚飯后開放一小時,許多同學都會提前去等著開門。我通常會帶著筆記本和速寫本,提前半小時離開宿舍,在去完成閱覽室讀書的這個主旋律之前,給自己先來上一個小樂段——完成一幅速寫。這個樂段通常是在常青園悄然進行。
常青園的南面是一幢黃墻青瓦的老蘇式樓房,當時美術班的畫室就設在里面,它斑駁的墻身便是常青園南面的圍墻。園子東、西、北三面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常見的半人高的磚墻和上半部分的鋼筋圍欄,三面各留了一道月亮門。圍欄上面爬滿了爬山虎,大片大片的青綠,陽光明媚的時候,光影綽綽,層次豐富。常青園因常青而得名,除了葳蕤浩蕩的爬山虎,不大的園內還有七八棵梨樹。每到春來,梨花便鋪天蓋地地開著,有時會看到有人在樹下吹笛子,花瓣簌簌落下,我懷疑是被那裊裊的笛聲顫落的。那笛聲不但顫落了梨花,還顫動了我同窗好友的芳心,她的校園戀情幾經波折,在畢業三年后終于修成了正果,這是后話。北門邊有一個花架,是用來支撐一棵古老的紫藤,它藤莖遒勁,如書法中筆走龍蛇的行草。梨花開的時候,紫藤也一串串競相開了,每天路過這里,我都會圍著余暉中的藤蔓、花葉,選一個角度,在閱覽室開門前五分鐘完成一幅速寫,一邊沙沙地畫,一邊聽花瓣偶爾落下的聲音。這個園子,這個時節,可入畫的還有小路旁花壇中的杜鵑,白杜鵑白而清透,纖塵不染;粉杜鵑如云似霞,溫柔爛漫,洇染著畫紙,也洇染著花季女孩的心事。杜鵑花旁有一棵四季常青的老柏樹,像一位智者駐立在那兒,風吹則清揚,風平則靜安。
有時這個樂段也會在電教館進行。閱覽室對面有一棵法桐,主干需兩人合抱,枝葉繁茂,特別是秋天,掌狀的葉片在風中俯仰,翻飛出深深淺淺的青綠橙黃,映著湛藍的天,煞是迷人。閱覽室外等待的人們會先拿出自己手中的書看著,我會走走停停,選取最佳的角度,給法桐來一個速寫,或畫全貌,或畫一枝。后來,我翻開速寫本,發現除紫藤、杜鵑、柳樹、石桌石椅外,畫得最多的還是那棵法桐。每年十月底,法桐開始陸陸續續落葉,我便每天撿一片夾在筆記本中,這些葉子一片片由青黃、明黃到橘黃、枯黃過渡著,連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黃色系色卡。每片葉子上我都寫上日期,偶爾也寫上一句“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所有的開放都浸透著憂傷,芬芳和美麗從來都脆弱易碎”“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等諸如此類傷春悲秋、“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句子。速寫本、筆記本在我手中隨機切換,當時的我始終確信,對于眼前那些方寸的美好,我能用畫筆將它描繪出來,畫不出來的亦可以用文字表述出來,到了光陰知味的年紀,愈發懷念少年時那青澀莽撞、不諳世事的自信和勇氣。
待到閱覽室開門,便隨眾人蜂擁進去,選好自己要讀的書,把學生證交給管理員擺在那本書的位置上,便可以接過書找個空位坐下來。讀自己的書可以在上面寫寫畫畫,讀借閱的書就不能這樣任性了,見到心儀的句子連忙抄到筆記本上,待回去以后細讀細品,感覺唇齒留香,興之所至,還會在旁邊即興地寫寫畫畫。讓人倍感糾結的是,正抄到酣暢淋漓處,“叮——”閱覽室關門的鈴聲響起,如剛剛到口的佳肴,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來。收拾好筆記,換回學生證出了閱覽室,一路牽腸掛肚,當晚,連睡覺都不踏實。第二天必定早早去等著,一開門直奔那本書,急切又小心地翻到昨天那頁,如獲失而復得的寶貝,暢快地抄起來。如果有事耽擱了,遲到一步,書被別人先借去,就會覺得一個晚上都沒著沒落的,特別沮喪。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讀《名作欣賞》,有中外名作賞析,還有書法和繪畫作品的品鑒,我會反過來去找文中提到的書或文章來讀,這種以書找書的方式,短時間內擴大了我的閱讀量,我很享受這樣亦讀亦賞、亦賞亦讀的狀態。閱覽室的管理員是一個留著齊耳短發、眉眼娟秀、有著書卷氣的小姐姐。有幾次我在書架上找不到《名作欣賞》的時候,發現她手中正是這本書,原來她也喜歡讀這個。她抬起頭來,看到我,會順手把書遞給我,我感到有些過意不去,便說:“我找別的書看看。”她笑笑說:“沒事,等你們上課去了,我再讀。”到后來,只要看到我進門,她都會事先把書拿下來放好在桌子上。這樣的默契,讓我感到一種秘而不宣的溫暖。
除了《名作欣賞》,《美術》月刊也讓我很著迷。里面會有畫壇的動態,一些繪畫作品的欣賞、技法,還有畫家的故事。有一位高我們一屆的師兄,他是美術專業班的翹楚。他們班經常以常青園東面的外墻做“展廳”,在飯點的時候展出他們的作品:素描、水彩、水粉、油畫、靜物、人物、風景。打飯路過的師生們各自端著碗一邊吃,一邊看,站的站,蹲的蹲,有的還用舀飯的勺子或是穿著饅頭的筷子“指點江山”,而這位師兄的作品總是會被一眼認出,辨識度很高。我看過他們班在常青園寫生,模特穿著鮮艷的民族服裝,臉部和五官的輪廓硬朗有型。其他學生畫完模特后都是以實景為背景,或是一面爬山虎,或是一段斑駁的老墻,或是那棵紫藤,都因自己寫生的角度而定。唯有他的背景是東升的旭日和山崖上一塊沐著橘色晨光的磐石。就是屢屢畫出這樣“驚世”之作的師兄,他來閱覽室也是直奔《美術》月刊來的,可每本雜志只有一本,彼時他剛畢業留校,在他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和閨蜜也和他們打飯菜拼餐過,所以我還是會有“他是學長”的思維定勢,并不拿他當老師來畏著,心里還偷偷地想:我要早去閱覽室拿下那本書,他是老師,老師是可以借回去看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穿過常青園,奔向電教館時我便一路小跑。一邊跑,一邊透過北邊圍欄上枝蔓間的空隙看向主干道,看看他那輛斑馬自行車有沒有倏忽閃過。聽說,他的自行車變“斑馬”是有來由的。那一段時間,偷自行車的特別猖獗,他也不可避免地丟了好幾輛,后來他索性弄來點白油漆一條一條畫上道道,儼然是一匹精瘦有型的斑馬,從此,江湖任我行,再沒丟過。好幾次從圍欄綠植的縫隙間看到那斑紋穿花度柳一閃而過,心里一激靈,不好,又遲一步,果然,到了閱覽室門口,那漂亮、不羈的小斑馬,已然在一眾黑色普通的自行車中清新脫俗地小憩著了。就是在跑不過“斑馬”的時候,我又開拓了新的“領域”,讀起《散文》月刊來。在其中一期的借閱卡上,我發現了我們舞蹈老師的名字,記憶中的她很美,白皙、知性、優雅,從未大聲說過一句話。
當然,關于《美術》月刊的借閱,我也享受過一次“教師待遇”,也是僅有的一次。不記得是哪一期了,里面有許世虎先生的水彩作品欣賞,其中有一幅畫的是窗邊書桌上的玻璃花瓶里插著一束菊花,橘黃的、暗紅的、淺綠的、素白的,背景是透著光的淡紫色的窗簾,流動的色彩和光影讓人感覺陽光也是柔軟的。寫實與寫意悄然融合,水色迷離、花影搖曳。他筆下的玻璃花瓶分外清透,花朵氤氳的氣氛又是那么恰到好處。尤其是色彩之間的對比和過渡尤為絕妙,在仿佛油畫般的濃郁渲染中,飄溢著水彩畫特有的透明輕盈的質感。這種清水洗塵、溫婉和煦的美一下子讓我心旌蕩漾,我要把它畫下來!當時就暗暗下了決心,也不知道我這個非美術專業的“票友”,哪來那么大的勇氣。那天,管理員小姐姐不在,聽說她考研去了,是學校一位教《文選》的劉老師先來頂崗幾天。我又激動,又有些不安地等到關門的鈴聲響起,看書的人陸陸續續離開后,來到書架前,跟劉老師說,我想把這本書借回宿舍。他聽了有些詫異,我翻開那幅畫給他看:“我想把它畫下來。”他看看書,又扭頭看了看我的學生證,面露難色。“我一定盡快畫完,保證愛護好。”他聽了隨和地笑笑:“沒事,你慢慢畫。”“謝謝!”我抱著書高興地飛奔回宿舍。

接下來的幾天,逼仄的宿舍里,三分之一的空間成了我的畫室。我不知晨昏地畫,畫到酣暢處,濃墨重彩,水色淋漓;畫到瓶頸處,無從下筆,就看著天上的藍天流云和窗外的柳樹發呆。同窗、舍友習慣于看著我的背影偷偷關注我,在我洗完調色盤的時候,我的飯盆已被悄悄扣上了碗,里面的飯菜還有余溫。在我外出讀書或寫生回來的時候,舍友們正悄悄欣賞我的作品,為我收拾沒有徹底清除的顏料,多年以后,我才由衷感動——感謝那些年她們能那么悅納一個有些清冷,又有些一意孤行的女孩。記得一周后,我將書交還劉老師手里,并把我臨摹的畫也偷偷給他看,他看看書上的,又看看我畫的,慈藹地笑著,朝我豎起了大拇指,如今劉老師已過世多年,他溫厚的笑容卻清晰如昨。
二
讀師范時遇到教我們《文選》的左老師亦是莫大的幸運,他博覽群書、才情飛揚。《文選》課上得慷慨激昂、回腸蕩氣,特別是上古典文學的時候,他會不時地開懷大笑,笑得極爽朗,讓我一度想到:這么清癯嶙峋的他,竟會笑成京劇中豪氣沖天的銅錘花臉!吟到詩詞的時候他時而鏗鏘,時而低回,興之所至,他會微瞇著眼睛搖頭晃腦地唱起來,然后習慣性地用右手將額前的頭發往左邊一捋——那叫一個酷!滿臉陶醉的笑意。真是腹有詩文氣自“狂”!這樣的課堂,如正在釀造一壇清冽、芳香的美酒,我們的青澀、懵懂、求知、感悟、愉悅和老師的博學、睿智、灑脫、孜孜不倦……一股腦兒釀入其中,歷久彌香,回味悠長。課堂上的他旁征博引,融匯古今,他所給予我們的遠遠超出了教材,我們都以能找到他引用的詩詞典故為榮。
他愛書,熏陶得我們也愛讀書,每個人每周有一次到學校圖書室借書的機會。圖書室先是在學校那一排琴房盡頭的一幢蘇式建筑的一樓,周圍樹木掩映,就像西方油畫中的林中小屋。里面空間狹小昏暗,一進門就有書味,是那種新書、舊書很多書混合的味道,和那木制的老書架、蘇式的老屋很是契合。在里面尋書,就像在一本巨大的老書中尋寶。從圖書室借來的書,舍友們一個傳一個,巧妙“錯峰”,人人都有得讀,有時,還和其他宿舍的交換讀。大多都是被子里面打電筒,廢寢忘食也要一本不落地讀完。當然,也有人等宿管走后,點蠟燭讀的,讀得入迷,蚊帳燒了一個大窟窿,整個宿舍一夜驚魂未定。《包法利夫人》《簡愛》《茶花女》《文化苦旅》《平凡的世界》……就是在那個時候,一本接一本排隊讀完的。記得讀到《穆斯林的葬禮》的時候,一個個被楚雁潮和新月感動得稀里嘩啦,無限感慨,能遇見這么美好這么長情的愛,死了也值。
有一次,我從學校圖書室借來一本《宋詞縱談》,這本書真正為我打開了宋詞這扇窗。富有樂感的長短句、唯美的表達形式,賦予了宋詞極強的畫面感和極富韻律的節奏感。我為“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兒女柔情、“大江東去浪淘盡”的風云豪情、“怎一個愁字了得”的富貴閑情著迷。它的美感,不僅僅是能夠表現精致的細節,打動人心,它還可以表現浩瀚的氣魄,窮盡山河。也許真正美好的藝術大抵如此,當它擺在你的眼前,透過遠古的塵埃,你真正能夠看懂其中多少的美妙意蘊,就在于你的眼、你的心。它似閃爍著美之光芒的春波,倒映著翩鴻般的古典情懷,讓我徹底沉醉其間。我跑遍全城大大小小的書店,想買到這本書自己收藏,反復玩味,可惜都一次次無功而返。不得已以遺失圖書處理,給圖書室交了三倍罰金,才如愿以償。后來又花“巨資”買下了《唐宋詞鑒賞辭典》,“大快朵頤”。
當時左老師教兩個班,每學期開學他都會給每班買十本書讓我們傳閱,到學期結束,各班《文選》科目前十名的同學就有幸去挑選自己鐘愛的書。那可是我們最崇拜的老師給買的,何等殊榮啊!按當時的書價,二十本書大約在兩三百元,老師的工資并不高,可他每個學期都買,雷打不動,令我們甚是感動,更重要的是他及時地讓豆蔻年華的我們浸潤在書香里,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多年以后讀到了一句話才了悟:他固守著孤獨和清貧,卻是用生命來提攜學生。
記得有一次,左老師通知前十名的學生到他那兒去挑選書,按名次先后挑,考得越好挑的余地就越大。當時我和另外一名同學恰好不在學校,老師就幫我們一人挑了一本,當我們回校去取的時候,我發現另外那個同學的《楊貴妃秘史》封面艷麗好看,而我的封面是灰灰的水墨畫,上面寫著《美的神游——從老子到王國維》。我有些不高興,為什么我的不是那本漂亮的呢?多年以后,我才發現,原來,老師是懂我的。
左老師是慷慨的,但也有吝嗇的時候。記得當時他有好幾架子書,每架書都用布簾遮好,我們很難一睹“芳容”。有一次我去交作業,老師正在讀書,布簾是拉開的,露出了許多我們耳熟能詳卻無緣一讀的書。于是,我壯著膽輕聲說:“左老師,我想,我想借本書……”看著他面露難色,我有些后悔我的冒失了,可說出的話收不回了。只見他沉思片刻,伸出三個指頭,一個一個掰:“第一,不許弄丟了;第二,不許弄壞了;第三,不許有折痕。”為了讀書我只好忍受他的“再三刁難”,然后挑了一本遇赦似的飛奔回宿舍,封上書殼如饑似渴地讀起來。記得書名是《凝重與飛動》,講的是中國的雕塑和書法,書里說:“雕塑是凝固的音樂,書法是紙上的舞蹈。”作者試圖去探尋“為什么我們民族的藝術那般空靈,歷史卻那般沉重”。我細細品讀,琢磨,又找了一些關于雕塑、書法的書來讀,還找了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和李澤厚的《美的歷程》來對照賞讀,受益良深。
我們畢業后,左老師考上復旦大學的研究生,離開了師范學校,只身赴上海碩博連讀。畢業后輾轉了幾個城市,如今,回到了大理,在山環水抱的大理大學安定了下來,每日授課、讀書,居于蒼山腳下,櫻花深處。每年初春,這里的櫻花繽紛開落,他就在這書香中和花香中,時而疏狂,時而簡靜。每次放假回巍山,他都會送給我許多書,少則十來本,多則三四十本,他總會說:“有些是我做研究用過的,有些是買重了的,你隨便看看。”這些“隨便看”的書中有《我們仨》《顧隨詩詞講記》《獻芹集》《芳園筑向帝城西》……年逾不惑的我,還如期接受近三十年前老師的饋贈,接受這份精神投喂,真是倍感溫暖和幸福。
三
遙想當年,學校圖書室和閱覽室的那些書,是滿足不了全校師生這么大的閱讀量的。當時的我們正值囊中羞澀的年紀,除了泡閱覽室、泡圖書館,最期盼的是賣舊書的來校園里的樹蔭下擺攤,一來,四角錢一公斤的廢報紙可以練好長一段時間的書法;二來,可以五毛、一元地淘上幾本諸如《李義山詩箋注》《讀者文摘》《散文詩》一類的小冊子來讀。除淘舊書外,還經常到大大小小的書店書屋去蹭書看,如今想來這“蹭書”真是一件最忐忑不安又快意無限的事。走進一家書店,在林立的書架間漫行,自帶的搜書雷達此時會飛快運轉,少頃,目光落處便是鎖定的目標。當然,有時是來續“蹭”的,也不能輕車熟路直撲目標而去,還是要按耐著內心的雀躍,淡定又若無其事地走過它,又折回來駐足,余光快速掃瞄店主,若沒被發現便飛快取下,一頭扎進書里,隨之淪陷在字里行間,先前的忐忑悄然銷聲匿跡。直到腳麻了才會動動,抬起頭,瞬間清醒自己的處境,若是與店主的目光撞個正著,那份不安也瞬間歸位,遇到寬容的店主,他會很快把目光移開,假裝是不經意一瞥。遇到洞悉你的小把戲,又按耐不住心中不快的店主,只能在他犀利的目光中,默默把書放回原位,當然不忘飛快掃一下頁碼,以期到下一個書店接著讀。這樣的橋段和林海音的《竊讀記》差不多,都有著隱秘的忐忑和歡喜。
如今想來,在風城大大小小的書店里都留下了我們竊讀的蛛絲馬跡,很多店主的寬容滿足了當時還是窮學生的我們對閱讀的渴求。也許因為他們自己也是讀書人,從而生出一種同心相惜,讓我們收獲了一份心照不宣的感動。當然,在書店里也會遇見別樣的不期而遇的溫暖。
一個周末的午后,我又和閨蜜去學校附近的一個書店蹭書看。藝術書架上的《馬奈莫奈畫風》不經意地躍入眼簾,我抑制不住心頭的激動,迫不及待地抽下來翻看,那天光云影、那柳絲繾綣、那裊裊婷婷的蓮影,讓人心動神搖,欲罷不能……

第一次看到這本畫冊是在一位友人的畫室里。春日的午后,陽光透過淡藍的窗簾斜斜灑進來,案頭的陶罐里是一束淡紫的雛菊,翻看著那本莫奈的畫冊,和著淡淡的調色油的清香,莫奈的睡蓮是那樣猝不及防地擊中我,那種不諳世事的不染,莞爾在淺粉淡藍的如淪如漾的夢幻中,溫婉輕斂,一下子攝住我的心,那顫動的筆觸和閃爍、跳躍的色彩,讓我分不清哪里是水面,哪里是水底,哪里是倒影。這種寫意的手法用在油畫中竟然那么悠遠靜謐,猶若沐浴著江南的杏花春雨。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沉浸于那古典曼妙的畫境中,能自己擁有那本畫冊成了時時縈繞我的愿望。
不想在這兒和它不期而遇,甚是欣喜!但是一看書價:四十元!當時,普通人的工資也不過百十元。四十元,接近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我摩挲著,反復翻看了許久。當我輕輕放回書架的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輕聲問我:“很喜歡那本書,是嗎?”我有些驚訝,慌張而木訥地點點頭。他微笑著拿下那本書,并攏他手中的另兩本書朝收銀臺去了,不一會,他拿著書折回來,把那本畫冊遞給我:“給。”我怔怔地站著,不敢接他手中的書,他笑了笑,輕輕地將書放在我身旁的一疊書上,轉身走了。我愣了一會兒,拿起書飛奔出去,想還給他,可當我追出去的時候,穿梭的人影中已不見他的蹤影。手中握著畫冊的我忐忑地立著,不知所措。
我的閨蜜看到心滿意足,帶著一臉的愜意找到我:“走了!”“我……”看著我不安的樣子,聽完我簡單支吾地敘述,她的娃娃臉笑開了花;“呵呵,傻啊,有人給你買書還不敢要,要是我呀,樂死了!來,你不敢拿,我幫你拿著!”往回走的路上,我緊張地張望,生怕那個買書人會在某個角落出現,臉上帶著狡黠的笑意……后來以至于我不敢翻動那本書,直到多年以后,當然也從未邂逅那位買書人……
二十幾年后的我,已過不惑之年,特別是當了母親之后心也逐漸柔軟,也懂了當年那位買書人,他不過是看到一個愛書卻買不起的孩子,生了惻隱之心,而那個年紀的青澀懵懂卻讓自己懷揣了多少自以為有道理的“心眼兒”,如今想來,我若遇到類似的情景也會欣然滿足一個陌生孩子的愿望。幾十年了,這本畫冊依然放在我的書架上。在整個書房三面頂天立地的書架上,它已然淹沒在書叢中,只是我依然清晰而準確地記得它的位置,偶爾會抽出來翻翻,去觸摸那搖曳在時光流里的蓮。
因為它依然溫暖著我,溫暖著我對書的記憶。所以逛書店、買書,依然是令人愉悅的事情,青年書店、三人書店……都是最好的去處,后來又有了新知圖書城,看書買書的領域隨之擴大。
初識新知,是1998年2月,我到云南師范大學去讀函授。一個微雨的夜晚,春城的冬日依舊華燈閃爍,流光溢彩。我獨自漫步在街上,沿街的霓虹閃耀著漠然的光輝,雨絲滑落在地上,映著燈光游絲浮動。一個個艷麗如霓虹的陌生面孔也如霓虹般漠然地和我擦肩而過,心里涌動著一種淡淡的孤寂。
走到建設路的一個街口,一幅巨大的商場廣告吸引了我:玫紅的底板上,一條黑色的飄帶矯若游龍,設計簡單,卻令人難忘。原來這是百匯商場的標志,就在這時,我意外地發現標志的旁邊豎著一個不大的燈箱,寫著“昆明新知圖書城”幾個字。在這個商業味十足的商場里居然有一個圖書城,這大概就是“知識經濟”的最好詮釋吧,我有些調侃地想。隨著電梯徐徐上升,我來到了新知圖書城。在這里,我真正領略了“書城”的內涵:寬展延伸的空間、林立的書架、云集的讀者,讓我既驚喜又興奮。特別是墻上的話令我非常動容——“為讀者找書”。一種久違的親切感隨即彌漫開來,讓人驀然間找到一種歸屬感。“為書找讀者”,賦予了書以生命和靈性,只為知音者賞,其價值的內涵已升華到精神的空間,折射著一種人文的氣息。私以為,經營書店不能是一種純商業的行為,更應該是經營一項文化事業,經營一種操守,書店本身也應該是一方滋養文化的沃土。因為這俯俯仰仰的人群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正在或即將推動社會各方面的發展。
從此,來這兒讀書,成了我的心理日程,好像與它有一個重要的約定。在各個書城間流連,書架透視成無限延伸的空間,一直到視線的盡頭,心中升騰著一種磅礴的感覺,這是一個精神自由徜徉的所在,靈魂在這里得到了徹底的放松。這里彌漫著互不相識又渾然一體的氣氛,相互間有一種自然的默契:手伸向同一本書時的謙讓;踮著腳也夠不著書時,一只大手幫助取下來時的愜意;對書中某一個細節輕聲討論后會心的笑容。在這兒,總能和許許多多素不相識的人不期而遇,相互間無言的親和力讓人感動:讀者之間是不設防的。
我與新知的約定依然繼續。不知有多少次,抱著從各個書店挑選來的書,坐在供讀者休憩的椅子上不得不重新篩選——在外求學的我總不能隨心所欲地買吧,怎么弄回去呢,當時還沒有快遞這一說。可還是有好幾次拎著一大堆書徒步返校。記得每次抱著書來到驗書處,這里的服務生總是看著桌上的一堆書微笑著說:“要章嗎?”“要。”我總是不假思索——這是與新知每一次約定的軌跡。
每一次的約定,我都能更深切地感受新知。在讀者群中,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都是學生模樣,有的蹲在書架前,有的坐在椅子上,都在專注地讀書,翻看書頁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的,看得出他們手中的書沒有一絲折痕。服務員們已開始用餐,人們也陸續散去,他們掏出兜里的食物——或饅頭、或面包,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吃完后,把手擦干凈,又繼續讀書。不知過了多久,人又陸續多起來,學生中有人看看表,小聲招呼自己的伙伴,孩子們依依不舍地放下手中的書,再回頭反復確認是哪本書的哪一個頁碼,哪本書在哪一個書架。觸景生情,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我一邊讀書得一邊觀察店主的臉色,若發現苗頭不對,趕緊把書放回,帶著對書中文字的牽掛和對店主的歉意,悵然地離開書店。不過,也感受過書店老板的寬容,不知多年以后這些好讀的學子們是否也會對這里心懷感激。
想起一位叫蕭軼的作者在《依舊有味是青苑》中所說:“一個書店的靈魂,不僅僅是靠書的熏陶,更是源于讀書的種子的每一次流連忘返。城市的靈魂,也就在書店的艱難前進中慢慢得到培養和熏陶。”所以書店又不僅僅是書店,對于讀書人來說,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一份精神姿態,一段成長記憶。
與新知相約總是在微雨的時候——每年的2月和8月,正是冬雨紛紛、秋雨綿綿的時節,也正是我赴昆讀函授之際。就這樣與之走過了三個秋冬,以書為友,不離不棄。將自己埋進書叢,置身于淡淡的書香之中,就會感到久違的生命的靜謐,隔絕了外界的紛擾嘈雜,也使置身于紛繁生活中的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塵埃落定時,反復審視生命的厚度。
2000年8月,我的中文函授畢業了,恰好當年的10月1日,昆明新知(大理)圖書城開業了,與新知的相約又得以繼續。最開心的事,莫過于暢游書城,挑選鐘愛的書,驗書處的服務生笑容依舊:“要章嗎?”“要。”我依然不假思索——我們相約的軌跡既然已“保持連接”,當然要讓它繼續。書架上《傾城之戀》《長恨歌》《額爾古納河右岸》《溫一壺月光下酒》《行者無疆》……一冊冊充實著我自己的書架,充盈著我的內心。我也開始在綠色格子稿紙上寫文章,手寫,頗具儀式感,投稿要郵寄,貼上好看的郵票,投進郵箱的一剎那就升騰起一種牽系,一種希望。
四
從未想過,多年以后,我自己也會出書,一本關于戲曲的散文集。
一個人對于文字、戲曲或其他領域的熱愛,有的是電光石火的一瞬,便開始深深迷戀,比如白先勇先生對昆曲的熱愛,早在他幼年時就埋下了種子。當時不到十歲的白先勇,由母親帶著在上海美琪大戲院看了梅蘭芳先生《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園驚夢》。那是他第一次遇到昆曲,美妙的音樂和戲詞卻悄然沁入腦海。確實,世間的許多事情,一旦起心動念,就有了因果。因孩提時代的驚鴻一瞥,就有了后來青春版的《牡丹亭》。
而我對戲曲的喜愛又是因為耳濡目染,一點點的滲透和浸潤的。在我幼年時,巍山古城有過一個滇劇團,我的小姨便是這個劇團的大青衣。上了妝的她,就像是從古畫中走下來的,美得驚心動魄。我經常跟著她,在后臺化妝、背臺詞、候戲。我六歲的時候就有了第一次跑龍套的經歷。為了那一句兩句臺詞插得恰到好處,小姨教我熟悉念白和唱詞。這樣的幼年在同齡人中是一個異數,在同齡孩子追著母雞滿院子瘋跑的時候,我手中是一張薄薄的信箋,上面是用藍黑墨水寫的唱詞,俊逸的楷書,煞是好看:“賈寶玉進瀟湘淚如雨灑,西風起見葉落滿徑黃花,那壁廂破芭蕉空造雨打,這一旁只剩下幾樹山茶……”還在我讀中學的時候,我就讀過《牡丹亭》劇本,不大懂,但讀著“夢回鶯囀,亂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感覺美得不行。后來讀《紅樓夢》,發現黛玉聽了這段唱詞,也是“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癡,眼中落淚”。對于我來說,或許當年背下來的那些唱詞就是最早的文學啟蒙。
那些絲絲拉拉的胡琴聲和點點滴滴的司鼓聲已經浸潤了我的整個童年,直至成年以后聽戲、看戲已成為一種日常。從青衣婀娜委婉、大氣端然,到老生的沉沉蒼蒼、黃沙漫漫。聽馬連良、余叔巖、周信芳,聽梅派、尚派、程派、荀派,最先讓我意惹情牽的是程派,“她淚自彈,聲續斷,似杜鵑,啼別院,巴峽哀猿動人心弦,好不慘然。”那唱腔,斷而后續,若斷若虛,絲絲繞繞,婉轉纏綿,欲罷不能。梅派是華美的,是盛唐女子,是云做的衣裳、花做的容,不由得你不喜歡,但又不是可以太親近的那種喜歡。尚派幾近失傳,留存劇目不多,寒山瘦水,大漠孤煙,但總有一股浩氣在,有一種人見猶憐的悲壯。荀派是花旦,真正的花旦,很嬌俏地帶著那種花枝斜插的艷,裊裊婷婷,如水如花紅妝。
想起早些年的時候,我是羞于談自己喜歡戲曲的,聽戲的時候怕人聽見:“喜歡聽戲?沒搞錯吧,你有那么老嗎?”后來,讀了《合肥四姐妹》才知道四小姐張充和八十多歲還唱昆曲呢。直到近百歲,她仍舊吹笛子唱昆曲,到老來不見衰朽,愈發好看,有著昆曲雅韻深深浸潤過的淡遠、清朗。人們稱她為“最后的閨秀”。羨慕她被書法、昆曲、詩詞浸潤的一生,多么幸運、芬芳。張愛玲傾城的文采也和戲曲根脈相連,她很多次在文章里講述自己看戲經歷和體會,她說:“為什么我三句離不了京劇呢?因為我對京劇是個感到濃厚興趣的外行。”寫《韭菜花》的汪曾祺會吹笛子,唱昆曲。年少時,跟著父親的胡琴唱老生,也唱青衣。以前讀他的《人間草木》《尋常茶話》,只覺得其中的文字干凈質樸之外有著樂感和韻律,后來才知道他是國家京劇院的編劇。他在《人間有戲》中流露著的對伶人的悲憫:“我聽得耳熟,他唱得悲涼。京劇伶人身懷絕技,頭頂星辰,春夏秋冬,周而復始,粉墨人生,風流云散,由伶人身世,看盡世情悲歡。”

這些被戲曲浸染的有趣靈魂感染了從小泡在戲里的我,戲曲已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它貫穿于我的成長和喜好中,我一邊聽戲,一邊寫文章,用文字表達自己。2010年的時候,我開始在新浪網上寫博客,寫的也都是一些零星的經歷和感受,或長或短,和自己對話,表達自己,安放自己。后來,我開始寫戲曲散文,寫方寸舞臺,閱世情悲歡。書寫這些故事和感悟,也是在梳理自己成長淬煉的過程。同時也從戲曲舞臺上了悟: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披甲上陣的前臺,也該有卸下盔甲,讓心靈小憩的身心清寧的后臺。前臺是粉墨登場的所在,回到后臺,悅納自己的優雅從容,亦悅納自己卸妝后疲憊的容顏,甚至是戲裝上的泥漬,在這里,不用妝容精致,不用發絲不亂,偶爾的脆弱可以在這里安然釋放。當我們一次次體面地轉身于前臺的滿堂華彩的時候,我們也有梳理自己、安撫自己、沉淀自己的后臺。于我而言,閱讀、寫作就是這個后臺,我在這里和自己和解,與生活言歡。所以,讀書、寫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個人秘密幸福的一部分,我不想讓這一切帶有一絲強迫性和表演性。
隨著戲曲散文在報刊雜志上的陸續發表,我也能更舒展地表達我對戲曲的迷戀,書寫著自己和戲有關的幼年。
年幼時戲在心里是單純的,就是小姨咿咿呀呀粉墨登場的樣子。從小生長的巍山古城,在記憶中如老照片一樣,灰蒙蒙的,又像輪廓不甚清晰的版畫,或是黑白變幻的電影膠片。惟戲是清晰的,濃墨重彩的,那鑼鼓笙簫、絲竹胡琴,如水墨畫中的“破色”,而臺下平日灰蒙蒙的眾生,一旦登臺亮相,便讓這色破到絕妙之處,驚艷無比,仿佛跨越時空過著另一種人生。
小姨便是這樣,生活中一樣柴米油鹽過日子,一旦上了妝,上了戲臺,便成了跨越千古的絕美青衣。她是滇劇團的角兒,她到哪兒都帶著我,我便成了她的“小跟班”。我陪她在后臺化妝、候場。因不知在鏡中看了多少回,那場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如繪:化妝師取過肉色的彩底,擠在掌心,均勻地一點一點往她臉上、脖子上、手上抹,然后,調眉,包頭,戴頭套,用黑色眼彩勾眉眼,蘸胭脂輕染,點上絳紅的唇彩,艷若丹寇,服裝師為她披上水衣。那時的她是云鬢珠花、水袖盈風的嫦娥;是一花不與眾花同的白蛇仙子。
妝成之后,她便背過身默戲去了,每次有演出她都要早早到場,為的就是默戲。這個時候,誰也不敢驚擾她,連我這個“小跟班”也不能黏著她了。她要進入另一種人生,悲喜都是那個人生的,現實中的她被那個人生一點一點滲透,浸成戲中的那個人,沒有了自己一絲的痕跡。
待小姨默完戲,轉過身來候戲時,她眼里已經沒有我,沒有周遭,恍惚間讓人感覺天地虛無,神智不知落在哪個朝代沒回來,已然是戲中人了。只聽側臺一聲:“蘇三,上。”有人把那“出將”的簾子掀開,“苦哇——”小姨便出去了,“好——好——”每場都是這樣“掀簾彩”。她是名角,她的身段、行腔、唱念做打,特別是那戲的靈魂精魄和這“掀簾彩”匹配得絲絲入扣。燈光盞盞照在戲臺上,有一種特別的繁華和隆重。我早已溜出去趴在前臺,看她繡花鞋尖上頂著的朱紅毛絨球顫顫悠悠,她則步步生蓮地走圓場。滿場翻飛的裙裾,花飛蝶舞,像刮過了一整落花風。
記不清多少個夜晚,不諳世事的我陪著她,演繹著別人的悲歡離合,喜著自己的喜,悲著自己的悲。她清透的嗓音乍破銀瓶一般穿透禮堂,穿過城樓,在月明星稀的夜空縈繞,有一種曠然清新、耳目一明的感覺。這樣的冰雪嗓音配上這樣的清風明月,真是廣寒宮里嫦娥展袖,天上人間共此一曲。待她回到后臺,摘了行頭,卸了妝,帶我去吃宵夜的時候,她已魂歸原位又是我親切、貼心的姨了。看著她和其他叔叔伯伯我就覺得戲好神奇,它能把我身邊這么親近熟悉的人,用粉墨,用行頭,用程式,用功夫,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轉瞬之間變成跨越千古的英雄美人;而卸了妝,又是“洗盡鉛華呈素姿”了,花栽泥里,云浮天上,各歸其位,妥當安穩。
長大后的我沒有學戲,但隨身帶著一把胡琴,這兩根弦一張弓,顫動的是我心底的余音,是姨的姣好身影和那眼底化不開的憂怨。戲,是我心上的刺青,我浸潤于它的幼年,悄然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在心底尋我前塵的余音——那淺吟低唱已消散在喧囂和匆忙中,有時,我覺得自己被一只無形的大手拽著,不知方向地往前趕,再往前趕。只有在夜深人靜,心的深處又響起那唱腔和唱詞的鋪陳的時候,心才有了歸屬,腳才踩到了土地,我已然是一株悄然生長于斯的作物,我的生命有意無意間搖曳的是她的芳華。我坐在電腦前,拉平時間的褶皺,一點一點地碼字,寫下這些芳華、這些吉光片羽、這些金粉金沙的艷。
2019年伊始,我便開始整理這些關于戲曲的文字,準備結集出書。此時的紙質書和戲曲一樣,已經式微,且一疊書稿到一本書的蛻變,要經歷多少個回合,亦是可以想見的。但是,我愿意。因為我深愛的文字、深愛的戲曲,更何況,這是一本關于戲曲的文字。或許,這也是當年在圖書室、閱覽室、書店一排一排靜謐安詳的書架間穿行流連時,悄然種下的青春的夢想。歲月杳然,回顧所來徑,夢想的嫩葉新枝在不知不覺中已吐新芽,默默生長。從稿子的篩選、修改、內容的三審三校,到紙張的挑選和裝幀風格的甄別、選擇,再到封面和插圖的設計、手繪效果的N次修改,確實是一個漫長而繁復的過程,每一個細節都得仔細推敲,耐心協調,帶著“書為閱己者容”的期許,或者說有無“閱己者”、有多少“閱己者”都已經不重要了。我、編輯、設計師都帶著對書的敬畏和堅持,將戲曲的那些翩若驚鴻的身段、百轉千回的聲腔,那些沉斂嫵媚,那些氣沖霄漢,那些忠貞大義,那些繁華蒼涼,牢牢焊入紙頁中。
我始終相信,每個人都是一本有故事的書,人和書的每一次相遇都開啟一段新的旅程;人和書、人和人的相遇相知又形成了每個人的人生故事。人成了書,書成了人。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書卷是讀書人的心底山河,那紙頁散發出的淡淡書香,那翻頁時簌簌作響的紙張,那一個個飽滿整齊的漢字,哪一個不能觸發人的無限情感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