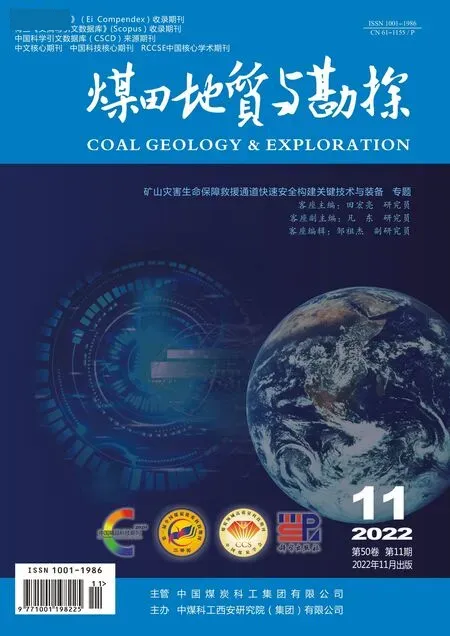水泥基注漿材料析水時變特性量化試驗研究
張潤畦,徐 斌,2,3,尹尚先,李樹霞,常永旺,連會青,曹 敏,6
(1.華北科技學院 河北省礦井災害防治重點實驗室,北京 101601;2.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陜西 西安 710077;3.吉林大學 建筑工程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6;4.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地球科學與測繪學院,北京 100083;5.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山西 太原 030024;6.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能源與礦業學院,北京 100083)
注漿法常用于礦業工程中,通過充填地層中的裂隙或孔隙,改變其物理力學性能,以達到注漿加固和防滲堵漏的目的[1-2]。注漿工程中所用漿液可分為穩定漿液和非穩定漿液,其判別指標通常采用析水率、結石率與最終析水時間[3-5]。考慮到工程中常用漿液密度為1 300 kg/m3左右,大部分都是高水灰比漿液,析水性較強,屬于非穩定漿液[6-7],當非穩定漿液注入裂隙介質后,隨著漿液運移速度的降低,漿液顆粒發生析水沉淀,出現漿水分層現象[8-10],漿液在介質中的運移方式也隨之發生改變,不再以完全驅替充填的方式進行,這是非穩定漿液和穩定漿液運移最大的區別[11-12]。而現有的漿液擴散理論大部分都是基于穩定漿液進行的推導[9],認為漿液擴散為驅替充填擴散。注漿工程參數選擇時,若套用穩定漿液擴散的理論進行注漿擴散范圍估計,則會導致出現較大偏差,為此,非穩定漿液擴散理論的探究勢在必行,常規非穩定漿液析水特性的量化研究是非穩定漿液擴散理論研究的基礎。
從初始純水泥漿發展至今,注漿材料種類層出不窮,大致可分為水泥類注漿材料與化學類注漿材料[13],基于環保考慮,化學漿液在工程中的應用逐年減少,而水泥基漿液憑借價格低廉等優勢脫穎而出[14],而且其可以通過加入摻合料來滿足不同需求,例如常用于提高注漿材料電阻率的摻合料葉臘石粉、聚乙烯醇[15],或常用于改善漿液力學性能的摻合料粉煤灰、水玻璃等[16]。
水泥基注漿材料的力學性能、黏度、耐久性等特性也是關注的重點,國內外學者通過試驗觀察現象,利用數學方法總結規律,并借助現代計算機技術推導數學模型,現已構建起較為完善的技術體系[17-19],但對于漿液析水時變特性的研究尚不完全,目前很少有學者對漿液析水時變特性進行量化模型研究。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葉臘石粉、聚乙烯醇與粉煤灰3 種摻合料,通過漿液靜置析水試驗,采用析水率、結石率判別法和最終析水時間判別法,分析三者在水固比為2∶1 的前提下不同摻量的析水現象,并引入析水厚度(析水過程中,漿體擴散運移分層后上層水體的厚度)對析水效應做進一步刻畫,通過對比3 類物質的析水時變過程,總結析水時變規律,并引入生長曲線皮爾模型,與冪函數模型進行比較,對規律進行量化,選擇出合適的析水時變特性模型,以期為注漿材料優選奠定基礎。
1 漿液析水特性試驗
1.1 試驗目的
本次漿液析水性試驗參考GB/T 50448-2015《水泥基灌漿材料應用技術規范》[7]規定和實際注漿工程中的水固比,確定試驗水固比為2∶1,探究葉臘石粉、聚乙烯醇與粉煤灰3 種摻合料摻量對析水過程的影響,并通過析水率、結石率、最終析水時間與析水厚度變化曲線對常用水泥基注漿材料析水時變特性進行分析,利用數學模型進行量化處理,力求獲得一種精度高、擬合效果好的量化公式。其中,水固比為水體質量與固體質量之比;葉臘石粉摻量是葉臘石粉質量占水泥質量的百分比;聚乙烯醇摻量是聚乙烯醇質量占水泥質量的百分比;粉煤灰摻量是粉煤灰質量占水泥質量的百分比。
1.2 試驗裝置、材料及屬性
為研究析水效應,研制了全程監控漿液析水效應的試驗裝置。試驗裝置由若干試驗量筒與試驗架組成,錄制裝置為佳能800D 高清照相機,試驗量筒豎直擺放在試驗架上模擬漿液在重力作用下的空間分布。試驗裝置如圖1 所示。

圖1 試驗裝置Fig.1 Test device
本項試驗研究材料為水泥、葉臘石粉、聚乙烯醇與粉煤灰。各項性能指標如下。
1) 水泥
試驗采用鈞牌礦渣硅酸鹽水泥P.S.B 32.5,水泥品質符合GB 175-2007《通用硅酸鹽水泥》標準與《通用硅酸鹽水泥》國家標準第2 號修改單(GB 175-2007/XG2-2014)。
2) 葉臘石粉(PRI)
注漿試驗選用38 μm 葉臘石粉,白度良好,質地細,具體組成見表1。

表1 葉臘石粉組成Table 1 Pyrophyllite powder composition
3) 聚乙烯醇(PVA)
聚乙烯醇是一類常用作砂漿添加劑,可以改善水泥砂漿的性能,提高砂漿黏結程度的高分子聚合物,具體化學性能見表2。

表2 聚乙烯醇性能Table 2 Polyvinyl alcohol properties
4) 粉煤灰(FA)
注漿試驗原料選用河北邢臺礦區電廠粉煤灰,孔隙率較大,對水的吸附性能很強,具體組成見表3。

表3 粉煤灰組成Table 3 Composition of fly ash
1.3 試驗原理
由水泥材料配置的水泥懸濁液,受重力作用的影響,水泥顆粒會自由下沉,在水分上層逐漸析出,最終造成漿水分層的現象,該現象稱為析水效應[20],待漿液與水達到穩定平衡狀態,此時析水效應停止,具體試驗原理如圖2 所示。

圖2 試驗原理Fig.2 Principle of the test
析水程度通過析水率來衡量,析水率一般采用量筒觀測法[21]。由于析水率會隨攪拌時間發生變化,本試驗規定各組水泥漿液均高速攪拌2 min 后觀察其析水情況。利用下式計算各組析水率。

式中:ω為析水率;Vw為水分體積;V為總體積。
由于析水厚度的增長規律也是析水過程中一大重要特點,本文通過記錄析水厚度變化過程,分析漿液的析水規律。
為分析葉臘石粉摻量、聚乙烯醇摻量與粉煤灰摻量對析水率、結石率(結石率=1-析水率)、最終析水時間與析水厚度變化曲線等參數的影響,本次采用控制單一變量法進行試驗設計[22],即試驗中僅允許一個變量,其他參數保持不變,以此來研究該變量對試驗結果的影響。最終通過試驗觀察漿液分層現象,并隨時拍攝記錄變化情況,最后經計算獲得各組漿液析水率、結石率、最終析水時間與析水厚度變化情況,并運用相關軟件進行析水規律的展示。
1.4 試驗方案
設計4 大組對照試驗:對照組、葉臘石粉摻量變化組、聚乙烯醇摻量變化組與粉煤灰摻量變化組,其水固比均為2∶1。對照組(A)為純水泥漿液;葉臘石粉摻量變化組(B1-B7),分為7 個小組,聚乙烯醇與粉煤灰摻量設為0,葉臘石粉摻量在5%~35%改變;聚乙烯醇摻量變化組(C1-C12),分為12 個小組,葉臘石粉與粉煤灰摻量設為0,聚乙烯醇摻量在0.5%~8%改變;粉煤灰摻量變化組(D1-D9),分為9 個小組,葉臘石粉與聚乙烯醇摻量設為0,粉煤灰摻量在10%~90%改變。4 大組具體試驗參數見表4。

表4 水泥基漿液析水試驗配比方案Table 4 Scheme of cement-based slurry water separation test
試驗具體步驟如下:
(1) 漿液制作,按照漿液配比方案制作水泥漿液,稱量精度為0.1 g,使用攪拌棒攪拌2 min,將攪拌均勻后的漿液倒入25 mL 量筒中進行重力靜置析水試驗,為減少誤差,每小組制作3 個漿液樣本。
(2) 試驗過程保證實時監控,佳能800D 高清照相機正對試驗架,對靜置在試驗臺上的量筒進行間隔拍照,設計監控時間為2 h,前一個小時間隔3 s 拍攝一次,即1 200 張照片,后一個小時間隔30 s 拍攝一次,即120 張照片,共計1 320 張照片。
(3) 圖片數據采集,借助PS 軟件[23]的腳本功能,批量切割出所需圖像,依次對各組析水情況進行統計。
(4) 試驗結果處理,對每一時刻每種摻量與分層厚度的數據進行提取,計算漿液析水率、結石率、最終析水時間與析水厚度變化情況,并運用相關軟件進行漿液析水時變規律的分析。
2 結果分析與討論
為降低試驗誤差,以3 個樣本的平均值為最終值,析水率、結石率與最終析水時間等數據在不同葉臘石粉摻量、聚乙烯醇摻量、粉煤灰摻量條件下的試驗結果見表5。

表5 漿液析水試驗成果Table 5 Results of slurry water separation test
2.1 析水率
析水率是驗證析水性能強弱最普遍的參數[8],為便于對比各類物質對水泥漿析水效應的影響,利用表5 中的試驗數據,分別繪制葉臘石粉摻量、聚乙烯醇摻量、粉煤灰摻量變化的水泥漿液析水率變化圖像,如圖3 所示。

圖3 漿液析水率雷達圖Fig.3 Radar chart of slurry water separation rate
由圖3 可知,總體而言,添加3 種摻合料對于水泥基注漿材料都具備一定降低析水率的功能。
對葉臘石粉摻量變化組來說,隨著葉臘石粉摻量的增加,析水率逐漸降低,析水率最大值為50.00%,最小值為40.67%。平均來看,每增加1%的葉臘石粉,析水率會降低0.76%。
對聚乙烯醇摻量變化組來說,隨著聚乙烯醇摻量的增加,析水率呈現波浪形,在0.5%~2.5%、2.5%~5.0%與5%~7%,析水率呈“U”形分布;當摻量為2.5%時,析水率最大,其值為50.12%;當摻量為3.5%和6.0%時,析水率最小,其值為47.33%。平均來看,每增加1%的聚乙烯醇,析水率會降低0.24%。
對粉煤灰摻量變化組進行分析,隨著粉煤灰摻量的增加,析水率逐漸降低,析水率最大值為46.40%,最小值為31.24%。平均來看,每增加1%的粉煤灰析水率會降低0.27%。
綜上所述,葉臘石粉對水泥基注漿材料析水率影響程度最大,其次為粉煤灰,最后為聚乙烯醇。
2.2 結石率
結石率同樣是對析水程度的一類評判標準,其反映了漿液中水泥顆粒沉積的比例[24],利用表5 的試驗數據,分別繪制葉臘石粉摻量、聚乙烯醇摻量、粉煤灰摻量變化的水泥漿液結石率變化圖像,如圖4 所示。

圖4 漿液結石率雷達圖Fig.4 Radar chart of grout stone rate
由圖4 可知,3 種摻合料摻量對于水泥基注漿材料都具備增強結石率的能力,對于形成密實的結石體具有積極作用。
通過對葉臘石粉摻量變化組與粉煤灰摻量變化組觀察,二者曲線范圍連接起來呈現出扇形,結石率隨著葉臘石粉摻量或粉煤灰摻量的增加而增加,葉臘石粉摻量變化組增加幅度較小,結石率最大值為59.33%,最小值為50.00%,粉煤灰摻量變化組增加幅度較大,結石率最大值為68.76%,最小值為53.60%。
聚乙烯醇摻量對結石率的影響曲線就呈現一種類似于皇冠形狀,共有4 個冠頂,當摻量為3.5%和6.0%時,結石率最大,其值為52.67%;當摻量為2.5%時,結石率最小,其值為49.88%。
2.3 最終析水時間
最終析水時間同樣可以作為一種衡量析水變化規律的指標[5],利用表5 中的試驗數據,分別繪制葉臘石粉摻量、聚乙烯醇摻量、粉煤灰摻量變化的水泥漿液最終析水時間變化圖像,如圖5 所示。
從圖5 中可以看出,葉臘石粉可以有效縮短漿液的最終析水時間,聚乙烯醇在1.5%~8.0%摻量內可以縮短漿液最終析水時間,粉煤灰在10%~60%摻量內可以縮短漿液最終析水時間。

圖5 漿液最終析水時間雷達圖Fig.5 Radar chart of the final water separation time of the slurry
葉臘石粉摻量變化組中,當摻量為25%時,最終析水時間最長,其值為38.50 min;當摻量為10%,最終析水時間最短,其值為32.05 min,總體而言均小于對照組的最終析水時間。
聚乙烯醇摻量變化組中,當摻量在0.5%~1.0%時,最終析水時間相比對照組有所延長,在1.0%摻量時達到最大值為44.10 min;當摻量在1.5%~8.0%時,最終析水時間有效縮短,尤其是在3.5%摻量時,最終析水時間最短,為30.15 min,這對于縮短漿液的析水時間有著很大幫助。
粉煤灰摻量變化組中,隨著摻量的增加,最終析水時間也隨之延長,最小值為29.92 min,最大值為44.83 min,當摻量在10%~50%時,最終析水時間增長幅度較小;當摻量在50%~90%時,其增長幅度較大。
2.4 析水厚度
析水厚度作為一種新引入的評價漿液析水特征的指標參數[6],同樣可以有效地反映漿液析水效應的規律。根據析水厚度變化幅度情況,將其繪制成折線圖,如圖6 所示。
由圖6 可得,三者變化曲線有2 個共同特點:(1)三者均過原點;(2) 三者變化趨勢呈現半“C”形,即前期快速增長,后期增長速度下降,末期趨于平穩。
圖6a 中顯示在水固比為2∶1 的前提下,不同葉臘石粉摻量之間前期差距較小,后期呈現較大差距,隨著葉臘石粉摻量的增加,析水厚度逐漸降低。
圖6b 表明,聚乙烯醇摻量變化時,析水厚度生長曲線比較密集,表明聚乙烯醇摻量各組漿液析水厚度相差較小。
圖6c 表明,粉煤灰摻量組在不同摻量下變化幅度比較明顯,表明粉煤灰摻量各組漿液析水厚度差較大。

圖6 不同配比漿液的析水厚度變化曲線Fig.6 Chart of the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thickness for different slurry ratios
3 模型量化擬合
通過觀察,發現3 種摻合料添加后的漿液析水率、結石率與最終析水時間變化規律一致性較差,唯有3 種漿液的析水厚度變化存在共性,且變化曲線特征與生長曲線函數特征類似,因此,引入皮爾生長曲線模型[25]與冪函數模型進行對比。
3.1 皮爾生長曲線模型
生長曲線是指研究對象隨時間變化產生類似于生物生長發育規律的一種非線性模型,皮爾曲線首次由比利時數學家P.F.Verhulst 在1938 年提出,后來被近代生物學家R.Pearl 和L.J.Reed 兩人再次拓展引用[26],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S為析水厚度;t為析水時間;K、a、b為待定系數。
3.2 冪函數模型
通過觀察發現,析水厚度變化曲線與冪函數圖非常接近,因此,選取以下冪函數模型進行擬合。

式中:λ、c為待定系數。
析水厚度在析水過程完成以后基本保持不變,為一個恒定值,因此,使用以上函數擬合析水厚度變化曲線時,只適用于時間t小于最終析水時間tm,即t≤tm。
將以上諸多函數方程代入計算軟件,進行自定義函數擬合,漿液析水厚度變化曲線擬合結果見表6。

表6 2 種模型擬合結果Table 6 Fitting results of Pearl growth curve model and power function model
3.3 擬合效果評價
擬合效果用擬合優度R2評價[27-28],其公式如下:

式中:xi、yi為待擬合數值,為其平均值;n為個數。
通過查閱資料[29],整理出擬合優度判斷標準見表7。

表7 擬合優度判別Table 7 Goodness-of-fit judgement
從表6 中可知,皮爾生長曲線模型擬合效果并不理想,其擬合優度R2均小于0.55,平均為0.21。針對以上結果,本次決定采用冪函數模型進行擬合。
選用冪函數模型擬合效果較好,擬合優度R2平均為0.98,R2最小值為0.96,均大于0.95,與皮爾生長模型相比,擬合優度R2平均提高了0.77。結果表明,漿液析水厚度在3 種主控因素影響下存在時變性,并符合冪函數模型:S(t)=λtc。
4 結 論
a.通過試驗分析,葉臘石粉、聚乙烯醇、粉煤灰3 種摻合料都可以提高漿液穩定性,其中葉臘石粉效果最佳,但漿液仍屬于非穩定漿液范疇。
b.常用水泥基注漿材料的析水效應與時間密切相關,隨著時間的增加,其析水厚度變化不因摻合料種類及摻量的改變而改變,始終保持半“C”形生長,故認為其析水過程存在一定規律的時變性。
c.對比析水厚度變化曲線擬合結果可知,漿液析水時變性比較符合冪函數模型,可為同類型非穩定漿液的析水厚度預測提供理論模型。
d.本次試驗嘗試了對析水厚度的量化研究,獲得漿液析水厚度的數學模型,但僅針對常壓注漿條件的析水規律,未考慮實際注漿過程中高壓狀態的影響;同時,試驗中未考慮注漿壓強、流速、摻料種類等因素對漿液析水特征的影響,今后研究中可進行完善,以便更好地指導現場注漿工程。